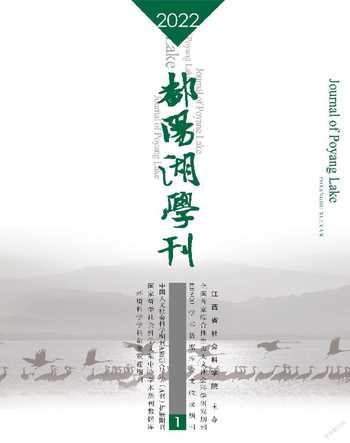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觀視域下的生態社區建設實踐
黃毅 王治河
[摘 要]生態社區建設并非僅僅為社區居住者提供舒適、環保、美觀的居住環境,它更是共同體的創建,是對工業化消解社區生命力的重建,是倡導人人參與、在合作中共創可持續發展的新生活方式和理念。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以過程哲學為基底,強調人與世界的存在方式是關系性、生成性和有機性的;特別是其對內在性關系的理解,即將工業文明范式下“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引向生態文明范式下“共同體中的人”的假設,使健康活潑的社區氛圍、團結友愛的社區支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念得以在生態社區建設實踐中得到深度有效的推進。山西永濟蒲韓生態社區建設實踐,將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思維方式下的“塊莖理論”運用其中,使生態社區建設從理念、設計到落地真正符合生態文明發展的內在要求。
[關鍵詞]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社區;共同體;生態文明
社區是文明的鮮活細胞,生態社區興則生態文明興。2020年新冠疫情后,“逆全球化”更加彰顯社區建設在抵御系統性風險和生態災難時的重要作用。生態村、生態田園綜合體、城市可持續宜居社區、生態老年公寓等生態社區的不同形式,正在從以往簡單的人類生產生活聚落區探索轉變為一種集“環境-社會-人”于一體的和諧共生的組織方式。
目前,國內外生態社區建設的理論支撐大多來源于生態系統論、生態控制論或循環經濟論。例如,1984年中國著名生態學者馬世駿和王如松等提出了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以及生態控制論原則原理;①1985年德國建筑師格魯夫針對現代社會出現的因一味追求生活便利與效率而犧牲自然環境與人性化特色的“都市型社區”,提出了與環境、人文共生的城市“生態型社區”模式;②1987年出版的布倫特蘭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概念,③很快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和廣泛認同并迅速成為生態社區思想的核心理念。在這些理論的指引下,更有涵蓋社會、經濟、環境、建筑等多維度指標體系的《生態社區評價指南》出爐,①用以指導生態社區建設。但無論這些理論和思想的初衷是什么,到生態社區實踐者的手中往往都變成了線性思維下標準化的工業文明產物,能夠很快取得成功的是技術上的功能性滿足,即圍繞為居住者——人提供舒適、健康、環保、高效、美觀的居住環境,而健康活潑的社區氛圍、團結友愛的社區支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念很難在實踐中得到有效的推進。
哲學及其思維方式對人類的實踐活動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一項實踐活動是否有效,能否在最廣泛的內涵和外延上體現出其本源意義和價值,取決于其背后的世界觀及其哲學的思維方式。本文提出將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作為生態社區建設的理論支撐,從過程哲學視角為生態社區建設提供一種后現代的思維方式,一種系統整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使生態社區建設從理念、設計到落地真正存有某種寬廣的視野、高遠的志向和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一、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觀
后現代主義是當代西方具有重大影響的哲學文化思潮,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是其中不同于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流派,其理論基礎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過程哲學(又稱“有機哲學”),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后現代思想家小約翰·柯布(John Cobb, Jr.)和大衛·格里芬(David Griffin)。
以過程性思維為思維方式,以強調流變性和生成性為基本立場,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在贊同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本質主義、中心主義和實體主義的批判態度的同時,始終強調“建設性”這一基本主張。②柯布和格里芬認為,對于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而言,“過程性”或“有機性”的世界觀比“實體性”的世界觀更加具有建設性。在過程性思維方式的基礎上,他們為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設計了一整套建設性理論,其中精髓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世界以及個體存在方式的關系性、生成性和有機性。懷特海堅持關系支配性質,而不是實體哲學所認為的性質決定關系。以事件為出發點,最為重要的不是事物的本質,而是事物在事件中發生的關系,事件本身就是關系的集合。真實存在的只是過程當中的關系。對于物和人來說,生成或合成的過程就是關系性的生成。過去、現在和未來呈現于某種相互觀照的聯系當中,沒有過去的事件就沒有現在的過程,自然就沒有未來的可能。在此基礎上,格里芬認為,個體的人的生成關系和群體的世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聯系,使得世界在空間上彼此關聯、在時間上相互觀照,無論是人的生命活動還是人與世界的關系都處于富有生機的有機體當中。③自我當然也是關系性的存在。自我不是單一的、封閉自足的實體,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自我不是一個與個體的身體、環境以及與個體有關系的他人隔絕的存在,而是延伸到了社群和環境之中并與它們息息相關。④
第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以一種整體論的方法,對生態文明實踐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矛盾和張力進行綜合與調和。現代科學的分化和線性思維使每一門學科都相對獨立。每一門學科各自發展了研究其自身世界的模式以及研究方法,它們的工作是技術理性的。例如現代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就是技術理性下的“經濟人”模式,它探討的人是一些自給自足的個人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市場交易關系。它不會考慮自然界的嚴重退化問題,在面對資源耗竭和環境危機時會因為超越其研究邊界而力不從心。例如,土地在現代經濟學中被當作生產的被動要素,并被當作財產的一部分而從產權和地租的角度加以研究。經濟學的這種價值觀來源于笛卡兒。笛卡兒將世界分為精神主體和物質客體,形成主客二分的二元論。這為經濟思想提供了背景和假設的基礎,即只有人的主觀欲望才是價值核心,土地以及其他一切都是為了滿足這種“核心價值”的外在客體。毫無疑問,主流經濟學對土地的認知是從物質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角度展開的。但物質世界的現實性又一再告誡人類:土地是生產要素,但它絕非僅僅如此。土地在廣泛意義上代表所有自然資源,包括所有需要土地供養的生物。人類與土地的依存關系遠遠超越主客二分。土地不僅為人類提供物質層面的產出,而且同樣具有精神層面和靈性層面的內涵。人類棲居于土地上,也成為土地的一部分,繁榮并滋養著土地。人類和土地原本是共生的整體關系。①現代性思維方式對待土地的辦法是將其“商品化”,其后果已經為世人所見:一方面是可耕種土地和土地中的不可再生資源從“相對稀缺”變成“絕對稀缺”,另一方面是土地上人的心靈的異化和破碎。B34FDA31-1A06-492A-ACC5-3C31F209EC5F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將人類的經濟問題納入人類共同體和自然界的關系之中。這樣一來,人們在看待和解決問題時就有了全然不同的視角。同樣面對土地問題,人們將土地去商品化,使其成為共同體的公共托管物,共同體與土地休戚與共。共同體在健康的土地方面的利益,可以在稅收政策或者一種獎懲體系中得到體現。如果表層土壤流失或土地受到污染,農民可能就會因為他們給土地造成的這些損害而被征收額外的賦稅。如果作為托管者的農民改善了土壤質量,讓土地變得更加肥沃,那么他們對社會福利作出的這種貢獻,就可以從他們應繳的賦稅中扣除,而他們自己也可以從提高的農業利潤中持續獲益。②
(一)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觀建立在對“關系”的超越性理解之上
現代性受機械世界觀的影響,對關系的理解是抽象和機械的。人在現代性那里是孤立的存在,即所謂“原子式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把占有視為人的本質,特別是對私有財產占有的崇尚使得競爭在社會關系中起主導作用。過程哲學認為,人并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靈魂或心靈;相反,人每一刻都從周圍世界中攝取東西,每一刻都在整理那些攝取的東西并賦予其價值。人們由此界定那一刻自己是誰,自己正在成為什么樣的人。在任何特定時刻,人們都根據自己的身份來行動和回應。然后,人們的行為對周圍的人產生影響,進而為之攝取來進行身份識別和價值認定。③從根本上說,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認為,關系的內在性是第一性的,而現代性將關系建立在外部性上。因此,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最大貢獻在于扭轉了人們的思維定勢,拓展了人們的思維蒼穹,促使人們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
1.內在性關系
建立在機械唯物主義之上的現代性把世界理解為空洞的荒漠性的存在,而過程哲學認為宇宙是情感的海洋,“感受”(feeling/prehension)貫穿于整個世界之中,存在于自然界的萬事萬物之中,因為構成自然的基本單位是有經驗的、有情感的、自主的、創造性的動在。盡管所有的動在都受到先前動在的影響,但是每一個動在并非完全由過去決定,每一個動在至少都體現了某種自我決定或自我創造的性質,從而對未來施加某種創造性的影響。①因此,“普遍的存在感”在懷特海看來“即感到自己作為他物中的一員,存在于一個有效驗的實際世界”。②這其實是中國“天人合一”觀念的另類表達。格里芬等過程哲學家把自然萬物看作是有感情、有目的的能夠進行自組織活動的存在。這意味著自然萬物與人們的關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這是一種相互依存、榮辱與共、血肉相連的內在關系。由此一來,人們就能夠理解自然和他者都具有內在價值,并學會尊重它、感激她、欣賞他;人們就能夠理解世界的多樣性的實在和價值,以及自然過程的復雜性和互依性。
2.基于內在性關系的“共同體中的人”
現代性將人首先預設為“理性經濟人”,現代經濟學大行其道更加強化了“經濟人”尋求自我利益的價值屬性,這也成為了一種集體意識。然而,很少有人否認,人類也是政治人、文化人或宗教人,人的多維性構造了人的完整人格。只有將人的多維性及其關系放入社群以及公共政策中加以研究,人們才可以看見完整的個人的善以及所有人共同的善。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小約翰·柯布博士認為,“人是由他們與其肉體和更廣泛的自然界,特別是和他人的內在關系構成的。除了這些關系以外,他們根本就不存在。他們是在人類共同體中形成和成長的。正是在共同體中并通過共同體,他們獲得了真正的個性和人格”。③柯布將這種關系的最佳模式表述為“共同體中的人”。
“共同體中的人”與“理性經濟人”中的人以及集體主義下的人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共同體中的人”的關系是內在的,而后兩種模式下的人的關系是外在的。“理性經濟人”的人之間是原子般的獨立個體,他們之間的連接主要通過市場交換來完成,競爭關系為其主要關系,個體行動的主要動力源是個體利益的增加,甚至原子化般的人組建的最小經濟單位——家庭,其成員之間的連接在“原子”價值理論的支配下也呈現出不同程度的“物化”“去心靈化”,使現代家庭關系岌岌可危。集體主義在西方是以階級等級來確定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的,在中國則以傳統的倫理共同體出現。它們的共同特性是人在集體中的不平等性,人在集體中的差序格局下保持連接穩定的是外在強制力量。不管這種集體性在歷史進程中如何進化,都會由于低估個性而導致其喪失生命力。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對“共同體中的人”的基本假定是:“無論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和他人的內在關系構成的,但他們每時每刻都在做出自己的決定。”④因此,在共同體中,個體差異、個人自由和個人的首創性都應得到強調和鼓勵。內在價值通過個體經驗得以呈現,所以人們追求的終極價值乃是個人的。共同體最終怎么樣,要根據它如何服務于構成該共同體的那些個人而加以判斷。真正的個性和真正的共同體是極性的(polarity)而非二元的,即它們處于一種相互支持而非二元張力的關系中。用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N. Bellah)的一句話加以總結就是:“個人只有在共同體當中并通過共同體才能實現自我;強大健康、道德高尚的共同體乃是造就強大健康、道德高尚的個人的前提。”①
3.存在于“共同體中的人”的后現代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社會關系
存在于“共同體中的人”的后現代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和社會關系必然是健康的。健康的關系存在于健康的共同體中,其最根本的實現前提是共同體成員對共同體的歸屬和“參與治理”。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對其作出的決定和共同體的方向有某些影響,而且參與的程度越高,共同體就越健康。
在“經濟人”模型中,關系的展開基于“競爭是第一位的,合作與互益是第二位的”。而在“共同體中的人”的模型中,關系的展開基于“互益及共同體的健康是第一位的,競爭是第二位的”。在這樣的集體意識排序下,關系的緊密依存在內外張力中保持和諧。從外部來講,后現代共同體的支配權力超越現代性中強制性權力占主導地位的情境,它包括說服性強制權力(為了支配并達成統一)、建議的權力(為了擴大他人選擇范圍的可能性)、善于接受與主動施予的權力(以此讓共同體成長)和共享合作的權力。這種多元化的權力安排基于后現代的一個基本認同: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是一種相互關系,其關系準則并非一人有所得時另一人就有所失,而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②任何一個共同體中的人的全面發展都將促進共同體的整體福利;同樣,一個共同體獲益也會促進所有共同體及更大的共同體的福利。從共同體中的人的個體內部來講,他保有奉獻和犧牲的意愿。雖然在共同體中的人們也是彼此競爭的個體,但共生共榮的意識讓犧牲和奉獻成為個體發展的某種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對共同體恰當的服務不是犧牲某個個體的生命,而是通過“美、真、道德、勇氣和平和”的經驗深度來提升個體自己,從而提升共同體的方式。B34FDA31-1A06-492A-ACC5-3C31F209EC5F
因此,后現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致力于構建“我們”,而非充滿敵意的“他們”。
(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觀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觀來源于將懷特海過程哲學創造性地運用于生態世界觀的建構和闡釋中。“雖然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有許多維度,然而最重要的維度是其對于人類現代物質文明與自然界之間整體的和諧關系的驅動導向作用。因此,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也可以稱為‘生態后現代主義。”③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秉持的生態觀主要包括:
第一,尊重他者,欣賞多元差異之美。在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看來,任何事物都具有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內在價值的實現及其大小取決于受造物自身的經驗強度,正如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包含歡樂、痛苦、愉悅、失望等諸多經驗,經驗強度越大,內在價值越大。個體的自由發展通過主動性的自我選擇來增強體驗中“美的力度”(strength of beauty),因而人們終其一生都在通過自我提升追求真、善、美與平和,追求和諧美好的生活體驗。工具價值是個體服務他者的價值,猶如食物之于生命、鋼琴之于演奏者。如果說內在價值是個體依據自身并服務于自身的價值,是以豐富自身的體驗、實現美的經驗為目的,那么工具價值作為外在價值就是每一條經驗對其他經驗的價值。比如社區中的醫生,他對社區成員的外在價值是幫助改善他人的健康,這個價值來源于他自身的內在價值,即他作為醫生的過往所有內在整體經驗的總和。因此,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同等重要。在一個系統當中,較小內在價值的個體往往具有較大的工具價值。例如海洋中的鯨魚和浮游生物:從個體上說,與浮游生物相比,鯨魚有著更大的內在價值;但從生態系統整體角度看,浮游生物處在海洋食物鏈的底層,大多數生物依賴浮游生物來生存,相比之下,浮游生物對整個海洋生命系統的工具作用要比鯨魚大得多。①建設性后現代生態觀倡導尊重每一個個體、每一個生命,包括非人類世界的生命,因為每一個生命、每一個個體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為自身而存在的內在價值,同時每一事物都具有對他者、對生態系統大小不同的工具價值,而美通常意味著差異和多樣性中的和諧。
第二,重視內在關系,禮贊有機共同體。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重視內在關系,認為個人是由其關系構成的,經驗的豐富性就是關系的豐富性,并依賴于經驗對象的豐富性。這表明,個人存在于社群共同體中,并由他們賴以存在的共同體構成。②這樣一來,處于有機世界(社區)中的人不可能是絕對自私的,因為在這一世界(社區)中的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尊重他者、愛護他者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愛護自身。當然,這里的他者同樣包括構成有機共同體(社區)的植物、動物和一切參與合生過程的實體。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社群所倡導的新的生活方式,無疑將使人回到共同體(社區)的生活之中,重新獲得家園感和親緣感,并以此重新獲得生命和生活的真正意義。
第三,推重創生力和創造性轉化。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拒絕重復、渴望創造,這種創造與現代主義強調復制化、模塊化的生產不同,它強調的是人的創造和創意的獨一無二,是根據情境智慧地進行創造性的轉化。這些創造存在并體現于日常生活的一切領域之中。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所說的創造不同于現代主義個人英雄式的創造,它在體現個人創造力的同時更加注重合作和創生,因而凸顯了社會責任感和某種共同的使命。
第四,高揚美的價值。在后現代這里,整個宇宙的目的是達致美。與現代性所指的美不同,后現代的美的本質是動態和諧,是動態的美、深度的美,這種美存在于既實現了整體的和諧又不犧牲整體的各個部分的高超藝術中。③故而后現代美學鼓勵發展一種相互支撐的美學關系。在社群關系中,整體的每一個成員自身越好,每一個成員越愿意支持其他成員,該整體就越好。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認為,宇宙間的每一個動在都具有內在美的價值,都包含情感、蘊含著美,因此它們都是人類的同胞,都值得人們珍惜與呵護。因此,無論是從個體所在的小的局域環境來看,還是從個體所在的大星球視角來看,個體要生存并生存得更好,就要發展對環境和他者的敏感性,進而獲得相互支撐,為了共同福祉而共創豐富多彩的靈動世界的高層次和諧。
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對生態社區建設的再闡釋
生態社區旨在發展出一套全新的高質量共同居住的社區生活模式。它不受社會經濟壓力的驅使,不一味滿足社會的期待;它帶領社區成員奔赴美好生活的愿景,在彼此尊重和互助的精神中鑄就團結凝聚的共同體;它通過生活多元性來表達無限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以解決當前世界上所面臨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危機等問題。
(一)生態社區建設的本質
生態社區建設本質上是共同體的創建,是對工業化消解社區生命力的重建,因而它是新的組織創新和治理創新的體現。生態社區建設依靠的是一個以追求人與自然共同福祉為共同志向而聯結在一起的生命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人們守望相助、相互關心、求同尊異、共同成長、互補并茂。在這個共同體中,每個人都可以創造性地因時因地地同當地資源進行智慧性的鏈接,自食其力并維持生計,充滿活力和凝聚力地安頓于一方水土。
(二)生態社區建設的內涵
生態社區共同體的內涵在于喚起其中的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周遭一切彼此相連、互為責任的意識。同時,這些緊密相連的社區能夠為負責任、關心社會的公民成長提供一個身心健康、生機勃勃的環境。
自古以來,社區共同體的恰當作用是提供規范和理想,并支持那些促進其實現的活動。但是規范和理想從何而來?現代性預設的那種關系是“外部”的,人可以從對他人和自然界的所有關系中抽象出來,因而“理性人”的行動邏輯是尋求自我利益。個體商人追求更高的利潤,個體雇員要求更高的工資,個體消費者尋求更低的價格。當社會或社群作為一個整體被理解為“理性人”構成的總和,且他們的行動目標被主要定義為經濟利益上的目標時,共同體的理想是線性增長,規范主要來源于外部制度約束。如果沒有除增長之外的特定內容來維系社群存在,那么人作為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作為生產要素就只會流向投資回報更高的領域。鄉村空心化就是明證。B34FDA31-1A06-492A-ACC5-3C31F209EC5F
如果“關系”是內在的,共同體的理想就更有可能與個人的理想相一致,規范也將在他律和自律中共同展開。生態社區建設的內涵就是要以行動無限靠近由“內在”的關系所構建的張力之中。這些行動包括:(1)社區成員的生態明智和精神上的滿意;(2)社區建設行動足以激發社區成員的個體創造性;(3)社區活動能夠激發社區最大范圍的參與度;(4)社區行動體現了公平和互助,沒有人落在最后;(5)由于社區福祉與更大的福祉相一致,因此社區健康將強化更大的共同體的健康。
(三)生態社區建設的難點
自古以來,人們都向往和諧統一的社群和共同體,多少智士哲人畢生奮斗于此。然而,生態社區建設的難點有其內在的邏輯根源和每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外在掣肘。
從內因上來看,對于任何一個社群或共同體來說,自由和秩序都是一對天然矛盾。秩序導向過程的平順和效率,自由導向因情境而變的直覺和創造性。秩序的產物是集權,自由的產物是分權。在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制下,社會組織通過金字塔的科層結構完成自上而下的命令,科層鏈條越長,執行命令和反饋的過程越容易導致組織失去活力。純粹的自由往往導致混亂和失序,難以讓眾多個體在組織中有效完成有利于社群的多重目標。因此,尋找秩序與自由的平衡點是擺在人類社會治理上的一道難題,也是后現代思想下生態社區建設中最為人們所關注的課題。
從外因上來看,目前工業文明通過全球化主導了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使與之伴生的社會治理模式岌岌可危。以市場經濟來詮釋“自由”的資本主義通過分工和不斷擴大的生產規模改變了原有社群的意義——經濟生活成為人類的主要生活,社群的多重目標被簡化為單一的經濟目標。社會治理模式不得不以金字塔式的科層制來應對不斷擴大的市場規模和相應簡化了的經濟目標,人類在社群中的其他生活和目標被抽離,人與自身之外的連接逐漸弱化。
工業文明和現代性對生態社區的消解極為嚴重。人們生活在共同體內,但大部分時間運行在工業機器的齒輪中,交往變得單薄稀松。在傳統社會里,人和人的交往是立體的、多層面的,大家不僅在一起聊天,還在一起勞動和生活。以前搬個家必須找幾個朋友來幫忙,現在搬家直接找搬家公司就可以了。以前農村婚喪嫁娶辦宴席要請鄰里來幫忙,并通過換工完成社會交往,現在可以直接外包給飯店。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并沒有誰真正需要誰,人和人之間缺少豐富的紐帶來幫助其建立更深層次的連接。同時,現代生活越來越趨于碎片化,個體在與共同體的分離中走向裂變。人的共同體屬性的日益缺失,造成了個體的人無法在紛繁復雜的道德適應環境中尋求自身的統一,從而導致原有倫理共同體的斷裂。①
由此看來,生態社區建設需要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來突破工業文明范式的藩籬,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建設性后現代的思維方式。建設性后現代主義以一種整體論的方法超越碎片化的分析,因而對生態文明實踐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矛盾與張力具有調和性和綜合性。
三、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觀視域下的社區建設實踐
正如柯布先生所言:“工業文明往往剝奪人們的權利,而生態文明則往往賦權給人民。工業文明切斷人與人的聯系,而生態文明則鼓勵人們在小型社區中相互幫扶,同時也鼓勵不同的社區,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合作。工業文明鼓勵競爭、跨國流動,而生態文明強調在彼此共有的社區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②毫無疑問,建設性后現代思維方式下的生態社區建設是賦能的、合作的、共創的。理論與實踐都在不斷擘畫和具象這一構想。
(一)理論支撐
一種后現代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可能制定特定的規則,它鼓勵各種實驗。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③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生態觀視域下的生態社區建設主要圍繞“塊莖理論”展開,構建多元主體在實踐中內在的、自主的、和諧的“共生”狀態。
“塊莖”(rhizome)這一概念出現在后現代思想家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和瓜塔里(Pierre-Felix Guattari)合著的《千高原》一書中。“塊莖理論”相對于“樹狀理論”而言。“樹狀思維”描述一種生長形態,即以樹根為主體和中心,樹干和樹枝是樹根的同質性表達。樹形系統是等級分明的系統,它在生長過程中具有自我復制的特點。與樹狀思維不同,具有塊莖特征的植物如地瓜和馬鈴薯,它們并不是獨立的存在,而是一個包含了諸多個體的整體,而且地瓜的藤蔓可以在其延伸的過程中重新生長。塊莖的生態學特征呈現出多元化、開放性、非中心、無規則的形態,它不存在像樹那樣的邊界,而是通過自身生命力的強弱表現出延伸的空間形態。④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思維方式下的生態社區建設就是這種類似于塊莖的組織分布。社會由若干個社區組成,每個社區依照自己的組建邏輯形成自己的規模和邊界。每個社區就是一個共同體,它由更小的基本共同體單位——家庭構成。不同的社區共同體憑借它們自己的故事和記憶以及所有成員的參與而緊密聯結在一起,并構成獨特的自我。⑤社區與社區之間也相互支撐,它們在更高的層面上有相同的目標和合作事件,它們的關系也是內在的。因此,不同的社區組成更大的共同體,整個社會治理呈現一種去中心化的分布狀結構。
“塊莖”是一種平面化、多樣性的存在,可以在不同“質”的相互交融中結合形成新的生命。生命體的存在不是單一的、孤立的存在,在塊莖中的延伸并非同質性的伸展,而是新生命的形成,即“更大發展的需要”,這恰恰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關于健康社群構建的指導意義所在。它強調“個體”是具有創造性的豐富的個體,強調社群的重要特征在于自組織,在于共同的參與和奔赴。關系的豐富性和經驗的豐富性取決于新的個人的創造性自由。健康的社群關系能為這種具有豐富創造力的自由提供條件,其基礎是充分理解“多樣性”和“參與”機制的重要性。每個人在社群中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其經驗的豐富性是同等重要的。與現代“理性經濟人”將勞動看作謀生的手段不同,“共同體中的人”始終認為真正的生產者是創造中的生產者,即他們在勞動中的享受和在創造性活動中的滿足同樣可以得到社群充分的尊重。這樣的社區首先關心的是本社群和社區內每個家庭的生計。社區致力于發展其成員在各自能力基礎上的分享、合作、創新精神,致力于智慧地利用本地資源、強化本地的多樣性和自我服務的能力,致力于發展同外部大市場的一種公平貿易。①B34FDA31-1A06-492A-ACC5-3C31F209EC5F
有鑒于此,生態社區當然呼喚不同于傳統社區的領導者——為社區轉型賦能的創建者。這樣的創建者在面對問題的時候會充分考慮事件的情境和決策的長期效果,他們相對于傳統的領導者更傾向于采用整合且系統的思維方式而非線性的思維方式,更傾向于通過關注系統的反饋來選擇某種非二元對立的可替代方案。傳統的領導者總是將目光聚焦結果而不管過程中所有精神層面的負反饋,而生態社區的領袖們真正關心的是所有參與者是否能夠在不利的情境面前發展出創造性的轉化能力。②
(二)落地辦法:以山西永濟蒲韓社區實踐為例③
山西永濟蒲韓社區實踐可視為“塊莖理論”的應用范例。蒲韓鄉村社區位于山西省運城市永濟市,因當地村民自1998年以來陸續成立了多家合作組織,覆蓋并服務于蒲州、韓陽兩鎮12個行政村3865戶農戶(兩鎮共計6520戶),遂自稱為“蒲韓鄉村社區”。管理這一空間的民間自組織被稱為“蒲韓鄉村協會”。2010年以來,蒲韓鄉村年均總產值增長均超過20%,2015年農產品銷售經營收入超過5000萬元,凈盈利超過300萬元,在農業技術培訓、老人服務、兒童教育等方面形成了多元供給機制。④
蒲韓社區帶頭人鄭冰女士和她的團隊在多年的共創中內化了“尊重他者、欣賞多元”“更多參與、公平互助”的價值理念,在關系的互動中激活個體豐富的創造性,在共同體中強化“共同體中的人”的特質,在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件中創造了跳出自身局限的可能性。本文試從以下七個方面總結蒲韓社區的共同體實踐:
第一,社區生活滲透在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方方面面,是社區共同行動的焦點。健康的社區可持續生活包括:蓬勃向上的社會精神與文化;自給自足的社區經濟;同自然與土地和諧融洽的社區生態;自由與秩序統一的社區組織。社區居民共同行動的目標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社區項目或社區活動,將社區成員聚集起來并鼓勵他們參與其中。蒲韓社區一開始是通過開辦農資技術培訓課、組織村民清理全村垃圾、組織農民婦女參加廣場舞等活動展開共同行動的,發展到后來,合作社的業務擴大到老人服務、兒童服務、手工藝、農產品銷售、信用互助、土壤轉化等方面。①這些活動關乎村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強了社區連接的基礎。社區活動常常是自發的,并且根據社區本地化的特點和時刻的需要而展開。
第二,社區帶頭人在“關系”連接中極為重要,是社群“自組織”的閥門。蒲韓社區的帶頭人鄭冰女士是一位有勇有謀的社區能人。她善于化解矛盾、調和關系,勇于在困難面前集思廣益、迎難而上,用具有開創性的思路和辦法凝聚社群精神,發展健康的社區生活。例如鄭冰在自己深陷人生低谷時沒有消沉失意,反而反思困境、向上生長。她通過組織婦女跳廣場舞,讓自己的人際關系重新恢復,也讓婦女們在集體活動中煥發了活力和積極性。這些力量被婦女們帶到家庭的夫妻關系和親子關系當中,也被帶到社群后續活動的創建當中。比如自愿清理村里的垃圾這種在以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即便鄭冰不在村子里,婦女們也都能完成。社區帶頭人從鄭冰一人變成了以不同項目為首的多人。往往在社群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帶頭人不一定是通過選舉選出來的,而可能是在做事情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也體現了個體內在價值豐富的可能性。
第三,形成社區共識需要多條腿走路。構建社群需要一個相對底層的共同價值觀。在工業文明對社群嚴重消解的當下,價值觀也支離破碎。如何統一社區居民的信念和行動,調動更多的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和共同奔赴,變得十分重要。蒲韓社區在實踐中不斷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用行動的力量統一社員的思想。比如大家在對單一種植和多樣化種植進行實際比對后統一了認識:多樣化種植更加能夠充分利用農忙季節的勞動力錯峰成本,并分散農戶的種植經營風險。又如大家在對向政府要資金同自己籌措資金兩種選擇進行對比之后統一了共識:向政府要資金有可能因為二次分配不公而使社員之間的關系更加惡化,不利于大家將重心置于項目本身上來。對于更加細化的村社構建過程中的選擇,他們創造性地采取集體辯論的辦法。比如關于蓋樓房好還是蓋平房好、農村發展是經濟重要還是環境衛生重要等問題,大家經過辯論就能得出具體事件背景下的最優結論。用辯論賽的方式議事,加強了社區精神凝聚力和社員之間精神能量的傳遞和流動。
第四,扎根土地,關注自身與土壤的連接。鄉村社區最大的生產生活都是與土地直接相關的,農民與土壤的連接是最深切的。面對工業化農業的大勢所趨,蒲韓社區的農業合作社卻堅持要求每戶拿出一定的田畝來做有機種植和土壤轉化,建議社員根據自有土地的情況進行多樣化種養,用實際效果教育和引導農戶關注土地的可持續生產。在農業生產組織方面,合作社嘗試過規模化耕種和農戶獨立耕種兩種方式,結果發現規模化耕種反而不利于調動社員的積極性。農戶獨立耕作時(不論他耕種的是承包地還是流轉地),因為土地上要產出他自己的勞動果實,所以他在勞動上是不計成本的,在對待土壤上是最為認真細致的。蒲韓社區下的農業合作社為了保證精耕細作,要求每個農戶耕種的土地不超過30畝,多余部分可以流轉給其他農戶耕種。合作社為農戶提供生態種養的建議和指導,也為農戶提供農資統購、農產品統一銷售、統一機耕、統一培訓的服務,幫助合作社對接市場。這樣,對于農戶生產經營來說,生產的“獨立”和產前產后服務“聯合”的統一,能讓農戶安心種地,用心對待土壤和生產。
第五,生產多元化,保證基本的生計和自給自足。在健康的社區中,生產生活常常是融為一體的,而且多樣化的生產生活蘊含了社區居民的創造性和智慧,表達了社區自給自足的獨立精神。例如,蒲韓社區在2006之前已經凝聚了社區力量,大家自愿組織“生態家園理事會”來自籌經費、自主行動清理村莊垃圾。2006年新農村建設的政策一下來,“生態家園理事會”被村長叫停,取而代之的是從政府取得“村容整潔項目”經費。這樣一來,村民反倒不積極了,他們認為既然村里拿了政府的錢,那么村干部就應該負責此事。錢事掛鉤,大家都覺得自己免責了,結果村里又變臟了。鄭冰想了個辦法,讓社區工作人員挨家挨戶收一元垃圾費。雖然只是象征性收費,卻讓村干部和村民之間在這種互動中建立了信任,最終大家都自覺不亂丟垃圾,積極主動輪值清運垃圾。通過這件事,蒲韓很少再拿政府的補貼和資助。他們動用聯合社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一方面打消了村民依賴政府的念頭,另一方面激發了社員的合作熱情和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精神。B34FDA31-1A06-492A-ACC5-3C31F209EC5F
第六,以生活富裕經濟,而非以經濟富裕生活。生態社區建設,一定是社區成員在豐富的社群生活中建立了充分深度的連接和良好的關系之后,才談得上合作發展經濟和其他社群目標。蒲韓社區剛成立合作社的時候,大家所有的目標都奔向“經濟”二字。從2005—2007年,他們幾乎把所有活動都停止了,全部集中力量搞經濟,結果經濟沒搞出來,人卻全散了,反倒是之前舉辦技術培訓、婦女活動的時候人都凝聚起來了。①鄭冰由此總結:公共服務、文化活動和經濟發展要多條腿走路,社員往往是在社群生活的深度連接中激發了更多的市場活力和潛能。所以,只有先讓使大家的生活內容和生活空間富裕起來,才能最終使大家的錢袋子富裕起來。
第七,經濟的內循環與外循環相協調。經濟作為最活躍的因素,連接了共同體內部與外部的力量。只有社區經濟內循環做得扎實,才有健康的外部循環。蒲韓社區的農業合作社在統購統銷的業務基礎上建立了信用互助。信用互助的對象只為社員提供小規模生態種植、生態養殖的資金貸款,不提供信用給外部做生意的社員。對于村里最弱勢的群體,信用互助提供無償借款,其目的就是為了鼓勵這些農戶建立自信、勤勞自立。除了信用互助之外,合作社還拿出盈利部分的60%二次返還給社員,20%—30%用來做社區公益。②在這樣堅實的經濟內循環下,合作社也積極向外對接市場,為永濟和運城兩個最近的大市場提供糧、油、米、面和蔬菜。在經濟外循環的過程中,蒲韓社區也保持同外部消費者的真實連接,比如配送員在配送貨品的時候指導消費者如何正確地選用生態食材。
蒲韓作為鄉村社區,具有生態構建的基礎,即廣泛存在于中國的傳統鄉村社群和土地。它保留了生態社區所需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恰好有能夠為社區轉型賦能的領導人鄭冰女士。在城市,生態社區建設的最大障礙是工業文明對社群體系的瓦解,但這恰恰也會成為生態社區建設的急迫要求。總而言之,不管是鄉村生態社區還是城市生態社區,其目標都是為了推動公正的、參與式的可持續健康社群的發展,都是為了服務于建立網狀的生命支持系統,以恢復地球這個有機體的生機和活力,恢復生命的健康與繁榮。
責任編輯:胡穎峰
[作者簡介]黃毅,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安徽合肥 230039);王治河,美國中美后現代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基金項目]2020年度安徽省社會科學創新發展研究課題“‘村社共同體視角下的鄉村振興與扶貧攻堅有效銜接路徑研究”(2020CX028)
①馬世駿等:《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生態學報》1984年第4期;王如松:《高效和諧——城市生態調控原理與方法》,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7—67頁。
②高吉喜、田美榮:《城市社區可持續發展模式——“生態社區”探討》,《中國發展》2007年第4期。
③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ur Common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文譯本參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王之佳、柯金良等譯,夏堃堡校,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81頁。
①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生態社區評價指南》,2021年5月21日,https://www.bzw86.com/205727.html,2021年12月17日。
②史巍、韓秋紅;《面向生態文明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兼論建設性后現代的邏輯進程》,趙成、姜德剛、王治河主編:《中國過程研究》第4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39頁。
③格里芬等:《超越解構:建設性后現代哲學的奠基者》,鮑世斌等譯,曲躍厚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303頁。
④王治河、樊美筠:《論建設性后現代的“有機自我”——當代西方“自我”概念發展的新取向》,楊麗、溫恒福、王治河主編:《中國過程研究》第5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60頁。
①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oston:Beacon Press,1994,pp. 100-105.
②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oston:Beacon Press,1994,pp. 253-256.
③菲利普·克萊頓:《過程哲學與系統管理》,趙成、姜德剛、王治河主編:《中國過程研究》第4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250頁。
①王治河:《過程哲學讓我們的愛拓展到他者》,《世界文化論壇》2015年第7期。
②大衛·格里芬:《復魅何須超自然主義:過程宗教哲學》,周邦憲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55頁。
③John B. Cobb,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 121.
④小約翰·B. 科布:《后現代公共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70頁。
①轉引自John B. Cobb,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 129-130.B34FDA31-1A06-492A-ACC5-3C31F209EC5F
②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oston:Beacon Press, 1994,p. 202.
③大衛·格里芬:《序二》,李惠斌、薛曉源、王治河主編:《生態文明與馬克思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①小約翰·柯布:《懷特海的價值理論》,張學廣譯,《天津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②曲躍厚:《過程哲學與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82頁。
③樊美筠:《懷特海有機美學初探》,趙成、姜德剛、王治河主編:《中國過程研究》第4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71—183頁。
①李建華、劉剛:《現代倫理共同體的斷裂及道德適應性補救》,《江蘇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②《柯布:不能將城市建設中的價值觀帶到鄉村》,2021年8月25日,http://www.zgcxxw.org/pro_news.php?id=12133,2021年12月17日。
③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
④潘于旭:《基于“塊莖思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邏輯探析》,《理論與評論》2018年第3期。
⑤Clifford W. Cobb,Responsive Schools, Renewed Communities, Calif. : ICS Press, 1992, p. 205.
①David C. Korten, Change the Story, Change the Future: A Living Economy for a Living Earth,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15, p. 101.
②Rick Smyre and Neil Richardson, Preparing for a World that Doesn't Exist-Yet: Framing a Second Enlightenment to Create Communities of the Future,Winchester: Changemakers Books , 2016,pp. 60-81.
③該案例所采用的素材來源于作者2017年8月在蒲韓社區的實地參訪。
④龍蕭如、葉裕民:《鄉村合作治理模式研究——以成都市戰旗村和運城市蒲韓鄉村社區為例》,《小城鎮建設》2021年第6期。
①楊柳:《蒲韓鄉村社區:我們家園我們建——永濟蒲韓鄉村社區發展的自組織模式》,《學術評論》2015年第2期。
①②侯賞:《蒲韓故事:凝聚社區,蹚出鄉村振興之路》,2021年3月27日,https://mp.weixin.qq.com/s/yX5SGsn5PaxXyjHOzKr_RQ,2021年12月17日。B34FDA31-1A06-492A-ACC5-3C31F209EC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