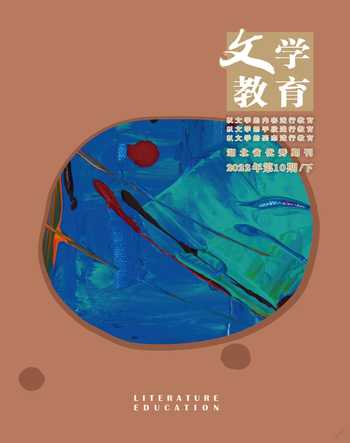城市懷古視角下《板橋雜記》中的遺民認(rèn)同
孫莉
內(nèi)容摘要:余懷于暮年寫作《板橋雜記》,透過城市懷古刻畫秦淮繁華景,在今昔對比中展現(xiàn)明清易鼎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明遺民曾經(jīng)的地位與身份被打破,自我價(jià)值重構(gòu)成為普遍難題。余懷作為明遺民之一,在“今”與“昔”之間重新尋找自己的身份,并通過傳承“道”來體現(xiàn)身份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身份認(rèn)同。
關(guān)鍵詞:余懷 《板橋雜記》 城市懷古 明遺民 身份認(rèn)同
《板橋雜記》是作者余懷于康熙三十三年完成的作品,采用筆記體的形式,分為上卷雅游、中卷麗品、下卷軼事三個(gè)部分,其中中卷所用筆墨最多,勾勒出了眾多江南名妓的形象。寫作完成時(shí)的余懷已經(jīng)七十九歲高齡,他借城市懷古,回憶往日秦淮繁華的景象,通過今昔對比哀嘆江山易代的滄桑,在“今”與“昔”之間重新尋找自己的身份,實(shí)現(xiàn)自我身份認(rèn)同。
一.追憶往昔繁華景
易代之際的文人常常回憶往昔繁華。靖康之變后,北宋皇朝覆滅,東京往日的繁華落盡,人們漸漸淡化了對東京的記憶,再度回憶時(shí)難免失于事實(shí)。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欲在人們心中復(fù)活故都盛景,記錄北宋都城東京的一景一物,形成“夢華體”敘事的傳統(tǒng)。《武林舊事》創(chuàng)作于宋末元初,“及時(shí)移物易,憂患飄零,追詳昔游,帶入夢寐,而感慨系之矣”[1],同樣是記載往日繁華,借盛世之景抒發(fā)對故國及往日生活的思念。《武林舊事》《夢粱錄》《板橋雜記》等作品均沿襲了“夢華”的傳統(tǒng),在物是人非的背景下神游故地,既留存過去生活的絕妙圖景,又哀悼繁華的消亡,抒發(fā)黍離之悲。
《板橋雜記》中的景物描寫主要集中于上卷,詳細(xì)展示了舊院、貢院、長板橋、秦淮燈船等標(biāo)志性地點(diǎn)和景物,為讀者展現(xiàn)了一幅繁華熱鬧的人文畫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對秦淮燈船的描寫,他透過這一焦點(diǎn)還原秦淮河曾經(jīng)的盛況。“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yáng)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guān)至通濟(jì)門水關(guān),喧闐達(dá)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2]燈船數(shù)量多、參與人數(shù)多、聲響大、持續(xù)時(shí)間長,往日的歡騰景象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而作者筆鋒一轉(zhuǎn),由樂轉(zhuǎn)哀,發(fā)出了一聲長嘆:“嗟乎,可復(fù)見乎!”[3]昔日盛況今日卻無法再見,余懷在對比今昔的秦淮燈船時(shí)感到無限悲涼。
秦淮燈船本身就是一個(gè)特殊的文化意象。如“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fēng),壞檻當(dāng)潮,目斷魂消。當(dāng)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4]“闌干浸在波濤底,畫船那得出游遨。夷船驟至連天漲,夷船退后江不浪。”[5]秦淮燈船的消失標(biāo)志著美好時(shí)光的消逝,文人心中的哀痛不言而明。秦淮燈船代表著繁華,也代表著富貴。孔尚任《桃花扇》中提到:“你看人山人海,圍著一條燭龍,快快看來!(眾起憑欄看介)(扮出燈船,懸五色角燈,大鼓大吹繞場數(shù)回下)(丑)你看這般富麗,都是公侯勛衛(wèi)之家。”[6]公侯勛衛(wèi)之家才能乘坐富有裝飾的燈船,于秦淮河上盡情游樂。余懷在《板橋雜記》上卷中著重提及從前秦淮河上燈船畢集的場景,不僅僅是追憶前朝,同樣也是追憶當(dāng)年的富貴生活。
明清朝代更替,作為明遺民的余懷在感嘆秦淮景物不可復(fù)見的同時(shí),又何嘗不是痛心于往日生活不可復(fù)來。吳偉業(yè)在《滿江紅·贈(zèng)南中余淡心》中稱贊余懷:“問后生、領(lǐng)袖復(fù)誰人,如卿者?”[7]余懷年少時(shí)期生活安逸,家境殷實(shí),且欲積極參與政治活動(dòng)。而明朝的滅亡給他的人生帶來極大的轉(zhuǎn)折,家產(chǎn)遭清軍洗劫,妻子受驚而亡,余懷自己也只能在多地輾轉(zhuǎn)漂泊。在清政府的鎮(zhèn)壓下,抗清勢力被摧殘殆盡,復(fù)明無望,余懷移居蘇州終老。他自稱“舊京余懷”,成為不仕清朝的典型遺民文人。但就像余懷在《板橋雜記》中所說:“以上皆傷今吊古、慷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dāng)哀絲急管。”[8]故國風(fēng)光已消失殆盡,隨之逝去的也有曾經(jīng)的個(gè)人財(cái)富與風(fēng)光,空留下遺民們心中的哀與傷。余懷意氣風(fēng)發(fā)的時(shí)光也已不可再現(xiàn),巨大落差之下的他將自己定位為明遺民,仿佛是滯留在了往日的繁華當(dāng)中。但遺民的身份終究無法讓余懷得到心靈上的安定,他要做的是真正認(rèn)同這一身份并重新尋找到自我價(jià)值。
“燈火游船,鼓吹名場。秦淮一水,閱盡興亡。”[9]余懷追憶秦淮昔日風(fēng)光中的具體城市景觀,帶有濃厚的懷古色彩,不僅表達(dá)對前朝的百般留戀,也借秦淮風(fēng)光之變映射自己的身世變遷、命運(yùn)遭際,余懷尋找著自己在新環(huán)境中的地位,尋求自我身份認(rèn)同。
二.哀嘆秦淮名妓悲劇命運(yùn)
名妓也是當(dāng)時(shí)城市中的一個(gè)重要部分,晚明狎妓之風(fēng)盛行,江南才子大多喜歡以風(fēng)流自居。魯迅于《中國小說史略》中談到:“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習(xí)俗相沿,以為佳話,故伎家故事,文人間亦著之篇章。”[10]《板橋雜記》中卷記述了多名名妓的風(fēng)姿與事跡,她們?nèi)菝叉谩⒚佳廴绠嫞医?jīng)由藝苑培養(yǎng),擁有才藝專長,如知書、善畫、懂琴等等。余懷筆下的她們與文人的交游中交易性質(zhì)往往不明顯,更多的是情投意合,很多名妓最終也嫁與文人名士。但是在政治動(dòng)蕩的大背景之下,名士或壯烈獻(xiàn)身,或退隱沉寂,而這些女子們的命運(yùn)也頗為坎坷。她們中的許多人在動(dòng)蕩的社會(huì)背景下香消玉殞,結(jié)局凄涼。透過秦淮群艷的悲涼遭遇,可以看到明清易代之際百姓生活的悲劇色彩。名妓失路與名士落魄相似,作者借群艷之凋零言明清之際名士們地位巨大轉(zhuǎn)變產(chǎn)生的苦痛。
作者詳細(xì)描寫了近三十位秦淮名妓,其中必定帶有緬懷當(dāng)年南京浪游生活的成分。“據(jù)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征江左之風(fēng)流,存六朝之金粉也。”[11]將昔日名士與美人的交游與今日各自飄零的凄涼局面對比,生發(fā)出無限嘆惋。余懷并沒有像許多文人一樣,單純寫作“狹邪”之文,“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艷治之是傳也”[12]。秦淮佳麗們不只有色與藝,余懷打破時(shí)人的固有看法,在容貌及才藝描寫之外記述表現(xiàn)名妓們的德行與大義的言行。比如甲申之變時(shí),葛嫩被執(zhí),面對清軍主將的凌辱,葛嫩大罵,嚼舌含血噴其面,最終被殺。柔弱的女子能迸發(fā)出如此強(qiáng)大的力量,盡顯其俠肝義膽、柔情傲骨。
秦淮群艷的情與義側(cè)面表現(xiàn)了余懷與清政府勢不兩立的決心。在他的筆下,從前的秦淮河風(fēng)光是美妙絕倫的,曾經(jīng)文人雅士與佳麗們的交往是情誼深厚的,生活有著說不盡的樂趣與雅趣。而清軍的入侵使一切化為泡影,他對此深惡痛絕。在清政府嚴(yán)苛的“文網(wǎng)”之下,余懷借看似“狹邪”的題材傾吐真實(shí)想法。他作詩書不寫清朝年號,隱居吳門,以賣文為生也拒不出仕,執(zhí)著地固守著明遺民這一身份,堅(jiān)守自己的價(jià)值觀念。
與將女性描繪成男子附屬物的文章或才子佳人模式的文章相比,余懷在《板橋雜記》中描寫的秦淮名妓更為客觀真實(shí)。然而,在某些方面仍可以明顯看出作者的情感偏向及過于美好的想象。他筆下的這些女子基本都容貌才藝雙絕且兼具德行與品格,個(gè)個(gè)都美好出眾。吳偉業(yè)曾言:“江左全盛,舒、桐、淮、楚衣冠人士避寇南渡,僑寓大航者且萬家,秦淮燈火不絕,歌舞之聲相聞。”[13]晚明秦淮相聞的歌舞聲中又有多少余懷筆下才貌雙絕、真情厚意的名妓?又有多少是兼具才思與民族大義的文人雅士?余懷似是有意挑選部分女子的命運(yùn)加以突出,試圖描寫名妓們面對國破家亡時(shí)的情與義,對她們進(jìn)行道德評判,作證自己固守“遺民”身份的行為,追逐著道德與政治方面的“正確”,在她們身上找尋身份認(rèn)同。作者有選擇性地突出明朝的繁華,著力書寫文士佳人風(fēng)貌才情與大義,這種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方式是帶有幻想色彩的。
三.遺民的價(jià)值探索與身份認(rèn)同
明清易代,山河淪喪讓名士們痛苦不堪,他們陷入身份焦慮之中,迫切地想要重構(gòu)自己的身份以獲得自我認(rèn)同。余懷就是其中之一,對故國深切懷念并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遺民”身份,拒絕出仕清朝。然而明朝已經(jīng)覆滅,他與當(dāng)下的清朝格格不入,因此產(chǎn)生了理想身份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志士選擇以身殉國,表明忠誠不渝的品格。比如張煌言曾在詩中說過:“大廈已不支,成仁百事畢。”“寧進(jìn)寸,毋退尺。寧玉碎,毋瓦全。”[14]死節(jié)是壯烈的,在當(dāng)時(shí)似乎演變成“忠”的象征。同時(shí),也有心屬故國卻不死節(jié)的人,他們提出了對死節(jié)的別樣看法,如陳確《死節(jié)論》:“死合于義之為節(jié),不然,則罔死耳,非節(jié)也。人不可罔生,亦不可罔死。”[15]然而在社會(huì)普遍觀念中,與死節(jié)之士相比,在新朝生活下來的明遺民在一定程度上是“應(yīng)死未死之人”。因此,他們不僅需要表明自己對故國的赤誠之心,更需要為自己在“夾縫”中的生存尋找理由。就余懷而言,雖然在明朝時(shí)有為國效力的志向和才能,但作為明遺民,為新朝效忠顯然是不現(xiàn)實(shí)的。黃宗羲曾說:“遺民者,天地之元?dú)庖病H皇扛饔蟹郑蛔绮慌c,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16]明遺民們不與清政府合作,以此保持對前朝的歸屬感。有志于政治的志士仁人面對這一局面會(huì)感到生不逢時(shí),無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身為精神上的明朝人為何容忍自己生活于清朝?繼續(xù)生活下來又能創(chuàng)造出什么樣的價(jià)值和意義?
《板橋雜記》下卷講述了很多曾經(jīng)瀟灑風(fēng)流的名士或貴族,在明亡后生活陷入困頓。張魁亂后還吳,最后竟窮困而死。中山公子徐青君乙酉鼎革后淪落至為人代杖。“余之綴葺斯編,雖以傳芳,實(shí)為垂戒。”[17]余懷雖然說下卷的主要作用是垂戒后人,但其實(shí)仍是借這些人的遭遇突出今昔強(qiáng)烈對比。明朝滅亡后人們的生活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從前盡享地位、財(cái)富的人們面臨著失去原有高貴地位及財(cái)富的境況,如何謀生成為了大問題。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走向民間,行醫(yī)、經(jīng)商、賣畫以維持生計(jì),但用“平凡”的方式謀生,心中的志向與當(dāng)前的生存狀態(tài)相差甚遠(yuǎn),如何能體現(xiàn)出“明遺民”這一獨(dú)特身份的價(jià)值?這使得他們越發(fā)急切地要尋找自身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自我身份認(rèn)同。
清初,統(tǒng)治者施行暴政,實(shí)行民族壓迫政策,圈地導(dǎo)致民眾流離失所,頒布“剃發(fā)令”,強(qiáng)制民眾服從異族風(fēng)俗。在這種情況下,明遺民們普遍擔(dān)心本民族文化與“道”將在強(qiáng)制或潛移默化中消失殆盡,民眾會(huì)被異族統(tǒng)治者的思想體系同化,失去漢族人特有的品格。因此,他們力圖通過著述等方式恢復(fù)“道”與“禮”,強(qiáng)調(diào)漢族道德標(biāo)準(zhǔn),維護(hù)儒家倫理綱常、價(jià)值體系。明遺民們拒絕與新朝合作,便無法從政治的高度上傳播“道”,轉(zhuǎn)而將目光轉(zhuǎn)向民間,以求“正人心”,移風(fēng)易俗。明遺民們尋求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路徑之一便是傳“道”,通過這一方式實(shí)現(xiàn)自我的安頓。
余懷實(shí)現(xiàn)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途徑便是留存過往美好記憶,在作品中將“道”傳承下來。無論是贊美秦淮舊風(fēng)光,還是追憶曲中佳人,余懷記錄下來的都是曾經(jīng)的美好,他心中的故國情懷得以安放,也勾起廣大明遺民的回憶,向后世的讀者展現(xiàn)如夢似幻的明朝。同時(shí),余懷也不忘在作品中傳承“道”,擁有“大義”的名妓就是承載“道”的載體之一,余懷在群艷事跡中偏偏擇此一種來寫,足可見他對道義的重視,通過社會(huì)地位并不高的女子們身上折射出的“道”,反映堅(jiān)守“忠”的重要性,以此堅(jiān)定自己的信念。
整部作品充滿了作者對明朝的懷念,體現(xiàn)了繁華與凄涼轉(zhuǎn)換時(shí)巨大的落差感。余懷不時(shí)在文中發(fā)出嘆息:“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棲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18]“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19]余懷也有意將作品的效仿對象定位于《東京夢華錄》這樣的懷古城市筆記,而不是青樓小說、“狹邪”筆記,并不將立意局限于展現(xiàn)舊時(shí)秦淮聲色。從這一點(diǎn)來看即可以明確其在《板橋雜記》中的深沉寄托。
暮年的余懷追憶秦淮風(fēng)月,通過城市懷古,刻畫秦淮一帶繁華景象,充分描繪景與人背后的文化內(nèi)涵,并在今昔對比中展現(xiàn)明清易鼎給人民生活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文人的地位與曾經(jīng)的身份被打破,余懷試圖通過深切懷念舊朝來證明“遺民”身份,傳承“道”以體現(xiàn)身份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身份認(rèn)同。
注 釋
[1]周密:《武林舊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2]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3]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
[4]孔尚任:《桃花扇》,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170頁。
[5]魏源:《魏源全集》,岳麓書社2004年版。
[6]孔尚任:《桃花扇》,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33頁。
[7]吳偉業(yè):《吳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08頁。
[8]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9]繆荃孫:《繆荃孫全集筆記》,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頁。
[10]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頁。
[11]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12]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13]吳梅村:《吳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4]張煌言:《張蒼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5]陳確:《乾初先生遺集》卷五,《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頁。
[16]黃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二,康熙二十七年刊本。
[17]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18]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頁
[19]余懷:《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頁
參考文獻(xiàn)
[1]李瑄.《明遺民群體心態(tài)與文學(xué)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書社,2009年.
[2]周曉琳、劉玉平.《中國古代城市文學(xué)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鐘繼剛.《艷冶之游與文化情懷——論〈板橋雜記〉》[J].《中華文化論壇》,2005年第03期.
[4]陳寶良.《明代士大夫的節(jié)義觀念及其行為抉擇》[J].《明史研究》,2014年第00期.
[5]齊鈺.《〈板橋雜記〉在青樓軼事小說中的典范作用研究》[J].河北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7年.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