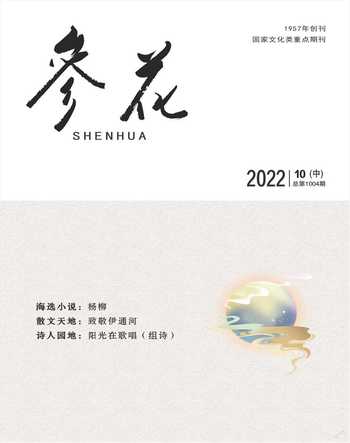印記生命:讀《同在陽光下》
曲慶彪
捧讀一本詩集,往往就會禁不住去想:詩歌稀有的品質是什么?詩人何以贏得詩歌之神的眷顧?當我們談論詩歌的時候,是更在意詩歌本身帶給我們的形式上的美感?還是要關切詩歌背后詩人情思如紗入水般的浸潤和涌動?
掩卷回想,《同在陽光下》帶給我們可碰觸的形式美感和深層意蘊——
取材不拘細大,立意誠篤質實。詩含三輯,第一輯《記憶是一首老歌》輯十七篇詩文,以星空問道起勢,銜之以生日之思、燭光夜話、活著的感慨。這里有童真似幻、青春如祭、漸行漸遠的年華和永不褪色的記憶;這里有撞擊生命的重大礦難、某一年某一處雨中的冥想、情愛激起的生命之痛、給摯愛親人的紙短情長。此輯收于《燃燒》和《選擇》,落筆在寧愿燃燒的執著和自由選擇的無悔上。第二輯《在路上》輯十四篇詩文,成都、重慶、資陽、井岡山、武漢、長春、榆樹治江村……雖非戎馬倥傯,卻也南征北戰。歷來羈旅伴斜陽,遷客騷人最易生慨嘆,而此輯中的詩文,充滿蜀國深情、故土之戀、圣地遐思、客途清歡。在路上,看腳下,作者把每一步都走得扎實穩妥。第三輯《古格王朝》輯十九篇詩文,從記憶中的老家寫起,點出“西藏把我帶回老家”的至深至戀。詩人娓娓傾訴布達拉宮紅與白的往事,沉浸于拉薩星月可親的夜色,詠唱拉薩河的年輕、歡樂、沉默、驕傲,嘆惋古格王朝的寂落與悲涼。與此同時,詩人也不忘為進入藏區的孤獨旅人譜一曲情歌,書寫與戰友、與藏民的深情厚誼,謳歌雪域高原的真山、真水、真精神。誠如作者所言:“西藏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執迷西藏自由的心靈。我是西藏的兒女,樸實無華;我是高天厚土間的白云,追尋我日夜向往的歸處。我執著,我野性,我崇尚西藏不遮掩的生命。”天地人神,四季風物,現實關切,靈魂問答。凡所會心處,或感于一沙一葉之幽微,或嘆于宇宙大千之宏闊,皆入于淺吟低唱;行旅匆匆的奮斗生涯,與大江大河的生命對話;舊雨新知間的應和酬答,對親慈骨肉的至愛牽掛,都融進長句短札。
意象簡括自然,賦語凝練穩妥。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寫道:“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詩人的心是最易與外物共情的,而詩人凝思結想的創造能力遠遠大于對現實的簡單模仿。這里既有生活的痕跡,更有心靈的光芒,尋常物事往往寄意深厚,真山真水更加讓人動容。意象是詩歌最基本的組成部分。詩人龐德曾說:“一個意象是在一剎那的時間里呈現理智和情感的復合物的東西。”詩中的意象組合能清潔或去蔽世界的本來面貌,為讀者照亮一個充滿生命情趣的世界。作者將眼中所見、耳中所聞、手中所觸、心中所念,如采擷花蕾般,一一裁剪鋪陳。寫實者,如蜀雨、梅雨、東湖、濕地、夜色、蓮花、年輪、大樹;寫意者,如古格王朝遠去的背影、雪域高原寂寥的海思、城市高墻、心靈鎖鑰、乾坤的呼吸……借用《周易·系辭·上》所言,“圣人立象以盡意”,準確的審美意象能使作者所要表達的自我感受,那種意味,那種復雜而又不可言喻的情緒找到“對等物”,這也是意象的獨特價值所在。作者擷取工作生活中那些觸碰心靈的客體,開敞去蔽后融于主體的無盡遐思,曲盡物性人情,化作筆底波瀾、詩中意象,為讀者帶來豐富的體驗。
在詩歌語言的運用上,作者融古于今,駢散結合,那些對仗、韻腳的使用,那種凝練精致、直抒胸臆的筆法,鋪墊出古典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的底色,而散落各處的詞性活用、隱喻象征、個體感悟的奇特化書寫,又使詩歌或多或少地呈現出一點現代朦朧詩的特征,恰如朝暾光輝映照下的雪域,峭拔高峻而設色溫暖。詩意往往源自詩歌語言的奇特化,而詩歌語言的奇特化,關鍵在于處理好那些撲入詩人眼底心頭的可融合的異質性因素。“那些/期待烘烤的記憶/變成了/荒蕪和月色”“刨開的路面/透出了腥味的喘息”“無意坐看葉脫枝,忽聞風落山水間”。這些詞語的活用,隱喻、象征等修辭手法的使用,讓詩歌的異質性因素得到瞬間組合,創造出一道陌生而又能引起共鳴的心靈風景。也正是通過詩歌語言的奇特化書寫,作者獲得了對歷史、對生活的最誠懇的觀照和反思。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曾說過:“詩之難,其《十九首》乎!蓄神奇于溫厚,寓感愴于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在這本詩集中,神奇與溫厚、感愴與平和、深與淺同樣作為對立因素,相互抗衡、完美共存于詩歌的語言之中,用奇而不用險,質實卻不落窠臼。
運思靈動自然,落筆理趣交輝。詩人筆致超脫,不膠著于事,不凝滯于物,不停留于對意象的簡單摹寫,而長于點染情韻、揭示哲理。他對自己的靈魂是有期許的——“我一直渴望/站到一個高處/問候早晨的太陽”;他有詼諧自謔的勇氣——“留有寸心好自嘲”;他對德行與自然同等重視——“大道朝天德作梯/小溪歸海月為橋”;他深諳變化之美,人的渺小與自然的闊大,生與死的辯證和超越——“在大自然的襯托下,人是如此的渺小,何等的脆弱……”從很多詩中,我們都可以讀到誠于肺腑的赤熱、天藍水藍的透徹。那是生命深處的回眸,歷盡千帆后的從容。不空洞,不無病呻吟,不是暮年哀婉,而是從世情百態里穿越過來的長者智慧、善者良知。人在世俗世界里會有謊言,對別人,尤其是對自己,而人在詩的國度里是撒不了謊的,因為詩心正是宇宙的直覺,真與善如伉儷相攜,美是愛的孩子。所有幽潛的內在,經由語言化作遼闊的外在,詩人吐露的一定是對自己、對世界至真至誠的語言之花。而語言之所以被稱為詩,是需要張力的。詩人的獨特經歷和真誠表達,造就了《同在陽光下》獨特的張力結構。《同在陽光下》的張力結構既不是語言的,也不是題材的,而是源自詩人的思辨與激情。感性的絢爛與理性的中正很好地交融在字里行間,詩的總體風格是剛健輝光、溫厚自適的。文如其人,這些詩文綿里裹鐵,有著溫柔敦厚的硬朗。
更難能可貴的是,充滿歷史感和個體經驗的時間自覺,天涯海角、蒼穹一隅的空間意識,貫穿在整本詩集之中。詩人給我們展示的,是這闊大宇宙中無邊的心靈風景。
乍一看,詩行里隨處都是領略了“社稷沉浮人百態”、束身于“樓高難下、廟宇之大”的身份印記。作者書寫仕途浮沉——“可貴的鳥兒……沉默的羽毛,散落在大街小巷”;三緘其口的無奈——“不再發出聲音”;何去何從的茫然——“此時,我佇立在十字路口”;同時,也抒發了自己縱使戴著鐐銬舞蹈,亦能盡力舒展雙翅,在有限度的自由內,追逐藍天與夢想。他憧憬未來——“希望給了/牙牙學語的嬰兒”;他更無悔選擇——“不想隨流而下/寧愿,站著/在荒野中凝固……不想躬身而朽/寧愿,燃燒/在塵埃中飄逸……”雖然其特殊的身份帶給詩人一定的內斂特質,但詩人仍然坦言:“放棄……是人的一種解放”。詩人用詩完成了對世俗身份的超越。同時,這些帶有明確身份印記的詩歌,因為情感的克制和奔騰,多出一份咬嚼不盡的味道。
細細品味,詩集中體現得更多的是敏于感悟、擅于沉思、敢于放歌的心靈印記。在《選擇》一詩中,作者將自己眾多的“人格面具”歸類為“我”“你”,以“我”“你”之間,鏡與燈式的交互,向讀者敞開了自己。“我”是自卑的、丑陋的、貪婪的;“你”是自然的、善良的、執信的。因為相互選擇,“你”不得不結束純真、過早成熟,而“我”或者迷失原路,或者躲過災禍。因為交換了價值,痛苦和幸福,得到與失去都在其中。作者沒有對人的原始本性及社會化規訓作二元對立式的評判,而是洞悉了人生之路的兜轉無常,辯證地看到“反者道之動”的轉化。這樣的坦誠,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靈魂的豐富和醒覺,感受到了融貫始終的內隱性張力:潛意識和文化理性之間的張力。
可以想見,作者在夜闌人靜時,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綴念成詩,心旌搖蕩,滴滴點點,都是生命的印記。康德說:“詩使人的心靈感到自己的功能是自由的。”《同在陽光下》讀來蘊藉中有明朗,婉轉里涵堅實,是一種精神的舞蹈和靈性的舒展,是存在的澄明。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云萬里天。一個人心中印記著一個世界,朗心澈照時,云舒云卷萬幻如畫;虛頤無念處,萬物靜息自在圓融。一本詩集,便是一江水,萬里天。
(責任編輯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