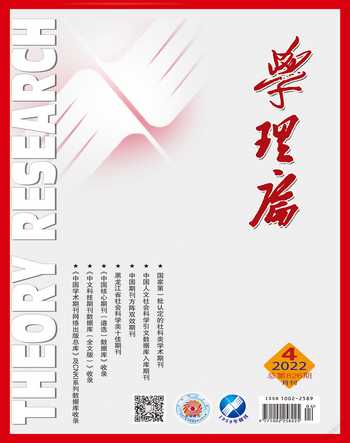對三種矛盾及其關系的分析和探討
徐祿 毛建儒
摘 要:矛盾作為一個概念既重要又流行,但它有不同的含義,概括地講有三種:形式邏輯意義上的矛盾、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這三種矛盾的含義和關系是,形式邏輯意義上的矛盾屬于表達層面的矛盾;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則是本體論層面的矛盾;至于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其所指是人與人關系層面的矛盾,即人與人之間的摩擦、糾紛和爭斗。就第一種矛盾而言,它是必須排除的;第二種矛盾不同于第一種矛盾,它是一種客觀存在;第三種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產生后必須予以清除。
關鍵詞:矛盾;形式邏輯;辯證法;社會日常;探討
中圖分類號:B0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22)04-0037-04
矛盾,在中國理論界是一個重要術語,在中國政界是一個重要概念,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是一個流行用詞。但對矛盾的含義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此帶來的爭論和爭議也持續多年。本文試圖就三種矛盾問題進行分析、梳理和探討,以期澄清含義、走出誤區,使其關系回到真的“軌道”。
一、形式邏輯意義上的矛盾
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區別之一就是創造文字,并使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表達的過程中,為了使別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就要遵循一定的原理,正是在這種需要的推動下產生了形式邏輯。形式邏輯在古代的許多國家都有其萌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早在戰國時期,《韓非子》中就有這樣的論述:“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1]三國魏嵇康運用此法駁“兩可之說”,提出“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認為以“兩許之言”求“兩濟”,必陷“矛戟之論”[1]496。這里講的就是矛盾律,即人的表述不能矛盾。當然,這里的矛盾律還隱藏于具體的事例中,尚未上升至理論的高度。
形式邏輯發展的最高水平在古希臘。柏拉圖在《歐蒂德謨篇》中對矛盾律已有所表述:“那就是說,你仍然是個沒有知識的人了?可是你早先承認自己是有知識的;所以,你顯然承認你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即承認在同一關系下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2]亞里士多德是形式邏輯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形式邏輯的三個原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還探討了形式邏輯的很多問題,如“三段論推理”等。關于矛盾律,亞里士多德指出:“證明的原理……例如對每一事物必須或肯定或否定,以及事物不能同時存在而又不存在……所有第一原理中最確定的原理是,同樣的東西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同一方面屬于又不屬于同一事物。”[3]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可概括為三點:一是對于同一事物必須或肯定或否定,而不能既肯定又否定;二是事物不能同時存在而又不存在;三是同樣的東西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同一方面屬于又不屬于同一事物。簡而言之,在表達思想的過程中不能存在矛盾。如果存在矛盾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就會產生理解困難,就會妨礙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因此就表達而言,必須排除矛盾,不能讓矛盾存在。
為了排除矛盾,歷史上還產生過一些學者集團,如西方的智者、中國的名家等,他們具有豐富的邏輯知識,并使用邏輯知識去挑剔他人的矛盾,同時也制造出不少違背規律的“詭辯”。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些學者集團推動了形式邏輯的發展,在提高表達能力的方面也做出了貢獻,特別是他們提出的問題還間接刺激了科學的發展。
這就是形式邏輯所講的矛盾。這里的矛盾是消極的,是不允許存在的。形式邏輯的這個要求也適應于科學。實際上,形式邏輯在科學中發展起來,后又被應用于科學之中,其典型的事例就是歐幾里得幾何,歐幾里得幾何就是在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的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可以說沒有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就沒有歐幾里得幾何。在古希臘之后,特別是近代之后,科學的發展一直遵循著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當然,在科學中完全消除矛盾是不可能的,科學中總是有新的矛盾在不斷產生,一旦新的矛盾被發現,科學又開始了消除新矛盾的過程,這個過程循環往復以至無窮。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得到了發展。
二、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
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就是對立統一。對立統一早在古希臘就有論述,例如阿那克西曼德認為:“對立物是包含在一個東西里面,并且借著分離作用從這個東西里面跑出來的。”[4]畢達哥拉斯認為,“對立是存在物的始基。”[4]189赫拉克利特更為明確,“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把它分為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了。”[4]193“一切都由對立而產生。”[4]195“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組造成最美的和諧;一切都是通過斗爭所產生的。”[4]195對對立統一做系統描述和分析的是黑格爾。“差別自在地就是本質的差別,即肯定與否定兩方面的差別:肯定的一面是一種同一的自身聯系,而不是否定的東西,否定的一面,是自為的差別物,而不是肯定的東西。……因此本質的差別即是‘對立。”[5]“……因此肯定與否定都是設定起來的矛盾,自在地卻是同一的。兩者又同是自為的,由于每一方都是對對方的揚棄,并又是對它自己本身的揚棄。”[5]258-259“矛盾是推動整個世界的原則,說矛盾不可設想,那是可笑的。這句話的正確之處只是說,我們不能停留在矛盾里,矛盾會通過自己本身揚棄它自己。”[5]258
赫拉克利特和黑格爾所講的矛盾是指本體論上的矛盾。這種矛盾概括地講,具有以下含義:一是事物包含對立的兩個方面,即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二是肯定的方面與事物是同一的,它是保持事物的力量;否定的方面與事物是對立的,它是推翻事物的力量。三是否定的方面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與事物對立,另一方面又是在事物之中生長和發展起來。四是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相互揚棄。所謂揚棄,就是既克服又保留。這是一種辯證的否定,即肯定的方面否定否定的方面包含著肯定,否定的方面否定肯定的方面也包含著肯定,肯定和否定相互交織、相互滲透。五是作為揚棄,它包含著克服的一面,而克服就是斗爭。赫拉克利特對斗爭評價很高,認為一切都是通過斗爭所產生的,正義就是斗爭。他還對斗爭的特殊形式——戰爭進行了分析,“戰爭是普遍的。戰爭是萬物之父,亦是萬物之王”[6]。六是矛盾是推動整個世界的原則,其作用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首先,肯定的方面為維持事物的運行就要反對否定的方面,與此同時肯定的方面還要把否定方面的有益成分吸收到自身之中,肯定的方面變得強大和完善;其次,當否定的力量超過并戰勝肯定的力量時,新事物代替舊事物,推動事物的發展。57D22726-AC13-41CD-9218-37059AE6F53D
顯然,赫拉克利特和黑格爾所指稱的矛盾是事物自身的矛盾,即事物所包含的肯定方面與否定方面的矛盾,這是本體論層面的矛盾——矛盾源自事物的差別,差別是內在的差別、本質的差別;由差別引起對立,對立不是其他對立而是事物內部肯定方面與否定方面的對立。因此,矛盾是事物的矛盾,是事物自身的矛盾,它存在于自然界、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之中。如此,事物自身的矛盾是“矛盾”嗎?可以肯定地說,這種矛盾并非形式邏輯的矛盾,因為形式邏輯的矛盾不涉及事物,只涉及事物的描述。就描述而言,形式邏輯要求不能存在矛盾,并且在形式邏輯中矛盾是消極的、是被排除的對象。雖然矛盾在被發現前總是以潛伏的形式存在,但形式邏輯并沒有放棄其目標,也在不斷地發現矛盾、不斷地排除矛盾。而事物自身的矛盾就不同了,這種矛盾是不可排除的。不僅如此,這種矛盾還是積極的,其積極性表現在:它是事物運動的源泉,它推動了事物的發展。可見,事物自身的矛盾是一種不同于形式邏輯的矛盾。
那么,這種矛盾是如何產生的呢?存在兩種解釋:一種是矛盾為事物自身所固有,矛盾概念不過是對事物矛盾的反映;另一種是矛盾來自于主體(人),是主體把矛盾概念映射至事物本身,因而產生了事物的矛盾。這兩種解釋孰是孰非,需要進行分析。具體而言,矛盾概念不可能憑空產生,而是源自事物。事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社會事物,其在矛盾概念產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矛盾概念更多地依賴于社會事物,更多的是對社會事物的反映;就自然事物而言,它存在類矛盾現象,促成了矛盾概念的形成,但自然矛盾主要移自社會矛盾,是社會矛盾的推廣,因而從這個角度看,自然矛盾具有擬人化的傾向。例如,自然中的吸引和排斥、化合和分解、遺傳和變異等都只是具有相反性質的屬性,它們既不會對立也不會斗爭,而是按照一定的規律和比例共聚于事物之中。對于規律和比例,它們并沒有自覺的意識,僅是主體賦予自然之上的,即主體按照概念構造去賦予自然、認識自然。矛盾的擬人化傾向并非完全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自然具有自己的規律,擬人化要服從規律,否則將在規律面前碰得“頭破血流”。矛盾的擬人化亦指稱“自然的價值化”,即主體根據自我需求來評價自然,其背后隱藏著主體價值,因而主體的價值觀起決定作用。
這就是我們關于擬人化的認識。當然,黑格爾的矛盾觀不僅涉及擬人化的問題,在他的體系中,概念的矛盾是先在的,自然和社會的矛盾都是由概念的矛盾衍生的。從哲學層面上講,黑格爾矛盾觀的問題主要在于將認識論問題演變為本體論問題。就認識而言,主體通過學習形成概念世界并在概念世界的指導下認識事物,因此認識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是主體、概念世界、客體三者的關系。概念世界一方面依賴主體,另一方面亦可離開主體自我運動,這種自我運動具有相對自主性或獨立性。然而,黑格爾將概念世界的自主性予以絕對化。在體系建構中,首先是概念的獨立運動,然后由概念世界演化出自然和社會。具體而言,在認識事物時,概念世界具有先在性,主體總是在概念世界的指導下去認識事物,但黑格爾卻將認識問題推向本體層面,即概念世界在本體上也是先在的,如此便陷入遮蔽主體的錯誤,將概念世界與客觀世界(包括自然和社會)的關系顛倒,進而割斷了認識的歷史。正是基于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黑格爾進行了嚴厲批判,并將黑格爾顛倒的世界顛倒過來。馬克思曾指出,“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我們說,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7]。對此,恩格斯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所以是顛倒的,是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看來應當是‘思想的自我發展,因而事物的辯證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實際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只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進行的、并服從于辯證形式的現實發展的反映”[8]。當然,這里的顛倒僅指本體論上的顛倒,即讓辯證法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
此外,黑格爾認為事物的運動和發展屬于自我的運動和發展,其動力源泉是事物內部的矛盾。黑格爾的觀點克服了機械論的弊端,但本身存在片面的色彩。這種片面性主要表現為三點:一是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依賴內部矛盾,但事物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二是事物的運動和發展越來越受主體操控,其操控須在事物運動和發展的規律上進行;三是主體根據自我需要創設人工自然,人工自然雖然逐漸智能化并具有自我運動和發展,但這只是相對而言。
三、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
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不同于前兩種矛盾,它基于人們的日常生活,是一般人對矛盾的理解。這種矛盾在不同社會中具有不同的特點。就中國社會而言,人們承認差異,但差異并不是矛盾,有差異可能導致矛盾,這是人們竭力避免的,人們追求的是在差異基礎上的“和”。這就是“和而不同”:“不同”是差異,“和”則是一種關系、一種目標。因此,“和”在中國社會中處于關鍵地位,衍生出各種關于“和”的詞匯,如“和為貴”“一團和氣”“和衷共濟”等。“和”源于“差異”,但“和”與“矛盾”是對立的。如果有了矛盾,就要解決矛盾,解決矛盾的目標就是達到“和”、實現“和”,由此社會才能進步和發展。
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其含義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摩擦、糾紛、爭斗。這種矛盾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講,有經濟原因、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等,多種原因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就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作用而言,它總是消極的,矛盾影響生產的進行,使日常生活陷入紊亂,引發沖突,甚至阻礙社會發展。盡管如此,我們仍無法徹底斷絕它。這種矛盾是一個客觀的存在,無論你喜歡與否,它都會以自己的方式“矗立”在那里。所以,針對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回避只是一種“鴕鳥政策”,它會導致更大的矛盾、付出更大的代價,這在歷史和現實中都不乏其例。回避是不可取的,直面這種矛盾才是正確之法。直面矛盾就要弄清矛盾、解決矛盾,前者是知后者是行,要把知行統一起來才能真正解決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
解決矛盾還存在一個解決方法的問題,不同質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這就是所謂的“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例如,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其解決的方法就不同;即使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也有不同的解決方法。為什么要采用不同的解決方法,首先是由矛盾的性質決定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外部環境的問題。這就是說,外部環境不同,解決矛盾的方法也自然不同。并且,解決矛盾的方法需要創新。這里具有兩層含義:一是解決舊矛盾的方法不一定能用來解決新矛盾,即使新舊矛盾類似度很高,對舊的方法也不能照搬照抄,因為新舊矛盾之間必然存在內部差異和外部差異;二是新矛盾和舊矛盾在“質”上具有根本不同,舊的方法基本上失去效用,這就需要根據新的矛盾來創造新的方法。創造的過程充滿艱難和曲折,需要反復試驗和摸索,只有找到了新的方法才能真正解決新的矛盾。通過方法創新解決問題,矛盾各方之間的摩擦、分歧、爭斗不復存在,其關系變得協調、和諧,進而推動事物的發展。57D22726-AC13-41CD-9218-37059AE6F53D
四、對三種矛盾關系的分析、探討
形式邏輯意義上的矛盾、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可以說是“顯矛盾”,學界研究較多,當然也存在一些偏差和失誤;而對于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盡管它對一般人、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影響很大,卻是一種“隱矛盾”,學術界很少、特別是很少從傳統文化的角度去探討它;至于三種矛盾之間的關系,更是研究領域的“空白”。基于此,有必要對三種矛盾的關系予以分析和探討。
第一,就人們的思想表達而言,形式邏輯是絕對的,是不能被否定的。這就是說,對于思想的表達必須遵循形式邏輯的規則,必須清除一切矛盾,否則就會悖論連篇,就會導致思想的混亂,進而阻礙思想的交流。更為嚴重的是,它還會影響思想的實行,這樣就不再是思想問題,而成為實踐問題。實踐問題會產生實在性后果,會對生產和生活造成諸多爭論甚至沖突。正因如此,古今中外都要求遵循形式邏輯,按照邏輯的基本規則表達認知、傳達思想。
第二,形式邏輯不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指的是一種世界觀,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靜止的,即便存在運動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沒有質變和飛躍。這種世界觀在歷史上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它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近代科學的產生和發展。然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違背了世界是聯系和發展的真實情況,遭到了恩格斯的猛烈抨擊,“它已被自然科學的新成就沖擊得千瘡百孔,代替它的是辯證的世界觀”。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對形而上學的批判是應當的,它確實存在問題,但使用形式邏輯來處理本體論問題或者把形式邏輯視為形而上學的做法卻是錯誤的,它使形式邏輯陷入了荒謬的境地。杜林就是這樣,他把形式邏輯本體化,由此否定客觀世界存在矛盾。杜林的觀點同樣遭到了恩格斯的批判,在恩格斯看來,客觀世界充滿矛盾,思維領域也同樣充滿了矛盾。可以看出,恩格斯的批判,其立腳點是本體論,但我國部分學者卻把恩格斯的批判移至形式邏輯,認為形式邏輯就是形而上學并開展對形式邏輯的批判。事實上,這是對形式邏輯的一種誤解,因為形式邏輯與形而上學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對象。形式邏輯僅論及思想表達,不涉本體層面;形而上學作為一種世界觀,本身探討的就是本體問題,因此不能將形式邏輯等同于形而上學,并用批判形而上學的方式去批判和否定形式邏輯。
第三,辯證法的矛盾屬本體論層面的矛盾。在本體論上,矛盾(或類矛盾)確實是存在的。矛盾簡單地講就是對立統一,就是統一的事物包含著相互對立的力量。當然矛盾并非客觀世界的全部,在客觀世界中除了矛盾,還存在非矛盾。即便矛盾本身也不是只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而是存在多種相互對立的力量。矛盾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表現也各有特點,決不能一概而論。這就是說,即使是本體論上的矛盾,也有許多問題需要分析、需要討論。過去在這個方面存在教條主義傾向,只依名人言論為圭臬,當下必須克服這種傾向,必須面對自然、面對社會,一切以客觀事物為標準,以實踐為標準。
第四,辯證法矛盾最大的問題在于:把矛盾當作事物發展的動力。一些學者還進一步把斗爭當作事物發展的動力。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需要厘清發展的機制。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對已有事物的維持以及新事物代替舊事物。對已有事物的維持取決于事物內部各因素的協同,如果無法協同合作,已有事物就會走向混亂和崩潰。新事物代替舊事物則復雜得多,它牽涉到舊的因素、新的因素,牽扯到舊的結構、新的結構等,其中最根本的是新的結構代替舊的結構,這種代替包括舊的因素和新的因素的重組、融合、協作。在這個過程中,矛盾和斗爭肯定是存在的,但僅靠矛盾和斗爭,事物是發展不起來的,因為事物的發展同樣依靠協同與合作,而矛盾和斗爭只有利于協同與合作才能推動事物的發展。
第五,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不同于邏輯矛盾,兩者分屬不同層面;至于辯證法的矛盾,兩者既有相似也存在差異。就相似性而言,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同辯證法的矛盾一樣是涉及本體問題的;差異性則在于:辯證法的矛盾是一種客觀性存在,而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則是一種關系性存在,即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交往,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是不存在的,由此這類矛盾可以產生也可以不產生,其中沒有必然性。此外,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產生后并沒有積極意義,人們總是想方設法去解決它、清除它。
第六,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不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僅如此,它還會阻礙社會的發展。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無法徹底清除,因為它總在不斷產生,為了清除它對社會的阻礙作用,就要不斷解決它。如果它被解決了,而且解決得很及時,便推動社會進步。這里的推動,并非源自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而是源自對社會日常意義矛盾的解決,因此不是它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而是對它的清除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對于這個問題,過去曾陷入過“誤區”,即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的解決可推動社會發展,而解決它的前提是它的存在,這就產生一個悖論:解決它可以推動社會發展,由此推論解決它越多就越能推動社會的發展,它存在得越多就相應解決得越多;然而,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又是消極的,它存在得越少則越好。這個悖論的根源在于:把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存在與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解決混淆起來。就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本身而言,它是消極的,它越多就越不利于社會的發展;解決它則不同,解決的目的是清除它,對它清除得越多就越能推動社會進步,因此,它和清除它并非同一件事情。
在此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社會日常矛盾的產生與人相關。根據它與人的關系,社會日常矛盾可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人的力量無法控制的;第二類是人不作為導致的;第三類則是人故意制造的。對于第一類矛盾,人沒有辦法阻止它的產生,而只能在它產生之后創新方法予以解決;第二類矛盾則不同,因為它產生的根源在于人,如果人并非不作為而是積極為之,這類矛盾就不會產生或很少產生;至于第三類矛盾,則完全是人造成的,需要對此類“人”進行改造和提升。過去我們講社會日常意義上的矛盾,往往離開“人”而抽象地論及問題,因而無法解釋很多社會現象,我們應重拾主體因素,以人的客觀實際為出發點解決矛盾。
以上便是形式邏輯的矛盾、辯證法的矛盾以及社會日常的矛盾之間的關系。厘清三者關系,不僅具有較大理論意義,而且還具有較大的實踐價值。因為這涉及主流意識,既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又直接影響到人們的行動。然而在這個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我們的分析和探討只能說是一種嘗試,在這一嘗試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說清楚,我們的探討還將繼續下去,以求達到真理之目標。
參考文獻:
[1]馮契.外國哲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496.
[2][蘇]阿·謝·阿赫曼諾夫.亞里士多德邏輯學說[M].馬兵,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72.
[3][英]威廉·涅爾.邏輯學的發展[M].張家龍,洪漢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60-61.
[4]張傳開.古希臘哲學范疇的邏輯發展[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188.
[5][德]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254.
[6]苗力田.古希臘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41.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8.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3.57D22726-AC13-41CD-9218-37059AE6F5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