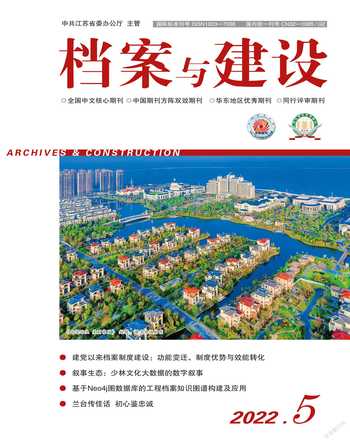“檔案行動主義”:內容、實踐與實質探析
蘇立
摘 要:“檔案行動主義”發軔于20世紀70年代,孕育于社會和文化運動推動、后現代檔案學興起與媒介行動主義發展,主張檔案職業需要推動問責和變革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文章認為,強化認同與維系情感、推動問責與揭示真相、謀求變革與伸張正義三方面是“檔案行動主義”的主要實踐表現;網絡社會的權力結構變遷、對檔案功能的重新認識、對檔案職業的重新定位是“檔案行動主義”誕生的實質。
關鍵詞:檔案行動主義;檔案職業;社會正義;社群檔案;身份認同
分類號:G270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Practice and Essence of Archival Activism
Su Li
(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
Abstract: Archival activism originated in the 1970s and it was nurtured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movements, the rise of postmodern archival sci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activism. Archival activism argues that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needs to promote accountability and change in order to pursue social justice.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practices of archival activis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dentity and affection, accountability and truth-revealing, and change for justi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social power structures in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archives,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archival profession are the essence of archival activism.
Keywords: Archival Activism; Archival Profession; Social Justice; Community Archives; Identity
受當代社會思潮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行動主義話語逐漸走進國外檔案領域,“檔案行動主義”(Archival Activism)成為近年來國外檔案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國外檔案學界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關注“檔案行動主義”的相關話題,自2013年起研究成果逐年增多。近年來國內圍繞該話題也進行了初步探索[1-4],但現有研究僅針對“檔案行動主義”主要理念進行梳理或與某一具體視角相結合以對其表示贊同,缺少對“檔案行動主義”發展脈絡、相關實踐和實質等的深層次探究,為此本文通過梳理相關文獻與案例,探討上述問題并提出反思,以期為學界提供一個觀察檔案實踐的視角。
1 “檔案行動主義”的內涵、提出背景及發展
1.1 “檔案行動主義”的內涵解析
行動主義(Activism)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可指一戰后一批表現主義者的文學批評話語和原則[5],也廣泛指個人或集體為改變社會而采取的實際行動。[6]在社會治理中,行動主義關注的是多元主體于治理網絡中共生共在的行動者系統的形塑。[7]“檔案行動主義”從字面上理解即“檔案”+“行動主義”。廣義上看,“檔案行動主義”就是用行動主義的視角來審視檔案現象、檔案學理論并指導檔案實踐;具體來看,“檔案行動主義”因其涉及到諸多行動主體并受不同的思想指引,難以達成一個統一的定義。不少學者也對其概念和內涵進行了討論,如Andrew Flinn和Ben Alexander[8]認為“檔案行動主義”的內涵有三方面:一是拒絕檔案職業的被動與中立,主張檔案職業的主動和參與;二是要求檔案機構和檔案工作者以社會正義為目標并采取行動,收集和記錄與政治、社會運動和活動團體有關的檔案;三是認為“檔案行動主義”的實踐是社會運動活動的一部分。而Joy Novak[9]認為“檔案行動主義”難以定義,需要在“檔案行動主義”的6個核心概念中來考察其內涵:(1)社會權力;(2)中立性/檔案透明度;(3)多樣性/包容性;(4)社區參與;(5)問責制;(6)開放政府。
從上述學者的觀點可以發現,“檔案行動主義”發現和承認了檔案、檔案職業與權力的密切關系,主張拒絕“中立”的態度。其通過主動參與記錄團體、社群或社會議題等相關檔案的實踐,以推動問責和變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由此,“檔案行動主義”核心內涵可總結為三個方面:首先,檔案和檔案保存系統是被建構的非中立之物,故無法反映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需開放給多方參與以體現多元與包容;其次,檔案是認同、問責與推動變革的工具,追求社會正義是檔案職業需恪守的信條;最后,倡導身體力行的行動,而非筆尖上的論爭。
1.2 “檔案行動主義”的提出背景
第一,20世紀中后期社會與文化運動的推動。二戰后人權意識逐步覺醒,非殖民化運動風起云涌,新社會運動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這些社會與文化運動給檔案界帶來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其促成了關于個體身份認同與族群自豪感的反思,檔案學也積極回應,開始關注如女性、同性戀、少數族裔等一系列課題。[10]而在實踐層面,各種社群建檔實踐的開展也聲勢浩大,那些一直以來為主流檔案機構所忽視、被邊緣化或被誤述的群體發起了他們自己的檔案項目,以此作為自我陳述、身份構建、權力賦予的重要手段。[11]另一方面,這些運動在民眾的族群認同、民主觀念和社會價值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檔案作為證據、歷史、記憶、遺產,是推動問責、還原真相、糾正不公、強化認同的重要工具,檔案的這些特性也讓人們的反思延伸至檔案職業層面,反詰檔案職業倫理,并要求作出回應。
第二,檔案理論與實踐的后現代轉向。Jacques Derrida在《檔案狂熱》中曾云“沒有對檔案的控制就沒有政治權力”。[12]后現代主義思潮下的檔案學理論質疑和挑戰現代檔案學理論,并言明了檔案和檔案職業的權力屬性,檔案職業的中立性和客觀性在此時也屢遭質疑——檔案工作者在按照程序對檔案進行收集、編排與描述、保存、鑒定的過程中就不斷在對檔案施加著主觀影響。Gerald Ham、Terry Cook等人倡導的檔案后保管模式,則強調檔案管理職能的拓展,主張檔案工作者從“消極”走向“積極”,在塑造檔案文獻遺產中發揮主體地位和扮演積極角色,擺脫檔案實體管理的窠臼并與廣袤的社會網絡相聯結。
第三,媒介行動主義的發展。媒介行動主義(Media Activism)指“那些引導集體行為以批判主導媒體和(或)建立資訊生產替代機制(Dispositifs Alternatifs)的社會進步運動”[13],也指利用各種媒介和傳播手段來促進社會變革的行動主義。20世紀80年代,媒介行動主義從批判西方大眾媒體文化霸權轉向保衛本社團的權利、語言、文化等層面,同時,計算機通信技術的發展也深刻地改變著信息的生產機制,大量社團涌入計算機通訊網絡,互聯網平臺成為這些社團傳遞信息的首要陣地。“檔案行動主義”意圖將特定檔案收集起來,建立一個有別于官方檔案機構的檔案庫并加以保管和利用,以保存社群記憶并表達自我主張,而當前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也為其開辟了新的空間,不僅大大降低了檔案保存和傳播的成本,也極大地增強了其參與性。綜上,當前“檔案行動主義”實踐案例,多數都將網絡平臺作為其信息傳遞和動員的重要媒介。
1.3 “檔案行動主義”的發展脈絡
國外檔案學界通常將“檔案行動主義”的發軔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彼時世界局勢的變化以及各種民權運動與文化思潮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刻而有力的影響,在檔案行業內部要求變革的呼聲也在此時開始浮現。1970年,歷史學家Howard Zinn于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年會上主張檔案工作者要反思“中立”的概念,并敦促檔案工作者成為“行動主義者”(Activist),投身于有社會意義的工作。Zinn認為“檔案工作者甚至比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更傾向于謹慎地保持中立……但這種中立是一種虛構”[14],這被視為是“檔案行動主義”思潮的肇始。
Zinn的講話在北美檔案界掀起了熱議的浪潮,由此引發的思想和實踐上的變革也影響到了檔案學和檔案實踐的發展。1971年,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會議上成立了“檔案促進變革委員會”(Archives for Change Committee),由此開始著手進行行業內部的改革。同年,一些自稱“行動主義者”的檔案工作者組成了“檔案工作者行動小組”(Archivist for Action)以響應Zinn的呼吁,冀望創造一個更具有代表性和更平衡的歷史記錄。[15]曾任美國檔案工作者協會主席的Ham也對Zinn的批判表示贊同,認為檔案界缺少對傳統檔案之外的關注,呼吁要使檔案典藏能反映人類社會之“邊緣”。[16]20世紀70年代正值公共史學在美國興起,公共史學將對歷史的研究深入到族群、性別與家族等層面,并主張歷史學者運用其專長來推動公共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廣泛的公共利益與有限的檔案資源成為檔案實踐中的一對矛盾,關注更廣泛的社會性的檔案也成為檔案學和檔案工作面臨的現實問題。美國檔案界的思想碰撞與現實困境也在西方其他國家得到了回應,如加拿大提出的“總體檔案”就主張檔案館應收藏所有類型的檔案,從而反映出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
20世紀90年代以降,后現代檔案學者從更深的層次剖析了檔案本體。Joan Schwartz和Terry Cook就直言檔案具有特權化和邊緣化的力量[17],并主張檔案和檔案工作者的權力應開放給質疑和問責。這一時期將維護社會正義作為檔案職業倫理之追求備受推許,成為國外檔案學界熱議的焦點。Verne Harris是“檔案與社會正義”研究領域的代表學者,極力推崇檔案工作者應當以追求正義作為檔案事業之發展目標。Randall Jimerson也指出,“檔案工作者可以利用檔案的力量來促進問責、開放政府,推動多樣性和社會正義”。[18]
至此可以看出,“檔案行動主義”在前期強調檔案工作者在檔案收集、管理和鑒定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在主動參與檔案文獻遺產塑造中充分尊重和維護檔案的多樣性。有學者就指出史學和檔案領域的“行動主義者”有兩種含義:一是有意識地選擇,使其收集范圍多樣化的人;二是試圖實現社會變革的人。[19]而在后期“檔案行動主義”顯然更加呼吁后者的出場,提倡檔案和檔案工作者在促進社會變革、推動問責以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作用。
2 “檔案行動主義”的相關實踐
當前“檔案行動主義”相關實踐多以社群為紐帶,以社群檔案項目為依托,希望通過收集、存儲和傳播與自身相關的檔案來達成其目標。根據其動機和目標,“檔案行動主義”實踐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2.1 為強化認同與維系情感的實踐
“檔案行動主義”主張通過檔案來維系社群的身份認同和情感,正視社群歷史,凝聚社群力量。“檔案行動主義”通過大量的社群檔案實踐以強化身份認同、傳遞社群情感、保存社群記憶、促進包容理解。[20]譬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就有多個由社群成員創建的少數群體社群檔案館,其不僅是保存記錄的重要地點,也對研究、收集和學習社群歷史具有重要意義。[21]社群檔案記錄了社群的行為和身份,構建了群體的身份認同。[22]
2.2 為推動問責與揭示真相的實踐
“檔案行動主義”主張通過運用檔案來問責、糾正或賠償歷史上的非正義行為。典型案例就是利用檔案促成對日裔美國人的賠償。二戰期間,美國政府拘禁了12萬多名日裔美國人,將他們視為是美國人民的敵人。戰后,歷史學家和行動主義者利用拘留期間形成的檔案證明拘留是非必要的,成功推翻了最高法院的裁決,為被拘禁者爭取到了賠償。[23]原本用來控制日裔美國人的檔案成為了讓人們認識到不公的證據,讓慘遭囚禁的日裔美籍公民不再是沉默的受害者。
2.3 為謀求變革與伸張正義的實踐
“檔案行動主義”主張通過積極參與、主動記錄來推動社會變革,呼喚公平正義。例如Rosa Sadler等[24]研究了英國謝菲爾德女性主義檔案項目,指出女性主義者們將這些積極參與建檔和收集社群記憶的活動視為是女性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希望這些檔案能夠幫助改變公眾對婦女、婦女權利和性別關系的看法。除公共議題外,“檔案行動主義”也主張檔案工作中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如Sue McKemmish等[25]和Rose Barrowcliffe[26]在考察了澳大利亞的檔案工作實踐后都觀察到,澳大利亞的檔案工作實踐深受殖民化及其遺留問題影響,雖然在實踐中開始關注到弱勢群體與公平正義,但其做法仍然嚴重偏向殖民者的視角,亟須對檔案工作進行去殖民化改造以彌合“敘事鴻溝”。
“檔案行動主義”有諸多表現形式,以上的歸納方式實際上也未能完全窮盡其所有的實踐形式。Vladan Vukli 與Anne Gilliland[27]曾提出“檔案行動主義”的四種形式:(1)社群檔案(館);(2)在政府資助的檔案館和其他“主流”檔案館內,通過提升機構的透明度和問責能力,開展有社會責任感的(Socially Conscious)工作;(3)基于研究的行動主義;(4)體制外的檔案工作者進行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工作。然而,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復雜得多。具體的實踐動機呈現出較大的復合性,且動機可能會隨著時間改變而改變;實踐形式呈現出多樣性,既有基于網絡的數字檔案館,又有實體的檔案存儲空間;實踐方式呈現出合作性,非官方的社群檔案和官方檔案館進行合作也不是個例。此外,一些實踐中的新思想也推動著傳統檔案管理思維的變革,如檔案“共同形成者”(Co-creator)、“檔案自治”(Archival Autonomy)、“參與式檔案館”(Participatory Archives)、“檔案多元觀”(Archival Multiverse)等,也可納入“檔案行動主義”的體系之下,這些思想也進一步豐富了“檔案行動主義”的實踐。
3 “檔案行動主義”的實質探析
“檔案行動主義”孕育于社會變遷和學科范式轉換的背景下,背后有更為具體的推動邏輯,其實質可從信息權力、認同建構以及檔案功能、檔案職業的角度來考察。
3.1 網絡社會的權力結構變遷
傳統社會權力結構表現出對信息的控制。而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推進,社會成員皆擁有了信息生產和傳遞的能力,信息存儲也從集中走向分布,與此同時檔案的來源、內容和形式也隨之愈發廣泛和多樣。Cook曾指出,利用網絡,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的檔案工作者。[28]這體現出網絡社會中信息權力的下移。信息權力的下移促使當代社會權力結構發生結構性的變遷,在傳統權力結構中嵌入了新的信息權力,權力的運行表現出自下而上的路徑。
信息權力通過人們的認同展現出強大的力量。Castells認為認同的構建總是與權力的關系密不可分,并提出了認同的三種形式:合法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抗拒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規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29]合法性認同是有社會制度引導或規制的認同;抗拒性認同是處于社會底層的社會成員為抵抗社會主流意識而產生的認同;規劃性認同則是社會成員重新確認自己的地位、伸張自己要求、構建某種制度并尋求社會轉型的認同。縱觀社群運動的發展,可以看出一些社群運動正在從抗拒性認同走向規劃性認同,而各種行動主義的社群建檔活動,正是從抗拒性認同走向規劃性認同的手段之一。在“檔案行動主義”的倡導下,檔案工作者、社群成員或公民廣泛收集和存儲檔案資源,這些檔案資源的社會價值、情感認同價值有著強大的能量。而信息權力這種非物質的精神或心靈的權力,通過符碼影像的直接呈現,建構社會成員的觀念和意識并影響其行動。種類繁多的社群檔案實踐,也是為了將信息權力牢牢地攥在社群自身手中,維護自己的敘事權。
3.2 檔案功能的重新認識
“檔案行動主義”的思潮與實踐,從檔案本身來看是源于對檔案功能認識的改變。自20世紀中后期起,檔案文化功能、記憶功能逐漸被人們重視,檔案被視為是判斷一個國家文化底蘊豐厚與否的重要資源,同時也認識到檔案在構建社會記憶以及身份認同中的獨特價值。一方面,由于現代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加強,加之網絡空間中虛擬社群的涌現,社群建檔運動的興起和壯大,檔案在身份認同方面的作用備受重視,社群希冀運用檔案留存社群記憶、構建身份認同,以增強社群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人們也發現運用檔案可以糾正或問責歷史上的非正義行為,認識到了檔案在推進社會正義中的獨特貢獻,檔案被用作是記錄以往的斗爭與問責過去的罪行的證據,被看作是支持伸張社會正義和療愈社群創傷的資源,亦被視為是理解過去、審視當下、塑造未來的工具。如此看來,這是檔案政治價值的“重新發現”,只不過此時是作為社群成員“反敘事”(Counter-narrative)的工具。
3.3 檔案職業的重新定位
長久以來,檔案工作者被視為是消極被動的檔案保管者,而“檔案行動主義”倡導呼吁檔案職業走出故紙堆。檔案職業曾長期依附于歷史學科,Ham在20世紀就疾呼道,若不改變與學術市場聯系過于緊密的現狀,檔案工作者只不過是隨編史興趣變化而改變的“風向標”。[30]后現代檔案學者更是激烈批判檔案職業是在規則之下被裹挾的“傀儡”,是不光彩的“幫兇”。種種批評激蕩起對檔案職業的重新審視和反思,檔案工作者果真是“幫兇”?還是歷史的守護者與正義的捍衛者?“檔案行動主義”給出的回答是:摒棄在原有檔案實踐中所持有的“精英主義”觀念,關注那些長期被忽視的人群,積極參與到各類文獻的收集與保管中,轉型為積極的中介人和社會活動家,為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進程貢獻自己的力量。Cook等檔案學者曾多次號召檔案工作者應成為“積極的檔案工作者”,從被動的檔案保管者轉為主動的知識服務提供者。但“檔案行動主義”顯然更進一步,主張檔案工作者超越“積極的檔案工作者”成為行動主義者,將檔案工作視為是社會、文化和政治行動主義的一種形式,參與到更廣闊的社會實踐中。綜合上文對“檔案行動主義”相關內容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發現“檔案行動主義”所倡導的實則是實質正義觀視角下對檔案職業倫理的呼喚,易言之,“檔案行動主義”主張檔案工作必須要與人類道德觀念、價值訴求中的正義追求相呼應,并將推進公平與社會正義視為是檔案職業倫理之愿景。
4 結 語
“檔案行動主義”要求檔案工作反對中立、積極行動的初衷固然是為了追求社會正義這一崇高目標,但這也并非毫無爭議。反對的聲音認為若檔案職業“一旦喪失了中立立場,檔案工作者就要在并不明確的正義呼喚中艱難掙扎,這將讓他們的工作陷入面臨高度不確定性的困惑狀態”。[31]Mark Greene直言不諱地批評檔案工作需反對中立的觀點,認為追求社會正義盡管聽起來高尚,但有可能對檔案職業造成多重損害,并擔心這會削弱檔案職業的道德地位和權威。[32]檔案工作作為一個與社會事務緊密結合的職業,自當融入社會事務的各個環節,其實踐性必然要求不斷反思職業倫理與社會的聯系,然而社會正義的取向具有動態性,一味反對職業中立很可能釀成立場先行、紛亂繁蕪之局面。
現階段社會力量參與檔案事業、檔案參與社會治理也成為我國檔案學研究的熱點問題。相較于制度主義治理,行動主義治理的多主體參與、積極行動及強烈的現實關照等思想內核,其對當前機構改革背景下檔案職業積極走進社會,充分回應社會關切,主動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具有啟發和借鑒價值。如近年來開展的精準扶貧檔案工作正是對檔案職業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責任的呼應,也是我國檔案職業立足國情的積極行動。“檔案行動主義”作為舶來品有其特有的社會結構、思想文化和實踐土壤,如何批判借鑒,書寫立足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檔案學話語是未來需探索的方向。
注釋與參考文獻
[1]潘未梅,曲春梅,連志英.國際檔案學界十大熱點研究領域——基于六種國際檔案學期刊論文的分析(2017—2020)[J].檔案學研究,2020(6):128-138.
[2]于英香,張雅頡.“檔案參與”科學數據監管:緣起、現狀與動因[J].檔案學研究,2021(2):104-110.
[3]張珊.新時代中外檔案合作交流研究——實踐探索、理論基礎與新模式構建[J].浙江檔案,2019(12):26-28.
[4]聶勇浩,黃妍.“積極參與”的檔案學:檔案行動主義探析[J].檔案與建設,2021(12):12-16.
[5]張黎.表現主義的社會批判傾向[J].外國文學評論,2002(4):128-134.
[6]鐘聲揚,徐迪.行動主義3.0還是懶漢行動主義:關于網絡行動主義的文獻評述[J].情報雜志,2016(9):55-61+23.
[7]柳亦博,瑪爾哈巴·肖開提.論行動主義治理——一種新的集體行動進路[J].中國行政管理,2018(1):81-91.
[8]Flinn A,ALEXANDER B. “Humanizing an inevitability political craft”: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archiving activism and activist archiving[J]. Archival Science,2015(15):329-335.
[9][15]Novak J R. Examining activism in practice:A qualitative study of archival activism[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3:2+27.
[10]李娜.檔案為人人:美國公眾史學與檔案學[J].史學理論研究,2016(3):53-63+159.
[11]連志英.歐美國家社區檔案發展評述與啟示[J].浙江檔案,2014(9):6-9.
[12]Derrida J. Mal d’Archive :Une impression freudienne[M]. Paris:Galilée,1995:15.
[13]多米尼克·卡爾頓,法比安·格朗榮.媒介行動主義者[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4.
[14]Zinn H. Secrecy,Archives,and the Public Interest[J]. The Midwestern Archivist,1977(2):14-26.
[16][30]Ham F G. The Archival Edge[J]. The American Archivist,1975(1):5-13.
[17]Schwartz J M,Cook T. Archives,records,and power: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 Archival Science,2002(2):1-19.
[18]Jimerson R. Archives for All: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Justice[J]. The American Archivist,2007(2):252-281.
[19]Yaco S,Hardy B.B. Historians,archivists,and social activism:benefits and costs[J]. Archival Science,2013(13):253-272.
[20]Flinn A. Community Histories,Community Archives: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2007(2):151-176.
[21]Wakimoto D K,Bruce C,Partridge H. Archivist as activist:Lessons from three queer community archives in California[J]. Archival Science,2013(13):293–316.
[22]Platt V L. Restor(y)ing community identity through the archive of Ken Saro-Wiwa[J]. Archives and Records,2018(2):139-157.
[23]Hastings E. “No longer a silent victim of history”:Repurposing the documents of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J]. Archival Science,2011(11):25-46.
[24]Sadler R,Cox A M.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archive:documenting women’s activism and experience through the Sheffield Feminist Archive[J]. Archives and Records,2018(2):158-173.
[25]Mckemmish S,Bone J,Evans J, etc. Decolonizing recordkeeping and archival praxis in childhood out-of-home Care and indigenous archival collections[J]. Archival Science,2020,(20):21-49.
[26]Barrowcliffe R. Closing the narrative gap:social media as a tool to reconcile institutional archival narratives with Indigenous counter-narratives[J]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2021(3):1-16.
[27]Vukli V,Gilliland A J. Archival Activism:Emerging Forms,Local Applications[C]//FILEJ B. Archives in the Service of People-People in the Service of Archives. Maribor:Alma Mater Europea,2016:14-25.
[28]Cook T. Evidence,memory,identity,and community:four shifting archival paradigms[J]. Archival Science,2013(13):95-120.
[29]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6.
[31]陸陽.檔案倫理與社會正義關系研究的深層解讀——基于實質正義觀與程序正義觀的沖突[J].檔案學通訊,2020(6):22-30.
[32]Greene M A. A Critique of Social Justice as an Archival Imperative:What Is It We’re Doing That’s All That Important?[J]. The American Archivist,2013(2): 302-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