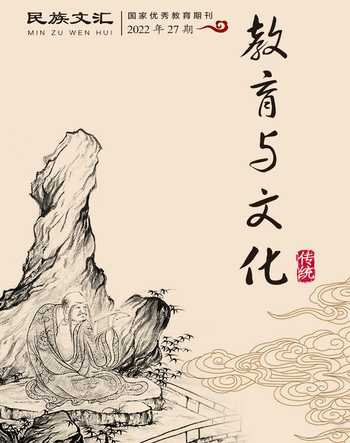淺析《命運》、《田園》、《春之祭》中的音樂美學意義
摘 要:本文從具體的音樂作品,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入手。逐層剖析人類審美的共通性規律和機制,也嘗試發現音樂與人類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普遍聯系。
關鍵詞:音樂美學 《命運交響曲》 《田園交響曲》 《春之祭》
引言
音樂美學的研究有三個目的:其一是音樂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其二是音樂引起人類審美的原因及其方式是這樣的;其三是音樂中產生的“美”是什么?在研究目的明確的情況下,方法就是關鍵。
本文以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為研究對象,使用哲學思辨方法來進行音樂美學的深入分析和研究。音樂是人類生活的剛性需求,是人類精神中對真善美對追求所形成的一種創造性“存在”。音樂是人類精神中的強大力量,這種力量跨越人種與地域,跨越歷史與文明。
一、貝多芬的交響曲
貝多芬在形式方面的創新始終是如此的特別——不論是單樂章作品還是多樂章套曲,以至于要把其中一首作品列為“典型”是不可能辦到的事情。在他為交響曲開創出的根本的、全新的各種手法中,第五交響曲是一個嘗試,即通過主題的變形和對音樂內部運動的回憶達成串聯式的統一。第六交響曲“田園”考慮到了人類與自然界的交匯,因而探索出了器樂音樂的形象化潛能——其范圍從模糊(如第一樂章的標題,“初抵田園的歡喜之情”)到令人吃驚的明晰(在慢樂章結束時的鳥鳴,就細化到了鳥類品名的程度)。
第五交響曲也是一部有著非凡歷史重要性的杰作,尤其是關于其串聯性統一的問題。一個短小動機在多樂章中的明晰運作;最后兩個樂章之間模糊的邊界;在末樂章中再現了前一個樂章(第三樂章),這些使得這部交響曲具有了串聯統一的表層布局——這種手法很早就有,但不會如此明顯。就其末樂章的情感重量而言——即再次引入和解決了之前樂章未解決的問題和觀念,第五交響曲也是意義深遠的。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貝多芬給予了交響曲末樂章空前的比重,這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總體而言,相互獨立的四個聲部間更為精細關聯手法的使用同樣地被重建起來,更加依賴于互補的原則,讓對比性的單元成為了一個統一整體。
二、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
《春之祭》是斯特拉文斯基“俄羅斯風格”時期的代表作品,產生在古典音樂受到巨大挑戰的20世紀初。恰逢西方音樂價值觀及其各要素轉型發展的特定時期,因此作品內蘊含諸多對立沖突,存在二律背反現象。筆者在分析作品中的二律背反現象時,也嘗試探索其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事實上,20世紀初矛盾復雜的西方音樂文化和斯特拉文斯基特殊的個人創作經歷共同決定了《春之祭》的歷史價值,它是歐洲社會和多元音樂文化共同作用下的時代產物。
(一)《春之祭》的創作背景
二律背反是由 18 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命題,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指出:“當人們的認識從感性、知性發展到理性階段時,人的思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兩個相反的命題都可以得到證明 的矛盾現象。也就是說,人們的理性在追求絕對、無條件的總體認識時,必然產生矛盾與對立,這種矛盾與對立即是一種二律背反。《春之祭》產生的歷史環境,恰如康德的闡述: 延續自19世紀的巨大變革陸續深入政治、社會、道德、藝術等各個方面,挑戰的矛頭直指“古典—浪漫”時期的教義并將其引向終結。在西方音樂發展的漫長進程中,歐洲古典音樂一直都被認為是音樂藝術的最高水平和唯一代表。進入 20 世紀,西方音樂呈現出更明顯的多元化發展態勢。受諸多新藝術思潮的影響,幾乎所有受推崇的新觀念都與以往的音樂傳統大相徑庭。因此,繁榮的經濟和發達的科技不僅沒有再次推動傳統音樂文化的繁榮,反而使其基本原則陷入史無前例的質疑中。
(二)二律背反論在《春之祭》中的體現
《春之祭》的二律背反首先體現在作品內部音樂自律論與他律論間二元對立與統一性的問題上。作品中,尖銳的矛盾來源于作曲家潛意識里“風格思維”與音樂本體“形式主義”的密切關系。音樂藝術本體的“無目的性”和非常規創作技法的“表現性”,使兩者的對立在《春之祭》中得到了鮮明體現。《春之祭》中核心樂思蘊含的固有程式性與音樂進程體現的即興性構成另一組二律背反現象。高度程式化的儀式音樂傳統契合斯特拉文斯基推許的“普遍性”概念。“普遍性要求人們服從公認的秩序,這種要求不僅很有必要,而且具有充分理由。不管人們對秩序的服從是出于同情還是謹慎,都會很快從中受到裨益。”但《春之祭》的音樂內容中,不論是戲劇因素的安排,還是樂思的發展都表現出一種自由、不固定,具有原始風格的即興手法,這使得他的祭祀儀式音樂透露出一絲“漫不經心”的印痕。
《春之祭》中的那些極端音樂技巧和傳統寫作方法的交織,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放縱游戲與神圣祭祀的沖突,實則是一個俄國作曲家將其性格及情感里二律背反的因子置于音樂創作中的集中體現。
結語
一個作品的形態是作曲家理性的客觀呈現,這一理性顯現絕非是作曲家本身所固有或天生的,而是國家、民族、時代背景等客觀因素對于一個作曲家的塑造而形成的作曲家所遵循的一個標準及規范。但同時作品的形態也是符合人類的普遍審美的,人類審美的共通性其實是一種和客觀世界、事件所建立的普遍聯系結構。從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中我們可以看到能夠引起審美活動的三個基點:善與惡、生與死、愛與恨。
黑格爾說:惡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是客觀世界的普遍規律。所以,在審美中惡的推動是善所以建立的根本。而對抗惡的就是人類精神力量的強力,就是善存在的意義,也是真存在的實質,更是人類對于美不懈追求的永恒動力。
參考文獻
[1]葉秀山(主編).《西方哲學史》[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汝信.《西方美學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3]里維斯·洛克伍德.《貝多芬·音樂與人生》[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4][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李立永,徐茜.《俄羅斯國民性格的二律背反及成因簡析[J].俄羅斯研究,2004,(01).
作者簡介:鄭媛芮(1996-5)女 漢族 山東臨沂 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音樂(聲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