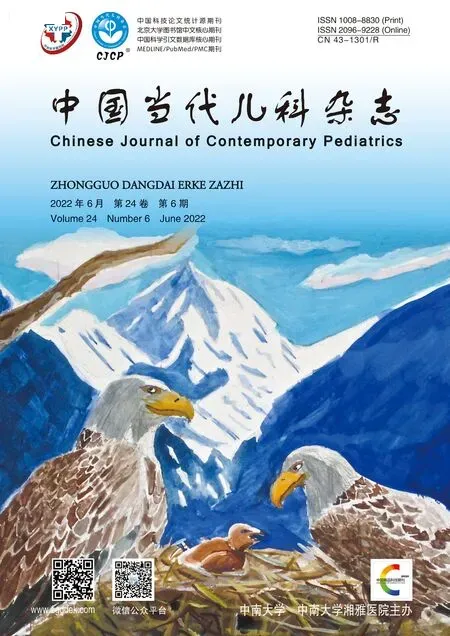川崎病急性期肝損害與冠狀動脈損傷和免疫球蛋白無反應的關系
胡慧敏 陳笑征 張永蘭 杜忠東
(1.國家兒童醫學中心/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心內科,北京 100045;2.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北京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科,北京 100006)
川崎病(Kawasaki disease,KD)是一種急性全身性血管炎癥性疾病,多發生于5歲以下兒童,近年來在多數國家發病率逐年上升,已成為常見的小兒心血管疾病之一[1]。KD可引起全身性炎癥及血管炎,主要累及全身中動脈,故可導致多系統并發癥如冠狀動脈損傷、胃腸道不適、肝損害等。肝損害作為KD最常見的合并癥之一,其發病機制尚不明確。既往觀點認為KD患兒出現的肝損害與藥物不良反應關系密切,或被認為是KD繼發的消化系統并發癥之一。近年來一些研究發現KD患兒早期出現的肝損害可能與病原體途經門靜脈進入體內時引起局部炎癥反應造成肝臟損傷,疾病引起的肝臟血管炎及肝細胞內發生的氧化應激反應或細胞因子瀑布有關[2-3]。流行病學研究發現,肝損害的發生率近年有增高趨勢,因此肝損害也是KD患兒除心血管并發癥外需要關注的嚴重并發癥之一[4-5]。用于評估KD嚴重程度的評分系統之一的Egami評分系統已經明確將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納入評估KD嚴重程度的最主要因素之一[6]。本研究通過對我院925例KD患兒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總結KD肝損害患兒的臨床特征,并應用統計學方法分析肝損害是否為冠狀動脈擴張及對大劑量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治療無反應的相關因素,為臨床治療及評估KD患兒預后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從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KD病例數據庫中選取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首次診斷并住院治療的全部KD患兒為研究對象,收集每例患兒的病史、臨床表現、住院期間實驗室檢查及影像學檢查結果、治療情況,并進行回顧性分析。該研究得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14-56)。
1.2 診斷標準及排除標準
KD的診斷標準參照世界KD研討會上頒布的第5版KD診斷標準[5]:(1)持續發熱5 d以上(含經治療5 d內退熱的情況);(2)多形性紅斑或皮疹;(3)雙側球結膜充血;(4)口腔和唇所見:口唇干紅、皸裂,楊梅舌,口腔及咽喉黏膜充血;(5)急性期出現頸部非化膿性淋巴結腫大(≥1.5 cm);(6)四肢末梢的改變:急性期手足末端硬腫,恢復期指趾端甲床皮膚移行處可見膜狀脫皮。上述6項主要癥狀中出現5個或以上可診斷KD,若上述6項癥狀中僅出現4項癥狀,但超聲心動圖檢查證實冠狀動脈病變形成(冠狀動脈擴張或冠狀動脈瘤),除外其他疾病后也可診斷KD。不完全KD的診斷標準參照2020年JCS/JSCS的KD診斷及治療標準進行[6]。
KD合并冠狀動脈損傷標準參照第8版《諸福棠實用兒科學》[7]:(1)冠狀動脈擴張:≤3歲兒童,冠狀動脈內徑≥2.5 mm;>3~9歲兒童,冠狀動脈內徑≥3 mm;>9~14歲兒童,冠狀動脈內徑≥3.5 mm。(2)冠狀動脈瘤:冠狀動脈內徑>4 cm。
IVIG無反應性KD定義為[8]:KD患兒在發病10 d內予首次IVIG(2 g/kg)沖擊治療,治療48 h后患兒體溫仍高于38℃,或在熱退2~7 d甚至2周內再次出現發熱,并符合至少1項KD主要診斷標準者。
肝損害的定義參考國外對于KD患兒肝損害的類似研究,并考慮到利于數據的分析,將所有住院患兒入院時生化指標中ALT作為評價肝損害的指標,即患兒入院時生化指標中ALT高于正常值(40 U/L)定義為肝損害[9]。
排除標準:(1)不滿足KD的診斷標準;(2)非初發并首次確診的KD患兒;(3)臨床資料不完整。
1.3 分組與方法
根據患兒入院時生化檢查中ALT水平分為2組,入院時ALT≤40 U/L為非肝損害組;入院時ALT>40 U/L為肝損害組。對兩組患兒的年齡、性別、入院時間、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治療效果等進行比較,以探究KD患兒肝損害的臨床特征及相關危險因素。實驗室檢查均在首次IVIG治療前完成,C反應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白細胞(white blood cell,WBC)計數、血小板(platelet,PLT)計數、紅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取治療前多次結果中的最高值,血清鈉離子和白蛋白(albumin,ALB)取最低值。冠狀動脈中至少1支冠狀動脈擴張或者冠狀動脈瘤形成者定義為冠狀動脈損傷。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兩樣本t檢驗;不服從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應用logistic回歸分析冠狀動脈損傷和IVIG無反應的相關因素。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臨床特點
納入本研究的KD患兒共925例,其中男567例(61.3%),女358例(38.7%),男女比例為1.58∶1。發病年齡1~136個月,中位發病年齡24個月,5歲以下兒童占總人數的89.6%。所有患兒在病程急性期均出現了持續發熱,患兒的平均入院時間為發熱第6天。所有患兒在住院期間均予IVIG沖擊治療(首次劑量為2 g/kg),并酌情加用阿司匹林及雙嘧達莫抗凝、抗血小板聚集治療。所有患兒在首次IVIG治療前均完善了心臟彩超及冠狀動脈超聲檢查。入院時出現冠狀動脈損傷患兒共212例(22.9%),在予首次IVIG 2 g/kg治療后呈IVIG無反應KD患兒共198例(21.4%)。
2.2 KD患兒入院時合并肝損害情況及出院轉歸
根據患兒入院時生化檢查中ALT結果,共284例合并肝損害(30.7%)。入院時ALT最高值為808 U/L。其中40 U/L<ALT≤80 U/L占41.9%(119/284),80 U/L<ALT≤120 U/L占24.3%(69/284),ALT>120 U/L占33.8%(96/284)。284例合并肝損害KD患兒出院時,220例(220/284,77.5%)ALT指標恢復正常(ALT≤40 U/L)。
2.3 肝損害組和非肝損害組的臨床特點
非肝損害組入院時間為發熱病程的第(6.6±2.2)天,肝損害組入院時間為發熱病程的第(5.9±1.9)天,肝損害組患兒入院時間更早(t=-0.952,P=0.001)。非肝損害組中男孩發病391人,肝損害組中男孩發病176人,兩組性別構成比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79,P=0.826);非肝損害組與肝損害組發病年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8±23)個月vs(35±24)個月,t=5.161,P=0.350]。而對KD診斷有價值的5項主要臨床表現發生率在肝損害組及非肝損害組之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兒的臨床表現發生率比較 [例(%)]
2.4 肝損害組和非肝損害組IVIG治療前的實驗室指標比較
肝損害組CRP、ESR、ALT、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TBIL)、γ-谷氨酰氨基轉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及肌酸激酶同工酶(creatine kinase isoenzym,CKMB)水平較非肝損害組明顯升高(P<0.05);ALB水平及PLT計數較非肝損害組下降(P<0.05);而WBC計數、血紅蛋白(hemoglobin,HGB)水平、血清鈉離子水平及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水平在兩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兒的實驗室檢查指標比較 (±s)

表2 兩組患兒的實驗室檢查指標比較 (±s)
注:[CRP]C反應蛋白;[WBC]白細胞;[HGB]血紅蛋白;[PLT]血小板;[ESR]紅細胞沉降率;[ALT]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ST]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LB]白蛋白;[GGT]γ-谷氨酰氨基轉肽酶;[TBIL]總膽紅素;[CKMB]肌酸激酶同工酶;[LDH]乳酸脫氫酶;[Na]鈉離子。
組別非肝損害組肝損害組t值P值n 641 284 CRP(mg/dL)51±41 71±44-6.389 0.034 WBC計數(×109/L)13±6 14±5-1.916 0.117 HGB(g/L)109±13 113±14-3.386 0.317 PLT計數(×109/L)356±145 320±116 3.715<0.001 ESR(mm/h)57±29 65±26-3.964 0.010 ALT(U/L)18±8 130±117-23.865<0.001 AST(U/L)29±10 71±14-11.074 0.001 ALB(g/L)35±5 33±4 5.161<0.001 GGT(U/L)29±11 116±61-23.111<0.001 TBIL(μmol/L)7±4 16±11-10.610<0.001 CKMB(U/L)15±11 21±14 2.870 0.013 LDH(U/L)274±90 278±122-0.541 0.064 Na(mmol/L)135±9 132±6 1.206 0.597
2.5 肝損害組和非肝損害在冠狀動脈損傷及對IVIG療效之間的比較
肝損害組患兒在入院時出現冠狀動脈損傷者共78例(27.5%),非肝損害組患兒在入院時出現冠狀動脈損傷者共134例(20.9%),肝損害組入院時合并冠狀動脈損傷率高于非肝損害組(χ2=4.794,P=0.034)。在首次IVIG(2 g/kg)治療后,肝損害組中34.5%(98/284)表現為IVIG無反應,非肝損害組中則有15.6%(100/641)表現為IVIG無反應,肝損害組IVIG無反應性KD患兒發生率高于非肝損害組(χ2=41.815,P<0.001)。
2.6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考慮到AST、GGT、TBIL是間接反映肝功能的指標,在logistic回歸分析中不將其作為回歸分析的變量。以KD患兒是否發生冠狀動脈損傷為因變量,以頸部淋巴結腫大(否=0,是=1)、四肢改變(否=0,是=1)、口腔黏膜改變(否=0,是=1)、皮疹(否=0,是=1)、HGB、PLT、CRP、ESR、ALT、CKMB及應用IVIG天數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KD患兒發生冠狀動脈損傷與HGB水平下降、PLT計數升高、CRP水平升高和ALT水平升高有關(P<0.05)。見表3。

表3 KD患兒發生冠狀動脈損傷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以KD患兒是否對IVIG治療有反應為因變量,以頸部淋巴結腫大(否=0,是=1)、四肢改變(否=0,是=1)、口腔黏膜改變(否=0,是=1)、皮疹(否=0,是=1)、HGB、PLT、CRP、ESR、ALT、CKMB、應用IVIG天數及冠狀動脈損傷(否=0,是=1)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KD患兒發生IVIG無反應與四肢改變、HGB水平下降、PLT計數升高、CRP水平升高、ALT水平升高及冠狀動脈損傷有關(P<0.05)。見表4。

表4 KD患兒發生IVIG無反應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由于KD是一種主要累及全身中動脈的血管炎性疾病,KD在急性期常常出現全身多系統的合并癥[10]。KD未經治療的病例中約25%會出現冠狀動脈瘤,是發達國家兒童獲得性心臟病的主要病因[1]。近年來,隨著KD相關指南的完善,各國對KD的診療趨于規范,KD患兒在正規予免疫球蛋白聯合阿司匹林治療后,冠狀動脈并發癥的發生率降至2%~4%[11]。
隨著人們對于疾病認識的增強及KD冠狀動脈病變發生率的顯著降低,在KD病程中出現的肝臟系統并發癥受到越來越多人重視。一項回顧性研究發現KD患兒入院時合并肝損害(AST、ALT指標中至少1項升高)的發生率為45.4%[2]。近年來一些研究發現,KD患兒在病程早期(IVIG、阿司匹林等治療前)即出現肝損害,因此有學者提出,一些KD患兒的肝臟系統合并癥可能與KD的發病機制相關,尤其對于疾病初期(如病程前5 d內)出現肝損害的患兒,其肝臟受損應是在病程早期已經發生,甚至在疾病的發病過程中起關鍵作用[4]
本次研究中入院時ALT水平升高的患兒約占住院總人數的30.7%,本研究分析所有住院患兒入院時(即IVIG、阿司匹林藥物治療前)的實驗室結果,除外阿司匹林等藥物因素對肝功能相關指標產生的影響,明確為疾病本身所致肝損害;肝損害組和非肝損害組的臨床特征及實驗室相關指標進行統計學比較分析結果表明,兩組患兒在入院時的發熱天數、CRP水平、ESR、PLT計數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肝損害組在入院時發熱天數更短,CRP水平、ESR均高于非肝損害組,另外肝損害組的ALB水平更低,而GGT、TBIL及AST水平均高于非肝損害組。研究結果提示肝損害組的發熱程度更重,住院時間更早,且非特異性炎性指標水平更高,間接提示肝損害組在KD急性期的疾病程度更重、全身血管反應更強。
KD患兒ALB水平降低的發生機制尚不明確,目前認為可能與疾病導致的全身性血管炎及微血管通透性增加有關。在KD急性期,炎性細胞因子直接影響蛋白質的合成過程,導致急性時相蛋白的合成增多(如CRP),其他蛋白水平降低(如ALB)。其次,在炎癥反應時期,在激素、神經及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2、白細胞介素6,α-干擾素)的共同介導下,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ALB經血管滲出增多,進一步導致ALB總量下降[12]。有研究發現ALB降低程度與KD合并冠狀動脈病變的發生率呈顯著相關,ALB水平越低,冠狀動脈病變的發生率越高[13]。而在一項為期9年的回顧性研究中也發現,ALB水平降低或許是發生冠狀動脈病變的先兆指標,ALB水平甚至可以作為預測KD患兒發生冠狀動脈病變的重要指標[14]。本研究結果表明肝損害組入院時ALB水平較非肝損害組低,肝損害組患兒在入院時出現冠狀動脈損傷者明顯多于非肝損害組,均提示對早期出現肝損害患兒,血清ALB水平下降,在病程中出現冠狀動脈病變的風險可能更高。但通過對KD合并冠狀動脈損傷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HGB水平下降、PLT計數升高、CRP水平升高和ALT水平升高為發生冠狀動脈損傷的危險因素,而ALB水平下降未納入回歸方程。因此,KD急性期出現ALT水平升高患兒出現冠狀動脈損傷的風險增加,但ALB是否對預測KD急性期發生冠狀動脈損傷有預測價值仍需對諸多肝損害實驗室指標進行詳細分類,并擴大樣本量進一步明確。
KD患兒在急性期給予IVIG治療后,冠狀動脈損傷發生率可降至2%~4%,但有10%~15%的患兒在發熱10 d內予IVIG 2 g/kg單次輸注后48 h體溫仍高于38℃,或是熱退后2~7 d甚至2周內再次出現發熱,即IVIG無反應性KD,這也是KD治療面對的挑戰之一[15]。KD發生IVIG無反應的機制,目前認為可能與在這些患兒體內的免疫活性細胞高度活化、炎性細胞因子產生過多,而IVIG用量相對不足有關,也可能因效應細胞的FC段及血管內皮細胞發育不成熟導致IVIG發揮的治療作用欠充分所致[16]。有研究證實,IVIG無反應性KD患兒發生冠狀動脈并發癥的風險更高,對初次IVIG治療無反應是冠狀動脈損傷的危險因素[17],因此,早期預測患兒發生IVIG無反應性KD,對于降低冠狀動脈病變發生率,及減輕此類患兒疾病的嚴重程度有重要意義。
最新研究報道PLT計數與冠狀動脈損傷及IVIG無反應有關[18],另外也有文獻報道血清降鈣素原、ALT及TBIL水平等在IVIG無反應組與有反應組均有顯著性差異,但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僅降鈣素原和TBIL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9]。韓國的一項多因素研究發現[17],血N-端腦鈉肽前體、CRP、AST、ALT是發生IVIG無反應性KD的獨立危險因素;Liu等[20]進行的一項有關IVIG無反應性KD危險因素的Meta分析中發現,除了多形性皮疹或四肢腫脹外,患兒出現IVIG無反應性更可能發生在慢性乙型肝炎、嚴重貧血、低ALB血癥、PLT計數下降和ESR、TBIL、ALT水平升高者中,尤其是男性、低鈉血癥、AST和CRP水平升高被確認為發生IVIG無反應性的危險因素。同樣有研究表明,IVIG無反應性KD更容易發生冠狀動脈損傷,且黑色人種發生IVIG無應答風險更高[21]。本研究結果表明,肝損害組發生IVIG無反應性比例更高;對發生冠狀動脈損傷及IVIG無反應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肝損害是KD患兒發生冠狀動脈損傷及IVIG無反應性的相關因素。
綜上所述,KD合并肝損害的發生率較高,KD發生肝損害者發生冠狀動脈損傷及IVIG無反應性的比例增高,且統計學結果證實ALT水平升高是發生冠狀動脈損傷和IVIG無反應的相關因素之一,對于KD急性期合并肝損害患兒的治療需予以高度重視,以減少冠狀動脈損傷及早期識別IVIG無反應性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