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符號學到現象學: 歐美劇場表演研究基本方法的確立
馮 偉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論道:“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而這種摹仿是通過行動中的人物進行的,這些人的性格和思想就必然會表明他們的屬類[……]人物不是為了表現性格才行動,而是為了行動才需要性格的配合。”(亞里士多德63—64)不難發現,除了核心術語“摹仿”,“行動”是該界定的重點。《牛津戲劇與表演指南》()指出,行動包含兩層含義:“體現在劇中的意義、動機和目的”,以及“演員實際的肢體運動和言語(戲劇性的行動,而非敘事的行動)”(Vince8)。這與亞里士多德對摹仿的媒介、對象和方式的區分相呼應。通過論及悲劇行動最終的效果——憐憫與恐懼——亞里士多德也引入了觀眾主體肉身的維度。對于實際演出,摹仿的媒介包括演員的聲音、身體等,而這些具身性的內容與文本結合,作用于觀眾,最終抵達“凈化”。由此可見,肉身的重要性在《詩學》中有所暗示。
可惜的是,后世研究者在討論戲劇時,卻往往忽視實際演出中的動作和言語,將戲劇的肉身性剝離,而側重行動的第一層含義,即寄托于文本的意義、動機、目的,從而將行動簡化為情節。這與歐美歷史上經久不息的“反戲劇偏見”(anti-theatrical prejudice)對肉身的忽視和蔑視不無關系。與此同時,其他非文本要素,如戲景等,在亞里士多德的筆下也一并被淡化:“戲景雖能吸引人,卻最少藝術性,和詩藝的關系也最疏。”(亞里士多德65)于是戴維斯斷言:“行動沒有必要被看到[……]行動一旦被理解了,這出戲實際上不是非得要演出。它可以只是用來閱讀。”(戴維斯63)以情節為核心的戲劇觀奠定了歐美后世戲劇批評的一大走向。由于看重行動中事件的組合,戲劇批評總是糾纏于結構、性格及相關的思想分析;由于敘事基于語言,文本研究成為戲劇批評的主要策略。在棄非文本要素于不顧的情況下,戲劇藝術被簡化為戲劇文學;而劇本的合法性,也源自其文學性或附屬的倫理意義。以上種種,皆可被視為對亞里士多德強調的“情節是悲劇的根本”(亞里士多德65)的具體發揮。最終,戲劇批評成為以文本批評為主導和中心的言說。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基于表演分析的劇場研究遲遲無法建立,也在情理之中。
直到20世紀初期先鋒主義戲劇興起,文本壓倒舞臺的趨勢才開始有所扭轉。先鋒主義的根本,在于對文藝之形式本身的質疑與反思。在戲劇實踐中,構成劇場藝術(而非戲劇文學)的非文本舞臺要素以各種形態強勢出場,使人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劇本外的其他本體要素。流于感性認識的傳統劇評和更加客觀的學術性舞臺批評也開始有所區分。包括劇場表演研究在內的戲劇學隨之建立,成為大學課程的一部分。而真正促進劇場表演研究蓬勃發展的催化劑,是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工具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然而,文本中心思維的幽靈依然附著于早期的劇場表演分析,符號學也難以幸免。
一、 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出場
符號學關注意義的交流,即“符號的組織、傳遞和接收”(Scheie264),尤其適用于再現的藝術。所謂再現的藝術,并非特指自然主義或完全追求形似的摹仿藝術,還包括追求使用固定程式來傳遞意義的風格化藝術,因為程式的本質也是符號。故,再現的戲劇形式自然也包括某些反寫實的藝術,如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敘事劇、超現實主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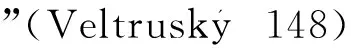
在戲劇研究領域,符號學因為與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也深受其基本思路的影響。結構主義者強調,文本(無論是演出文本還是劇本)意義是封閉的,無須外部條件的干擾,而符號學家的任務,便是找尋符號的深層含義和結構;因為深層,這種結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劇場符號在共時的社會環境或演出框架下,自然會生發出特別的意義。而在傳遞和接受過程中,觀眾和讀者通過適當的闡釋,也可獲知符號的內涵。其中不難發現符號學的基本預設: 主創有一以貫之的理念要傳達,借助系統的符號分析,該理念可以被闡釋出來。如胡妙勝所言:“為了保證將信息從一點傳到另一點,演員與觀眾必需共享一套規則。”(胡妙勝52)這一點基于對索緒爾“語言”(langue)的洞見。布拉格學派符號學家彼得·鮑加達列也夫論道:
我們可以將“語言”和“言語”的概念從語言領域移至藝術領域。如此一來,聽話者為了理解說話者的個體化表達,必須掌握這種語言,也即作為社會事實的語言;同理,在藝術中,觀眾必須做好準備,去接受演員或其他藝術家個體化的表演——比如說他的特殊的言語行為——而這種接受所依托的便是對藝術語言及其社會規范的掌握。(Bogatyrev45)
自然主義戲劇為這一論點提供了例證。自然主義戲劇家認為,通過觀察生活的細節,人們可以發現其中的規律,從而改造社會。而劇作家的任務,是盡可能多地去還原生活的細節,賦予細節意義,讓觀眾去尋找和分析(Pickering110)。因此,在斯特林堡、易卜生、契訶夫、蕭伯納的作品中,有關布景的描寫和舞臺提示往往篇幅不小。此外,自然主義和符號學也共享“科學的態度”,因此主創針對一些問題給出自己的暗示,觀眾在第四堵墻外觀察和思考,去領會主創試圖傳遞的意義。戲劇符號學家對各種舞臺符號的分類和定性,以及對敘事模式的分類,便暗合了這種對普遍舞臺語言的追求。
二、 符號意義的不確定性
然而,因為忽略語境和漠視主體,結構主義的視角也導致了一些問題。以固定的方式去接受和闡釋,對于觀眾既不可能,也不切實際。因為這不僅取締了觀眾的能動性,更是忽略了觀眾的多樣組成。在符號完全相同的情況下,對于認知能力與背景有別的觀眾,意義和體驗可能千差萬別。譬如,比亞爾就提出了“雙重編碼”(double-coding)的理念,認為同樣的作品在不同群體看來,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Bial144)。但是,早期的符號學家在探討劇場交流時,大多將重點放在編劇和導演身上(Carlson,xiii),突出二者對意義闡釋的權威,而忽視了觀眾這一層。70年代開始,艾柯等符號學家將接受美學引入符號學中,突出觀眾主體的多樣性;與此同時,皮爾斯的符號學著作重新被發掘,并開始產生影響(Carlson, “Semiotics and Its Heritage”19)。與索緒爾強調去主體的“能指—所指”二元結構不同的是,皮爾斯的符號學強調“符號—解釋項—對象”的三元結構,其中尤其突出主體性明顯的“解釋項”(interpretant)。既然觀眾的主體性被前置,那此后的符號學也不可避免地會去關注具體的語境,而非一味地追求抽象的客觀。
60年代末以來,世界格局發生劇變,歐美政治運動此起彼伏,顛覆和斷裂成為文藝領域的主題詞。表演開始走出劇場空間、文本被拋棄、社會實踐與表演難以區分、反抗的聲音不絕于耳,展演藝術(performance art)也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這種常規被不斷打破的局面下,七八十年代的戲劇研究者一手握著符號學的手術刀,一手扛著文化唯物主義的大旗,將看似客觀和抽象的符號語境化,揭露其在各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和機制。通過將此前符號學忽略的歷史與政治語境帶入闡釋,以蘇-艾倫·凱斯和吉爾·道蘭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開始拆解男權如何利用重復的符號和話語固化既有的性別秩序(Case; Dolan,)。同樣,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帶有后結構主義色彩的批評實踐,也將符號學引入,反思和批判看似不言自明的宏大敘事。結構主義者關注的靜止“產品”(product),逐漸被后結構主義者強調的動態“生產過程”(production)所取代。進入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時代后,觀眾主體的構成愈發復雜,去語境化則更顯不合時宜。
即便將語境納入,符號學也面臨著更根本、也更具顛覆性的問題: 劇場中的交流是否只能依靠符號?意義的傳遞是否表演的全部?布拉格學派符號學家指出,舞臺上的事物兼具符號性和物性(thingness),但先鋒戲劇誕生之后,物性不斷被凸顯,而意義也隨承載主體之文本的淡化,而變得愈發不確定。在《普通語言學問題》中,法國結構主義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提到,以圖像和聲音為代表的藝術系統,往往難以被徹底符號化,因為很多時候,藝術家“不接收已成定論的符號集成,而自己也不構建一個集成”(本維尼斯特132)。換言之,在客觀和主觀兩個層面,符號都未必是交流唯一的工具。
客觀而言,劇場與戲劇文本的重大區別在于,劇場是活的(lived)藝術,也是現場藝術(live art)。劇場中難以被徹底符號化的元素,如燈光、聲音、空間、身體、動作,會觸及觀眾感官,使其產生喜怒哀樂,以及難以名狀的震動。其間的感受,具體但不明確,可感卻不可知,事后許久還有余波——學界一般將其稱作感觸(affect,又譯“情動”)。它對戲劇事件的發生和作品意義的建構起著關鍵作用。但感觸該如何分析?對應的符號是什么?有何意義和政治潛能?符號學無法回答。即便能找到上述感觸的來源,也很難斷稱,給觀眾帶去奇異感受的,是其本身的意義,或作為符號的特性。
就藝術家主觀而言,隨著先鋒戲劇的進一步發展,符號性因為容易承載既定的意識形態,在戲劇交流中的重要性有意被減弱,而舞臺要素的非符號性則不斷被戲劇實踐者凸顯。布萊希特的敘事劇以陌生化來破壞能指與所指的固定關系,而阿爾托的殘酷戲劇更是旗幟鮮明地宣稱再現性舞臺語言的死亡。在他們的啟發下,新時代的戲劇創作格局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隨著藝術與生活邊界的模糊,強調體系和等級制度的結構主義式創作模式也不再盛行,不少藝術實踐成為一種社會實踐,以對抗壓迫性的宏大敘事。在作品和意義的生成中,編劇和導演的權威被大幅弱化: 有的當代劇團強調集體編作,甚至取消編劇;有的劇團突出演員肢體和場景設計,弱化文本的表意;有的追求即興和觀演互動,將演出的創造和解讀讓渡給觀眾。觀眾進入劇場,獲得的不再是某種明確的“意義”,而更多是較為含混而多元的“感受”,而如何感受、感受什么,觀眾也有自由選擇的空間。
無論是出于客觀現實還是主觀考慮,現當代的劇場都在突出非文本性和意義的不確定。面對這種情況,單純的符號學顯然無從下手。在很多時候,這種符號學無法進入、無法言說的地帶或經驗,往往伴隨著意義的斷裂和體系的碎片。為了應對這種新的實踐策略,80年代末,強調主體本質直觀的現象學被引入劇場表演研究,成為該學科的另一種基礎方法。
三、 現象學與戲劇的相遇
現象學一詞在西方哲學史上早有出現,但真正成為影響深遠的學科,有賴于胡塞爾。胡塞爾之后,現象學發展方向各異,但基本的思路由其奠定,即關注現象如何向主體的意識顯現。現象學作為一種方法,目的是為了達到“本質直觀”,即強調通過直觀,使主體在懸置任何知識的情況下,抵達對事物本質的把握。現象學的具體方法是還原,便是將事物事先設定的存在性去除。而經歷了還原之后的世界,并沒有縮小,反而更大,因為有些被遮蔽的事物出場了(張祥龍54)。懸置是現象學還原事物本來之貌的第一步,要點在中立和不作判斷,即在主體與事物相遇時,將一切科學的、哲學的、文化的、歷史的、經驗的知識擱置,令主體判斷免于干擾。第二步是使一切被認識者只作為顯現者顯現出來,讓現象自我顯現。現象學方法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主體的經驗,而如何經驗、經驗的內容、經驗的主體都是其研究的基本組成。但現象學并未強調純粹的主客二分,而是認為,主體和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關聯,根本無法截然分開,如索科拉夫斯基所說:“事物向我們顯現,實際上也是被揭示出來的,而我們也和事物一樣,向自己和他人顯現。”(Sokolowski12)現象學重新在強調客觀和抽離的分析方法中加入了主體的體驗,如梅洛-龐蒂所言:“世界的樣貌并非通過思考獲得,而是通過親身經驗獲得。”(Merleau-Ponty xviii)總之,現象學需要從第一人稱視角出發,懸置任何具有真理訴求的知識命題或體系,從而為真正知識的客觀性奠定基礎。現象學本身并非系統化的學派和統一體,其間各種觀點充斥,研究對象和方法也蔚為大觀。后世哲學家如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德里達等,均基于胡塞爾,提出了諸多可供戲劇研究參考的視角,如海德格爾對空間和物性的關照、梅洛-龐蒂對身體的分析、德里達對在場的理解。
以現象學的視角觀照戲劇,便可推知,戲劇現象學的研究內容,是作為第一人稱主體的觀眾(以及表演者)如何感知和經驗劇場中的元素(客體)。從經驗主體來看,可以關注表演者和觀眾如何使用身體感知。從經驗客體來看,可以關注所有舞臺要素(包括身體、布景、燈光、色彩、音效、空間、多媒體、時間、不在場之物等),亦可關注意向性行為,如記憶、情感、欲望、想象等。當經驗主體明確感覺到自身的出場,現象學的方法便可發揮作用。所謂出場,往往“關乎相遇的實踐,關乎對差異的感知,以及與其他人、其他事物的關聯,當然還有那種暗恐般的與自身的相遇”(Giannachi, Kaye, and Shanks2)。而因為相遇的關系,出場總是伴隨著含混和不確定性。
現象學研究方法的興起是對先鋒戲劇的回應。面對以先鋒戲劇為代表的作品創造出的難以名狀的含混體驗,符號學捉襟見肘,而善于把握含混體驗的現象學則有了發揮的余地(Bleeker, Sherman, and Nedelkopoulou1)。現象學的出發點在于主體感知,尤以觀眾主體為主,具體思路如下。在戲劇演出中,觀眾隱匿在黑暗的觀眾席,被舞臺吸引,乃至忘記自身的存在。但總有一些時刻,觀眾的感官受到非常的刺激,從而感覺到了自己的在場,而這種突如其來的在場感就是現象學分析的入口。此間涉及的主要是身體和意識,甚至是無意識——而非理性。無論這種感受是什么,它都是陌生化甚至是不可名狀的,故斯坦頓·加納將德魯·萊德提出的“猝現”(dys-appearance)這一概念引入戲劇現象學中(Garner,32),以描述這種現象。不可名狀的在場感意味著,劇場中的某些事物可以即刻被感知,但卻未必可以被迅速認知,而陌生化則往往會激發一系列無法被完全框架化和結構化的轉變性體驗。這種轉變性的體驗,正是先鋒戲劇孜孜以求的。
早在50年代,杜夫海納就在《審美經驗現象學》(’)中主張以現象學研究戲劇和表演,并明確指出“表演者不是作者的藝術”(Dufrenne20);波蘭美學家英加登也曾在著作中討論同樣的問題,強調舞臺演出相對于文本的獨立性(英加登303—308)。但二者的觀點并未受到戲劇界的重視,因為他們過度沉迷于現象學科學,未能跳出純粹美學的邊界。真正明確將現象學和劇場表演研究相結合并產生影響的是伯特·奧倫·斯代茨(Bert Olen States)的作品《小屋中的奇想》()。斯代茨是首位指出符號學不足并提倡以現象學彌補的學者。他認為,劇場中包括兩種觀看方式,一種是符號學的,一種是現象學的(States8),分別對應意義和體驗。斯代茨敏銳地捕捉到了符號和現象的區別,并以符號(sign)和意象(image)為例,說明對符號的把握始終會同時涉及能指和所指,并在他處建構意義,而對意象的把握可以縮短指涉的過程,直接關注生理反應和不適(24)。他在書中提出兩種思路,為此后現象學方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首先,他強調關注舞臺要素的物性,而非只是其符號性——此條明顯源于海德格爾的啟發。作為符號的舞臺元素本身也有生命,在一定程度上拒絕被完全符號化(20)。斯代茨暗示,符號學作為邏各斯言說的一部分,以命名和意義強加的方式遮蔽了事物的本性,從而抹殺其存在的深度和厚度,因此,現象學的目標,是在對事物的不斷重命名中,將事物的本性解放出來。斯代茨的第二條思路是觀演關系中身體的重要性——此條源自梅洛-龐蒂的影響。他強調共情的潛力,認為再現式的摹仿并非劇場體驗的全部現實,而是有很大一部分關乎觀演身體共情式的交流——這種直接感受正是新意義的起點(27)。
四、 物與身體的現象學審視
對物性的關注使現象學可以回應那些哲理性的演出。從追求含混性和精神性且反對寫實主義的象征主義戲劇開始,歐美舞臺上時常出現意義含混的事物,有的是有物質形態的在場(如尤奈斯庫《椅子》中的椅子),還有一些是可被感知的不在場之物(如《椅子》中的客人)。菲舍爾-利希特精辟地總結道,先鋒戲劇從以前的關注符號性轉移到了關注物質性(Fischer-Lichte,17)——實際上這是對布拉格學派提及的“物性”的體認。90年代以來的歐美戲劇在這方面越走越遠,在羅伯特·威爾遜大受歡迎的“意象劇場”中,敘事和文本已經可有可無,取而代之的是突出場景設計(scenography)的“建筑布局”(architectural arrangement):“音樂中的對位法、光束、身體在空間移動中的線條、道具的擺放”(Shevtsova61)。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現當代戲劇對亞里士多德的偏離。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對戲景一直持貶斥態度,認為“恐懼與憐憫可以出自戲景,亦可出自情節本身的構合,后一種方式比較好,有造詣的詩人才會這么做”(亞里士多德105),因此包括道具等物質性存在在內的戲景一直被傳統戲劇遮蔽。這種遮蔽,并非指拒絕使用,而是指被化約為符號和工具。在偏離亞里士多德的戲劇作品中,觀眾很難明確索解舞臺之物的意義,只有訴諸現象學式的感知。通過將自身對戲景帶來的感受敞開,觀眾重新認知戲景,并重塑自身。
由此可見,現象學意義上對物的處理,并非將其客體化,而是突出物我的相互作用。作用本身也同時涉及了表意之外的施為性和能動性。雷納認為,一方面,它們在舞臺上,構成舞臺的世界,為舞臺所擁有,但另一方面,道具本身也給了空的空間以物質屬性,以占據的方式去主導和占有空間(Rayner180)。以波蘭導演塔德烏斯·康托為例。在對物的處理上,他以兩種方式來解放物的能動性: 第一,是以物與物組合;第二,是以物和演員組合(McKinney125-126)。實際上,康托的做法也為其他劇場實踐所共享。那么,該如何去面對這種去符號化的物?
首先,可以關注物的本體性。劇場中出場的已不完全是意義固定的符號,而是意義不確定的開放和延異的現象。在這個意義上,物可以獨立于思維之外,也無法被化約成符號,而是有著自身獨立的生命過程(Rayner186);“它不是永恒的,而是出于生成和消失的短暫的時間性之中”(Rayner188)。在其作品中,康托便總是在再現功能之外使用現實生活中已被廢棄的物件,將其作為道具置于舞臺,使其獲得以往功用之外的新的生命,從而剝離既有的意義和工具性。這種實踐暗合了海德格爾對純然物的理解:“純然物是一種器具,盡管是被剝奪了其器具存在的器具。物之存在就在于此后尚留剩下來的東西”(海德格爾16)。荒誕劇中常見的失敗和斷裂的詩學也出自這一邏輯。當代劇場踐行了新物質主義所強調的重新賦予物以生命的策略,然而這種實踐并非指向固定,而是在組合和關聯中產生流動性和鮮活的潛力(McKinney137),無限朝感知者敞開。

90年代現象學的方法在學界并不太受重視,一是因為符號學依然大行其道,二是因為現象學與后結構主義色彩的文化研究強調的“歷史化”有所隔閡。但是,通過與其他領域的結合,加納等戲劇研究者發掘了現象學在倫理學、政治學等方面的潛力,“將個人的反應與更有社會性和公共性的框架相結合”(Allain and Harvie224)。而這其中的關鍵聯結便是身體。作為被規約的對象,身體承載了諸多議題:“身份與文化、交流、權力與約束、主體性、技術、表演、再現,以及對種族、階級、衰老、殘障、性別和性別特質”(Blackman3-4)。鑒于此,身體幾乎是20世紀以來尤其是60年代以來歐美藝術的核心,無論是展演藝術還是其他摒棄文本的戲劇作品中,都出現了身體轉向,并賦予身體更大的表現空間和更豐富的闡釋維度。
傳統戲劇中的身體不是物質的身體,而是作為符號的身體,其功能在于再現劇中人,突出其代表的意義,如民族性、階級性、心理類型、性別特征等。在邏各斯中心色彩的戲劇作品中,身體作為表意的符號,本身并不在場,而表演者身體的特性也被盡量遮蔽,如使用木偶、面具、臉譜或千篇一律的服裝等。這種做法根源于笛卡爾式的精神肉體的二分。因為意義屬于精神的范疇,只有在借助符號系統(如語言)的情況下才能清楚表述。但相較之下,表演者的身體則沒有那么安分,所以在演出中,務必要削弱其肉身性,以使觀眾注意力聚焦于戲劇人物,而不是表現人物的表演者身體(Fischer-Lichte,78)。簡言之,符號的身體主導,而現象的身體則被打壓,其最終目的是將意義簡化或純化,不讓表演者的身體侵犯作者的表達。如此一來,表演者只是工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然而,在諸多弱化或取締文本性的戲劇和展演藝術中[如貝克特、薩拉·凱恩、Franko B的作品],身體的物質性被不斷彰顯。就表演者而言,去符號化的身體以各種異常的方式出場,使觀眾注意到身體符號意義之外的內涵。同前文提及的“物”一樣,身體不再只是一種表意工具,還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一旦身體不被化約成結構化的符號,那它就成了強度和能量的制造者,[……]分析的重點也成了對強度、風格化和感觸的分析,以及它們對觀眾的影響”(Pavis31)。菲舍爾-利希特將演出中這種具身化的身體分為四類: 顛倒表演者與角色的關系、展示表演者的身體特性、突出表演者身體的脆弱性、異裝。這些無不是讓觀眾注意到身體本身的策略(Fischer-Lichte,82-92)。在現象學身心一體的話語中,一切思考和存在都是具身化的,脫離了身體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覺和感受。因此,對肉身性的關注也包括了認識論意義上的反思。當肉身性帶著明確的性別、族裔、年齡等指向,身體的文化批判性就自然顯露。
就觀眾的身體感知而言,如何使其在參與過程中感受到陌異性的出場,也是表演設計之要。借助非自主的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觀眾可以具身化地感受和模擬表演者身體所傳遞的感觸。換言之,當視聽等知覺將外部的信息吸收和內化之后,就容易形成一種自反性的認知,從而促進思考(Reynolds and Reason130)。這也是共情的發生機制。它令主體超越自身狹隘的世界,利用想象力、直覺和觀察來理解另一個世界(Krasner255),從而進入一種等待轉變的臨界狀態。而另一方面,技術媒介創造的聲、光、色等戲景也能輕易通過感觸來刺激觀眾;浸沒劇等互動式演出中的嗅覺、觸覺等經驗,更是直接地逼迫觀眾的身體出場。這些新出現的藝術手法都在召喚現象學式的感知,而作為連通理性與激情、身體與心靈、自我與世界的事物(Hardtix),“感觸”這一跨學科的綜合性概念也自然成為關鍵詞。
感觸本身具有應激和原始特征,它以溢出于“否定性和對立性”(Gregg and Seigworth10)的姿態,迫使我們懸置既有的觀念,從而開啟自我內部的對話,讓身體同理智溝通。其運作原理是,因為外部刺激,觀眾主體的肉身出場,體會到身體對一些觀念和現象的感受和回應,而相比于思維與存在的二元對立,這些感知屬于更為本源或源初的意義層次和領域,因此容易造成含混,但卻也可以激發持續的反思,并最終給思想帶去轉變。于是,在感觸的流動中,自我與他者的邊界模糊,與之相關的個人身份和主體(間)性也變得不確定。阿爾托、格羅托夫斯基、謝克納等戲劇家儀式感極強的作品,往往以身體為中心,借助文本外的流動性感觸要素,喚醒體內蘊含的原始力量,給觀演的精神以洗禮,從而對抗資本主義、啟蒙主義等結構性的壓迫。身體藝術(body art)等更加極端的展演藝術,更是直接拋棄語言,用脆弱的身體帶來的感觸與觀眾交流。以上種種,所依托的都是斯代茨在80年代就指出的“感觸性的肉身性”(States27)。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身體是一種文化實踐,感觸也是社會化和政治化的。艾哈邁德在《情感的文化政治學》()中指出,客體本身不會激發情感,情感由與客體的接觸而塑造(Ahmed6)。換言之,相遇和接觸是產生感觸的基本條件,相遇之后,主體處于臨界狀態,可感觸,也可被感觸,因此身體與感知的對象也會發生不可逆轉、難以重復的變化。當身體出現感觸,便處于生成(becoming)狀態,而擺脫單一的存在(being)。帶有解構色彩、消解二元對立的當代政治性戲劇尤其擅長將既有的觀念打破,但又能讓觀眾被即切的肉身體會說服,從而更加平和地去接受打破后的新觀念。在斯賓諾莎看來,感觸的倫理學和政治學意義在于可以將激情轉化為行動力(Hardt x),因此,觀眾受到的震動必然會帶來新的行動。70年代后期興起的各類社會化、政治性的文化批判戲劇作品,都在以這種方式不斷打破禁忌、質疑常規,從而不斷解放人們的觀念,推動社會進步(Dolan,; Thompson; Diamond, Varney, and Amich)。可見,當現象學同反再現、去中心的實踐相結合,便能產生強大的批判力和效力。
之所以強調結合,是因為如果單純使用,現象學無法發揮其批判的力量。90年代后,現象學成為一種基礎性的分析視角和態度,在結合其他視角(如后結構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媒介研究等)的情況下被廣泛使用,方才賦予諸多表演中的事件性因子以文化內涵(加納,《戲劇現象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22—24)。從原理上來說,現象學的政治批判性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現象學所關注的含混和難以把握的對象,往往容易削弱固有的身份和身份認同。用石可的話說,“現象學式的模糊性也可以被當作是一個普遍的模型,用來處理其他由簡單的二元對立引發的問題”(10)。因為當代的諸多政治問題根源于二元對立,先鋒戲劇時常召喚不在場、記憶、幽靈等難以捕捉的事物,以邊緣消解中心,以模糊對抗簡化的敘事,并通過喚起觀眾的陌生化感受,制造超越二元對立的交流機制,在劇場中表達烏托邦愿景。這種藝術精神正好對應了現象學的方法。
此外,現象學的核心是主體體驗與顯現的現象之相遇,強調事物本身向意識的敞開,而無需訴諸任何外部的知識體系。通過削弱既有知識體系在解讀中的作用,破壞強加的框架性敘事,現象學的思路成為消解意識形態壓迫的利器。懸置本身就是去歷史化的,目的是讓既有的知識被主動忘記,但懸置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懸置之后依然需要還原工作。莎劇在當代的跨性別、跨族裔、跨文化、跨媒介改編,往往就在解構的層面運作,令觀眾懸置經典解讀,以全新的方式去審視原文本中被遮蔽的議題,并創造新的闡釋空間。在這個意義上,現象學的方法可以結合社會批判理論與實踐,以介入性的姿態反思被邊緣化和遮蔽的文化政治敘事,為日漸肉身化和政治化的當代歐美劇場與展演藝術提供爭論的框架。
結論: 符號學與現象學之互補
通過比較符號學與現象學關注的重點和策略,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二者的長短。符號學強調的是重復,而現象學則關注初次感受,尤其是引人注意的陌異性感受。符號學的出發點是客體,而現象學的出發點是主體。前者的認知遵循從部分到整體的分析,后者是先把握整體的感受,再作分析。前者關注顯著而可見的事物,后者關注被遮蔽的事物或事物被遮蔽的一面,前者傳遞信息的是容易把握的符號,后者是難以捕捉的感受性的現象。如果說符號學不那么強調演出的即時性,可依賴演出錄像開展分析,而無需實地觀看,那現象學的體會就有賴于演出的即時性,即演出的特定時空中觀眾主體的具體感受。如果說符號學是貼標簽從而抹殺非標簽的一面,現象學就是撕掉標簽,撕掉物在人類體系中的投射意義,將其原貌展現。
現象學的方法為劇場表演分析提供了一種補充性視角。傳統符號學式的分析將文本和演出等量齊觀,但認知科學卻發現讀劇和觀戲的不同。根據這種觀點,人腦“存在兩種認知方式,一種是專門用來再現和處理非言語表達的物體和事件相關的信息,另一種專門用來處理語言類的”(Paivio53)。而符號學的方法,其實主要針對第二種。在劇場中,觀眾同時進行著兩種意識活動,一種是文本式的,一種是感受式的。現象學對劇場演出分析的意義在于,不用再單純去關注基于行動的戲劇性是什么,而只需考慮感觸如何產生、為何產生,并如何作用于主體。對戲劇的解讀也不再需要訴諸最終會化約為邏各斯的意義和主旨,而只需從身體出發,考量與感觸相關的環境和背景。
以符號學和現象學為基本坐標,20世紀歐美戲劇學之劇場表演研究的脈絡清晰可見。究其本質,符號學和現象學分別對應了20世紀西方相對峙的再現和非再現傳統。我們能輕易將再現與符號學聯系,將非再現與感觸等現象學色彩的事物聯系。兩種學科之所以成為劇場表演研究發展的根基,也是因為它們在方法論上呼應了兩種根本的思維模式,并得以與其他的文化研究、批判理論建立起聯系,回應先鋒戲劇兼顧的美學和政治訴求,聯通劇場內外、臺上臺下,從而拓寬劇場表演研究的邊界。至于如何將這些有益經驗移植到我國的戲曲和話劇研究中,還有待學界詳細辨析本土的政治和美學遺產及語境,做出更多的批評實踐。
① 如20世紀著名戲劇批評家埃里克·本特利的代表作《戲劇的生命》(, 1964年)一書在第一部分“戲劇諸面”中介紹戲劇的基礎,便是情節、人物、對話、思想和搬演(Bentley1-192)。表演本身在最次要的位置。
② 德國戲劇研究學者艾麗卡·菲舍爾-利希特認為,歐美劇場研究源自德國學者馬克思·赫爾曼。早在1918年,他就指出戲劇文學與劇場藝術的區別,強調觀眾對演出意義的創造。他之所以能提出這種觀點,與當時德國戲劇實踐者(尤其是萊因哈特)的創新不無關系。而幾乎是在同時,北美部分高校開始建立戲劇學科(Fischer-Lichte,13-14)。時隔百年,當今英語世界大多數戲劇類學術刊物,都不再刊登研究戲劇文學的文章,而戲劇這一專業,也獨立于文學專業,與電影、音樂等藝術學科并置。

④ 此書共三卷,第一卷由宮寶榮翻譯,名為《戲劇符號學》。
⑤ 索緒爾認為“語言”是所有人共有的基本的系統,與之相對的是相對個體化的“言語”(parole)。
⑥ 譬如,在表演中,臺詞的文字屬性看似可以確定意義,但演員的聲音屬性如音量、音調、音色、音長,則很難被完全符號化,因為它們太多變,內涵不僅因背景而異,還極其依賴觀眾主體的感受。換言之,聲音要素可以直接干擾臺詞的內涵,影響觀眾對演出的判斷。戲劇演出中這類要素不可謂不多,而符號學客觀式的分析方法,并無法完全應對這些交流要素。
⑦ 值得一提的是,在符號學家的論述中,這些方面其實也都有所體現,只是常被淡化或模糊帶過。
⑧ 國內學者中,汪余禮早在2004年就已自發地提出以現象學來切入戲劇。參見汪余禮,《現象學對戲劇研究的啟示意義》,《戲劇藝術》4(2004): 20—28。
⑨ 本文所謂“傳統”,僅是一種權宜的說法,用以指涉先鋒主義戲劇之前的歐美戲劇。
⑩ 在現象學中,語言符號與直觀并非沒有關系。胡塞爾之所以能破除邏各斯中心主義,前提是他發現了作為第一人稱的意識體驗是賦予形式化的語言以意義的基礎,而當重點從語言轉向這個意識基礎之后,如何使得體驗自身第一人稱現身就成了現象學的一個關鍵問題。以此觀之,為了理解符號學中的符號,主體需要與外部世界建立聯系,而現象學的理解,則要以意識和現象相聯(Power176-177)。

Ahmed, Sar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Allain, Paul, and Jen Harvie,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亞里士多德: 《詩學》,陳中梅譯注。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6年。
[Aristotle.. Trans.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Bentley, Eric.. New York: Atheneum, 1964.
埃米爾·本維尼斯特: 《普通語言學問題》,王東亮等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Benveniste, émile.. Trans. Wang Donglia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Bial, Henry. “Double-Coding.”:. Eds. Meiling Cheng and Gabrielle H. Cod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144-45.
Blackman, Lisa.:,,.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12.
Bleeker, Maaike, Jon Foley Sherman, and Eirini Nedelkopoulou. “Introduction.”:. Eds. Maaike Bleeker, Jon Foley Sherman, and Eirini Nedelkopoulo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1-19.
Bogatyrev, Petr. “Semiotics in the Folk Theater.”:. Eds. Ladislav Matejka and Irwin R. Titunik.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33-50.
Carlson, Marvin A. “Semiotics and Its Heritage.”:. Eds. Janelle G. Reinelt and Joseph Roach.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13-25.
- -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Case, Sue-Ellen.. New York: Methuen, 1988.
邁克爾·戴維斯: 《哲學之詩——亞里士多德〈詩學〉解詁》,陳明珠譯。北京: 華夏出版社,2012年。
[Davis, Michael.:’Poetics. Trans. Chen Mingzhu. Beijing: Huaxia Press, 2012.]
Diamond, Elin, Denise Varney, and Candice Amich, ed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Dolan, Jill.. Ann Arbor: UMI Research Press, 1988.
- -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Dufrenne, Mikel.. Trans. Edward S. Casey, et a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Elam, Keir.. London: Routledge, 1980.
Fischer-Lichte, Erika.. Ed. and trans. Minou Arjoma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 - -.. Trans. Jeremy Gain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 -.:. Trans. Saskya Iris J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Garner, Stanton B.:. Ithaca, N.Y.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戲劇現象學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駱玉輝譯,《戲劇》4(2019): 16—25。
[- - -. “Theatre and Phenomenology.” Trans. Luo Yuhui.4(2019): 16-25.]
Giannachi, Gabriella, Nick Kaye, and Michael Shanks. “Introduction: Archaeologies of Presence.”:,,. Eds. Gabriella Giannachi, Nick Kaye, and Michael Shanks. London: Routledge, 2012.1-25.
宮寶榮: 《戲劇符號學概述》,《中國戲劇》7(2008): 62—64。
[Gong, Baorong. “Theatre Semiotics.”7(2008): 62-64.]
Gregg, Melissa,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An Inventory of Shimmers.”. Eds.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1-25.
Hardt, Michael. “Foreword: What Affects Are Good For.”:. Eds.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and Jean Halle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x-xiii.
馬丁·海德格爾: 《林中路》,孫周興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20年。
[Heidegger, Martin.. Trans.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0.]
胡妙勝: 《戲劇演出符號學引論》。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
[Hu, Miaosheng..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1989.]
羅曼·英加登: 《論文學作品: 介于本體論、語言理論和文學哲學之間的研究》,張振輝譯。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Ingarden, Roman.:,,. Trans. Zhang Zhenhui.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Kowzan, Tadeusz. “The Sign in the Theat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emiology of the Art of the Spectacle.”16.61(1968): 52-80.
Kozel, Sus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Krasner, David. “Empathy and Theater.”:,,. Eds. David Krasner and David Z. Saltz.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255-77.
McKinney, Joslin. “Vibrant Materials: The Agency of Things in the Context of Scenography.”:. Eds. Maaike Bleeker, Jon Foley Sherman, and Eirini Nedelkopoulo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121-39.
Merleau-Ponty, Maurice.. Trans. Colin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aivio, Alla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larendon Press, 1986.
Pavis, Patrice.. Trans. Andrew Brow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ickering, Kenneth..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ower, Cormac.:.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8.
Rayner, Alice. “Presenting Objects, Presenting Things.”:,,. Eds. David Krasner and David Z. Saltz.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180-200.
Reynolds, Dee, and Matthew Reason.. Bristol: Intellect, 2012.
Scheie, Timothy. “Semiotics/Semiology.”:. Eds. Meiling Cheng and Gabrielle H. Cody. New York: Routledge, 2016.264-365.
Shevtsova, Mar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石可: 《從格羅托夫斯基到全息影像: 現場藝術中的肉身化與非肉身化》。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
[Shi, Ke.:.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Sofer, Andrew..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Sokolowski, Robe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tates, Bert O..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 1985.
Thompson, Jam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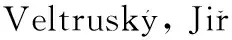
Vince, Ronald W. “Action.”. Ed. Dennis Kenne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8.
張祥龍: 《朝向事情本身: 現象學導論七講》。北京: 團結出版社,2003年。
[Zhang, Xianglong.:. Beijing: Unity Press,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