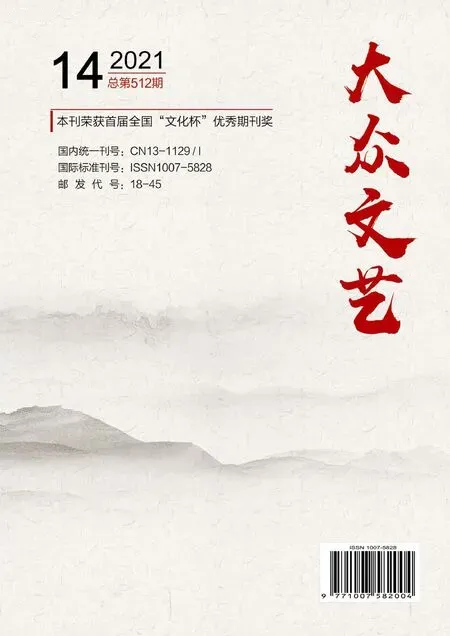文學人類學視角下的玄圭符號源流考證
韓昊彤
(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上海 200240)
大禹作為夏朝的開國君主家喻戶曉,但是大禹文本記載的流傳版本與后世其他帝王不同的是,其文本記載在表述帝王功績的歷史敘事的基礎上,文本整體敘事風格產生了神話學偏移。大禹治水是先秦典籍中記載最多的神話歷史,其神話性質的記敘在《尚書》《詩》等傳世典籍中都有出現,由此看來,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后,大禹治水的神話已然在社會間流傳。邵望平先生立足于考古學與典籍學的證據,考證了《尚書.禹貢》中所載的九州山川分布。他認為《禹貢》中保留了大量龍山時代的訊息,也就是說《禹貢》九州是自公元前兩千年前后就實際存在的地理自然區系,這使得大禹治水神話有了一定的實際歷史意義。大禹的豐功偉績在典籍中記載頗豐,袁珂先生將大禹的相關記載歸納為七件事,現整合略分為三:其一受命治洪水,得天之助平洪水,此為禹王天下的前提;其二除妖平亂(無支祁、相柳、防風氏等),禹會萬國立威,此為禹王天下的過程;其三聽政繼位,步量天地,定名山川,重建世界秩序,此為禹王天下的結果。圣王大禹的記載與王權神授、王權更替的符號原型無法分割,這種開國神話本身就帶有從“混沌”走向“秩序”這類創世神話母題的特點,圣王大禹(創世神)打破原始大水(混沌)狀態,進而敷土(原始陸地)建國,在創世神話之中,這種狀態的置換離不開顯圣物的傳導,如盤古的創始之斧、兄妹創世的葫蘆等,而圣王大禹所持有的顯圣物則是“玄圭”。由《尚書.禹貢》記載可知,大禹理想國的開創離不開天賜“玄圭”的幫助,“玄圭”的出現也標志著九州統一與天命之所在。

不過“圭”的禮器化過程并不是一朝完成的,圭與斧鉞相似,也經歷了從實用器到禮器的蛻變。唐啟翠認為“圭”取意于割殺之用器即“刲”,而去掉利刀旁后實用器的功能弱化,這也就使得“圭”字的功能轉向潔凈神器。《易歸妹》:“上六,女承筐無識,士刲羊無血”,此處刲即宰割祭祀犧牲,而《白虎通瑞執》記載:“以圭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結”,此處圭做潔。王永波先生依照圭首形態不同將玉圭分為凹首圭、平首圭和尖首圭,它們各自起源于農具耒耜、斧鉞等手工業具和兵器戈。唐啟翠總結,玉圭祖型源于手斧,分流為長方體平首和尖首兩種基本形制,前者以介圭、鎮圭等形式留存,后者在龍山晚期至夏商又有兩類分流:刃首三角形和刃首凹弧形或耒耜,這兩種類型從商周往后則以刃首三角形為主流標準器型。刃首三角形的玉圭在后世甚至被賦予了堪比“傳國玉璽”的功能,在《漢書王莽傳上》等典籍中詳細記載了禹獲玄圭、受舜禪讓的神話,并完全具備了帝王應運受命的寓意。自漢朝以后,獨攬大政的權臣為王權的穩定必引“九錫之命”與“玄圭之錫”,進而變為了一種應運改朝換代的標準信號。可見,在后世改朝換代創世之際,玄圭作為天命轉移的福瑞象征,與傳國玉璽互相作用,形成九錫加璽之禮,從而滿足了王權的正當合法性。
個人認為,約瑟夫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中所論述的英雄主義神話核心與大禹圣王感召神話相似。約瑟夫坎貝爾將英雄的故事分為了四個大章節,在第一章節中英雄在正常世界中會接受到冒險的召喚(感召),進入冒險的旅途后,在第三幕中英雄獲得寶劍(玉圭)并獲得最終的成功。所以,圣王感召的神話與西方英雄主義神話在關鍵點與轉折點的敘事結構基本相同,二者都在接受天命召喚的前提下,受到了“顯圣物”的幫助。為了進一步加強玉圭“顯圣物”的特性,玉圭與神鳥赤烏結合,創造出“赤烏銜圭”的神話。赤烏也稱三足烏,是神話中太陽的化身、生命之源,更是戰勝混沌黑暗的光明之神。唐啟翠認為,西周玉圭上刻印的赤烏紋飾,可追溯至龍山時代玉圭上刻印的鳳鳥紋,同時也是祖靈崇拜的一種體現。根據天文學者的研究,周革殷周的事件(“赤烏銜圭于周社”)發生在公元前1059年,那時發生了五星聚房的天象,在星象被刻在玉板上后,赤烏銜圭的神話又演變為了鳳圭河圖的新神話。禹賜玄圭是“赤烏銜圭”“天命于圭”的神話原型,玉圭是自天而降的瑞信和王權神授的憑證,在王權更替、開朝換代之時擔任著溝通天地的責任。
進入禮器系統后的玉圭將顯圣物的特點發揮在各個方面。首先是祝告禮儀中的玉圭。顧頡剛先生曾在《尚書校釋議論》中考證了“植璧秉圭”的故事,“植”同“置”與“載”或“戴”通用,陳喬樅認為“植璧”即置璧于帛之上,用于禮神降神,手執玉圭,用于依附自天而降的祖靈。因此唐啟翠認為,周公用圭、璧兩種玉器祝告三位先王,就是植根于古老的玉石神話信仰,圭璧是天人溝通的核心圣器。其次圭璧既是祭品又是傳遞信息之物。唐啟翠通過《山海經》《穆天子傳》等羅列了傳世典籍中的圭璧用玉傳統,輔以考古學出土物證,總結出:玉璧是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齊家文化以至商周秦漢的典型禮器,圭(平首與尖首)璋(牙璋)是龍山晚期至夏商周秦漢時期的禮器器類,龍山晚期至夏商時圭璋并行。圭璧組合以祭祀天地日月的實物遺存見于秦漢之際,并以此獻給祖靈以傳遞后世子孫所求。不過祭祀祖靈的專用玉禮器在典籍中均指向了“裸圭瓚寶”一說。唐啟翠將圭瓚研究略分為三:其一為玉柄金勺為瓚,是裸禮中的挹鬯之器;其二為圭瓚就是器柄作圭狀或璋狀的挹鬯器;其三為瓚為某種玉器。她結合李小燕、井中偉、嚴志斌的學術觀點,提出瓚為裸器通名之說,也即玉柄形器可以定名為瓚(但瓚不一定特指玉柄形器)。玉柄形器為三代裸祭的用玉之一,瓚作玉食,斗酌鬯酒,灌注于玉瓚的美食用于獻給祖先神靈歆饗。同時玉柄形器作為祖靈所依憑的象征物,在文化編碼中蘊含著祖靈強大的生命力和生殖力,以保佑子孫后代福延綿長。最后,玉圭在禮制文明中的影響力還體現在“圭碑石函”的文化編碼中。綜上,可見玉圭禮制化的符號編碼,從神主到裸圭再到執圭以祀祖靈。這體現了古人的生死觀中“一魂歸祖、一魂在墓、一魂在宗廟或家室”的基礎理念,而神主之魂憑借著玉圭一類的降神禮器返回生者的世界,保佑兒孫清潔,家族六畜興旺,乃至一方五谷豐登。
后世禮樂失傳,玉圭也走下神壇,轉而進入人間朝堂之上。唐宋時常用“析圭”或“命圭”表示上授或下賜之意,如唐王維《魏郡太守河北采訪處置使上黨苗功德政碑》:“至于析圭分組,跨壤連州,懷四術而自疑,見九重而失望。”而且,在戰國時楚國有種爵位叫作“執圭”,后來則成了任官授爵的代名詞。在漢畫像磚中官吏常手執玉圭,這種天子收歸并重授玉制憑信給諸侯或地方官員的行為叫作“班瑞”。至少在西周中晚期,臣有功而受王賜圭璋等,和賜命之禮后的臣下以圭璋等瑞玉反納覲已然形成定式的禮儀制度。孔穎達疏注《禮記》將圭角比喻為人的鋒芒,以“不露圭角”表示謙謙君子的含蓄儒雅。另外,還有“三復白圭”形容君子甚于言行,“篳門閨窬”形容貧賤不移。
就目前考古學出圖實例物證來看,大禹手持的那把“玄圭”似乎仍然沒有確切定論。不過從斧鉞到璋式圭再到商代戈式圭的演變軌跡都有跡可循,例如尖首的戈式圭、大玄刀和柄形器等,都有可能是商周以前無文字文獻記載的玉禮器圭,唐啟翠推測其中有可能與“玄圭”相接近的器型有兩種,一種是歷史沿用長且與測影卦畫相關聯的尖首圭,另一種是鳳鳥紋柄形器。依照《周禮》等典籍記載,“土圭”即“度圭”是一種可以測量天地、辯證方位、定時考潤的量尺。由此延伸出“奉為圭臬”等詞組,其中“圭臬”就是土圭和水臬,是用來測日影、度土地的天文儀器。在《周禮夏官》以及其他典籍中都記載了,掌管土圭的土官(地官)使用“土圭之法”測影度地,這也是國家初建之際維護國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其間還隱含著一種在混沌無序后重建秩序的創世觀念。唐啟翠認為,在建國之初,首要之務便是劃定國家疆界、確立國都、量地制域、制定歷法與敬授民時,這關系著新國家新王權的合法性與可持續性,也為農業生產提供準確的時間節點,而這一切都與“土圭”密不可分。不僅如此,土圭還代表著“王者居中”信念的象征性行為,并派生出以地中為代表的“五方”天下觀。圭表為中的代表實例物證是開元年間的“周公測影臺”,根據馮時的研究,此臺與兩周青銅祖槷形制大同,甚至與陶寺槷表垂直校正儀——玉琮的形制也大體一致。同時馮時結合《堯典》與楚帛書的表述印證出:圭表致日功的主要表現在“識陰陽”“辨四時”,槷表的設計通過方色的取舍表現揚陽抑陰、近德遠刑、祈生避殺的特點。英國的戈登·柴爾德認為,早期文明的人對自然系統觀察的初衷不是增進技術知識,而是培育社會控制和超自然控制的技術能力和行政能力。“土圭測影以求地中”經歷了從神話、技術到禮制的演變,神話原型與技術實踐的結合構成了禮制時代信仰之根與系統制度的保障。
個人認為,土圭的深層文化編碼還蘊含著“同心圓”式的政治地理觀。土圭測影定位的具體方法是日初生之時以正南正北放置圭尺,表直立于圭的正南端,然后以表為圓心畫一個大圓,記錄日出與日落時表影與圓圈的相交點,兩點的連線就是正東正西,而直線與表的連線方向就是正南正北。這種在太陽的指引下用畫圓的方法確定一個范圍,文化編碼蘊含著太陽(王權)引導下的權力范圍,也就是以帝畿為中心向荒服遞減的政治結構。《山海經》中山經與海經的敘事結構與土圭測影的實踐過程相似,其將“四方”設為山經章節分段之所在,這恰好與土圭測影所分割出的圓內四方空間相吻合,如果進一步將代表四方的分割線向圓外拓展,那么剩下的部分則是海經與荒經敘事之所在。《山海經》中所隱含的“圭表測影”型的敘事結構,也代表了古人將時空的規劃視作世界的創造之始的宇宙觀。不僅如此,《海內經》記載:“有木……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結合《淮南子》中對于建木的描述“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建木這種立于“地中”的巨大表木,體現了古代政體對于疆界與王權“不設邊際”的完美理想。圭表還有著“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的功能,葉舒憲先生在《山海經文化尋蹤》中將此表述為化“生”為“熟”的統治手段,換句話說,巫師王通過對世界詮釋權的掌握來強化族群的統治,同時將族群外的“文化他者”妖魔化,使得親族關系紐帶更加牢固。
玉圭中隱含著創世神話的編碼原型,循著其原型斧鉞的演變道路,完成了從實用器到禮器的蛻變。禮制化的玉圭代表著天命符瑞的王權建立,還作為溝通天地的“顯圣物”連接著生者與祖靈的世界。當玉圭走下神壇進入廟堂之后,便與“賜圭”的天子、“執圭”的朝臣一同構成了固定化、程式化的政治形象表征。而且玉圭在精神內涵方面,常被賦予德才卓絕之意,翩翩君子也常被比作“如圭如璋”。最后,圭表測影結合了神話原型與技術實踐,由此奠定了禮制與信仰的基礎。玉圭跨越時空走來,它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層面都推動著人類文明的前進,它見證政權興衰與時代的更迭,它隨著時光的筆觸,一筆一畫的譜寫著不為人知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