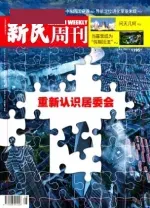居委、業委、物業,誰管誰
劉朝暉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完工的商品房小區成為一些社區矛盾的焦點。攝影/ 徐程
居委會本來是城市末梢幾乎唯一的自治組織。隨著社會的變遷,居委會似乎退到了一個不為人知的位置。而物業管理公司、業主大會及業主委員會的出現,讓現代的社區治理形成了“三駕馬車”并駕齊驅的局面,而在三方的運轉中,也出現了不少矛盾。
可以說,“三駕馬車”的配合程度直接影響著居民、業主生活的環境和品質,如何協調和理順三者間的職能與關系,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形成合力、共同發展的局面,是社區治理是否順暢的關鍵,關系到社區治理的成效。
某小區居民徐女士曾向記者反映過這樣一件事情。在疫情封控的5月的一天晚上,她突然覺得腹部劇烈疼痛,急需就醫。徐女士的先生聯系了小區物業保安,答復是要找居委會主任,而居委會主任給保安的答復是病人自己叫了120就可以去醫院。但由于小區7天內有陽性病例,120需要居委會開出的轉診單才能把病人接走。徐女士的先生再度電話聯系了居委會主任,但轉診單卻遲遲沒有開出,主任也沒有現身,門衛保安則依然是一副不見主任不放行的態度。直到徐女士疼得不行帶著哭腔放聲大叫,保安覺得情況有點不對了,才讓徐女士坐著先生的電瓶車去醫院就診,什么證也不要了。
像這種情況到底是公安管還是城管管,還是市場管?誰去制止他,誰去處罰他。這個權責,可能我們的行政部門還需進一步厘清。
實際上,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間,類似的事例不在少數,也造成了部分居民對居委會和物業的強烈不滿情緒。一時間,居委會成為了居民情緒的矛頭所向。其中,有誤解,也有居委會自身的問題存在。
虹口區曲陽街道東體居民區黨總支書記黃斌認為,為什么居民會將矛頭對準居委會,和居委會角色在居民區中長期的淡化不無關系。很長一段時間,居委會在整個社區中的存在感并不強,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居委會的辦公地點和電話。但這次的疫情,突然就把居委會推到了風口浪尖,推到了所有矛盾解決的一個核心位置上,因為這是居民身邊唯一能找到的可能代表政府身份的一個組織,雖然它被定義為一個居民自治組織。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郝宇青向《新民周刊》記者介紹,在當前國家社會治理的體系中,居委會作為社會基層治理的末梢,行政化的色彩越來越強,雖然這并不意味著居民自治角色的消解,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居委會需要承擔的由上而下分派的行政任務較過去大大增加。
在郝宇青的調研中,曾發現一個居委會的干部的手機里,有60個不同的群微信,分別對應了街道不同的職能部門和分派的任務,每天布置任務或下達通知,居委會干部都要回復。
“每天伺候這些群,他就要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郝宇青說,“如此一來,真正投入到運營具體社區事務的精力和時間就少了。居委干部變成對上不對下,反而減少了與居民的聯系。” 他介紹,復旦大學社工專業的師生在疫情期間曾有過調研,有的居委會承擔了119項職能。
黃斌對此同樣深有體會。“居委工作人員的工作雖然是按塊分的,但是實際深入到這個塊里每戶人家的具體情況,可能就不一定能完全講出來了。更多的是依賴于電腦辦公,成為只會做表格的‘表哥表姐’。我覺得這個跟過去那種主動化的居委工作模式,還是有代差的。走街串巷家長里短需要更多的是時間,但是這個時間恰恰是現在居委最缺的東西。”
隨著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下移到居委會的責任也多了不少,但是相應的權力和資源的下移卻并不一致。“這些是相對滯后的。這樣造成居委會權力小,責任大,處于一種很尷尬的一個境地。” 郝宇青說。
居委現在的權責不匹配,也是黃斌在很多工作當中的感受。“居委會雖然不是兩級政府三級管理中的一環,但是其實是政府各項政策、各個管理部門落腳社區的最后一公里。然而居委會的權責不匹配。”
黃斌舉了個例子,疫情封控期間保供跟不上的時候,他負責的小區里也在搞團購。“團購搞得好,能讓社區平穩是好事。但是如果搞得不好,居委摻雜在中間,有了利益糾葛,有了利益劃分的話,居委今后的工作是很難開展的。”當時小區里的團長超過100個,他就在東體小區組織了一次20個大團長參加的視頻會議,擬定了一份團購攻略和公約,對小區團購應該怎么做,做哪些東西,怎么監督,怎么實行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約定。不過依然有“野團長”我行我素,發放團購物資甚至不戴口罩,還有的聲稱團購目的“就是要掙錢”。
“上面強調要求居委必須要管好你的團購,不能因此造成交叉感染。但是我們沒有一個權力部門的支撐,職能部門很難叫得動。后來報警,警察也過來勸導一下,但有點隔靴搔癢。像這種情況到底是公安管還是城管管,還是市場管?誰去制止他,誰去處罰他。這個權責,可能我們的行政部門還需進一步厘清。”黃斌說。
一方面是社會治理下沉帶來的“行政強化”,一方面又是存在感的弱化,對于居委會來說,這是一個亟待破解的課題。
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一直是上海的一張名片。在推進逐步建立以居民區黨組織為核心,“三駕馬車”等主體共同參與的住宅小區治理框架方面,上海有很多成功的經驗與案例。然而在居委會、物業、業委會三者之間,依然有不少矛盾暴露。圍繞著三者的職責、權利、義務,并非所有的居民小區都能建立起平順運轉的機制,矛盾也一直存在。
居委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是本建筑物或建筑區劃內所有建筑物的業主大會的執行機構,按照業主大會的決定履行職責。居委會和業委會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在各個政府文件和法規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同時也指出,居委會對業委會進行監督和指導。在實際工作中,大多數居民同時是業主,業主多數也是居民。居委會和業委會的工作重點各有側重,但也有很多重合。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數據科學與大都市研究中心曾在幾年前開展過“上海都市社區調查”,調查顯示,上海市各個居委會與轄區內業委會之間的關系總體而言比較融洽。在已經成立了業委會的小區,居委會不但是業委會成立的主要發起者,也是換屆工作的主要負責者,主導著業委會的成立和換屆工作。居委會對業委會工作的指導與監督主要體現在對業委會成立和換屆過程中的程序監督、籌備組組建、業主大會選舉以及候選人確定工作上。
一旦涉及業委會組建、換屆,居委會就會如臨大敵,還有一旦涉及物業選續聘、物業費調整、停車規范等敏感議題的時候,居委會也會感覺壓力山大。
不過一旦涉及業委會組建、換屆,居委會就會如臨大敵,還有一旦涉及物業選續聘、物業費調整、停車規范等敏感議題的時候,居委會也會感覺壓力山大。“現在我們居委會書記最害怕的就是業主委員會的換屆改選。”寶山區楊行鎮福地苑一居黨總支書記李延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方面要進行監督指導,一方面又要考慮不能過度干預,這個“裁判員”并不好當。
“上海都市社區調查”也顯示,居委會和業委會之間在日常互動和社區公共事務處理過程中仍會產生分歧與矛盾,而且主要涉及利益糾紛。涉及的主要問題包括:小區公共事務的決策和執行、小區公共空間和設施的擁有和使用、小區公共收益或維修資金的使用分配、房地產或物業糾紛、業委會委員人選等。在這些糾紛矛盾中,有超過一半涉及小區公共空間設施、公共收益與維修資金、房地產和物業的利益糾紛。
有的時候,小區保養、維修資金動用等專業性頗強的事項,由于很多居委會成員非物業管理專業出身,在這些難題矛盾面前,沒有用武之地。業委會對居委會的“指導和監督”往往并不“感冒”。而有的業委會對資金動用的程序雖然合法,但只要不是達到一定金額,居委會也無法介入,對一些不甚合理甚至帶有濫用私用的資金動用,也無法對業委會實施約束。有的時候,居委會在社區公共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導致業委會的功能無法有效發揮,無法充分調動業主的參與熱情,不利于社區公共性的培育。
而在居委會和物業公司關系方面,物業是基于合同關系為居民提供服務,是一個營利性經濟實體,與居委會并無上下級的關系。雖然居委會也能指導監督物業管理,但由于具體職責不夠清晰、指導監督手段不多,以及居委會干部的物業管理專業知識不足、有時一個居委會需要面對多個業委會和物業服務企業等原因,居委會開展指導監督存在不少困難。同時, 一些小區業委會缺位、運作失序,物業服務企業“小弱散亂”,或者沒有物業服務企業,居委會“托底”的壓力較大。
雖然在社區事務上,目前很多小區都是由居委會、物業和業委會三方一起坐下來協商解決,但黃斌表示:“有些業委會或者物業,他不一定就是聽你居委會怎么說,他們就一定怎么做的。他承認居委會有管理這個職能,但對誰管誰的問題上是不是買你的賬,又是一說。”

鄭家巷居民區黨建活動。
上海正在逐步建立以居民區黨組織為核心,“三駕馬車”等主體共同參與的住宅小區治理框架。如何理順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甚至志愿者的關系,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形成合力、共同發展的繁榮局面,是社區治理能夠順暢的關鍵。
在黃斌看來,居委會與物業、業委會雖然可能會有一些博弈,工作中也存在著一些客觀的社會因素與實際問題的困擾,但這并不能成為居委會就此躺平甚至“撂挑子”的理由。據他的觀察,在一些新的小區,業主素質較高,物業也比較專業,居委需要處理的社區事務較少,疫情期間門崗管理、保供物資發放、核酸大篩等事務也許物業一條龍就能包辦,而在像東體居民區這樣物業薄弱的老舊小區,就更需要居委干部和工作人員有前出和擔當意識,承擔起該擔當的職責。
郝宇青在接受采訪時,著重提到了黨建引領的作用。在社區治理的“三駕馬車”外,社區黨組織的介入,正在成為第四駕馬車。
“這種引領作用最重要的是要突出人,做好人的工作。他是他我覺得就是黨建,他不是黨建的,他不應該體現出是一個硬件方面的,而是軟件建設。現在說的社區‘黨建+’的概念,不僅僅是說黨員隊伍,還有就是黨群關系的建設。黨建+,應該做好人心的工作。” 郝宇青說。
黃斌也談到了黨組織在東體居民區治理中發揮的關鍵作用。“黨建引領,核心是如何引領。現在我們社區核心的志愿者,這些站出來的年輕人,很多人都不是黨員,但是他們就是愿意出來做。在黨建的引領下,讓居民感覺跟社區有歸屬感,感覺我應該為了社區做點什么,我覺得這個居委會就做到位,就成功了。” 他結合自己的工作實踐,認為把黨建引領做到實在,關鍵在于兩個字:共情。
黃斌覺得,居委會確實是被強化了很多原來沒有的行政主體身份,但是該有的身份被弱化,是因為覺得居委干部年輕化了以后,丟掉了兩個傳家寶:一個是走街串巷,一個就是家長里短。所以從去年開始,東體居委會抓住這一點,搞了“一日居委小干部“、中華傳統節日為老人包湯圓送臘八粥等系列活動,讓社區居民更多地了解居委會,感受到居委會的溫情,從而推動共同的感情升溫。“我們通過一系列活動灌輸的一個理念是什么?就是居委會是大家的左鄰右里,不是行政單位,不是辦事大廳,是你們的隔壁鄰居。”
有專家指出,“三駕馬車”理想的社區治理模式是在黨組織的引領下,各方明確職責,做到相互協調——物業管理企業應當配合居委會做好社區管理、社區服務的有關工作,成為小區專業管理的主體,全面負責房屋維修、環衛清掃、綠化養護、治安保衛等“硬件”工作;居委會將主要精力轉移到抓好小區內居民的宣傳教育、民事糾紛調解等“軟件”工作;業委會則督促物業管理企業配合社區做好一些日常管理工作。
很顯然,只有在實際工作中讓“三駕馬車”產生的“正向合力”最大化,才能給小區的業主、居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