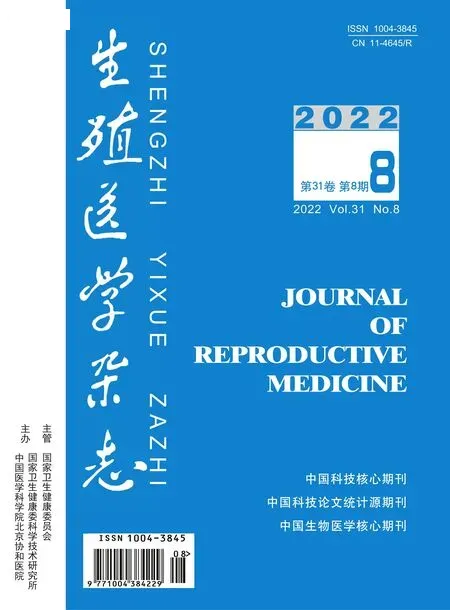子宮肌瘤術(shù)前凝血功能異常的陷阱與危機(jī)
甘靜雯,鄧姍
(中國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 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xué)院 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婦科內(nèi)分泌與生殖中心,國家婦產(chǎn)疾病臨床醫(yī)學(xué)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病例資料
患者,女性,45歲,G1P1。因“發(fā)現(xiàn)子宮肌瘤6年,近半年增大明顯”入院。平素月經(jīng)規(guī)律3~5 d/26 d,量中,無痛經(jīng)。末次月經(jīng)(LMP):2021年11月21日。2015年孕4周時初次發(fā)現(xiàn)子宮肌瘤,直徑約10 cm。產(chǎn)后(2016年)復(fù)查肌瘤直徑約5 cm,自述月經(jīng)量無增加,大小便正常,無明顯不適,故未定期復(fù)查。2021年5月起平躺時可自行捫及腹部腫物,超聲提示“子宮肌瘤10 cm,腺肌癥不除外”。就診我院后,檢查宮體如孕14~16周大小,質(zhì)地硬,活動欠佳;核磁評估提示子宮前壁巨大類圓形混雜信號腫塊影,范圍約10.4 cm×10.0 cm×11.6 cm,決定擇期行經(jīng)腹子宮肌瘤剔除術(shù)。術(shù)前常規(guī)化驗(yàn)時發(fā)現(xiàn)凝血機(jī)能障礙: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50.4 s(參考范圍23.2~32.5 s)、D-Dimer 0.83 mg/L(參考范圍0~0.55 mg/L)。追問病史,患者否認(rèn)既往血液系統(tǒng)疾病,亦無刷牙時出血、鼻出血、便血等自發(fā)出血傾向和產(chǎn)后出血、輸血史等,仍建議行APTT糾正實(shí)驗(yàn)并血液科會診,評估有無手術(shù)禁忌。查體可見雙下肢可疑網(wǎng)狀青斑,APTT糾正試驗(yàn)可見患者APTT改善但未完全恢復(fù)至正常范圍。血液科門診行凝血因子活性檢測:FⅪ 28.3%(參考范圍65.0%~150.0%)、FⅫ 14.3%(參考范圍50.0%~150.0%)、FⅨ 27.9%(參考范圍65.0%~150.0%)、FⅩ 71.2%(參考范圍77.0%~131.0%),考慮為Ⅻ因子抑制(該患者多個凝血因子活性減低,其中活性最低的為Ⅻ因子,因Ⅻ因子為內(nèi)源性凝血途徑的首個起效因子,其活性降低可影響其他參與內(nèi)源性凝血途徑的凝血因子活性,故結(jié)果判定為Ⅻ因子抑制),患者出血風(fēng)險不大,圍術(shù)期無需用藥預(yù)防出血。而為尋找Ⅻ因子抑制物,建議進(jìn)一步查腫瘤標(biāo)記物、抗磷脂抗體、狼瘡抗體等,結(jié)果示β2GP1-IgG陽性(+) 537 AU/ml(參考范圍<16.0 AU/ml)、ACL-IgG陽性(+) 148 GPLU/ml(參考范圍<8.0 GPLU/ml)、狼瘡抗凝物(LA)陽性(+)2.34 s(參考范圍≤1.20 s)。考慮為多種抗磷脂抗體導(dǎo)致的APTT假性延長,無明顯出血風(fēng)險,反而要警惕圍術(shù)期血栓形成,建議術(shù)后評估出血風(fēng)險不高時使用預(yù)防劑量的低分子肝素。
入院后擇期行開腹肌瘤剔除術(shù),術(shù)中剔除前壁FIGO 5型肌瘤1枚,直徑約10 cm(584 g)。手術(shù)順利,術(shù)中出血約200 ml。然而術(shù)后第1天查血紅蛋白(Hb) 88 g/L(術(shù)前140 g/L),患者一般情況好,無明顯陰道出血,未予重視。除補(bǔ)鐵治療外,術(shù)后第2天起加用低分子肝素4 000 U qd。術(shù)后第3天復(fù)查Hb 61 g/L,停用低分子肝素,查體除腹部傷口及大陰唇部位少許瘀青外,腹壁平軟,無壓痛和反跳痛。因無法解釋術(shù)后Hb的明顯下降,請內(nèi)科會診后復(fù)查血常規(guī)、肝腎功能、凝血功能,并完善網(wǎng)織紅細(xì)胞分析、血涂片、Coombs試驗(yàn)、尿常規(guī)+沉渣及腹盆腔增強(qiáng)CT+CT血管造影(CTA)檢查,排除活動性出血和溶血性貧血。腹盆腔增強(qiáng)CT+CTA提示膀胱前方存在7.5 cm×4.0 cm血腫,腹直肌前方可見片狀血腫。予同型紅細(xì)胞2 U輸注1次,皮下注射促紅細(xì)胞生成素(溢比奧)10 000 IU qd×3 d,靜脈輸注蔗糖鐵250 mg qd×3 d,術(shù)后第5天和第8天復(fù)查Hb分別為73 g/L和75 g/L。術(shù)后第10天出現(xiàn)傷口下方間斷性滲血,血色暗黑,紗布可見范圍約4 cm×5 cm暗褐色血跡,但擠壓傷口無明顯滲出,復(fù)查Hb 102 g/L,床旁超聲提示盆腔內(nèi)低回聲團(tuán)塊大小約10 cm×8 cm,與皮下相通;考慮為陳舊性積血,穿刺引流效果估計不好,考慮局部物理治療為宜。后觀察至術(shù)后第13天,患者每日換藥傷口紗布上暗褐色血跡逐漸減少,輕擠壓傷口未見明顯滲血,決定出院后定期門診進(jìn)行局部理療。
病例警示
一、APTT延長的鑒別診斷思路
APTT是臨床中常用的出凝血功能篩選試驗(yàn),主要反映內(nèi)源性凝血因子(Ⅷ、Ⅸ、Ⅺ、Ⅻ因子)活性。APTT延長提示有兩種可能:一是某種凝血因子缺乏,二是可能存在LA或其他凝血因子抑制物。當(dāng)患者出現(xiàn)APTT延長時,可先通過血漿糾正試驗(yàn)(簡稱APTT糾正試驗(yàn))初步判斷是由于缺乏凝血因子還是存在凝血抑制物所致。APTT糾正試驗(yàn)是將患者血漿(PP)與正常血漿(NPP)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多次檢測APTT,評估混合血漿APTT糾正的程度。當(dāng)缺乏1種或多種內(nèi)源性凝血因子時,理論上混合血漿中凝血因子活性均應(yīng)≥50%,APTT檢測結(jié)果可糾正至參考范圍內(nèi);而當(dāng)PP存在凝血抑制物,如抗凝藥物、凝血因子抑制物、抗磷脂抗體等時,混合后APTT不能糾正至參考范圍內(nèi)。概括言之,如APTT延長可被糾正,提示凝血因子缺乏,需進(jìn)一步行特異性凝血因子活性檢測;如APTT延長不能被糾正,則提示存在某種凝血因子抑制物,需進(jìn)一步排查[1]。
本例患者出現(xiàn)APTT延長,APTT糾正試驗(yàn)示PP和NPP 1∶1混合后即刻APTT和孵育2 h后的APTT均有所改善,但仍稍高于參考范圍,提示患者APTT糾正不徹底,不除外存在非時間和溫度依賴性的凝血抑制物可能。結(jié)合該患者術(shù)前于血液內(nèi)科門診檢測凝血因子活性(表1),結(jié)果示外源因子Ⅱ、V、Ⅶ活性正常,內(nèi)源因子Ⅸ、Ⅹ、Ⅺ、Ⅻ活性降低(Ⅻ活性最低,為14.3%),平行試驗(yàn)(即血漿梯度稀釋后再次檢測凝血因子活性,通常稀釋度越高受抗凝物干擾越小,然后取最大結(jié)果為最終因子活性)示內(nèi)源因子Ⅷ、Ⅸ、Ⅺ、Ⅻ活性有改善,更能證實(shí)存在凝血因子抑制物的猜測。因此下一步應(yīng)檢測抗磷脂抗體、LA、抗核抗體等直接驗(yàn)證。患者檢測結(jié)果提示β2GP1-IgG、ACL-IgG、LA均陽性,這些凝血因子抑制物的存在主要是增加血栓發(fā)生的風(fēng)險,而非出血風(fēng)險。王海疆等[2]回顧性分析了189例APTT單純延長的患者,發(fā)現(xiàn)大部分的單獨(dú)APTT延長并不導(dǎo)致出血,但有血栓傾向,其中凝血因子缺乏的患者僅占13.8%。因此對于APTT單獨(dú)延長的患者要謹(jǐn)慎使用新鮮冰凍血漿,不恰當(dāng)?shù)氖褂貌粌H會浪費(fèi)有限的資源,還會增加過敏、病毒轉(zhuǎn)播等輸血相關(guān)不良反應(yīng)的風(fēng)險。

表1 患者凝血因子活性檢測值(%)
二、警惕隱匿性失血(HBL)及其原因辨析
婦科手術(shù)患者如出現(xiàn)Hb下降,首先要考慮與手術(shù)相關(guān)的術(shù)野范圍內(nèi)出血。但本例患者除術(shù)后第1天明顯虛弱外,隨后一般情況良好,腹部平軟,無壓痛、反跳痛,不支持腹腔內(nèi)出血的表現(xiàn);同時陰道出血極少,也排除子宮出血的可能。然而患者Hb連續(xù)下降(術(shù)前140 g/L→術(shù)后第1天88 g/L→術(shù)后第3天61 g/L),故高度懷疑有隱匿性出血的部位或溶血性貧血的可能。在內(nèi)科協(xié)助會診下,完善血液相關(guān)檢查,網(wǎng)織紅細(xì)胞4.66%(>3%)提示骨髓紅細(xì)胞系增生旺盛,直接Coombs試驗(yàn)(+)說明紅細(xì)胞表面上包被有不完全抗體(比如IgG),需警惕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AIHA)的可能。但患者無黃疸、脾大等體征,肝功能結(jié)果未見直接膽紅素、總膽紅素升高,糞便潛血(-),不符合溶血性貧血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3]。完善盆腹腔CT+CTA后回報膀胱下方有一大小為7.5 cm×4.0 cm血腫,腹直肌前方存在片狀血腫區(qū)域,未見盆腔明顯積液及活動出血。結(jié)合雙側(cè)大陰唇可見范圍為4 cm×6 cm青紫色瘀斑,推測為術(shù)后初期盆腔術(shù)野包括腹直肌區(qū)域慢性滲血造成HBL,由于失血速度不快且相對局限,患者的外部體征并不明顯。
所謂HBL是指總的失血量(TBL)與可見的失血量(VBL),通常包括術(shù)中估算的出血量及術(shù)后引流量)的差值。盡管我們可以通過術(shù)中負(fù)壓吸引器的計量以及浸血紗墊的數(shù)量來估算術(shù)中出血,但低估失血量的情況臨床并不少見,尤其多見于子宮肌瘤剔除術(shù)和陰道分娩。除了人為低估的原因外,HBL還可能是由于:(1)術(shù)后應(yīng)激導(dǎo)致紅細(xì)胞破壞,造成溶血性貧血;(2)圍術(shù)期出血進(jìn)入機(jī)體的組織間室,如關(guān)節(jié)腔、組織間隙等[4]。Sehat等[5]通過對63位行全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的患者術(shù)中失血的統(tǒng)計,提出40%的HBL是由于溶血,大約60%是歸因于組織外滲。Ye等[6]對209例接受經(jīng)腹或腹腔鏡肌瘤剔除的患者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圍手術(shù)期VBL(經(jīng)腹手術(shù)137.81 ml;腹腔鏡手術(shù)104.43 ml)遠(yuǎn)小于估計的TBL(經(jīng)腹手術(shù)492.24 ml;腹腔鏡手術(shù)225.00 ml),經(jīng)腹手術(shù)的HBL(354.39 ml)約占TBL的71.52%,遠(yuǎn)高于腹腔鏡手術(shù)所估計的HBL(177.69 ml,占TBL 15.75%)。其中手術(shù)時間長、多發(fā)子宮肌瘤和肌壁間肌瘤是子宮肌瘤切除術(shù)中增加HBL的獨(dú)立危險因素。手術(shù)持續(xù)時間越長術(shù)中血液更可能進(jìn)入解剖第三間隙,難以引流;子宮多發(fā)肌瘤以及肌壁間肌瘤肌層受壓變薄、肌層收縮功能差、子宮修復(fù)不充分,進(jìn)而為術(shù)中以及術(shù)后的出血、滲血擴(kuò)大了可以浸潤的潛在空間。手術(shù)方式可影響手術(shù)出血,但并非增加HBL的獨(dú)立危險因素。
結(jié)合患者術(shù)前和術(shù)后紅細(xì)胞比容(Hct)采用Nadler公式和Gross公式,可以計算患者的估計血容量(EBV)和TBL,可用于評估 HBL。以本例患者為例,體重52 kg、身高164 cm,術(shù)前Hct 42.1%、術(shù)后第3天Hct 18.4%。Nadler公式:估計全身血容量EBV(L)=0.356 1×身高(m)+0.033 08×體重(kg)+ 0.183 3=0.356 1×1.64+0.033 08×52+0.183 3=2.88 L;Gross公式:TBL(L)=EBV(L)×(Hctpre-Hctpost)/Hctpre=1.621 L,總失血量超過全身血容量一半,與Hb水平是相符的。考慮到患者體內(nèi)存在隱性失血,起初還曾考慮過輸注血漿,但內(nèi)科會診認(rèn)為患者并非凝血因子缺乏,輸血漿意義不大。好在患者輸注紅細(xì)胞2 U后逐步出現(xiàn)Hb提升,也支持不再有活動性出血,且補(bǔ)充的鐵劑和造血系統(tǒng)逐步代償。后期雖間斷出現(xiàn)傷口滲血,超聲提示與腹腔積血塊相通,但不適合引流,亦無傷口裂開表現(xiàn),予局部理療的處理并觀察隨診。
通過本例患者的診治過程,我們對隱性失血有了深刻的認(rèn)識,加深了對術(shù)后血液常用指標(biāo)如Hb和Hct的理解,并鞏固擴(kuò)展了估算HBL的方法,更有助于臨床評估患者病情,制定適當(dāng)?shù)妮斠汉洼斞呗裕M(jìn)而改善患者術(shù)后康復(fù)。針對術(shù)中HBL,目前已有研究顯示術(shù)中使用氨甲環(huán)酸可以改善骨科患者的術(shù)后隱性失血[7],亦有研究指出對于既往無凝血因子異常而自發(fā)產(chǎn)生凝血因子抑制物的患者,除了快速止血以外,還可以通過去除抗體,如血漿置換、靜脈丙種球蛋白(IVIG)、糖皮質(zhì)激素、免疫抑制劑等方法糾正凝血功能[8]。盡管此患者術(shù)前評估無明顯出血風(fēng)險,術(shù)中過程亦相對平順,但術(shù)后確實(shí)出現(xiàn)了HBL等問題,提醒我們對合并凝血功能障礙的患者不能掉以輕心,術(shù)中止血應(yīng)盡可能確切,即便手術(shù)順利留置腹腔引流也是合理的,也許有利于更早發(fā)現(xiàn)內(nèi)出血;術(shù)后亦要關(guān)注患者的血液指標(biāo),APTT的延長絕非因凝血抑制物存在所導(dǎo)致的“假性延長”這么簡單,理論上的“高凝”或“低凝”還是要以臨床表現(xiàn)為核心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