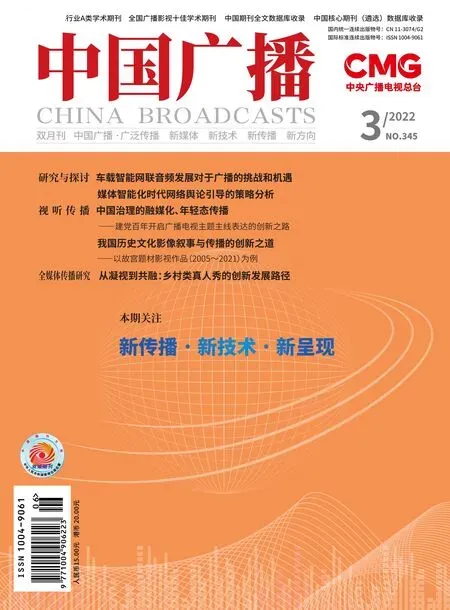我國歷史文化影像敘事與傳播的創新之道
——以故宮題材影視作品(2005~2021)為例
☉彭姝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長遠和根本之計在于增強文化自覺與認同。隨著一系列傳統文化主題節目的出圈,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然成為時下主流廣電內容創新與破局之路。故宮作為華夏大地綿延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與不朽成就之代表,經由影像媒介的數字化呈現,足以建構起民族國家的想象圖景,激發起民眾的文化認同、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
一、故宮文化的敘事表達變遷探析
考察21世紀以來我國拍攝的故宮題材影視作品,不難發現:從 2005年紀錄片《故宮》到 2012年微紀錄片《故宮 100——看見看不見的紫禁城》,再到 2016年 B 站上走紅的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敘事主題從對器物技術的刻畫走向關于規制習俗的闡述與精神價值的表達,敘事角度呈現由宏觀到微觀再到多元的變化態勢。
以表1 和表2 匯總的19 部故宮題材影視作品(以紀錄片為主,但敘事體裁逐漸多元化)為樣本,基于影像敘事的文本分析,可以勾勒出其大致的演變路徑。

表1:2005~2021年故宮題材影視作品匯總表

表2:各個主題作品數量和占比
(一)敘事內容:從宏大歷史主題到微觀多元視角
早期的故宮題材影視作品,主要解讀故宮建筑文物及宮廷歷史,往往主題先行,宣揚大國形象,配以深沉的解說詞,給人以“嚴肅說教”的刻板印象。此外,通常采用一維線性結構敘事,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連貫性及因果聯系。敘述時間與故事時間基本重合,以自然的時間流向講述歷史故事本身,不同片段之間由若干條敘事線索串聯以表達同一主題。

表3:各個主題作品首播時間分布
近年來熱播的故宮題材影視作品則不再拘泥于器物技術的呈現,而開始聚焦微觀層面的影像化表達。無論是詮釋匠人精神的《我在故宮修文物》,還是文化探訪類節目《故宮賀歲》,都更加關注微觀個體和真實生活,體現人文關懷。以《我在故宮修文物》為例,該片采用平民化的多視角敘事,將文物修復者們的工作與生活娓娓道來,在不加粉飾的同期聲之外輔之以平易近人的畫外音解說,從而淡化了作品與觀眾之間的疏離感。而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故宮里的大怪獸之洞光寶石的秘密》作為首部“真人+CG(Computer Graphics)”青少超級劇,賦予故宮屋檐、欄桿與壁畫上形形色色的怪獸雕像以生命,以孩童的視角講述一段關于傳統文化的奇幻冒險之旅,寓教于樂,潤物無聲地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二)敘事手法:從閉合式宣講到開放式表意
囿于早前影像資源的匱乏,影視作品往往采用“搬演”手法和全知視角,借助視覺化技術手段,重構并解讀已逝的歷史場景,以增強影像敘事效果。無論是影像內容,還是鏡頭的運動、畫面的使用等形式方面,都呈現出一種宏大而又沉重的宣講式風格。近年來的故宮題材影視作品則轉向多元復合視角交叉敘事,敘事節奏變幻多端、富有表現力,且畫面中每一幀都力求精致細膩。作品通過紀實當下的日常生活場景,更加關注當代人的生存狀態、真實的社會生活及社會心理,以揭示更深層次的結構關系及其意義。
以同是文物修復主題的《我在故宮修文物》和《故宮新事》為例,二者均采用內外結合視角介紹故事背景并隨敘事演進進行解說,兼具親歷性和客觀超然,由此再現文物修復師們工作、生活的本真模樣。《我在故宮修文物》是將不同修復組的文物修復工作片段拼貼在一起,這些碎片化的內容共同展現了中國匠人的技藝傳承脈絡,詮釋了當代社會“執著專注、精益求精、一絲不茍、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同樣的,不同于早期故宮題材紀錄片自始至終采用同一節奏敘事的傳統,在《故宮新事》第一集《文物搬家》中,養心殿文物搬出宮墻這一情節的剪輯節奏和轉場速度明顯快于文物修復與古建勘測、修繕等情節,這種動靜場景鮮明的對比在凸顯修復師和設計師們細致認真的工作態度及狀態、傳統文化與都市生活之間的節奏差異的同時,也增強了敘事表現力和張力,可謂是一個較為顯著的改進。
(三)敘事時空:從線性串聯到并列交錯
早期的故宮題材影視作品傾向于依照時間順序完整敘述故事的起因、經過、發展和結果各要素,以人物的場景移動為主線,將不同空間串聯起來,充分體現了其線性敘事特征,同時通過重復敘事引起觀眾對某一情節的重視,從而突出作品所要表達的內涵。
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當前故宮影像的敘事往往打破時間序列模式,轉而將長鏡頭的運用與鏡頭視角的不斷切換,平行交錯講述不同人物情境,在流變的圖景中瓦解不同受眾之間地域、時空與文化的邊界,孕育出更多的外延之義。如,《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分為中西方藝術兩大板塊,分別將其代表人物和藝術風格零散拼貼在一起,以表達中西方文化碰撞的主題。微紀錄片《故宮100》則呈現出更為鮮明的碎片化特征,每6 分鐘一集,每一集講述單一器物或建筑,共制作了100 集,彼此零散又有機結合,其后現代主義結構恰恰反映了當前視聽媒介的發展趨勢和受眾媒介接觸行為的變化。
為紀念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紀錄片《我在故宮六百年》(《我在故宮修文物》姊妹篇)于2020年12月31日開播。該片聚焦于古建修繕保護與修繕技藝傳承,通過故宮匠人的工作視角,穿梭于故宮磚瓦梁枋之間,講述了故宮六百年的歷史坐標、歲月記憶與人文情懷。同為講述六百年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厚重歷史的《紫禁城》于2021年10月22日開播。該片以講述人的在場講述貫穿始終,以歷史進程中諸多拐點性事件為切入點,將宏大敘事置于豐滿的歷史細節之中,搭建起歷史與當下的對話,以史為鑒,知興替、明得失,構成跨越時空的對望與反思。
二、故宮影像建構的文化景觀剖析
法國思想家、導演居伊·德波(Guy Debord)認為:“景觀不是影像的聚積,而是以影像為中介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故宮作為一個動態的永不止息的生命系統,其建筑、藏品、歷史、文創、匠人乃至宮廷御貓、四季美景等等,都蘊藏著中華民族的滄桑歷史,更在幾經蟬蛻、幾度新生之后依舊延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與價值體系。
(一)基于闡釋學意義的故宮話語互動
從闡釋學的角度分析,傳播者與載體、受眾與載體之間的循環互動,共同建構起作為主體的傳受雙方彼此關聯的理解話語。而影像作為符號化建構的視覺性載體,既指向傳者的價值觀念,同時也表征著受者的思維方式。
故宮題材影視作品的核心敘事對象是故宮,關于故宮這一生命體,傳受雙方均存在許多前見和前理解,盡管受主體間性影響,但基本處于共通的意義空間。故宮文化要素紛繁璀璨、琳瑯滿目,傳受雙方最初從宏觀和整體上對其進行完滿性前把握。基于此等語境,傳者進一步縱橫拓展闡釋其內在意義與超越意義,故而早期的故宮題材影視作品總是基于宏觀敘事與整體傳播。然而受眾對于作品的意義表達始終有著自己的接受期待,其預期一定程度上則會反過來影響作品的呈現。
如圖1所示,受眾對于我國2005~2021年間故宮題材紀錄片的表達基本趨于滿意,17 部紀錄片作品豆瓣平均分為 8.4 分(滿分 10 分)。由此可以管窺當前我國故宮題材影視策略基本符合受眾預期,且呈現穩步提升的發展趨勢。在現有政治、文化、技術等社會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故宮背后的生命個體逐漸走上前臺,與其他文化要素相互動、演繹,故宮題材影視作品被賦予了更多與時俱進的內涵與外延,敘事角度經歷了從宏觀到微觀再到多元的嬗變。

圖1 :2005-2021年故宮題材紀錄片作品豆瓣評分
作為歷史文化呈現的載體,故宮題材的影像在傳者編碼與受者解碼的動態過程中獲取意義與價值。作品呈現出來的意義建構了受眾的歷史文化“前”認同,受眾的歷史文化期許則影響著載體進一步呈現的內容與形式。傳受雙方與載體之間的意義互動與博弈循環往復,共同推進故宮題材影視敘事與傳播的發展與進步。
(二)基于傳播效果的故宮文化景觀
文化是依賴于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集體經驗。作為視覺符號文化的一種,故宮影像記錄著國家和民族的記憶與榮光,建構起民族對于歷史文化的瑰麗想象。影像和傳播技術、受眾需求等諸多要素合力締造了故宮文化景觀,而傳播媒介及渠道之寬、口碑形成之快與效度之強則使之更易形成。
一方面,在認知層面,故宮文化重塑受眾的知識儲備與認知結構。如《上新了·故宮》將故宮未曾開放的區域展現給觀眾,第一季中倦勤齋等建筑的展演,即為觀眾刻畫了一個更為充實飽滿的帝王形象。另一方面,在價值形成維護與社會行為層面,故宮文化所書寫的歷史記憶喚醒了受眾之間相似的文脈基因,基于“我們”的話語與行為形塑區隔于他者的集體記憶,維系族群認同,使受眾產生“此生無悔入華夏”的情感共鳴,也促進了個體對于自我行為的反思。從“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里去”的深入思考,觀眾從個人的文化認同走向群體的文化自覺。
值得一提的是,精神價值層面的故宮文化傳播更是在故宮這一中介化的媒介實踐空間中,時空交錯、人際穿越,構成一種特有的文化景觀。現代著裝的專家與工匠在古老的宮殿里,運用現代化的技術設備修復著神秘的朱墻金瓦,他們是生活在古代景觀中的現代人;墻外喧囂熱鬧,墻內寂靜安然,修繕師們樸素而認真地勞作、生活著,他們也是生活在都市景觀中的田園人。一墻之隔,卻營造出一種盤互交錯的時空與交融的文化景觀。古建文物修復之路亦是歷史文化傳承之徑。當故宮由皇室禁地走向煙火人間,古殿角樓被架起了腳手架,紫禁城的各種遙不可及與風起云涌在此間交匯,帝王將相的神話逐漸消解黯淡,而普通卻非凡的故宮守護者的故事將一直延續和流傳著。故宮不只是歷史人文的見證者,也是歷史人文的書寫者。
三、對歷史文化影像發展的思考
歷史文化影像指以影像形態記錄和表達歷史、文物與人文景觀,從而折射出當代人對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深刻認識與反思,并反映社會價值體系的藝術呈現方式。故宮作為舉世公認的“中國符號”和“中國智慧”,其影視創作在我國歷史文化影像創作中占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縱觀 2005~2021年間故宮題材影像的敘事變遷及其建構的文化景觀,可得出如下啟發。
其一,要注重集體記憶的建構,避免陷入“只記錄而不記憶”的窠臼。互聯網時代的海量數據,容易將人們湮沒于碎片化的信息與虛擬的空間之中,滯留在眾聲喧嘩與集體狂歡后的淺層與外在表面,而無法內化為個人認知與價值。作為建構與維系集體記憶的重要實踐主體,紀錄片創作應講述故事,加諸用以展演的情境與共振傳播的儀式秩序,從而跨越圈層和地域引發共情、產生理解,最后固化體認。其二,講好中國文化故事以弱化“他者敘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依舊面臨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話語權逆差”,提高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力、講好中國故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盡管跨文化交流“文化折扣”現象難以避免,仍應在認知差異中尋找對話的可能。其三,要警惕大眾文化消費主義,同時規避模式化、同質化生產的風險。隨著商業化的滲透,當前歷史文化影像愈發強調技術和娛樂。誠如著名傳媒人陳虻所言,“電視紀錄片要利用觀眾的感性到場,達到理性到場”,回歸日常、關照現實,以啟迪觀眾透過真實而自然的客觀物象進入問題核心、思考其思想內涵,最終和社會、時代、民族命運發生關聯。作為擁有三項世界級文化資源的故宮,理應為增進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自覺認同、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貢獻一份力量。而這也必然成為我國歷史文化影像發展的初衷和歸宿。
注釋
①《習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 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央視網,2021年8月28日,https://news.cctv.com/2021/08/28/ARTIFX9D3d4wpP8BPT3X0EeZ210828.shtml?spm=C96370.PPDB2vhvSivD.E0O8qNryTckW.3.
②劉泳:《講好中國故事:故宮題材紀錄片的敘事演化研究》,湖南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③翟春陽:《讓工匠精神深入人心》,《人民日報》,2020年12月25日。
④〔法〕居伊·德波(Guy Debord):《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 頁。
⑤費孝通:《鄉土中國》,青島出版社,2019年版,第31 頁。
⑥歐陽宏生:《紀錄片概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3 頁。
⑦胡百精:《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年第3 期。
⑧徐泓:《不要因為走得太遠而忘記為什么出發:陳虻,我們聽你講(收藏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