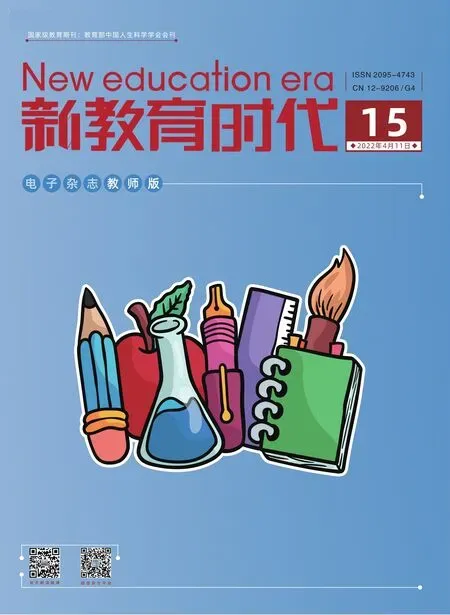雙語幼兒園的學前雙語教育探究:超語視角*
柯 藍
(廣東石油化工學院 廣東茂名 525000)
一、研究背景
超語實踐(Translanguaging)作為一個新興概念,自 2010 年穩步快速發展[4],眾多學者探究并應用了這個概念[1-5],特別是在外語教學領域。超語最初的含義特指一種雙語教學法,目的是通過使用第一語言來加強對目標語言的理解。隨著這個概念引介至英語世界后,超語實踐引起了學界的興趣。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其定義擴展為通過使用兩種語言來創造意義、塑造經驗、理解和獲得知識的過程。李嵬等學者進一步充實了這個概念。他們認為,雙語者所使用的語言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語言系統,而是高度異質化的,基于個人經歷的,動態的符號系統。在這個系統中,隨著場景、對話對象等外在因素不同,雙語者會調用其自身不同的符號資源。雖然不同學者對超語實踐的定義有所不同,但其涉及多語言,多模態的特征是共通的,并且相比起語碼轉換等相近的概念,超語實踐關注的是說話者的語料庫(repertoire),而不是特定語言的結構,這就使其具有很強的目標導向性,非常適合應用于外語學習效能分析。
二、研究概況
研究分為兩個部分:教學觀察(peer observation)和訪談。其中教學觀察時長為一節課(20分鐘),觀察對象為幼兒園某大班的外語教學。訪談為第二部分,于課堂教學觀察結束后開始,訪談對象為該班級配備的三位教師,訪談對象的基本情況見表一。

表一 訪談對象情況表
訪談并不考查教師本身的知識結構和語言能力等客觀因素,而是圍繞語言教師信念(language teachers’ beliefs)這一概念設計問題。這是因為和語言能力等客觀知識不同,信念基于教師的個人經驗和主觀體驗,它能影響教師對新知識的理解,繼而決定是否接受新的理念[9]。有學者認為信念是教師對過去記憶的描述,它能調整教師對事件的理解。在授課方式、授課進度等計劃的制定上,教師的信念比教師的知識有更大的影響。可以說,教師信念即教師教學上的行動指南。訪談問題主要圍繞以下幾類:語言態度認知,如教師對母語和外語使用的態度;語言管理,如課堂語言使用規則和課外語言使用規則;學情分析,如學生的年齡,語言能力,學習態度等;課程內容,如教材選用,教學進度以及教學目的等;以及外部因素,如家園共建進度推進,家長反饋,園內軟硬件建設等。
三、結果與分析
訪談分析后發現在學前教育層次的雙語教學中存在著兩個較為典型的特征:偏好基于單語制的教學模式;教師的信念及其教學實踐之間存在著系統的不一致。
1.偏好基于單語制的外語教學
國內雙語幼兒園總體上存在著三種雙語教育模式,即基于漢語的英語教學,全英語教學和沉浸式英語教學(immersive teaching,也譯作浸入式英語教學)[2]。其中前兩者都是基于行為主義原理,透過模仿和練習形成語言習慣,兩者在教學方法上多有相似。浸入式教學則在英語教學的基礎上,更強調環境的創設,教學目標也不局限于幼兒對英語的習得,更為強調培養幼兒對語言本身的興趣。在本次研究中,我們發現受訪教師都表達了對沉浸式教學的認可,他們認為沉浸式教學是該雙語幼兒園的組織開展學習活動的主要形式以及對外宣傳的一大賣點:
教師-A:“(我們幼兒園的)雙語課程都有特定主題的,我們用的是市面上最主流的英語教學材料和兒童教育節目……小孩子會在互動中學習到很多英語單詞和表達。”
教師-B:“上課都是說英語為主的,有時候是外教教英文,我們維持秩序,有時候是我們(中國教師)教孩子英文。”
這種認知這也符合國內雙語幼兒園的教育偏好以及家長對孩子學習外語的迫切需求。沉浸式教育發軔于上世紀60年代加拿大的法語教學項目。在這個項目中,教師使用法語作為唯一教學媒介,并最大程度避免母語英語的使用[7]。但這種以目標語為唯一教學媒介的教學方式在學界有著較大的爭議,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普遍認為外語學習中,母語時常起到阻礙作用,應該予以避免。而對此持懷疑態度的學者則批評這種基于單語制的教學法完全無視了第一語言的作用[6]。
這種對純英語環境的追求,在國內外都有著一定的市場。一方面,沉浸式的外語教育透過創造環境,使得兒童可以在學習過程中進行觀察、觸摸,繼而把所見所感和目標語言聯系起來,這對于認知程度還比較淺的學前兒童而言尤為直觀有效。另一方面,有學者研究指出,人們對雙語教學還存在一定的誤區,對于超語實踐的不信任在單語家庭里尤為明顯。在外語教學過程中使用第一語言,被認為是語言能力不夠發達的表現;有些家長還擔心學習外語時候會面臨母語的負轉移;此外,相當多的人認為,外語學習過程中,兩種語言交替混合使用會產生互相競爭的效果,導致學生產生混亂。此外,源自西方的OLON(OneLanguageOnly)和OLAT(One Language at a Time)語言教學思潮在我國外語教學中也有著深遠的影響,這些觀點指向的是在一個場合應該只用一種語言,具體到外語教學則是只能使用目標語。這些觀點都影響著雙語教師的教學信念,使之朝著純粹化,一語化的方向演變,同時對母語的使用產生的一定程度的偏見和污名化。
2.教師信念和教學實踐不一致
除了偏好單語教育外,本次研究還發現,囿于條件所限,受訪者對教師信念和其教學實踐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偏差,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對語言管理存在認知和實踐的偏差;以及對外語教學目標存在認知和實踐的偏差。
如上文所述,受訪教師對于幼兒園的外語教育的語言管理認知是“純英語”+“沉浸式”教學模式,其中前者保證了語言輸入的純度的強度,后者為語言學習創設了適合學前兒童的環境,但是從教學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實際教學實踐中,教師采取的是多模態雙語混合式的超語實踐,如以下的場景:
外教-C:“Can you raise up your left hands?”
外教-C:(舉起左手的動作)
教師-B:“Left hands!左手!”
學生:(舉起手)
限于學前兒童年齡小,我們無法直接透過測試方式對其語言能力進行量化,但就課堂上的教學觀察而言,學生在外教課堂指令下達后有著數秒的靜默期。在后續的教學觀察中,研究發現這種零反饋并不基于個人,中國教師下達英文指令同樣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因此教學過程中,教師往往需要在英文指令下達后配上相應的中文關鍵詞翻譯,以及其他的非語言元素,如手勢和圖片等,以便達到刺激-反應的教學效果。因此在語言管理層面,教師認為的“純英語沉浸式”教學,更多的時候是以多模態的雙語教學形式呈現的。
這并不是說受訪者并未系統思考過課堂語言管理。事實上,受訪教師都意識到了學前外語教育中的多語言,多模態特征,但兩種語言的使用比例并不均衡。在20分鐘的教學觀察中,漢語的使用總是極其有限,并且層次相對單一,只有一些詞匯,無句子。并且總是作為關鍵詞翻譯的形式出現。而與之相對的英語無論從時長,還是語言機構的層次來說都更加豐富,既有詞匯、短語,也有完整的句子。所以他們在評估教學效果時候往往把外語學習效果歸功于英語媒介的高頻率、高強度、高純度使用。然而,實際上并非如此,漢語的使用雖然在頻率和復雜度上不如英語,但就教學觀察的結果而言,漢語往往在兒童理解特定概念的關鍵節點起作用,特別是學前教育中,對話主題往往必須補充相應的漢語翻譯、解釋,或圖片、手勢、語氣和姿態等。純粹使用外語不能使兒童充分理解對話含義。學前教育中兒童年紀小,理解能力有限,外語教學又存在著“語言習得”+“知識/技能獲取”雙重任務,因此母語在兒童的學習過程中承擔著腳手架的作用,透過母語的支持,學習者能夠有效擴展學習半徑,縮短其潛在發展層次和實際發展層次的距離。
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所說的教師在信念和實踐層面存在偏差,并不意味著教學過程就一定出現了紕漏,更不意味著教學效果就一定會受到影響。雖然教師信念和教師實踐的關系是互動的[8],即信念指引行動,而在行動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和反思也會反過來塑造信念,但兩者的關系并不是線性的。有學者[9]就提出了教師信念中存在著兩組子類,一個是信奉的理論(espoused theories),另一組是使用的理論(theories-in-use)。前者獨立于教師個人教學經歷,形成于教師學習過程,通常也是為教師心中的最理想的應然狀態。后者則源自于教師在工作中的實踐,受教學條件、教師稟賦等外在因素影響,通常為工作中的實然狀態。就本次研究而言,受訪教師信奉的理論更多是基于單語制下的英語教學。一方面,沉浸式教學法在國內一直有著比較高的認可度,英語專業學生在求學過程中,英語教師在工作時都會接觸到此類觀點,另一方面,單語制教學也是社會需求的投射,當家長對孩子學習外語的需求愈發迫切的今天,幼兒園也面臨著教育小學化的壓力,而高強度、高純度的外語環境則是這種變化的其中一環。因此許多外語教師都認為單語教學是最優解,即使在教學過程中使用了母語,也未必有意識地、系統地思考其作用。
結語
相比起基于行為主義的傳統外語教學,沉浸式教學更強調語言環境和主題的創設,和語言媒介的純粹性,因此備受教學機構青睞。但語言習得,特別是二語習得,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除了受學習環境影響外,還受制于學習者本身語言能力、天賦、性格以及學習策略等因素。這種高度異質化的經歷使得每個語言學習者都有獨特的語言學習體驗和需求,再加上學前外語教育中兒童的低齡和心智未成熟等因素,這就要求雙語教育機構在制定外語教學策略時更應考量周全,摒棄形式主義,把教學重心回歸到學習效果的評估上。學前兒童的認知能力尚未發育完全,也無法像成年人一般建構起高效的學習策略,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會出現注意力較短,依賴非語言模態等特征。比起教學中的語言管理,語言媒介是否“純粹”,教育機構更應考察的是學習者是否適應該環境,是否在這種學習模式下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們在設計教學方案時,不要拘泥于外在的形式,限制教師和兒童使用母語,更要積極利用其母語的優勢,并且加入視頻、音頻等多模態元素以及手勢、動作和圖案等非語言元素,把語言習得的渠道盡可能綜合化,把外語教學從外在的條框中解放出來,使得教學真正做到以人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