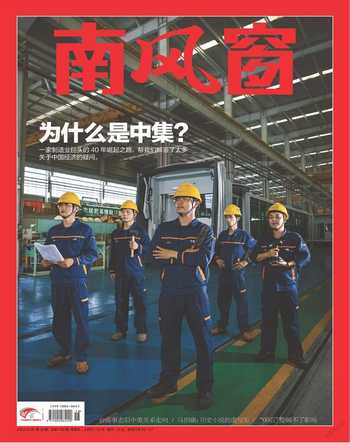在最底層讀哲學
陳直
1958年,鄧曉芒先生剛滿10歲,他時任《湖南日報》社長的父親鄧鈞洪被打成“右派”,母親因為不肯和父親劃清界限也被劃為“右派”。于是,他們一家墜入了社會底層。
到了1964年,16歲的鄧曉芒初中畢業,因為政治原因,無法升學。他“下放農村”,成為一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一兩百斤的擔子壓到肩上”。4年后,1968年,他開始認真讀書。直到他在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這10年間大約都是在底層讀哲學。
這期間,1974年鄧曉芒回到長沙后,他白天在郊區做挑土的臨時工,晚上回家看書。在做了兩年挑土臨時工之后,鄧曉芒被招到水電安裝公司做一名搬運工。與此同時,鄧曉芒的妹妹,被譽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的殘雪(鄧小華)也有類似的經歷。“1970年殘雪進入一家街道工廠工作,做過銑工、裝配工、車工。”后來殘雪做起了裁縫。
上面這些故事,我在很多年前開始了解,那時我也正在社會最底層“讀哲學”。歷史不斷在重復自己。我母親一直希望我不會重復她的艱辛人生,然而我卻重復了上幾代人同樣的“命運”。我也同樣重復了鄧曉芒先生前期的一些經歷。
從2010年開始,我在兩班倒(白班12小時,夜班12小時,一個月或半個月輪一次)的工廠里持續地工作著。上班時間長達12小時,下班后很難說有多少時間來“讀哲學”。不過,我一直以來都把上班當作次要的事情,如鄧曉芒先生說的那樣:“回城做臨時工,當搬運工,我覺得那都是維持生活的手段。我主要關心的是哲學,不光哲學,那時沒有界限,就是思想,文史哲不分家,這些都關心,最關心的是哲學、方法論。”
不過,鄧曉芒是“回城做臨時工”,我卻是“進城做臨時工”。“進城”幾乎是那個時候農村年輕人的唯一選擇。我所在的農村,幾乎沒有正式的工作機會。我所在的江西省贛州市,山多田少,人均耕地不足0.7畝,而且耕作條件差。因此在家里種地是最沒有希望的選擇,幾乎沒有年輕人會選擇。即便我想選擇在家種地,我也沒有選擇的條件,因此我只能進城打工。
記得剛開始時,每天辛苦工作12個小時,一個月幾乎不放假,但工資卻依然只有2000多元。(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最底層的工資也沒有增加多少,比如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是2300元。在工廠里做最底層員工,就是按這個標準來發工資。)
那時,我并不特別在意有多少工資,哲學依然幾乎是我生命的全部。雖然有時我會對在這樣的處境下讀哲學感到有些悲哀,但那時我相信,“處境”對于哲學來說是不相關的,在任何條件處境下,哲學依然不會變化其真理性。因此我也不在意那樣的艱難處境,盡管我經常感到自己“沒時間”。
我那時把哲學當作我的“事業”,還是如鄧曉芒先生說的那樣,“哪怕沒有高考、沒有考研這一套東西,我還是會一直學習下去,那是我一輩子關心的事情。后來我當搬運,純屬是為這個服務的。那時搬運三級工,維持生活夠了,解決了我糊口的問題。然后就是精神上面的一些探討和享受,如果沒有高考的話,打算就這樣一輩子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卻沒有鄧曉芒先生那樣的“精神享受”,相反我越來越感到來自日常世界的壓力,“無家可歸”的處境越來越讓我感到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