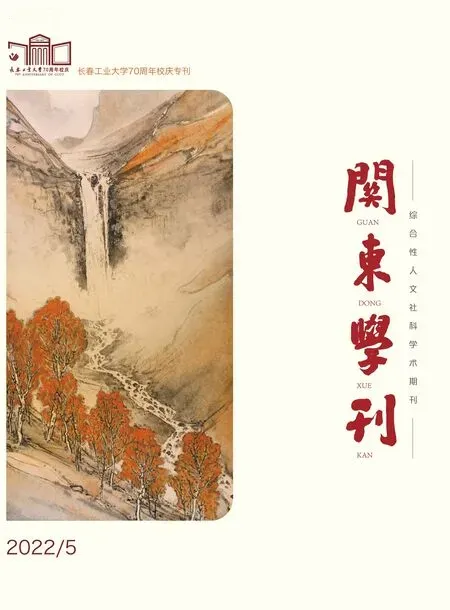超大型自貿協定背景下對典型區域內貿易關系的再審視
高 鶴
前言
一、歐盟區域內貿易關系
(一)歐盟一體化進程簡介
為更好地分析歐盟區域內貿易的變化情況,梳理歐盟一體化的進程非常必要。這便于考察成員國數量的不斷增加、一體化程度的加深等因素以及一些重要時間節點的事件可能對內部貿易帶來的影響。
如表1所示,20世紀50年代,由當時的西德、意大利、法國、盧森堡、比利時及荷蘭6國共同簽署系列條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相繼成立。60年代成立了歐洲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上述三個共同體統一為歐共體;80年代,歐共體12國達成了單一市場構想,于1992年簽訂了《歐洲聯盟條約》(也稱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歐盟(EU)的成立實現了深刻的發展性變化。1998年,歐洲中央銀行(ECB)成立,1999年歐元作為結算貨幣導入,從2002年開始,歐元紙幣和硬幣開始流通。

表1 歐盟(EU)一體化變遷簡表

表1 歐盟(EU)一體化變遷簡表(續)
歐盟以經濟、貨幣同盟和政治同盟為中心,加強了歐洲地區的統一,同時成員國也在不斷擴大。成員國數量由歐盟成立初的12個擴大到1995年的15個,2004年東擴至25個,2007年再入兩國,2013年為28個。直至2020年1月末英國脫離后,至今為27個成員國。正式參加歐元區的國家也從1999年的11個開始逐漸增加,2015年達到19個,至今數量未變。
(二)歐盟區域內貿易關系動態
1.歐盟區域內貨物貿易情況分析。

表2 1988-2020年歐盟和歐元區各自區域內以及對中美兩國貨物貿易的占比情況 單位:%

表2 1988-2020年歐盟和歐元區各自區域內以及對中美兩國貨物貿易的占比情況(續) 單位:%
觀察表2內的計算結果,可以總結以下幾點:
(1)歐盟和歐元區的區域內貿易份額整體上非常高且較為穩定。從五個細化分析對象的計算結果看,三十多年來,除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個別年份,歐盟(EU、EU28和EU27)內部貿易基本都占6成以上,歐元區(Euro和Euro19)也保持著5成左右的份額。以2013年前的歐盟28與動態歐盟的內部貿易比重相比,同時以2015年前的歐元區19與動態歐元區的內部貿易比重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時間結點前歐盟28的內部貿易份額始終高于動態歐盟的內部貿易份額,同樣地,歐元區19的內部貿易比重也一直高于動態歐元區的內部貿易比重。也就是說,在固定成員國的前提下,相當于擴大了的歐盟和擴大了的歐元區,各自區域內貿易份額均有提高,但各自的差距隨著成員國的增加逐漸變小。
(2)動態歐盟和動態歐元區的內部貿易份額均有下降趨勢。隨著歐盟成員范圍的擴大,區域內貿易份額整體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在上升階段內突出的特點是,在新成員加盟時間點或之后短期內的區域內貿易份額有比較顯著的提高。1995年,成員國數量從12個增加到15個,1995年的區域內貿易比重為63.6%,而1994年的區域內貿易比重為57.9%,陡然提高了5.7個百分點,而且比之前的年份占比都要高;2004年歐盟進一步東擴,25個成員國的區域內貿易份額上升到了64.8%,比上一年提高了3.4個百分點且超過之前所有年份的比重,此后連續提高;到2007年,歐盟囊括了27個成員國,當年的內部貿易比重達到了歷史最高值66.1%。2008年以來開始呈現略有下降的趨勢,期間起伏不定,2012年降到61.5%,比2007年減少了4.6個百分點。但2013年吸納了克羅地亞后,區域內貿易份額逆勢出現連續四年的增加后才又開始下降。英國正式脫歐的2020年,區域內貿易比重下降較為明顯,較2019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僅為61.0%,更是2004年以來內部貿易比重的最低值。相比而言,自1999年以來,動態歐元區的區域內貿易份額呈現的是整體下降的態勢,新成員加盟時間點的內部貿易比重也鮮有上升的情況出現。
(3)如圖1所示,以固定數量國家為對象的歐盟28、歐盟27和歐元區19的區域內貿易變化情況同中存異。三者基本都在2004年到2012年期間出現下降,降幅在3.9~5.8個百分點,但歐盟28和歐盟27的區域內貿易份額從2012年到2019年恢復了大約2個百分點左右,而歐元區19的內部貿易比重變化不明顯。EU28的內部貿易份額一直高于英國除外的EU27的內部貿易份額,但兩者的差距越來越小。尤其是,英國脫歐的2020年,EU27內部貿易比重未降反升,這些表明英國在歐盟內部貿易中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圖1 1988-2020年歐盟和歐元區對其各自區域內貨物貿易的占比情況(單位:%)
(4)動態歐盟與中美兩國的對外貿易份額變化顯著。從歐盟對外貿易的比重來看,歐盟對美國的貿易份額由2000年前后的8%下降到2010年前后的5%,2014年以后恢復到6%以上;另一方面,歐盟對中國的貿易份額雖然一直低于對美國的貿易份額,但有長期上升的趨勢。從20世紀90年代初不足1.0%到后期的1.5%,到2010年,上升到5.0%,與美國的份額接近。2015年以后上升顯著,2020年已經達到6.3%,甚至超過了歐盟對美國的貿易比重6.1%。受美國次貸危機蔓延引發全球經濟下滑的影響,2010年前后的幾年里,歐洲經濟的增長率相對較低,但中國經濟的增長率相對較高,在世界貿易中的市場占有率擴大,這些因素影響到了歐盟區域內貿易的份額。
2.歐盟區域內服務貿易情況分析。
如果從服務貿易方面看,EU28和EU27的內部貿易份額和對中、美兩國的貿易份額整體上相當穩定,見圖2所示。

圖2 2010-2019年EU對其各自區域內以及對中美兩國服務貿易的占比情況(單位:%)
2010年以來,EU28的內部占比為54.9-57.9%,EU27的內部比重為46.0-49.4%,如果以每一年作為時間點進行比較,EU28比EU27的內部比重最少高出7個百分點。從對外貿易占比上,無論是EU28還是EU27,對美國的貿易占比都在10%以上,遠遠高于對中國2%左右的對外貿易占比。另外,就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占比,EU28與EU27相差很小,也就是0.1個百分點,但是對美國而言,兩者相差1個百分點以上,詳見表3。可見,英國在EU內部服務貿易的份額上影響較大,在對外服務貿易占比上對美國的依賴強于對中國的依賴。

表3 2010-2019年EU28和EU27對其各自區域內以及對中、美兩國服務貿易的占比情況 單位:%
綜上,從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兩個方面的內部貿易份額情況來看,隨著歐盟一體化水平的提升,其內部貿易關系并沒有因此發生顯著變化。其中,貨物貿易的變化比服務貿易稍明顯一些,但總體平穩,只是略有波動。
二、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墨加自貿區)區域內貿易關系
(一)北美自貿區(美墨加自貿區)一體化簡史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前身是美加自由貿易協定(USCFTA)。1985年,加拿大向美國提議FTA并開始談判,直至1989年USCFTA生效。1990年,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達成FTA意向協議,談判于1991年開始,1992年10月簽署NAFTA后,1994年1月生效。在此期間,由于美國國內工會反對墨西哥的低工資和低勞動基準,認為他們剝奪了美國勞動者的就業機會,從1993年8月開始,雙方就勞動和環境等方面進行了補充協議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北美勞動合作協定(NAALC)和北美環境合作協定(NAAEC)兩個補充協議于1994年1月與NAFTA同時生效,并且NAALC要求各國努力促進其國內勞動法、規則的有效執行。
2016年,特朗普作為當時美國總統候選人,選舉活動期間多次抨擊NAFTA“是美國迄今為止簽署的最差的貿易協定”。在其當選總統后便宣告NAFTA要進行再談判甚至要脫離NAFTA。2017年1月特朗普政權誕生后,同年8月開始以美國為主導的NAFTA再談判,最終于2018年11月《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更名簽字,于2020年7月生效,如表4所示。

表4 NAFTA-USMCA變遷簡表
NAFTA及其后繼的USMCA,在一些方面與歐盟和歐元區有所不同。首先,加盟國的數量上存在巨大差距,無論是組建初期還是2020年開始的歐盟27國,亦或是歐元區,NAFTA(USMCA)與之相比,成員國數量都遠遠少于前者。其次,加盟國的數量動態不同。NAFTA及其后繼的USMCA的成員國始終是美、墨、加3個國家,而EU加盟國的數量則經歷了數次增加的過程以及英國脫歐,從6個最終變為27個,詳見表1。再次,加盟國間的經濟體量對比相差程度不同。現在的USMCA內,美國是經濟大國,而且是世界頭號經濟體,其他兩個國家與之相差懸殊;而歐盟成員國中,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是相對較大的經濟體,但與其他成員國相比,差距不如前者那么明顯。例如,2019年,美國占NAFTA三國名義GDP總和的88%,占對外貿易總額的70%,而德國僅占歐盟27國名義GDP總和的25%,對外貿易總額的24%,占歐元區19國名義GDP總和以及對外貿易總額的29%,這意味著美國的貿易動向將強烈影響整個自貿區的貿易情況。這一點在具體計算中得以體現,詳見表5。

表5 1990-2019年NAFTA區域內以及與中國對外貨物貿易占比 單位:%
(二)NAFTA-USMCA內部貿易關系動態
在統計上不同于歐盟和東盟的是,因缺乏將NAFTA作為一個整體的內部貿易和外部貿易的系列統計數據,考慮到可能因重復計算導致不準確的情況,本文主要計算單個經濟體對域內貿易的占比情況以及與個別國家的對外貿易占比情況,依此總結NAFTA區域內貿易的特點。
2.美、墨、加三國面向區域內的貿易額占各自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差異較大。1990年以來的30年里,墨西哥和加拿大對區域內部貿易的比重遠遠高于美國對區域內貿易的比重。1992-2001年,墨西哥的對內貿易占比高于加拿大的對內貿易占比,期間墨西哥連續數年的占比都高達80%以上。除此以外的時間點,加拿大的對內貿易占比處于最高水平,最低也在65.0%以上。而美國面向區域內貿易的份額最高只接近于33.0%,絕大部分在30.0%以下。
3.三個成員國對域內貿易的對象分布集中度高。墨西哥和加拿大對NAFTA區域內貿易的份額絕大部分是來自美國。從表5內的計算結果可見,墨西哥和加拿大對美國的貿易份額與各自對域內貿易的總份額相差很小。長期以來,加拿大對墨西哥的貿易份額以及墨西哥對加拿大的貿易份額基本在1%-4%的范圍內。但從2000年開始,墨、加兩國對美國的貿易占比有所下降,且彼此越發接近。與此相對的,美國對NAFTA區域內貿易份額中,則主要來自與加拿大的貿易往來。但隨著時間推移,美國分別與墨、加的貿易比重差距不斷縮小。20世紀90年代,美國與加拿大的貿易占比要明顯高于對墨西哥的貿易占比,但隨后前者逐漸下降。2015年以來,美國與墨西哥的貿易比重較之前有所提高,與之對加拿大的貿易比重越發接近,均為14%-15%,2019年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對外貿易占比均為14.7%,達到了持平的狀態。
4.三個成員國對區域內的貿易份額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20世紀90年代,三個成員國對區域內貿易的份額都在上升。墨西哥從1991年的68.8%迅速上升到1993年的80.1%,1999年進一步上升到83.1%;加拿大也從1991年的70.8%上升到1999年的78.6%;美國則從1991年的26.2%上升到2000年的32.9%。其中的一個插曲是,在NAFTA生效的1994年前后,美國和加拿大的區域內貿易份額上升了約1個百分點,但墨西哥的區域內貿易份額下降了約2個百分點。進入21世紀以來,各成員國的區域內貿易份額均大幅下降。2000年到2010年期間,墨西哥的區域內貿易份額下降最為明顯,到2010年降至67.5%,比1999年下降了15.6個百分點,美國同期下降了3.4個百分點。這種下降趨勢持續到2011年前后,趨于穩定。
5.三個成員國對中國的對外貿易份額呈上升趨勢。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美、墨、加三國對中國的對外貿易占比以不同的速度提高。墨西哥從90年代不足1.0%的占比,到2018年已經上升到9.9%;加拿大從最初不足2.0%上升到8.8%,而美國從低于6.0%上升到超過16.0%,2015年到2018年期間超過了美國對加拿大的貿易占比,中國是其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受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美墨加貿易協定簽署的影響,2020年三個成員國與中國的對外貿易占比均有所下降,其中美國下降最為明顯,較2018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
綜上,NAFTA(USMCA)的區域內貿易比重呈現先升后降態勢,但與中國等域外國家的對外貿易比重均有所上升。
三、東盟區域內貿易關系
(一)東盟一體化簡史
1967年8月,東盟(ASEAN)由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5個國家創建,以“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技術、教育等領域和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合作”為目標。ASEAN峰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1976年2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以后原則上每年舉行兩次。隨著文萊、越南、緬甸、老撾和柬埔寨的陸續加入,1999年東盟成員國由最初的5個國家擴充到10個國家,至今成員國保持不變(參照表6)。到2020年8月為止,東盟成員國的總面積為449.5萬平方公里,總人口6億5590萬,名義GDP為3660億美元,進出口總額28520億美元,近年平均增長率在5%左右,是發展中新興經濟的集中地區。

表6 ASEAN變遷簡表

表6 ASEAN變遷簡表(續)
自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東盟峰會決定東盟將向市場統一逐步邁進。如表6所示,1997年12月通過了《ASEAN愿景2020》,宣布2020年之前以實現經濟一體化為目標。2003年10月,明確以實現“2020年ASEAN共同體”為目標,發布《ASEAN第二協約宣言》(ASEAN Concord II),宣言中提出建成ASEAN安全保障共同體(ASC)、ASEAN經濟共同體(AEC)和ASEAN社會文化共同體(ASCC)三個共同體。2007年1月,簽署了旨在創建ASEAN共同體的《宿務宣言》,將ASEAN共同體的建成時間縮短至2015年。隨后的《東盟憲章》、《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AEC藍圖)、《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APSC藍圖)、《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藍圖》(ASCC藍圖)、《東盟共同體路線圖(2009-2015)》、《ASEAN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10》(MPAC 2010)等文件相繼通過,以此保障2015年年末如期實現東盟共同體建成的目標。
2015年是歐盟共同體的創設年,同年11月,東盟峰會再次通過了《東盟共同體愿景2025》,采納了《APSC藍圖2025》《AEC藍圖2025》和《ASCC藍圖2025》,增加東盟共同體的一體化強化目標。到2025年為止,建成以東盟單一市場為目標的東盟經濟共同體(AEC)。《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MPAC 2025)和《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Ⅱ2018-2025》(MPAC Ⅱ)分別于2016年和2019年采納,以此加強東盟內部互聯互通。這些行動指南將進一步推進東盟一體化的進程。

表7 2019年ASEAN各國經濟貿易及占比情況 單位:%
(二)東盟區域內貿易關系動態
1.東盟區域內貨物貿易情況分析。
縱觀東盟成員國內部貨物貿易在其全部對外貨物貿易中的占比情況,自1999年東盟囊括十國的20年來,先經歷了2000-2003年的短暫上升階段,2003年占比達到了峰值25.1%,但從2003年以后呈現穩中有降的態勢,2019年的占比與21世紀初的占比水平相當。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后半期對應地比前十年的后半期的每個年份都下降約2個百分點。比如,2007年為25.0%,2017年為22.9%;2009年為24.5%,2019年為22.5%。如果從出口和進口兩個方面來看,區域內出口額占東盟全部出口額的比重明顯高于區域內進口額在東盟全部進口額中的比重,但2013年后內部出口額占比下降明顯,從而進一步拉低了東盟內部貿易額的占比,如圖3所示。此外,如表6所示,各成員國在區域內貿易中的表現也存在較大差異。2019年,老撾對區域內貿易的占比最大,為60.5%;而越南僅為11.0%,是對內部貿易占比最小的成員國。特別注意到,除老撾外,東盟其他九國的區域內貿易份額均比美國對域內貿易的占比還低,比歐洲各國、墨西哥、加拿大等國家的占比低得更多。

圖3 1994-2019年ASEAN域內貨物貿易占比情況(單位:%)
2.東盟區域內服務貿易情況分析。
從服務貿易方面看,如圖4所示,根據東盟官網現有統計數據計算,2010年以來東盟區域內貿易占比呈顯著下降趨勢。內部服務貿易總額占比從2010年的15.6%下降到2019年的12.9%,內部出口額占比從16.4%下降到13.2%,內部進口額占比從14.8%下降到12.6%,其中出口占比始終大于進口占比,且下降的百分點也更多一些。

圖4 2010-2019年ASEAN域內服務貿易占比情況(單位:%)
綜上所述,隨著2015年底東盟共同體的正式建成,東盟一體化水平更進一步,但總體上看,2010年以來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東盟區域內貿易占比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這意味著東盟一體化水平的提高并沒有增加內部貿易的緊密程度,反而減少。
就東盟區域內貿易占比下降的原因,可以總結為如下兩點:
首先,東盟與其貿易伙伴的貿易份額有變。長期以來,中國、美國、日本和歐盟28國是東盟最主要的貨物貿易伙伴。從對外貨物貿易占比變化來看,2003年,上述四大貿易伙伴共占東盟對外貨物貿易的47.6%,2019年略有下降,但也為46.5%,均接近半數,如圖5所示。其中,雖對美國、日本、歐盟的貨物貿易份額有所下降,但對中國的貨物貿易占比大幅上升。2020年,東盟與中國的對外貨物貿易占比已經接近于其內部貨物貿易占比。除新加坡和文萊躋身于高收入經濟體外,其余東盟成員國均處于增加收入的發展過程中。據統計表明,2019年,東盟十國的名義GDP為3.2萬億美元,而北美自由貿易區為24.4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為21.4萬億美元),中國為14.3萬億美元,EU28為15.6萬億美元(其中,歐元區13.4萬億美元),日本為5.1萬億美元。對于東盟成員國而言,由于經濟發展階段和市場規模不同,與這四個經濟體開展對外貿易仍占據重要地位,中國、日本、北美和歐洲是東盟出口導向戰略的重要海外市場。

圖5 2003-2020年ASEAN域內貨物貿易占比及其與主要經濟體貨物貿易占比情況(單位:%)
其次,東盟內部成員新加坡對外貿易的影響較大。新加坡是東盟內部最大貿易國和高收入水平國家,如表6所示,2019年其對外貿易額占東盟全部對外貿易額的26.6%,比印尼、菲律賓、緬甸、柬埔寨、文萊和老撾六個國家的對外貿易額占比總和還高。眾所周知的是,新加坡的轉口貿易相當發達,再出口額占其總出口額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又是面向區域外國家,這必然會降低東盟整體以及新加坡在區域內的貿易份額,2019年其對東盟的內部貿易占比僅為25.4%,遠遠低于老撾的60.5%。
四、總結與啟示
前文以EU、NAFTA(現USMCA)和ASEAN為例,以近年來呈增長趨勢的區域貿易協定(RTA),尤其是超大型自貿協定不斷誕生為背景,以成員國之間的關系強化是否會提高區域內貿易份額為問題假設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一般來看,自貿協定運行之初的區域內貿易份額有所上升,但不久之后便會呈現穩定或下降趨勢。比如,歐元區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在2000年以后有下降傾向,盡管東盟內部市場強化動向明顯,但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針對上述情況,筆者認為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解釋:
第一,與中國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內部貿易關系。從前文的分析可見,無論是歐盟還是美墨加三國,亦或是東盟十國,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份額都呈現上升趨勢,中國日益成為這些國家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這些國家與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關系。但同時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結合前文已經解析的原因,隨著對中國貿易份額的增加,東盟十國對美日兩國的貿易份額卻有所下降,這意味著其對中國的貿易份額上升產生的影響需要打折扣。
第二,促成區域貿易協定締結的已有貿易關系基礎會減弱建成前后內部貿易的變化。任何一個區域貿易協定的達成都不是突然發生的,特別是三個以上國家的情況下,需要彼此間在一定時期內已經建立了緊密的經貿關系,經過磋商談判逐漸發展到簽訂區域貿易協定(RTA)、自由貿易協定(FTA)或者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因此,在這些協定締結前后,很難看到區域內貿易份額突然明顯擴大的情況。如果再次考察傳統關稅同盟理論的貿易創造、貿易轉移、貿易擴大三個效應,如果區域貿易協定成立前,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已經比較密切,相對優勢結構不會在短期內發生變化,這三種效應發生戲劇性變化的可能性很低。當然,取消或降低關稅的影響仍然存在,但除部分商品外,整體關稅率降低的情況下,關稅率的變化即相對價格的變化對整個內部貿易結構的影響不大。
第三,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和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等數量增加會部分抵消多邊協定效應。比如,目前美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生效的雙邊FTA已多達20項,除加拿大、墨西哥外,還與澳大利亞、韓國以及東盟主要成員國新加坡等國家達成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且,美國還與東盟國家建立了貿易投資框架協定關系。同樣地,東盟與中國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即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的“10+1”升級版,新加坡與中國也在簽訂FTA的基礎上再次升級。這些雙邊自貿易協定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原有多邊自貿協定成員國與區域外國家的貿易關系,雙邊協定和多邊協定縱橫交錯,從而可能抵消一部分多邊協定成員國內部的貿易份額。
對于中國而言,作為主要成員國之一,已經成功助推RCEP落地生效,并積極申請加入CPTPP,2021年11月1日又正式提交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截至目前,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署的雙邊和多邊自貿協定(包括升級版協定)已達19項,正在談判的多雙邊協定以及已達成協定的升級版還有10項。這里值得考慮的問題是,除去其他因素的考量,中國在這些超大型自貿區內的貿易份額是否會進一步擴大,能否有助于實現“貿易創造效應”還有待于進一步考察。關稅稅率發生變化后,也許一定時期內在個別商品或者個別行業上的區域內貿易反應明顯,但如果生產率上升程度、單位勞動成本和技術水平等比較優勢結構沒有較大的改變,那么區域貿易協定對區域內貿易和整體貿易結構的宏觀影響就不會那么明顯。
當然,在本文研究過程中,比較聚焦進出口貿易總額的份額變化,或許對某些區域一體化組織來說,出口和進口份額的變化并不一樣,進口的變化可能會抵消出口的變化,從而使得整體份額變化并不明顯。但是筆者在前文已經計算了東盟的進出口情況,對北美自由區的情況也進行了驗證,與進出口總額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另外,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也存在互補或者替代的關系,RTA對區域內直接投資的影響也需要研究,區域內貿易和區域外貿易的關系也需要理論和實證的分析。這些將是筆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