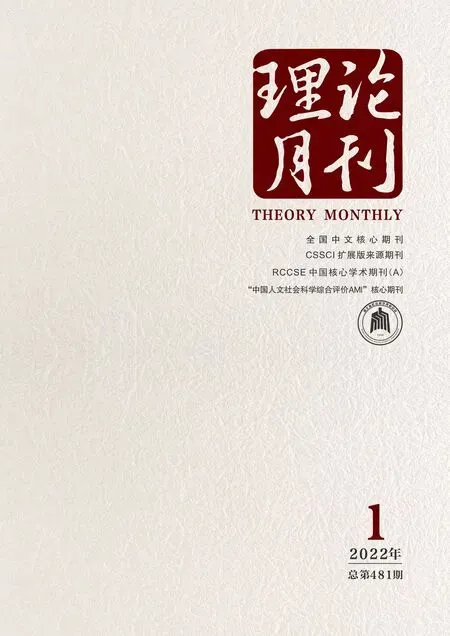《路得記》女主人公“他者”性別形象超越的層次性
□李 瑛
(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相對其他文學形式,女性在宗教文學中被重點記載的例子并不多見,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經典圣經文學中亦然。具體看《舊約》,就整體以女性為核心進行專章記載的文本數量而言,全書一共39 書,其中大多書以男性人物命名,以女性名字命名的僅有兩書,《路得記》即為其中之一,可見路得形象對基督教和猶太教歷史傳承的重要意義。《路得記》描述的是,喪夫后追隨婆婆拿俄米到伯利恒的摩押女子路得,在異國他鄉努力融入當地的父權文化,成功地與當地德高望重的富戶男士波阿斯聯姻。而后她生了一個兒子,不僅與無夫無子的前婆婆拿俄米分享“母親”名分,使其有了倫理意義的依靠,而且因對丈夫波阿斯家族的人脈傳承貢獻,后來以猶太民族偉人大衛母親的身份被記入猶太史冊。女主人公路得勤勞忠誠又勇于突破。一個女人從無依寡婦、可憐兒媳、寄居的陌生女子到富戶妻子、生子讓名的兒媳、未來民族領袖母親等一系列身份糾結和倫理矛盾的調和歷程,呈現出一位追求卓越的平民女子的性別形象特征,是學術界公認值得研究的經典人物。
《路得記》人物研究具體如何切入?從分析方法來看,在文學藝術領域,性別研究獨樹一幟,可以極大地拓展對人性深度的理解。作為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女性學領域具有開創性影響力的學者,李小江強調“具體到歷史文化集中濃縮的文學藝術形式,性別研究一直扮演著‘開路先鋒’的角色,從性別角度對‘文本’進行解構,挖掘出我們潛意識中的疏漏和壓抑,極大地豐富了人性的內涵,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擴展精神空間”。在《女性/性別的學術問題》一書中,李小江談到,性別分析方法“在哲學認識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同階級分析、精神心理分析方法一樣,深入切進人類社會個體生命,成為我們認識自己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性別分析的歷史進程中,“人與自然,從自在的同一(遠古時代)到人為的對立(文明時代)到自覺的認同(當代),是歷史在高層次上的會返。正是在這個最終的‘認同’中,人的行為終于有可能掙脫純粹自然的羈絆,在順應自然的約束力中獲得現實的自由”。作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宗教文學經典之一,《路得記》文本中記載的女性性別人物形象可能具有跨越歷史時空的代表性,性別視角的切入方法,應該可以挖掘到更豐富的價值。
查閱目前直接或間接涉及《路得記》人物研究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以家庭倫理類或信仰分析為主,有的強調《路得記》中人物關系中的信仰之愛,如《一首愛的贊歌——〈路得記〉的解讀》(何宏偉,2009),《從〈路得記:信仰之旅〉看世間愛為何物》(張景成,2013);有的解析《路得記》中緊密聯系的家庭關系或社會倫理,如《古猶太民族的和諧社會理想——以〈路得記〉為例》(梁工,2008)、《〈路德記〉和諧家庭與和諧社會》(李順華,2006)。另一類與西方女性主義哲學或與女性社會獨立分析有關,這些文獻或宏觀或微觀,有單純從女性性別的視角分析《路得記》中人物言行,如《狹隘女性主義〈圣經〉觀的弊端》(何花、胡宗峰,2012),《〈舊約圣經〉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讀》(李滟波,2004);有的從綜合的社會學角度詮釋《路得記》,如《〈圣經·舊約〉的女性形象再解讀》(黃瑋,2017)。
總體來看,這些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前一類研究偏向于粗泛神學的視角,難以對人物的復雜特質展開細膩分析;后一類研究容易陷于女性主義派別對立的政治視角,觀點分歧、難以整合。同時,二者都對文本在宗教哲學里的父權文化背景關注有限,對女性性別超越方式的多樣整體性考慮不足。因而本研究在宗教哲學父權文化視域下,以性別研究為主線,綜合女性主義的多元視角,從女性性別“他者”超越性具體層次出發,嘗試對《路得記》女主人公復雜的性別形象進行整合分析。
一、父權社會的性別關系框架
“父系社會是人類自覺意識的社會活動的真正起點”,但是父權背景下的女性觀卻并不一致。從性別哲學的思維模式上看,“性別差異可以一直追溯到精神本身最深的根上去”,映射了人類精神的基礎之源。女性主義性別分析立足于父權(Patriarchy)社會中的政治文化制度大背景,聚焦于主體人性別區分的二元對立統一關系。在近現代西方哲學史上,人際關系理論有不同的形態,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從社會歷史宏觀視角出發的交往進化論,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從多元主體關系中個體存在等價性出發的他者觀等,但真正實現了人屬性的二元差異對立關系“向類的回歸”的是宗教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的關系本體論(the Relational Ontology)。從宗教哲學史地位看,馬丁·布伯的關系本體論是將對立統一的二元關系進行美學論述的最高典范。
(一)“太初即有關系”:“我—你”,而非“我—它”。總體來看,馬丁·布伯將人類二元關系分為兩大類,即“我—你“(I and Thou/You)和”我—它“(IIt)。前者是立足個體的一種帶有高度人格乃至生命審美的人際關系,后者是隔絕世界的孤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利用他人的一種工具性人際關系。
關系本體論強調,人類社會“太初即有關系”,這個關系是“我—你”而非“我—它”。具體而言,先天之“你”實現于與相遇者之親身體驗的關系中。人可在相遇者身上發現“你”,可在唯一性中把握“你”,最后可用原初詞陳述“你”。這一切均筑基在關系先驗之根上。但是,隨著歷史制度的累積和人性復雜性的發展,世俗社會卻脫離本源而陷入以“我—它”為主導的社會形態。對于“我—它”,即一種人把世界以及世界上包括他人在內的所有在者都當成與我相分離、相對立的對象或客體,是為我所經驗、所利用的東西。對于這種人來說,所有這些在者,即所有“他者”(the Other),便都是“它”,整個世界因此也就成了一個“它”之世界,人與對象因此便是一種“我—它”關系。馬丁·布伯雖然承認人同世界的這樣一種關系是必要的,因為人離開了同世界的這樣一種關系,且不要說人類進步將會因此變得不可思議,而且人的自身也會因此而變得難以維系,然而在布伯看來,“我—它”關系畢竟不是基本的人類關系。因為當我們站在一個人的面前,用主客二分的眼光把他作為一個認識對象和利用對象來審視他,那他也就因此而不再是一個主體,而是成了與物品一樣的東西了,這是相互主體性價值所不容的。所以在關系本體論結構里,如果說“你”的主體性存在是被高度肯定的,那么“它”的主體性狀態則是被絕對否定的。
(二)“關系的動態化”。同時,馬丁·布伯指出“我—你”和“我—它”之間存在“關系的動態化”。他認為,雖然由于他人的唯一性,自我對他人產生了責任而以“我—你”方式相待,但“當關系事件走完它的旅程,個別之‘你’必將轉成‘它’”;同時,“由于他人的超越性,個別之‘它’因為步入關系事件而能夠成為‘你’”。也就是說,在具體的二元關系互動過程中,與“我”對應的“他者”可以從絕對工具性的“它”轉換成具有高度主體性特征的“你”,或者與“我”對應的“他者”可以從具有高度主體性特征的“你”轉換成絕對工具性的“它”。
馬丁·布伯關系本體論是整合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觀而衍生提煉的,他將此論述運用在人類的社會關系中,強調“人類的雙重性決定了世界的雙重性”,即“我—你”和“我—它”兩種關系雖然性質迥異,但在具體個人社會生活中同時并存、界限模糊,如果將具體的關系屬性單一化成“你”或“它”將導致人無法生存。人類即需要將外界人或事物看成“你”,也需要將其看成“它”。
(三)性別關系與關系本體論。就性別關系而言,在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明確定位上,馬克思進一步說,“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系是男女之間的關系……從這種關系的性質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種程度上成為并把自己理解為類存在物——人;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人和人之間最自然的關系。因此,這種關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人的行為,或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成了自然”。也就是說,男女性別關系品質其實濃縮了具體人性價值觀整體的方方面面,是個體社會價值觀的集中表現。因此,馬丁·布伯關系本體論雖然并不是直接針對性別區分提出的,但由于其描述二元關系的經典性,完全可以用在社會關系核心的男女性別關系中序二)。
關系本體論中,本源性的“我—你”關系是一種相互對等、彼此信賴、開放自在的關系;工具性的“我—它”關系則是一種考察探究、單方占有、利用榨取的關系。在“我—你”關系中,雙方是相對主體,來往是雙向的,“我”亦取亦予;在“我—它”關系中,“我”為絕對主體,“它”是絕對客體,只有單向的由主到客,“我”只取不予。因此“我—你”關系和“我—它”關系中的“我”本質上是不同的,如果前者意味著互利共贏的理性價值觀,后者則是剝削利用的欲望價值觀。具體到從父權社會男性本位出發的性別觀中,可以對應為表示男女性別平等的“我—你”性別觀和反映男尊女卑地位的“我—它”性別觀;前者男性尊重女性、平等待人,后者男性蔑視女性、壓抑人性。
二、女性主義研究的起點
女性性別“他者”是女性主義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是現代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究起點。在近代西方主體性哲學中,“他者”(the Other)與“自我”(the Self)是一對重要范疇。基于性別關系在漫長歷史中同一性的社會政治結構,在傳統父權社會歷史背景下,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奠基人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明確提出了“他者”概念作為女性性別研究的起點。波伏娃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和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他者”概念,融合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的身體哲學,將“他者—自我”的對立引入性別關系辯證法。根據波伏娃對女性的分析,女性作為“第二性”,父權制必然以代表“人”絕對標準的男性自我主體性第一性的需求將女性視為附屬的“他者”。需要強調的是,不同于傳統主體論為了突出“自我”而對“他者”形成的絕對否定,女性主義性別“他者”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男女同為主體的建構,其前提是對“他者”的異質現象的尊重。
根據女性在這種“他者”位置中可能實現的自由度,女性“他者”分為兩類:
一類是“絕對他者”(absolute other),即一種絕對被動的、客體性的存在,“其自身不能給出自己存在的正當性理由,需要他人來證明其存在的價值”。以這種狀態存在的女人“實質上就相當于物的存在水平,而失去了作為主體性存在的地位與價值”。類比父權背景的性別關系本體論,相當于典型的男性將女性當成完全的工具價值,利用性別政治壓抑女性的“我—它”關系中的“它”。
另一類是“相對他者”(relative other),即帶著主動的自我定義和超越性對另一方主張相應的權利,讓自己的“他者”概念以其相對性失去其絕對意義,使原來以“絕對他者”形式存在的“無我”狀態被放棄、并由此形成個體自我。對于平等關系而言,男女雖然有別,但彼此互為“相對他者”。類比父權背景的性別關系本體論,相當于男性帶著尊重女性為人絕對價值的起點,忽視性別尊卑的“我—你”關系中的“你”。
“絕對他者”是沒有擺脫客體性的人,“相對他者”是融合了他者性和主體性的人,前者完全處于性別文化的奴役之中,后者兼有主體性和客體性,同時兼具內在性和超越性。女性超越性別的目標就在于走出“絕對他者”成為“相對他者”;在男女性別類屬中彼此同為“人”,二者具有共同的主體性尊嚴的基礎上,從父權社會關系中曾經被否定的“它”轉變成被充分承認的“你”。
女性主義理論龐雜多樣,“他者”維度具有多樣性和內部矛盾。現代女性主義思想形態多種多樣,按美國著名女性主義學者羅斯瑪麗·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在其《女性主義思潮導論》(Feminist Thought:A More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一書中的歸納,按照歷史順序,可以歸為八個類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和社會性別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女性主義、多元文化與全球女性主義和生態女性主義。每個類別有多種分支,例如法國后現代女性主義,就有至少兩個經典分支:以埃萊娜·西蘇(Hélène Cixous,1937—)為代表的支派強調女性作家獨立于男性作家方式的“陰性書寫”,突出女性可以借用男性目光通過“他者的他者”實現性別自我的內在支持;以朱莉亞·克里斯多娃(Julia krystova,1941—)為代表的支派認為女性能夠融合母性的“符號期”和父性的“象征秩序”,在社會性別意義上實現在“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之間自由行動。總體來看,當代西方大多數女性主義理論發展有兩點共同主張:其一,肯定女性的重要性和價值;其二,女性需要進行社會變革獲得安全滿意的生活。面對性別不平等的現實和歷史,女性主義的核心目標是“消除所有形式的支配權,包括男性凌駕于女性之上的支配權和發生在女性之間的支配權”。
然而從內部看,女性主義理論觀點由于選擇了不同立場而形成巨大的“他者”差異,一些派別的觀點經常互相沖突對立,調和內部矛盾一直是學術界的重要課題。不容置疑,女性主義“每個流派都是了解女性經歷的一面鏡子,每個流派都有助于對某些特殊現象的理解”——可以說,女性主義觀點的多樣性,表明了不同的女性主義者對同樣問題持有精細的多維度見解;女性主義思想架構的豐富性是女性主義健康發展和成果豐碩的表現。但是不可否認,由于內部觀點分歧,女性主義可能會引起混亂。在美國,一些保守媒體利用分歧現象,通過一些負面的新聞事件對女性主義強化一種“女人反對女人”的刻板印象,他們認為,“使女性主義者和她們的想法看起來瑣碎而毫無價值的方法之一,是將女性描繪成一個彼此爭論不休的群體”,由此將“女性主義”學術進行標簽化和丑化。這也意味著,女性主義自身需要從更基礎的哲學維度上進行有效的整合,以化解其因差異而產生的一些弊端。下文以《路得記》女性為對象,試從宗教哲學的二元關系本體論角度做進一步探討。
三、路得性別“他者”凝聚的復雜性
“性別”(Gender)觀一直是父權社會秩序的底層邏輯,濃縮著國籍、種族、膚色、階層、倫理等各種差異,經常是政治文化爭論的焦點。經典的宗教文學是生存美學的底層價值,《路得記》中女性路得在具體性別關系中即呈現出這種弱勢混合的復雜性。
(一)路得在伯利恒作為女性“它”的復雜社會中的處境。雖然在故事的結尾路得贏得伯利恒女性鄉民的一致贊譽,不僅成為波阿斯家庭的生育功臣,而且由于后輩的偉大貢獻在當地史書中成為備受國家尊敬的“相對他者”之“你”。但是分析文本,初來乍到伯利恒的路得,從性別的社會內涵而言,她不得不承載著國籍、階層和輩分倫理等多方面的苦楚:
國籍身份。傳統猶太律法非常敵視摩押。在歷史上,猶太民族和摩押族勢不兩立,這在《舊約》中有多處且長篇的記載。例如,在《以斯拉記》第九章和第十章專章記載了猶太族權威譴責與異族的通婚、并立法嚴格終止包括與摩押族在內的已有事實婚姻,立法者把以色列男性與摩押族女子通婚視為最大的“叛國罪”之一。路得第一次在波阿斯田地拾取麥穗時,波阿斯家丁描述她的一句話中就兩次強調了她的國籍:“她是魔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路2:6);波阿斯在商議贖地和路得婚姻歸屬時為了盡力排除另一位親屬的可能性,也三次強調了路得的國籍:“從摩押地回來的拿俄米”(路4:5),“你從拿俄米和摩押女子路得手中買這地的時候,也當買死人的妻子”(路4:6)和“我也娶馮倫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得”(路4:10)。由此可見,來到伯利恒的異族女人路得,社會關系最大的困境可能是被完全否定乃至敵視的異國女性“它”之處境,面對當地社會民眾帶著強大宗主國身份的絕對自我感。
社會階層。波阿斯在伯利恒,出身于父母在約書亞時代有建國英雄貢獻的名門望族,而且他的父母是在以色列領袖約書亞的證婚下結合的。對于有顯赫出身背景的波阿斯,經過自己的努力,在伯利恒集名利于一身。正如《路得記》第二章提到波阿斯時,特別強調“是個大財主”;同時,波阿斯以仁義公正的形象建立了非常好的公眾信譽,從第二章與收割鄉民的招呼互動和第四章他在城門召集商議贖地和路得婚姻歸屬的過程看,他可能是全城最有號召力的公眾領袖,其父權男性“我”的社會影響力在伯利恒是屈指可數的。以此為背景,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路得第一次見到波阿斯時形象是“臉伏地叩拜”,她身為一個孤寡貧困不如波阿斯田間女仆地位的底層鄉民之“它”,更襯托出波阿斯擁有權貴威望的絕對優勢。
輩分倫理。路得的公公以利米勒家和波阿斯家族有親屬關系,從家族輩分看,波阿斯和路得跟隨的拿俄米是同一代人,因此,路得作為拿俄米的兒媳,對波阿斯來說屬于晚輩。從代際倫理看,波阿斯作為父權長輩對路得是有權威性的,這也是為什么第一次見到路得時,波阿斯和拿俄米一樣,對路得以“女兒”方式稱呼。從文本明顯可見,在家族倫理上,波阿斯的形象更有力量,路得相當于處于代際權力之“它”的家族位置。
從路得和波阿斯性別關系地位的整體對照來看,按照經文路4:12“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聲,愿耶和華從這少年女子賜你后裔、使你的家像她瑪從猶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顯示,最終實現的波阿斯和路得的聯姻繼承的是先輩猶大和她瑪的先例。比較路得和當年她瑪性別“它”之處境,她瑪不存在國籍和階層的劣勢,她主要是因為女性生育倫理之“它”受到許多委屈,然而路得不僅有生育倫理的約束,而且帶著國籍、社會階層和輩分倫理等多重劣勢。這也意味著相對于她瑪,路得“你”地位的實現需要處理來自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家庭地位等多方面的困境,她在伯利恒的成功立足說明她具有比她瑪更有影響力的“他者”能力優勢。
(二)路得作為女性“他者”對波阿斯的多重意義。路得相對于她瑪的優勢,集中表現在她對于波阿斯的多重性別意義。路4:11記載:“在城門坐著的眾民和長老都說,我們作見證,愿耶和華使進你家的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結、利亞二人一樣”,也就是說,按照性別歷史傳統,對于波阿斯(比當年的雅各年長)的婚姻,路得不僅有類似于夢中女神拉結的形象,有類似于利亞的生育形象;另外,波阿斯作為一個年長的男人,路得也類似于她瑪,帶著年輕女性充滿活力的性別形象。
顯然,路得作為女性“他者”具有相當豐富的內涵。對于波阿斯,路得有類似于拉結的甘心付出精神,她有父權男性渴求的靈魂伴侶人格自由獨立的美學意義;路得類似于利亞,她在倫理上有父權家庭期待的為妻的忠誠和為母的慈愛;路得類似于她瑪,她有拿俄米所不具備的開啟老年男性再次青春的生命魅力。聯系到女性主義“他者”觀的系統論述,路得這些能力可以有哪些理論依據,下文將作出分析。
四、路得女性“他者”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和層次性
從人際影響的角度分析《路得記》,路得作為摩押女子融入伯利恒猶太文化可以從她成為馮倫的妻子開始。綜合文本中路得言行和她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她有許多優秀品質,從人基本的物質生存到社會文化交融,依次表現為她的勤勞和自立、她的忠誠和孝順、她的貞潔自律和性魅力以及她的勇敢擔當和謙卑柔順四個方面。具體分析這些品質對應于女性的意義,可以發現它們分別以某種“他者”形式對應于某種女性主義派別,下面依次說明。
勤勞和自立對應“存在的他者”。這表現的是路得物質生存能力的一面,意味著實現經濟獨立的能力,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女性存在主義進行解釋。波伏娃在其代表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借助近現代經典的主體性哲學關于如何成為真正的“人”的思路,提出了同時享受自由和擔負責任的女性主體性理想,集中體現在她提出的超越第二性客體位置、無限靠近絕對第一性主體的“女性他者”概念。關于女性獨立目標的實現,波伏娃認為女性與男性有同等的選擇自由,因此女性為了維護自我的絕對肯定性存在,在作為第二性“他者”時需要像男性一樣利用自己身體力量參與社會勞動分工。波伏娃深刻認識到,由于肉身存在與物質需求息息相關,在傳統性別文化社會里女性的弱勢在于對男性物質資源的過度依賴,因此她特別注重女性主動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實踐。因此,波伏娃強調女性通過發展職業實現經濟獨立的主張,提出女性主義“存在的他者”觀。
陪伴拿俄米到猶太地的路得,一窮二白且一無所知,拿俄米的生存絕望處境就是她現實的起點。顯然,按照波伏娃女性“存在的他者”觀,路得摒棄了女性物質依賴的“絕對他者”之“它”的卑微處境,以吃苦耐勞的主體精神成為自食其力的“相對他者”。她親身投入社會工作——到田間拾取麥穗,保障了自己生活的需要。這顯然實現了波伏娃意義上的個人“經濟獨立”。從文本進一步看,路得在田間拾取麥穗直到晚上,并將拾取的麥穗打了約有一伊法大麥。她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又把她吃飽了所剩的給了婆婆(路2:17—18)。也就是說,路得不僅很好地養活了自己,而且成功撫養了她曾經的婆婆。她很好地承擔著類似傳統男性家長的勞作養家責任。路得在伯利恒拾取麥穗雖然身份卑微,但她獨立的社會化生存卻是美好的開始。正是因為如此,在物質生存上她作為性別的“相對他者”之“你”可以和獨立自主的男性齊眉并肩。
忠誠和孝順對應“倫理的他者”。這顯示的是路得作為女性基本人際關系生存的能力,意味著她很好地踐行了婚姻家庭的人倫關系,可用強調性別角色倫理超越的自我“窺鏡”說明,這契合的是法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后現代精神分析的女性主義理論。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大背景里,法露西·伊利格瑞在《他者女人的窺鏡》(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中回溯柏拉圖性別二元的傳統,批判地繼承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學說,認為女性角色對于男性建立自身絕對主體不可或缺,即“父權制依靠男性內化的男性形象確立社會關系,根據男性的自我定義去反觀女人,把女人構建成男人的他者和對立面”。因此,“由于依照男人的標準而存在,女人只能映照男人,從而喪失主體性,淪為父權制的鏡像”,即一般意義上的他者。然而,伊利格瑞強調,依據這種邏輯,女人可用反窺鏡的形式進行自我關照而成為自我的“他者”,由此在父權他者中以“倫理的他者”方式建立自己女性對應于男性的主體性。
路得在猶太文化中的社會關系,源于她的忠誠和孝順。但在伯利恒,由于丈夫已死、婆婆年紀老邁,基本上是從無依無靠的外鄉人開始的。她作為傳統伯利恒社會歧視的敵國人,雖然有婆婆拿俄米引導,但沒有父親、丈夫或兄長之類的男性家人支持,相當于在父權制度里沒有正常父權人際關系的支持。她面對人生地不熟的伯利恒世俗社會,倫理上基本上是“絕對他者(它)”。如果她不恪守伯利恒的家庭性別倫理原則,完全可能陷入被社會任意踐踏或羞辱的悲慘處境。但事實上,路得成為倫理性“相對他者”,無論作為拿俄米的兒媳/女兒,還是后來作為波阿斯的夢中情人乃至妻子、俄備得的親生母親,她的女性性別角色都非常成功,而且給伯利恒鄉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貞潔自律和性魅力對應“政治的他者”。政治的女性主義涵蓋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多元文化與全球女性主義和生態女性主義幾種理論形態,其中以美國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t,1934-2017)“性政治”觀最有影響力。在馬克思主義和生物進化論的影響下,凱特·米利特《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從意識形態、生物學、社會學、階級、經濟和教育狀況、神話和宗教、心理學等方面論證了男權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和隱蔽性,造成女性社會地位被固化的處境。凱特·米利特主要從階級斗爭的角度認為,女性是父權統治的對象,家庭是父權國家政治的原型,人類包括女性的“性”行為根植于人類活動大環境的最深處,傳統女性的“性”意義完全由男權意識形態操縱,是父權文化所認可的各種態度和價值觀的集中表現。總體上說,凱特·米利特認為,女性他者作為被統治的對象,“女性”的“性”是父權統治的中介、工具和資源,女性自我更新自立必須反對階級父權制并重新定義和守護自己的性與性別身份。個體女人解放的獲得,只有脫離男權性意識形態的統治,擁有自己獨立的性意識,才能真正建立作為人的主體性。由于對男女“性”行為中所蘊含的不同主從權力地位的重視,凱特·米利特的女性他者觀可以稱為“政治的他者”。
《路得記》中典型表現“政治的他者”的細節集中在第三章“路得與波阿斯在簸麥場上”。整個過程可分為四段,從路得與波阿斯在田間相遇開始,以拿俄米為路得謀劃婚姻為轉折點,以路得冒險委身并求助為高潮,到路得帶著禮物回到拿俄米身邊、等待波阿斯贖地聯姻和拿俄米對冒險執行者路得的安慰結束。大體上看,委身計劃的策劃者是拿俄米,路得努力執行,二人共同參與并成功,但整個過程關鍵部分由路得完成,所以路得是主角。能夠實施性政治,路得年輕而且很可能深具性魅力,雖然文本沒有直接描繪,但是按照精神分析觀點,由于波阿斯母親投奔猶太國的異域文化背景,路得的外籍文化身份很可能勾起了波阿斯的戀母情結,這從波阿斯第一次見到路得就對她進行稱贊可以推測;同時,相對于猶太族偏重女性性別的生育倫理,路得出身的摩押文化更強調女性的性愉悅魅力,據此可以推測路得相對于當地一般猶太女子是神秘美麗的,從伯利恒田間男性和波阿斯對她的接納可以證明。總而言之,在伯利恒鄉間嚴厲的女性貞操觀背景下,路得冒著人言可畏、身敗名裂的巨大風險,主動越雷池以委身性行為征服波阿斯的心,以性政治他者方式推動波阿斯執行婚姻聯盟的合法化行動。
勇敢擔當和謙卑柔順對應“審美的他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繼承波伏娃和伊利格瑞等幾代女性主義哲學觀,在其代表作《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和《消解性別》中引入福柯和德里達等人的理論,發展出女性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論。巴特勒認為,傳統性別觀是表達性的,而性別文化的本質是強調操演性的。所謂的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都是在一個二元建構里,通過類似于儀式化的社會戲劇,通過個人的身體經由相應的性別風格或程式化的過程形成。在這樣的主體建構過程中,巴特勒延續黑格爾主體構建中的“欲望和承認”共存的邏輯起點,將女性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欲、身體等范疇去自然化,認為女性的性別完全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作為現代女性主義發展的集大成者,其“他者”行為觀從性別角色的“戲仿”到“政治”,帶有文化藝術表現的感染力,因而可以實現人際美學情感的喚醒,可以概括為“審美的他者”。
從文本看,路得的女性言行是帶著美學特征的。初到伯利恒的路得基本上是被無視的,作為人她沒有被認可的社會位置。但在這種處境里,面對老邁無力的女性拿俄米,她模仿“男性”勇敢擔當,主動承擔了物質供養責任(路2:2)。在路得與拿俄米到達伯利恒時,路得像伯利恒民間家庭里的夫妻性別分工一樣,主動承擔了男性“養家”的責任。路得作為純粹“女性”面對波阿斯,在田間相遇時謙卑有禮,引起波阿斯的愛憐和幫助;秘密委身后主動求助、柔順依從,贏得波阿斯全力以赴迎娶成婚的決心。總體而言,性別審美的他者方式,路得通過超越性別的責任感和美好言行在異國他鄉伯利恒成功塑造出一個猶太父權貴族需要的女性形象,她作為女人性別主體的確立隱含在其操演性別的審美性言行中。
從存在、倫理、政治、審美依次遞進的程度看,路得整合了四種力量,具有“他者”多種方式綜合性的能力。路得能夠在伯利恒獲得成功的立足,她為人的卓越即在于此,她不僅勤勞謙卑,而且有膽有識,在風險中張弛有度地實現了社會地位的逆轉。總而言之,路得性別“他者”形象表現的四種能力具有整體性,從存在到審美,不僅實現一種女性性別超越性整合的閉環,而且分別在強調物質生存的存在與突出意識形態生存的政治,在強調女性對應多種性別關系(父女、夫妻、母子)的倫理和強調對應單一的性別關系(男—女)的審美方式上表現出對立統一,呈現出一個女人在性別他者形象上不容易達到的完美高度。
五、結語
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對分析《路得記》文學性別而言,綜合從“存在的他者”表現的經濟獨立能力,“倫理的他者”實現的倫理關系自知,“政治的他者”顯示的性意識獨立,“審美的他者”呈現的規范自立四個維度看,路得作為主人公的女性形象立體豐富,在父權文化里充滿美、愛和獨立自由的精神韻味。大致而言,路得的“他者”能力表現在:她超越國籍、階層、家族倫理、具體人際等多重集中于她女性性別的劣勢處境,以綜合性的“相對他者”方式,贏得拿俄米和波阿斯一致認同,以一個孤寡貧困的外來女人的婚姻方式加盟當地領袖家庭,不僅贏得了伯利恒民間社會的美譽,而且贏得了具有排斥異族傳統的猶太族特別的歷史認同。
總體上看,分析路得的四種女性主義理論側重女性他者表現能力的不同方面,從性別“相對他者”主體建構的邏輯順序角度,從存在、倫理、政治到審美,分別強調女性與男性性別共生共存的社會意義。于此,這一系列不同女性他者的表現,從存在到政治,從倫理到審美,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從廣義的公共社會領域到具體的私人生活領域;從存在到倫理,從政治到審美,將女性獨特的影響從一般的社會分工參與推展到深具規范力度的社會人際層面。從關系本體論角度看,“存在的他者”“倫理的他者”“政治的他者”和“審美的他者”作為女性從“它”到“你”的四種遞進的主體性建立方式,并行不悖體現在了路得的個體案例中。在父權男性本位的社會文化中,女性主義理論多樣性整合的機遇似乎就在于此,即從不同維度的“絕對他者”之“它”,到多樣性的“相對他者”之“你”,由此成為一個具有性別意義完全整合的、具有女性性別精神“自我”主體價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