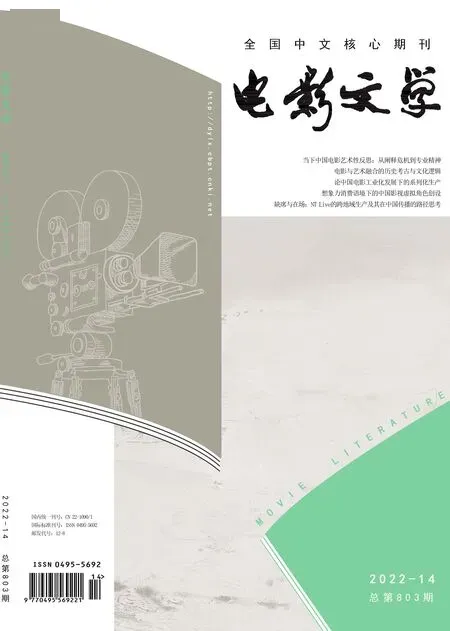從敘事到技藝:愛國主義題材電影的發展與變遷
李子揚
(東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在中國,愛國主義題材電影是以體現勞動人民頑強抵御外來侵略為主要內容,以弘揚民族精神、傳承愛國主義理念為表意核心,并具有獨立藝術范式和操作范式的一類電影。圖像是一個“充滿話語深淵的視覺形象隱喻”,依據圖像的表意,電影便成為信息傳遞的有效手段。當電影作為信息介質與民族精神相結合,愛國主義題材電影就開始成為傳承民族精神主流價值觀的優秀載體。本次研究主要以1984年謝晉執導的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和2021年陳凱歌等人執導的電影《長津湖》為例,分析愛國主義題材電影的變遷與發展。
一、新時期愛國主義題材電影的類型
愛國主義題材電影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其在主流價值觀的傳承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著相應的探索和創新,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呈現出比較大的發展變化。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以及中國開始全球化進程,一個嶄新的時代開始了。這一時期電影的創作,不僅延續了前期的創作傳統,還著重表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的形象。
伴隨著電影行業的發展,愛國主義題材電影的類型也越來越清晰,各種經典題材均得到快速發展。
第一類是革命歷史回顧影片,這類影片主要以中國近代反抗壓迫,抵御外來侵略題材為主。主要內容來源于歷史戰爭,表達艱苦歲月下,革命成果的來之不易。將重大歷史史實搬上大銀幕,讓觀眾重新感受戰爭的殘酷,引導觀眾正確認知歷史事件。在影片《開國大典》的創作過程中,使用了真實紀錄畫面,完整地還原了天安門城樓上激動人心的時刻。將真正的史實重現給觀眾,使得影片更具有說服力和生命力,觀眾能夠更加具有沉浸體驗。這類歷史回顧影片,通過真實的鏡頭激發了觀眾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民族凝聚力。革命歷史片引用歷史事件,將國家發展歷程與民族情懷相融合,以寫實的風格呈現,往往更容易具有紀錄片風格和屬性,具有強烈時代感。在時代的宏觀格局下,既有著時代的局限性,同時也往往會缺乏獨特的個性特征,主題思想的表達會覆蓋整個影片。
第二類是人物傳記影片。這類影片以偉人的事跡、大無畏的精神、特殊的時代背景為主要內容元素,展示偉人在國家的特殊歷史時期為國家和民族命運做出的貢獻和犧牲,讓觀眾在了解他們所做出的光輝事跡的同時,學習并體會蘊含于影片中的偉大精神。影片《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領導人生活為主要內容的電影。該片重點介紹了周恩來對國家的杰出貢獻,將時代和主角人物的個性結合起來,從點滴小事切入,用大量的現實片段來展現總理真實而生動的生活,描繪了總理的光輝形象,喚起了觀眾的民族文化認同感。雖然這些影片展示了偉人風采,但是在創作中多數影片通常會出現情節雷同、人物形象僵化等弊端。近年來,偉人傳記片也逐漸開始進行了轉變。影片主要以凸顯偉人的現實生活為主,如影片《出山》(2018)的表達重點不在于體現歷史人物的偉大,而在于客觀真實地表現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和值得崇尚的精神世界。
第三類是時代英雄影片。這類影片在創作過程中,將主人公的英雄形象全方位、多維度地進行刻畫,塑造出具有鮮明性格特征的英雄人物。這種人物形象是以集體利益為核心的英雄形象,是民族形象的代表。在本體的屬性上,集合了愛國主義理念的多重元素。在文藝作品中,英雄形象經過多剖面的解析和渲染,逐漸就具有了神化特征。因此英雄神化一貫是創作的主要方式。在類型電影中,過度頌揚和神化英雄的傾向,這反而消減了英雄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英雄人物形象打造的層面上,時代英雄片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二、愛國主義題材電影的變遷與發展
(一)敘事的主題:從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簡單敘述到民族情感化
電影作為藝術表達的媒介載體,其影像呈現的功能是藝術表達的外在形式,追溯其核心仍然是為了傳達理念以及表達情感。愛國主義題材電影都是為了推廣符合主流思想的價值觀,并能在思想意識形態的問題上起到引導公眾的作用。正是因為這一特殊作用,這一類題材電影便具有政治要求和宣傳的目的,革命史實類的故事內容在這類電影的故事情節創作選擇上占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影片《高山下的花環》和《長津湖》皆為此例。但二者不同的是,《高山下的花環》這部影片演繹了重大歷史事件,并在劇中設計了矛盾的核心節點,以故事矛盾的核心開展敘述,利用先抑后揚的表達方式將故事情節鋪展開來,細致展現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殘酷歷史:三名士兵在遇到敵軍后不幸受傷,兩名士兵犧牲;立志做元帥的士兵因兩發臭彈死去,傷口有酒杯大小;靳開來在砍甘蔗時踩到了地雷,左腿被炸斷;在戰爭達到高潮之前,全連有三分之一的人犧牲或受傷。這部電影重構了戰爭時期的歷史場景,頌揚了英雄主義精神。而影片《長津湖》則更為民族情感化。在敘事主題方面,影片重點通過宏觀的民族情感來激發微觀的民族意識,增加國家形象對觀眾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故事的內容情節聚焦于細節層面的刻畫,深化了對國家概念的描述,在表現戰爭殘酷的同時,更深刻地表達了民族團結和國家凝聚力的重要性。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與意識形態多元化的今天,具有核心凝聚力的影像更加成為喚醒民族意識的有效載體。由此可見,依托民族情感化的愛國主義題材電影在其敘事策略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史實,尤其是中國近現代革命史。故事背景通常立足于一場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通過主題人物最終完成使命的經歷,彰顯出中華兒女的英雄氣概。這種敘事方式一般利用英雄死亡的儀式性情節,進而激發出觀眾內心之中的愛國主義意識與民族情感。
此外,在電影《長津湖》中,二元對立在敘事格局在劇情中清晰可見。比如:兩者在軍備上存在著明顯差距。美軍擁有制空權,飛機、坦克較為先進。而相比之下,中國的軍備捉襟見肘。中國的無線電臺的數量非常有限,再加上損耗,輕易不敢使用,而美軍卻用電臺聽圣誕歌。梅生一直隨身攜帶的是女兒的照片,而美軍營墻上貼滿了性感廣告女郎的畫報。主要人物之一的雷公是家里僅存的一個人,回家也只是孤零零一個人,而美國士兵只想和家人共同過節。美國士兵的飲食豐盛,而志愿軍的干糧是冰凍的土豆。電影通過強弱明顯的二元對立格局的設置和展示,讓“主人公”趨于平凡,將其置于與觀眾相同的心理層面。同時也將“主人公”置于弱勢地位,讓觀眾產生壓抑心理。這種壓抑既是“敵我之間的對比”,也是“戰爭的殘酷和今天幸福生活的對比”,這也為故事中“英雄”最終勝利歸來時的情感釋放鋪平道路。正如大部分愛國主義題材電影一樣,所有的困難和逆境都只是主人公進步的磨煉。主人公為了完成爭取勝利的任務,克服了一切困難和艱辛,國家和民族意識便得以彰顯,影片的主旨便成為電影敘事表達的本質。總的來說,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有助于喚起民族情感。而愛國主義題材電影中所謂的“國家處于危機中的愛國主義敘事”則更容易讓人形成民族意識。因此,愛國主義的有效表達有助于主流意識形態的良好傳播。
(二)敘述話語:從低端技術到奇觀技術化與民俗化
法國后現代主義者居伊·德波關于“奇觀社會”的描述是,在由現代生產條件主導的社會中,所有的生活都被呈現為一種奇觀積聚。過去直接呈現的東西現在純粹是表象。在《奇觀社會》中,作者對奇觀社會提出了幾個觀點,包括“奇觀不是形象的結合,它是以形象為中介的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系”,“奇觀是權力的集權統治壓倒存在之條件的時代的權力自畫像”等。盡管他沒有描述“奇觀”和電影之間的關系,但他的觀點非常符合當代“視覺文化”的主要特征。實際上,這里的“奇觀”一詞在一般意義上是指在現實世界中難以看到的驚人形象。奇觀是一種講故事的策略,利用特殊的技術手段和獨特的角度,故意創造和呈現現實生活中人們難以看到的圖像,這是近年來電影中經常使用的一種方法。而在愛國主義題材電影中實現“奇觀”策略有兩種主要方式:技術化和民俗化。
技術化是指增加電影制作過程中的技術投入,利用高科技手段創造特殊的視聽成效,增加電影的真實性,提升視覺效果。梅里愛等人都非常重視電影的技術化,眾所周知的《星球大戰》等一系列當代好萊塢大片幾乎都是利用先進技術創作出的作品。在利用技術手段制造特效與增強電影的內涵的方面,早期的中國電影人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由于技術滯后、投資不足、電影制作觀念落后等原因,中國電影在技術層面長期以來沒有形成顯著的提升,導致中國電影的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即使好萊塢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電影進入了數字化時代多年后,中國電影還仍然停留在傳統技術的年代。如《高山下的花環》這部影片,它雖然體現了中越自衛反擊戰中的戰爭故事,但并未淋漓盡致地展示出宏大激烈的戰爭場面。
隨著視覺新鮮感、奇幻感、沖擊力等因素帶來的視覺體驗創新,導致了觀眾的審美觀念發生深刻的變化,這也對中國電影的創作提出新的技術要求,迫使中國電影制作人開始關注電影的技術內容,并更加強調影片所帶來的視聽表現力。自20世紀末期,中國電影制作技術團隊開始逐漸加大技術層面的投入,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綜合國力的增強,電影的視覺觀感逐步提升,制作出大批具有典型奇觀效果,技藝精湛的愛國主義題材電影。這些影片不僅大量使用了計算機合成的特效,還使用了現代技術來創造特殊的聲音效果,并使用現代化的剪輯技術來增強影片的真實感和“奇觀”。例如,《長津湖》作為一部典型的愛國主義題材電影,利用了大量高科技手段來創造奇觀。在電腦特技方面,導演黃建新介紹,片中有一些鏡頭,特技做了11個月才完成。“比如,一個CG動畫的成型需要17層才能達到要求,這還是當年膠片電影的要求,現在的8K數字電影對清晰度要求更高,要求的涂層也就更多。電影里的很多單個鏡頭都是100多人工作了11個月的成績,聚合了來自國內外的80多家特技公司。”該片不僅完全用數碼攝影機拍攝,而且還使用了許多高科技拍攝技術,包括從直升機上展開航拍,以創造出許多具有視覺沖擊力的宏大場景。比如片中多處展現大量規模龐大的爆破場面、運用多種拍攝角度體現美軍飛機轟炸的壓迫感場景以及冰雕連悲壯場景等,都為觀眾帶來了巨大的“奇觀”效果。影片中的戰爭場面極其逼真,令人嘆為觀止。
因此,渴望在屏幕上獲得感官刺激和獨特的視覺效果,以得到觀眾的審美“驚喜”,是這類現代化作品創作的主要動機。影片產生的語義效果不僅取決于畫面的內容,還取決于某些物質手段。而技術手段在主旋律電影中的作用超出了其本身的價值,電影的技術化不但成為愛國主義電影創造“奇觀”的比較有效和廣泛使用的手段,而且還具備了相應的視覺審美價值。這意味著,現代電子信息技術打破了傳統的現實主義審美模式,通過寫實、傳真和表演創造了模擬和現實主義,在屏幕上創造和產生了新的真實美感。這種審美是技術和物質文明快速發展的結果,也是電影成為民眾消費文化的必然結果。在后現代語境下,社會的文化逐漸變成一種消費性的、以視覺為導向的文化,電影便是這種視覺奇觀的消費。
這種“奇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愛國主義題材電影,在影片《高山下的花環》中出現了大量具有明顯的地域色彩的“奇觀”,影片通過“奇觀”展示了當時特定的自然和政治環境。例如:在電影開頭的片段中,云南邊境的山脈和懸崖奠定了雄偉和莊嚴的基調,具有視覺與精神的強大沖擊力;通過展示《人民日報》中的文章內容來表現戰爭形勢,并通過香蕉樹這一特殊的植物,暗示自然空間的變化,體現士兵們開始向中越邊境進軍的進度。但是,當時的電影創作對“奇觀”的使用還沒有達到完全自如的程度,“奇觀”在影片中的展現比例也比較小,更貼近真實場景和電影內容的主題表達,還沒有達到“夸張”的程度。
而影片《長津湖》則不同,在這部電影中,巧妙地使用了“大河”等意象以展現家國情懷。電影開頭的場景是在漁船上,伍千里帶著哥哥伍百里的骨灰盒回到戰后的家,對著船夫吹起了哨子,驚飛一串水鳥,就在這時,作為連長的伍千里終于回歸了現實。船號和沖鋒哨在此時此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造就了完美的沖突。而當伍千里再次出發時,與他回家之初的特寫不同,在遠景畫面中,船浮在水面上,身后的背景是岸上的房子,大河在他面前展開,泄流而下……當鏡頭切換到雷公時,觀眾看到他已經受傷流血, 但此時他正在哼唱《沂蒙山小曲》。對故鄉山水的懷念和渴望,是中國千萬里河山的縮影,也暗指著千萬人用生命守護的鄉土。
如果對一個地域的文化進行凝練,那么就可以稱之為民俗,民俗奇觀化就是地域文化資源的精華凝結,也是地域文化能夠進行弘揚和傳承的有效手段。民俗奇觀化是文化資源的有效組成部分。
以國際化的視野來觀察區域文化特性,就是民俗的國際化,民俗奇觀化是本土文化國際化的必然趨勢,是文化輸出的必然選擇之一,在國際上推廣地域文化的必然之路。
(三)敘事內容:從虛構的故事到真實故事的改編
意識形態的傳播不應該讓接受者感到是被灌輸的,或是具有距離感,不然就可能會導致來自接受者的抵觸。在意識形態轉移中,消除虛幻的感覺是非常重要的。愛國主義題材電影也開始從完全虛構故事逐漸演變為基于真實故事改編。目前,圍繞“將真實事件拍成電影”這一話題還沒有明確定義和統一的概念,不過這類作品通常是基于現實生活中的事件而改編的。根據拉康的“鏡像理論”,在觀看電影時,觀眾會不自覺地與電影中的主角產生共鳴,尋找自己的影像,并試圖將自己的欲望和想法與影片中的人物聯系起來。在自己和角色之間建立一種情感聯系之后,進而在角色的行動和動機中尋找對自我觀點的認同。影片以現實生活中的情節為基礎,并對選定的主題進行藝術化表達,是創作者圍繞現實社會事件進行的藝術性改編,使得電影成為普及推廣藝術的重要途徑。
就“基于真實事件”的電影而言,往往會更好地傳遞情感并思考問題。它一方面能在重現真實事件的前提下,通過藝術細節和情節沖突,可以更迅速、更直接地抓住受眾的情感痛點,同時將影片的重點放在事件發生的實際情況上,并從多個角度體現不同的觀點,重現每個角色所面臨的問題。這可以使觀眾能夠更好地與電影產生聯系,并聯想起現實世界的處境等,進而喚起人們的情感共鳴與認同,而這也正是“以真實故事為基礎改編”電影的魅力所在。“以真實故事為基礎改編”電影的目的并不是要成為一部展示“真實故事”的電影,也不是為了簡單地再現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或為受眾提供一種娛樂性的新奇事物,而是試圖通過藝術化再現和操縱現實生活中的事件,讓觀眾可以更深入地研究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潛在問題,然后對電影進行反思。當觀眾與電影所傳達的價值觀產生共鳴,并在客觀和理性方面認同這些理念時,就實現了二次認同。電影《高山下的花環》是根據同名小說進行改編的,故事情節與敘事背景更接近于虛構;而《長津湖》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事實增加了電影敘事的真實性,也使受眾更容易接受故事的邏輯,從而接受電影想要傳遞的理念和價值觀。影片再現了戰爭中的大部分歷史事實和場景,讓觀眾感受事件的真相,實現一次認同,然后通過強化特殊情節和細節展示,讓觀眾深入到影片的故事情節之中,讓他們對這一歷史事件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民族歸屬感,最終實現二次認同。
結 語
從《高山下的花環》到《長津湖》在敘事主題方面,已經從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簡單敘述轉向民族情感化,這與社會多元化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敘述話語方面,它實現了從較低技術到奇觀的轉變,反映了在經濟發展的背景下藝術審美形態產生的轉變,藝術化地再現了真實的歷史;在敘事內容方面,它從虛構的故事轉為對真實故事的改編,使電影具有真實性,并將意識形態宣傳和個人情感訴求結合在一起,滿足了國家意識形態、社會大眾民族凝聚力的意識期待和個人民族自豪感的需求。
邁入新時代,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愛國主義題材電影始終在持續不斷地變化發展,其生存和普及的環境也將更加嚴峻。如何彌合政治理念與大眾文化心理之間的差距,怎樣解決政治傳播意圖與藝術審美規律之間的分歧,怎樣把握商業目標與電影行業道德意識之間的尺度,能否在政治價值和商業價值中獲得新生,這些都是有待探索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