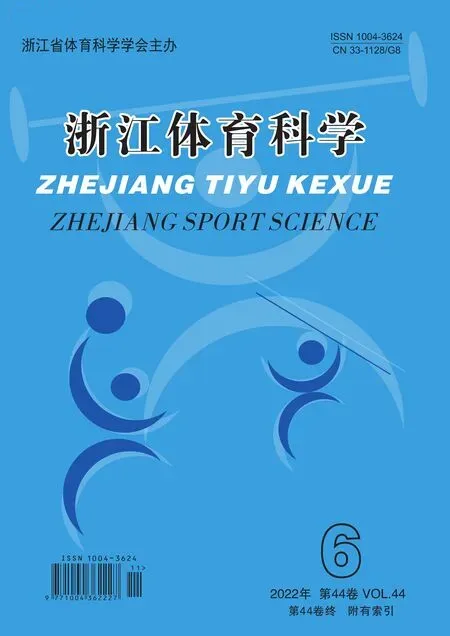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大學生健身需求與行為變化特征研究
王守都,黃曉州,葉星理
(1.溫州醫科大學 體育科學部,浙江 溫州 325035;2.浙江科技學院 體育部,浙江 杭州 310023)
新型疫情既給大學生身心健康帶來了嚴峻考驗,也引起其健身心理與需求的變化,并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關注。韓拓等人通過對405名大學生在線調查,發現近半數的大學生在居家隔離期間存在著抑郁、焦慮、壓力等負性情緒[1];周潔通過運用焦慮自評量表(SAS)對南京3所高校大學生進行測評,結果顯示,在大學生新型疫情期間普遍存在著焦慮情緒,其焦慮程度(SAS評分為38.40±7.77)高于中國常模(SAS評分為33.80±5.90,P<0.0001),而平時以及疫情期間經常參與體育活動的焦慮程度(SAS評分分別為37.80±7.83、37.35±7.80)則低于非經常參與體育活動的大學生(SAS評分分別為38.71±7.72、38.69±7.73),即大學生疫情期間的焦慮程度與大學生的體育鍛煉水平相關,鍛煉水平高則負性情緒低,鍛煉水平低則負性情緒高[2];朱佳睿等人以心境狀態量表(POMS)、鍛練誘導情緒問卷為研究工具,對武漢某高校180名在校大學生進行比較實驗,結果顯示鍛煉后實驗組被試的TMD分數顯著降低,且實驗組后測的積極投入分量與正向情緒分量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與TMD分數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說明體育鍛煉對大學生情緒具有重要調節作用[3];晏思怡等人通過對深圳市某高校調查,發現大學生每周鍛煉次數、時間及強度較疫情前有所下降[4]。這些研究論證了體育健身的重要性,但對于大學生健身需求與行為變化特征缺乏深度分析。事實上,在疫情常態化背景下,“鍛煉抗疫”已成為大學生參與體育的普遍價值追求。深入分析其健身需求與行為變化特征,對于深化高校體育教學改革、創新供給體育健身產品,具有重要價值。
1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浙江L大學學生健身需求與行為為研究對象,隨機抽樣954名大學生,其中男性大學生數量為492人,占比51.57%;女性大學生數量為462人,占比48.43%。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獻資料法。以“大學生”“新冠疫情”“健身動機”“健身行為”為關鍵詞,運用中國知網數據庫,搜索、整理和分析相關文獻,為概念界定與問卷設計奠定基礎。
1.2.2 問卷調查法。通過微信群發布“問卷星”,共回收977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23份,回收有效問卷954份,有效回收率為99.65%。參考相關文獻,自行設計問卷,根據專家意見和建議修改后定稿;本研究中健身需求、健身行為、影響因素題項的Cronbachα系數為0.88。問卷內容涵蓋調查對象基本信息、調查對象健身需求、行為及影響因素等。
1.2.3 數理統計法。使用SPSS22.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對體育健身的需求、行為及影響因素各維度的測量指標進行描述性統計,并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疫情前后大學生健身動機、行為及影響因素的變化。
2 結果與分析
2.1 疫情前后大學生體育健身需求變化
疫情發生后,大學生普遍認為體育健身對于增強體質、抗疫能力具有重要價值,通過體育健身實現增強體質和免疫力、燃脂塑身、緩解壓力、社會交往等目的,成為大學生的自覺追求。正因如此,大學生普遍對其有著強烈的需求。調查顯示,疫情發生前,大學生普遍需要體育健身,其中,表示“非常需要”“需要”的分別占比11.23%、53.52%,疫情發生后則分別占比25.42%、66.14%,需求度大幅提升。這說明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希望體育健身增強身體“免疫”“抗疫”能力。
進一步分析可知,大學生體育健身需求并非僅僅是量的增長,而且也發生了質的變化。調查顯示,疫情發生前,大學生傾向于精神層面的需求,即以體育健身滿足其精神追求,其中,體育健身動機為緩解壓力、燃脂塑身、社會交往的分別占比27.15%、25.13%、20.14%,而體質健康動機為增強體質及免疫力的分別占比12.33%、9.22%。疫情發生后,大學生體育健身的動機開始從“精神追求”轉向體質健康,其中,體育健身動機為緩解壓力、燃脂塑身、社會交往的分別占比9.21%、17.12%、7.23%,相比疫情前分別減少了17.94%、8.01%、12.91%;而體質健康動機為增強體質及免疫力的分別占比33.32%、28.97%,相比疫情前分別增加了20.99%、19.74%。這一方面反映了大學生生命意識的增強,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通過體育健身增強抗疫能力的自覺追求。
2.2 疫情前后大學生體育健身行為變化
表1列出的主要是樣本學生體質健康自評結果。結合表內數據可知,約有20.0%的樣本大學生認為自身身體健康狀況優秀,而僅有0.3%的樣本大學生認為自身身體健康狀況不良。這無疑說明:絕大多數新生代大學生對于自身的健康狀況都是有所關注,并且持以健康、積極的肯定態度的,而自我認知度越高,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可以促使大學生愈發關注自身體質健康,從而為擁有健康體質提供保障。

表1 樣本大學生體質健康自評結果
表2列明的為樣本大學生身體健康指數BMI數據。簡單來說,即身體質量指數=個體體重公斤數÷其身體米數的平方,是現今國內外通用的用以衡量個體實際肥胖程度以及真實健康狀況的數據指標。在我國,身體健康指數BMI參照標準主要分為偏瘦、正常、超重三類。偏瘦為<18.5,正常為18.5-23.9,超重為≥24。結合表2所示可知,所調查大學生中,有52.7%的樣本大學生身體健康指數BMI正常,34.2%的樣本大學生身體健康指數BMI偏瘦,13.1%的樣本大學生身體健康指數BMI偏胖。由此可見,我國高校大學生身體健康狀況本就亟需重視。

表2 樣本大學生身體健康指數BMI數據
而分別把每周體育健身次數分為不足1次、1~2次、3~4次、5次及以上,每次健身時間分為不足0.5h、0.5~1h、1~2h、2h等4個標準,分別賦值1~5分;把每次健身強度分為高、中、低、輕微等4個標準,分別賦值1~4分。并以性別為變量,對上述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大學生疫情前后體育健身行為差異較為顯著(詳見表3)。

表3 疫情前后男女生獨立樣本T檢驗
當然,從疫情期間的大學生身體以及心理健康兩方面進行進一步男女獨立樣本心理變化調查還可以發現:疫情居家隔離期間,近一半大學生都體重增加;70.2%的樣本大學生更是表示隨著睡眠時間增加,自身的體育鍛煉意識也相應提高,心理素質考驗得益于體育鍛煉而一定程度朝向積極、正面,面對鋪天蓋地的疫情新聞,樣本大學生多是有選擇性的閱讀觀看,不使自身長時間處于焦慮、煩亂狀態,但能始終堅持每日鍛煉的學生僅在少數,具體數據詳見表4。

表4 疫情期間大學生身體以及心理變化情況
整體而言:將疫情前后進行對比,大學生認識到疫情常態化后,大部分對于體育鍛煉的態度都呈上升趨勢,僅少部分學生表示不再持續進行特意鍛煉。由此可見,疫情出現后,大學生對待體育運動的態度實際上是有很大變化的。而大學生對于體育運動的態度改變,不僅是大學生健身需求發生了變化,也說明大學生的健身行為會同步變化。所以,大學生體育健身認知的深化、需求的增長,促進了大學生體育健身行為的變化。從橫向看,在疫情發生之前,男女生體育健身行為呈現出顯著性差異(P<0.05)。男生在每周體育健身次數、每次體育健身時間、體育健身強度上明顯高于女生;在疫情發生之后,男生在每次體育健身時間、體育健身強度上明顯高于女生,雖然男女性在每周體育健身次數上并無顯著差異,但女生之間的差異較為顯著。從縱向看,與疫情發生之前相比,男生每周體育健身次數、每次體育健身時間、體育健身強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女生在每周體育健身次數上有所提升,但其每次體育健身時間、體育健身強度上卻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2.4 疫情后大學生體育健身行為變化的影響因素
從上述分析可知,疫情后大學生體育健身認知、需求與其體育健身行為相悖。從理論上講,大學生對于體育健身價值功能認知的深化、需求的增長,必將帶來大學生每周體育健身次數的增加、每次體育健身時間的延長、每次體育健身強度的增加,但事實并非如此。凱爾曼態度理論告訴我們,人的態度變化包括依從、認同和內化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個體思想認知尚未融入自身的價值體系之中,其認知與行為存在非一致性特點;第三個階段,表明個體思想認知已融入其價值體系之中,其認知與行為便呈現出一致性的特點[5]。從調查情況看,雖然大學生充分認識到體育健身的多重價值功能,但這認知與其體育健身行為的相關性卻較低(見表5),相比疫情前、疫情期間及疫情后大學生不僅深刻認知體育健身具有增強體質、提高免疫力、緩解壓力、燃脂塑身、社會交往等價值功能,而且體育健身需求大幅增長,但體育健身次數、每次體育健身時間、體育健身強度卻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大學生對于體育健身的認知還停留在依從、認同階段,尚未將其融入自身價值體系之中。進一步分析,大學生體育健身的知行矛盾主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影響。

表5 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大學生體育健身認知與參與行為的相關性 N=954
結合浙江L大學實際情況,總結和提煉為性別、體育場地、健身設施、宣傳教育、學校要求、同學影響、學校健身氛圍、激勵、體育教程等10個影響因素。以大學生是否參與體育健身(1=參與,0=未參與)為因變量,以10個影響因素(賦值均為1=是,0=否)為自變量,進行二項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6)。

表6 疫情后大學生體育健身影響因素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N=954

表7 疫情后大學生體育健身影響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N=954
通過對9個影響因素進行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7),結果顯示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有7項,即場地不足、設施缺乏、宣傳缺失、學校要求、同學影響、健身氛圍、體育教學。然后對這7個自變量進行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體育場地、健身設施、宣傳教育、學校要求、同學影響、學校健身氛圍、體育教程等7個因素,與大學生體育健身行為有關(P<0.05)。
3 結論和建議
3.1 結論
3.1.1 在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大學生對體育健身的價值功能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不僅重視精神層面的滿足,更為重視體育最本質的功能,即通過體育健身,增強體質和免疫力。
3.1.2 在疫情常態化背景下,大學生體育健身認知、需求與其體育健身行為相悖,相比疫情發生前,其大學生每周體育健身次數、每次體育健身時間、每次體育健身強度存在明顯下降。
3.1.3 大學生每周體育健身次數、每次體育健身時間、每次體育健身強度的下降,與場地不足、設施缺乏、宣傳缺失、學校要求、同學影響、健身氛圍、體育教學等因素相關。
3.2 建議
3.2.1 加強體育健身宣傳教育,營造濃厚的體育健身氛圍。高校應依托校園廣播、校刊校報、校園宣傳欄等傳統媒體以及互聯網、新媒體等,加強體育健身教育宣傳,并邀請醫學領域、疫情防控領域專家學者進入高校,以線下講座或者線上網課的方式開展健身宣傳并答疑解惑,增強大學生體育健身的自覺性與自主性,在全校培育濃厚的體育健身氛圍。特別是在高校更好地推動“健康中國”戰略計劃,真正意義上提高大學生健身危機意識,幫助大學生認知自身身體健康條件。
3.2.2 完善高校體育設施。深入了解大學生群體的健身時間、健身項目,有針對性地明確體育健身基礎設施建設工作重點,提升體育健身基礎設施建設工作的針對性。在疫情常態化背景下,高校仍然面臨著重新回歸封閉式管理的可能性,這將加劇大學生體育健身需求與校內有限的體育健身資源之間的矛盾。高校應優化體育健身設施管理制度,提升體育健身資源調度與管理水平。例如,注重線上體育與線下體育相結合,有方向、有目的地既完善線下校園體育鍛煉設施,又同時加快在線體育平臺開發與利用。在此,以依托于直播平臺而推出的校園線上運動項目為例,相關工作人員以“人性化”“趣味化”為準則,根據學生群體需求,利用學生喜歡的彈幕互動功能,引導學生在抖音平臺積極運動打卡,相互促進。
3.2.3 深化體育教學改革。體育課堂是培養學生健身意識的主要陣地。高校應基于大學生體育健身需求,完善體育教學內容,豐富體育健身產品供給。積極探索現代教育技術與體育教學實踐融合路徑,增強教學技術、教學手段與教學模式之間的契合性,提升體育教育教學質量。長此以往,疫情常態化背景下的新生代大學生不僅可以自主重視體育健身,對體育健身有主動性、積極性,還可以接受更加健康的運動理念指引,在“文體兼顧”模式下,掌握更多的體育知識與健身技能,切實增強自身免疫力、抵抗力、抗壓力等個人素質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