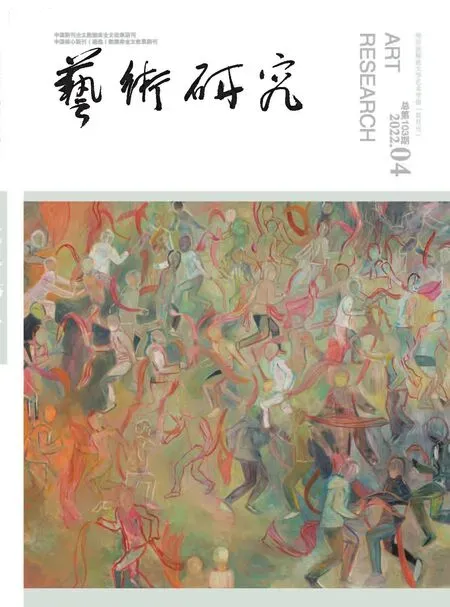由牛長鑫表演藝術(shù)看河南曲劇“牛派”生行表演體系的形成
南陽師范學院音樂學院/朱 意
牛長鑫是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河南曲劇項目省級傳承人,主工老生,是劇種發(fā)展的關(guān)鍵人物,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以牛長鑫為代表的曲劇老生行當被稱作“牛派”,成為曲劇的一支主要流派。他的表演唱做俱佳,具有數(shù)量多、戲路廣、密度高的特點。
一、“牛派”博采眾長的唱腔
河南曲劇作為一個年輕的劇種,上個世紀初才由街市走上戲臺,由鄉(xiāng)村走向城市,逐漸發(fā)展壯大,雖然各地劇團有如雨后春筍逐漸成立、發(fā)展、繁榮,但劇團及戲校對演員普遍沒有一套系統(tǒng)、規(guī)范的戲曲聲樂訓練方法,而牛長鑫自幼學習南陽大調(diào)曲子,為創(chuàng)腔打下良好的基礎(chǔ)。他的過人之處在于,善于學習和總結(jié),既向本行當?shù)乃嚾藢W習,同時也向不同行當?shù)难輪T學習,在發(fā)聲技巧、度曲等各方面學習他人長處為己所用,結(jié)合所扮演的人物,將自己在演唱大調(diào)曲子時的度曲技巧運用在曲劇演唱中,逐步建立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唱腔系統(tǒng)。牛長鑫對河南曲劇老生行當唱腔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南陽大調(diào)曲子韻律的特色創(chuàng)腔
牛長鑫受父親牛潤芝的教導,自幼學習南陽大調(diào)曲,長期的耳濡目染使他熟練掌握大調(diào)曲子的咬字行腔。在后來的曲劇舞臺實踐中,他始終堅持用大調(diào)曲子的行腔方式來處理自己的演唱。
河南曲劇音樂上的母體是大調(diào)曲子,其曲牌由大調(diào)曲子衍生而來。大調(diào)曲子只“歌”不“舞”,講究韻味,曲牌眾多,其中不少大曲牌字少腔多,不便于歌舞,由此衍生出許多小曲牌,為曲劇所用。曲劇中除“小漢江”及“上流”中的“垛子”與南陽大調(diào)曲子略有不同外,二者本質(zhì)上屬于同一曲種。曲劇將大調(diào)曲子中的小曲牌搬上舞臺成了“曲子戲”,以歌舞演故事。
大調(diào)曲子的長期訓練使牛長鑫在演唱曲劇時更加得心應(yīng)手,尤其在字韻上嚴謹?shù)刈裱笳{(diào)曲子的歸韻收音規(guī)范,曲詞設(shè)計中沒有與戲文無關(guān)的閑字,不為盲目追求聲音的響亮而跑韻。如曲劇《夜審潘洪》中唱段“萬歲爺傳口諭我的心情沉重”的“萬”字,他嚴格遵守戲曲吐字發(fā)音“字頭、字腹、字尾”的過程,咬字時突出圓唇音“wu”,強調(diào)字頭,歸韻時突出前鼻音“n”,強調(diào)字尾;又如“重”字,韻母“ong”屬后鼻韻母,由鼻腔歸韻,進入頭腔共鳴,聲如洪鐘,彰顯了寇準剛正不阿的性格特征。
戲曲聲樂要求“腔由字生”,而許多演員為追求演唱音色的響亮,通常會有意忽略一些韻律上的規(guī)范,或即興加入“啊”“呀”等無實際意義的虛字,“牛派”唱腔則堅持保留南陽大調(diào)曲子的行腔規(guī)范,因而具有濃厚的韻味,與其他生行演員有所不同。
(二)真假聲融合的生行演唱技藝
曲劇音樂來自于大調(diào)曲子、表演形式脫胎于邊走邊唱的高蹺曲子,演出中為方便演員把握,因此唱腔音域不寬,以自然聲區(qū)為主,多采用大本嗓,不用假聲。尤其是生行,人物唱腔的音高、旋律都是由男聲自然聲區(qū)的嗓音條件形成。
牛長鑫在接受筆者訪談時說:“我剛學戲的時候有位老師叫常文長,是小生行當?shù)拿恰3@蠋熖貏e擅長‘陽調(diào)’(曲牌名),唱法多變,其中一種就是二、四句翻高。”牛長鑫習得這種唱法,并在排演《武家坡》時用來演唱“大嫂傳話太遲慢,平貴站得兩腳酸,步出柳林用目看,見一大嫂把菜剜”四句。這四句“陽調(diào)”他用假聲翻高的唱法,目的是強調(diào)平貴此時的心情。“見一大嫂”心中為之一振,情緒自然高漲,隨之而來的唱腔也需要有所變化。唱由心生,若繼續(xù)使用傳統(tǒng)的唱法,不免趨于平淡,缺乏亮點,難于表達平貴激動的心情。而此處運用翻高唱法,體現(xiàn)平貴心情非常恰切,一改曲劇老生以往音域低沉的不足。經(jīng)他改革與創(chuàng)新,生行演唱技術(shù)的掣肘被破除,音域得以拓寬,唱腔色彩得以豐富。劇目題材上不再局限于“三小戲”,為曲劇演唱袍帶大戲、表現(xiàn)英雄人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早期河南曲劇主工花旦戲,但女演員幾乎沒有,大多是由男演員飾演。一些男演員為使自己適合女性人物角色,將日常生活中的行為習慣也進行了改變,媚眼含羞、裊裊婷婷,外在形象上甚至比女性更為女性化。由于女性特點深入骨髓,這些男演員在表演時形神兼?zhèn)洌雅猿粍?chuàng)作得極盡溫柔。牛長鑫學戲初期,劇團有位老師名叫喬林,工旦行,在《許仕林祭塔》中飾演白素貞,唱“上流”(曲牌名),常常尚未開腔臺下就喝彩聲不斷。牛長鑫非常喜愛喬老師的唱腔,就在自己的生行唱腔中揉進這種旦行的唱法。如,在旦行哭戲的聲腔中,為表現(xiàn)女性人物的幽怨、哽咽,常用一種“有哭音沒哭腔”的處理方法,使唱腔更為婉轉(zhuǎn)陰柔,有別于男聲的“悲聲大放”;而在《越王負荊》中勾踐的唱詞“心寒欲碎”牛長鑫就是借鑒了這種“有哭音沒哭腔”的潤腔方式,以此來表現(xiàn)勾踐此時心種有愧、有口難言的情緒恰如其分。
(三)彰顯抒情優(yōu)勢的曲牌運用
牛長鑫不僅善用抒情性曲牌,并且注重強化敘事性曲牌的抒情功能,將曲劇的唱腔優(yōu)勢最大化。如《武家坡》中牛長鑫飾演的薛平貴用了“上流”(曲牌名),“上流”原本是典型的敘事性曲牌,上下句,兩句為一單元,因其口語化、便于情感表達被廣為傳唱。
“‘曾記得妻享榮華夫受難’按照原來‘上流’的唱法起板唱,并不能唱出此時人物所思所想。三姐讓平貴敘述往事,顯然是對平貴見面卻不相認的懲罰。平貴邊想邊說,因而此句改用散板,無伴奏,為了強調(diào)‘夫受難’,打破原來‘上流’唱法的局限,加了拖腔,將人物情緒進行延伸,‘妻呀’語氣加重,從聲音到眼神盡顯平貴的重情。”“是我錯了”這句曲牌也是“上流”,若處理得原樣不變則遠達不到劇情的要求,必須對曲牌進行再創(chuàng)造,依情節(jié)需要變化而變化,以充分傳達人物情感。根據(jù)詞義的要求,用“上流轉(zhuǎn)垛”既可敘事又可抒情,慢時婉轉(zhuǎn)憂傷,快時激動昂揚,使表演節(jié)奏酣暢淋漓。
由于牛長鑫唱“上流”的次數(shù)多、掌握的唱法多,“上流”成了他制勝的武器。由他創(chuàng)腔的所有劇中人物沒有一出不唱“上流”,但凡參賽必有一段“上流”,且沒有一出戲中的“上流”是重復的。
再如,“離三關(guān)別代戰(zhàn)歸心似箭”這段唱是“詩篇”(曲牌名)。“詩篇”在曲劇中用途廣泛,唱法靈活多變,表現(xiàn)力豐富,既可敘事亦可抒情,上下句,既可兩句分開單唱,也可兩句連唱,還可根據(jù)詞的多少、句的長短,多句串連帶“剁”,調(diào)式完整,有起板也有收板。“離三關(guān)”句跌宕起伏,牛長鑫使用“詩篇”并把“詩篇”導板改為散板起唱。這是因為“詩篇”導板適合敘事,但用于抒情則過于平穩(wěn)呆板。若曲牌結(jié)構(gòu)原樣不變,就表現(xiàn)不出平貴歸心似箭、紅鬃馬飛奔跳躍的形態(tài)。原因在于,一則,導板的氣勢不夠,改用散板唱法靈活,句子可長可短,音樂可緊可慢,唱法回旋余地大,不受節(jié)奏的限制。“離三關(guān)”快速唱出,表明平貴心急如焚。當“別”字唱出時稍作停頓,突出“別”字,說明平貴心有不舍,緊接著唱出“代戰(zhàn)”二字,再次停頓唱“歸心似箭”,“似箭”兩字疾速吐出,表明歸家之心似離弦之箭,勢不可當。二則,可以利用音樂給人物的出現(xiàn)制造氛圍,開唱前利用高亢激昂的音樂,配以打擊樂,威武振奮,營造戰(zhàn)馬嘶鳴、飛馳奔騰的場面,觀眾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馬蹄聲由遠而近,人們急迫地循聲尋找,此時平貴側(cè)身出場亮相,形若流星,干凈利落,一連串動作站定,挺拔如松。雖心急如焚但不忙亂,動作沉穩(wěn)有序,整段音樂舒展流暢。
二、“牛派”推陳出新的做功身段
牛長鑫9歲學戲,10歲參加劇團,1991年進京匯報演出《情系青山》,為配合宣傳計劃生育排演《兒女傳奇》,該劇在全國現(xiàn)代戲匯演中引起轟動并被多個兄弟省份移植演出。21世紀初他排演的《驚蟄》進京匯演,并參加第七屆中國藝術(shù)節(jié),為河南戲曲爭得榮譽。他所在的南陽市曲劇團自建團以來,不斷上演緊扣時代旋律的新劇目,如《小女婿》《張河灣》《不能走那條路》《將相和》《王佐斷臂》《焦裕祿》,以及文化大革命后的《于無聲處》《孔繁森》《兒女傳奇》等。
(一)打破常規(guī)的舞臺身段設(shè)計
傳統(tǒng)的曲子戲以唱功見長,表演為輔。牛長鑫認為,傳統(tǒng)要繼承,但不應(yīng)墨守成規(guī)。他對傳統(tǒng)劇目中老生行當?shù)淖龉ι矶芜M行了新的創(chuàng)作和處理,使其所在的南陽曲劇團涌現(xiàn)出一大批老生行當擔綱的優(yōu)秀劇目,《狀元媒》就是其中之一。
曲劇《狀元媒》是須生擔綱劇目,以新科狀元呂蒙正戲份最多。由于曲劇《狀元媒》的劇本設(shè)計是由呂蒙正出場“報信”開始,全無前例可查,需要演員根據(jù)具體情節(jié)進行創(chuàng)造和發(fā)揮,劇中的做功身段對牛長鑫來說亦是新的挑戰(zhàn)。
按照劇本,呂蒙正一出場就是心急如焚地去向八賢王報信,唱詞為“驚聞邊關(guān)嚇破膽,圣駕被困銅臺關(guān),這才是樂極生悲適得其反,一霎時傾國大禍在眼前”:情勢危急,報信的卻是新科狀元,一介書生,又是由須生來扮演,若按傳統(tǒng)方法來處理,則遠不能表達此時的危機,更難把呂蒙正的驚慌失措和事態(tài)的嚴重性表現(xiàn)出來。對于如何把人物內(nèi)心的焦急慌忙不折不扣地傳達給觀眾,牛長鑫做出了考慮:如果連滾帶爬以顯示十萬火急,則有失文人身份;反之,按照須生的表演循規(guī)蹈矩,四平八穩(wěn)邁著方步,甚至圓場步上場,又都與劇情不符。于是牛長鑫對舞臺動作做了如下一系列設(shè)計:在打擊樂的撕邊鼓噪聲中,只見一人頭戴烏紗,身穿紅袍,似離弦之箭向前臺奔來,一個踉蹌,險些跌倒,用踢袍動作亮相開場;腳步一刻不停,說明人在急行,這一連串的動作由內(nèi)而外地表現(xiàn)了呂蒙正的慌不擇路。具體細節(jié)為:伴隨打擊樂“三槍鼓點”聲,呂蒙正右手抓袖,左腳踢蟒,右手抓蟒袍下擺,左手端玉帶,掖蟒袍,起步發(fā)現(xiàn)襯襟礙腿,于是右腳踢襯襟,右手抓襯襟,走圓場步,快步如飛,蟒袍下擺與手中的襯襟隨著身體動作飄揚飛舞;呂蒙正內(nèi)心的焦急外化為一路飛奔,既不失文人分寸,表演節(jié)奏又恰當契合了當時的特定情景,利用踢袍端帶的舞蹈動作體現(xiàn)了戲曲的程式之美,緊扣劇情,完成了劇本要求,使人物在情景中活起來。
(二)恰如其分的動作細節(jié)把控
《狀元媒》后,牛長鑫任團長的南陽曲劇團又排演了《武家坡》,現(xiàn)為該劇團保留劇目。曲劇《武家坡》是唱做并重的一個劇目。牛長鑫認為,演員應(yīng)該用形體動作表現(xiàn)出戲文未盡之意。表演是人物內(nèi)心情感外化的手段,通過做工表演彌補唱之不足,能夠提高戲曲的觀賞性。《武家坡》好唱,“趕三關(guān)”難演。連闖三關(guān),每一關(guān)的闖法都有不同,動作繁雜,唱腔“抖韁磕蹬緊加鞭”“勒馬停蹄提城邊站”與舞蹈同步,“抖韁”句跨左腿,踢右腿,跨腿轉(zhuǎn)搓步,“勒馬”句馬鞭上膀,右手抄底,身體旋轉(zhuǎn),勒馬狀撩起,雙腳輪番跳起,做硬垛泥,穩(wěn)穩(wěn)站定。伴隨“歸心似箭”的快速唱出,聲音由遠而近,打擊樂聲大作。關(guān)于薛平貴的上場,牛長鑫采用欲擒故縱的方法,先出現(xiàn)在觀眾面前的是鮮紅的馬鞭,而不是人物,把觀眾的注意力抓住,人們聚精會神,循聲尋找,期待平貴出現(xiàn),打擊樂“四擊頭”起,人物才背對觀眾快步出場。平貴第一個亮相干凈利落,觀眾看到整體形象。之所以采用背身快步出場轉(zhuǎn)身亮相,就是要把觀眾的視線集中到人物站定之后,眼前為之一震。演員的神氣先聲奪人,雖靜止但是給觀眾的感覺還在行進之中。此時,伴隨打擊樂長鑼鼓點制造氣氛,牛長鑫連用兩個搓步來表達人物的行進速度“馬走如飛還顯慢,一路不住緊加鞭”,利用馬鞭作為舞具,言不盡處,舞蹈之。
再如“紅鬃馬四蹄奮飛塵土卷,恨不能一步跨越萬重山”。文字上就能看出此時劇情的行動趨勢非常強,如果沒有形體舞蹈的配合,語言就顯得蒼白,于是,牛長鑫采用邊唱邊舞的方式,利用抖辮、跨腿、轉(zhuǎn)身,這一套圍繞馬鞭展開的舞蹈動作使語言活起來,馬鞭在空中畫個圓圈,身體也隨之快速轉(zhuǎn)動,表示馬在飛奔,馬鞭上膀作勒馬狀,利用搓步表現(xiàn)飛奔的馬慢了下來。歌舞結(jié)合,賦予抽象的馬鞭以生命。
在“八月十五”這一大段對唱中,牛長鑫為薛平貴設(shè)定了一套“兩拍一碰”的動作。“‘一碰’指的是平貴用胳膊肘去碰寶釧胳膊這樣一個動作。”此時平貴偷看寶釧一眼,為了使她更加注意自己,平貴向?qū)氣A趨近一步,聲音提高拉長說:“故而這內(nèi)中情由”此處右手食指劃一個圓,眼睛看著寶釧“我是知道的呀”,平貴抬右胳膊肘輕碰一下寶釧,寶釧不屑地用右手掃了一下被碰的胳膊,平貴本想表示親近卻碰了個軟釘子,并不覺得無趣,反而感到能與三姐這么近距離交談是何等幸事,十八年來求之不得,為中規(guī)中矩的沉悶情節(jié)平添了趣味。
“兩拍”時的唱詞是這樣的:“他是個浪蕩子勸說不醒,平日里揮金如土兩手空,錢到手肥吃海喝胡亂鬧,從不把結(jié)發(fā)妻子放心中”。當平貴唱到:“從不把結(jié)發(fā)妻子”時,發(fā)現(xiàn)三姐對這些詆毀的話無動于衷,于是平貴靠近寶釧,抬起右手在空中劃一個圓,唱到最后三個字:“掛心中”手拍在三姐肩膀上,這是第一“拍”。
這些話三姐并不相信,平貴看三姐一如既往信任他,心中底氣更足,繼續(xù)往下唱到“空頭家書有何用,一無銀,二無糧,難道你去喝西北風。”這一“拍”的手勢動作和第一“拍”一樣,同樣要畫個圓,再拍下去,不同的是,這次不像上次那樣慌忙抬起;這次拍下去,要輕推一下加深語言的可信度,意思是“你別不信我說的話”。“形體動作是為了彌補語言表達之不足,使人物形象更加立體豐滿,絕不是為了嘩眾取寵,不能加進任何可有可無的小動作,更不可以是低級趣味的庸俗表演。”
所有這些動作牛長鑫都非常注意把握“幅度”“力度”和“速度”。如,一碰只是用肘部輕輕一碰,很快就離開,身體與三姐還有一段距離。兩“拍”只能用手指的指尖輕點一下,立刻抬起,絕不可以用手掌接觸,連第二“拍”的一“推”也是點到為止。封建社會男女授受不親,不用說肌膚接觸,即使是言語交流,也不便面對面進行。平貴的身份和修養(yǎng)要求他必須堂堂正正、守規(guī)循矩,不能有半分失禮和不敬,因此分寸的把握很重要。再如寶釧唱“我問他好來”,平貴緊接“他倒好”只有三個字,為強調(diào)語言的含義,用右手拇指指腰部,眼睛看著寶釧,意思是“你還不明白嗎?”當語言含義不明晰的時候,形體動作做補充,對方偏又只聽不看,不解其意,觀眾替劇中人著急,而劇中人卻一無所知,揣著明白裝糊涂,可看性強,妙趣橫生。這種輕喜劇的表演方式,身體接觸一旦過“度”,就會將平貴演成輕狂的莽夫,因此牛長鑫非常注意故事發(fā)生的時代背景,嚴格控制動作幅度不隨意不夸張。
塑造薛平貴的過程中,在程式表演的基礎(chǔ)上,牛長鑫大膽采用了貼近生活的演法。“戲中三次拍掌、攤手的動作,傳統(tǒng)的演法是,先用兩手畫一圓圈,一只手握拳,擊掌心,雙手推出亮相。”按照生活中人們兩手平攤表示無奈的手勢,稍加變化用在平貴的表演中,使觀眾感到,平貴雖身居高位,但質(zhì)樸的個性依然未變。
除《狀元媒》《李白戲奸》外,南陽曲劇團排演的《越王負荊》(1984年)《哭廟》(1980年)《寇準背靴》等,均是須生擔綱戲,在這些劇目中牛長鑫對曲劇須生的做功身段進行了進一步地創(chuàng)造和發(fā)揮,并在《驚蟄》《楝樹坡》等時事新戲中依舊孜孜不倦地進行創(chuàng)新。《武家坡》《狀元媒》等劇目的上演,奠定了河南曲劇“牛派”生行做功表演的基礎(chǔ)。此后長期的舞臺實踐中,各類劇目的排演,無論是傳統(tǒng)袍帶戲,還是新編時裝戲,老生行當?shù)淖龉Ρ硌荻际窃诖嘶A(chǔ)上的進一步完善。
三、“牛派”風采各異的人物形象
牛長鑫塑造了一個又一個鮮明的河南曲劇老生行當人物形象,主要舞臺人物形象有:古裝戲《夜審潘洪》中的寇準、《困皇陵》中的宋太宗,《屠夫狀元》中的黨金龍,《王佐斷臂》中的王佐,《孫安動本》中的孫安,《狀元媒》中的呂蒙正,《李白戲奸》中的李白,《武家坡》中的薛平貴,《睢陽恨》中的賀蘭進明,《游龜山》中的田云山等;現(xiàn)代戲《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平原作戰(zhàn)》中的趙永剛,《驚蟄》中的父親,《情系青山》中的鐘青山,《楝樹坡》中的丁德山、《智取威虎山》中的李勇奇,《孔繁森》中的孔繁森等。李白的狂放不羈,呂蒙正的恭敬謹慎,寇準的干練機智,趙光義的沉穩(wěn)威嚴,越王勾踐的霸氣高傲、不可一世,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他的表演樸實無華,情感真摯,唱腔韻味醇厚,藝術(shù)風格獨樹一幟。其代表性唱段被廣為傳唱,深受群眾喜愛;除了源于他幼時學習大調(diào)曲子為演唱打下夯實的基礎(chǔ)以外,也與他遇到角色酷愛琢磨鉆研的習慣有關(guān)。
(一)查漏補缺的角色解構(gòu)
牛長鑫素來有記日記的習慣,在檢查和記錄中查漏補缺,總結(jié)經(jīng)驗,對自己飾演的每一個角色,首先研究角色定位,解析角色性格及成因,接下來尋找表現(xiàn)該人物的途徑和方法,使表演和人物性格、戲劇沖突的發(fā)展產(chǎn)生密切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進行藝術(shù)重構(gòu),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自己的表演流于表面。
父親牛潤芝對牛長鑫的文化素修一直非常重視。從10歲開始,每排一部戲,都要給他講解所扮演人物所處的朝代,與人物的關(guān)聯(lián)等。雖然戲文不同于寫實的史書,故事可以杜撰,但情節(jié)要力求合理。演越王勾踐,父親要求他看《東周列國志》;演《鳳凰嶺招親》,父親讓他看《宋史演義》。演小生的時候,《紅樓夢》他看過三遍。演《李白戲奸》的時候,他必須每天抄寫一篇李白的詩詞,從作品中來感受詩人的人生境遇和性格特點。
南陽曲劇團重排傳統(tǒng)劇目《武家坡》,牛長鑫擔綱主演薛平貴。平貴與寶釧的故事只是傳說,無史可查。若設(shè)定薛平貴的身份家世僅僅是個沿街乞討的花郎,怎能有如此武藝能夠降服紅鬃烈馬。怎樣表演,有何根據(jù),如果無的放矢,必然無所適從。為了讓表演有所依托,符合情理,牛長鑫設(shè)定平貴的父親為國捐軀、家道中落,平貴在逃難中流落街頭,沿街乞討,并非普通的乞丐。寶釧招親時見他氣質(zhì)不凡因而拋彩球并贈金相助。人物的行動路線有了心理依據(jù),表演起來就會得心應(yīng)手。
(二)同“行”不同“形”的類比分析
即使是同類型的角色,牛長鑫也會在排演中根據(jù)具體情況來選擇相應(yīng)的處理方式。他所在的南陽曲劇團先后于1980年、1984年排練創(chuàng)作了《哭廟》《越王負荊》兩劇目,都是須生擔綱戲,角色有很多共同點:都是帝王,年齡相近;戲的后半場都有大段哭戲。行當同樣是“王帽老生”,同是哭戲,具體處理形態(tài)卻大不相同。
想要塑造好宋太宗趙光義和東周列國霸主勾踐這兩個人物形象,首先要找出他們的不同點。雖然他們身份地位相同,但兩人個性不同:戲文中的趙光義襟懷坦蕩,勾踐心胸狹窄、濫殺無辜。所處環(huán)境也不同:趙光義被圍困情勢危急;勾踐是外敵入侵,內(nèi)部造反眾叛親離。雖都是哭戲,但心事各有不同:趙光義是“悲聲大放”,而勾踐卻是“心寒玉碎”,所以就決定了兩個人的哭法大不相同。找準心理,哭出不同,人物性格自然就有區(qū)分。
以上兩個唱段對用腔的要求迥然不同,因而必須在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新。兩唱段的開始用的都是“哭掃板”,根據(jù)人物情緒需要,牛長鑫對趙光義的扮演采取快節(jié)奏,開唱前用音樂烘托出強烈的氣氛,給人物情緒爆發(fā)以鋪墊,使趙光義的“悲聲大放”不感到突然。唱腔的處理猶如山洪爆發(fā)一發(fā)不可收,“趙光義跪太廟悲聲大放,哭了聲眾先王,我再哭了聲兄王玄郎”幾句唱腔一氣呵成,伴隨形體上渾身顫抖,利用胡須的抖動,配合唱腔將劇情推向高潮。
勾踐唱的同是“掃版”,牛長鑫把勾踐的“哭掃板”處理成了氣急敗壞的“喊”。當勾踐聽到外地入侵,情勢危急,文武百官卻要棄他而去,他無兵可派無將可遣,眼看國將不國,慌了手腳,顧不得體面。按常理此時該有音樂聲起,但是為了突出勾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可悲可憐,牛長鑫采取無伴奏演唱,全場所有人都背對他,任憑他大聲呼喊,空蕩蕩的舞臺全留給他,留他一人滿臺亂跑,大聲疾呼“慢來慢來”。“眼看江山欲墜,國是日非,你們?nèi)魲壒露ィ山泄峦跷已稣陶l?”雙手平攤,顧盼左右,可憐可悲、妄自尊大的帝王形象躍然眼前。
四、“牛派”刪繁就簡的劇本改編
除了唱功和做功上的傳承與創(chuàng)造,牛長鑫還在老劇新排的過程中對傳統(tǒng)劇目的劇本進行了增刪,對唱腔和唱詞進行重新創(chuàng)作。
(一)突出主線的劇本增刪
為使劇情和戲劇沖突更加集中,在重排劇目時,他把一些與主線關(guān)系不大的枝節(jié)能刪除的盡量刪除,實在刪不去的盡量處理在內(nèi)場,例如曲劇《武家坡》中,牛長鑫根據(jù)自身舞臺實踐,將劇本刪繁就簡,去除細枝末節(jié),重新整理和創(chuàng)造,集中筆墨放在主要人物身上,整場戲主線人物只留有兩個:王寶釧與薛平貴;集中講述武家坡前夫妻相會的故事,用有限的時間充分展示主要人物,抒發(fā)內(nèi)心情感,將故事情節(jié)說清講透。為發(fā)揮曲劇長于抒情的優(yōu)勢,原劇本寒窯前夫妻的對唱,本是幾句唱詞就過的部分,在重排的時候大幅展開,讓平貴和寶釧雙方各自把十八年的經(jīng)歷和思念講述一遍,為兩人分別增加了大段唱詞,唱者酣暢淋漓,聽者盡興過癮,使觀眾充分了解人物經(jīng)歷,加強對故事的理解,人物形象更加完整。
(二)拋棄封建糟粕的真情實感
在戲曲情節(jié)的處理上,牛長鑫認為戲曲要與時俱進,符合現(xiàn)代觀眾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僅體現(xiàn)在演唱技術(shù)上,更要表現(xiàn)在審美觀念上。劇目《紅鬃烈馬》傳統(tǒng)版本中體現(xiàn)薛平貴封建男權(quán)思想的念白與唱詞有很多,如“想俺平貴,離家一十八載,不知她的貞潔如何?看四下無人,我便調(diào)戲一番便了”。在對劇本的再創(chuàng)作中,牛長鑫把平貴用“銀兩試探”、寶釧“下跪掏封”這些情節(jié)全部刪掉,將薛王夫妻二人放在平等的位置,而不是把平貴擺在夫權(quán)的位置上,高高在上,盛氣凌人;將猥瑣的調(diào)戲變?yōu)榉蚱揲g的逗趣。牛長鑫認為:“王寶釧具有高貴的氣節(jié),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如果她看重榮華富貴,就不會離開相府苦守寒窯;如果平貴自詡高高在上,思想上男尊女卑,也不會拋下西涼榮華富貴,歷盡艱險逃脫代戰(zhàn)公主的追趕來尋找結(jié)發(fā)妻子。”他分析,平貴對三姐充滿了敬重和感激,更多的是愧疚而沒有蔑視,更不應(yīng)有懷疑,因此將這里的唱詞設(shè)計為“離三關(guān)別代戰(zhàn)歸心似箭,一路上花花美景無心觀。紅鬃馬四蹄奮飛塵土卷,恨不能一步跨越萬重山。渴飲清泉水困在馬上眠,遙望長安古樓現(xiàn)。破瓦寒窯在城南,十八年前朝離散,別夢依稀在眼前。心急只嫌馬行慢,武家坡前會寶釧。”十八年后,武家坡前,夫妻之間悲喜交加,夫?qū)ζ蘩⒕胃屑ぃ迣Ψ蛏钋械肽睿适碌那楦谢{(diào)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使《武家坡》對薛王二人夫妻情分的展現(xiàn)達到了高度的藝術(shù)真實。
(三)明確戲劇情境的唱詞設(shè)計
“離三關(guān)別代戰(zhàn)歸心似箭”這是《武家坡》中薛平貴的第一段唱。此樂句按照傳統(tǒng)的表達是“一馬離了西涼界”,這樣的唱詞詞義含糊,交待情境不準確,人物身處何地、要到哪里、是什么樣的心情都無明確的表述。這樣唱雖然可變性強,容易處理,但個性不鮮明,細節(jié)不突出,與整出戲的情節(jié)聯(lián)系不夠緊密。牛長鑫將這句改為了“離三關(guān)別代戰(zhàn)歸心似箭”。緊扣劇情,人物所處地點哪里、情緒如何,都交代得清楚明了,能夠準確反映出此時人物的心境。
五、結(jié)語
牛長鑫作為河南曲劇老生行當?shù)拇砣宋铮诙嗄甑奈枧_實踐中,博采眾長,結(jié)合自身優(yōu)勢,在保留傳統(tǒng)唱腔韻味的同時,根據(jù)新時代先進文化發(fā)展的需要不斷推陳出新,從唱腔、做功身段、劇本創(chuàng)作和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建構(gòu)起了曲劇“牛派”的表演藝術(shù)體系。大量“牛派”優(yōu)秀劇目的不斷涌現(xiàn),使河南曲劇擺脫了“三小戲”的藩籬,一個由地方曲種發(fā)展來的戲曲劇種,現(xiàn)位列河南省第二大劇種,并流傳至全國各地。以牛長鑫為首的南陽曲劇團仍在不懈努力,創(chuàng)作排演了《丹水頌》等緊扣時代脈搏的時事新戲。河南曲劇的成長,“牛派”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