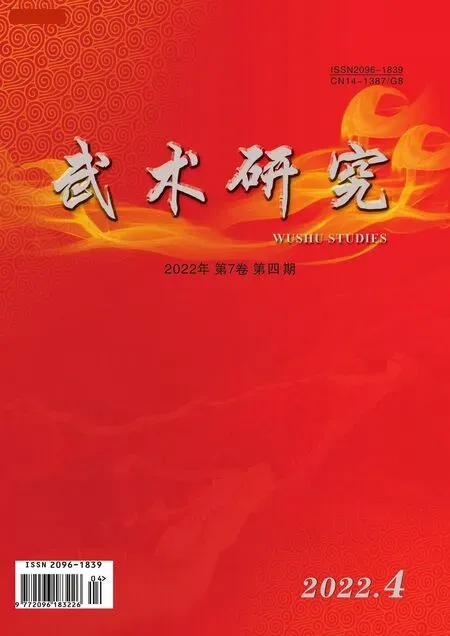哲學視閾下武術散打“戰術原則”運用探析
劉建芳 江志強 褚玉杰
南昌交通學院體育學院,江西 南昌 330100
哲學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思想體系,是人類文化的核心,是通過對某一領域中核心概念的深刻分析來揭示該領域中的觀念預設和思想邏輯,解說該領域的主要思想觀念,進而為解決該領域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提供方法論的研究活動。所謂武術散打戰術的表現,主要指的是散打選手在訓練以及比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靈活多變的戰術行動以及戰術形式。武術散打作為中國武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凝聚著從古至今傳統武術中優秀的戰術思想,這些優秀的戰術思想受古典哲學、戰略學和軍事學的影響下能夠靈活運用是對中國傳統武術文化和武術散打戰術思想的一種傳承與發展。
1 在哲學視域下對散打“戰術原則”運用的闡釋
1.1 知己知彼,戰術之理
“理”被認為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主題,是通向“道”的邏輯所在,是人們說話或行事遵守的客觀規律,是一種本體存在。因此戰術之理是散打戰術發展的認知,是散打戰術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孫子·謀攻篇》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知己知彼是孫子兵法的中心戰術思想,是軍事戰爭中不可忽略的戰術因素,也同樣是進行散打實戰之前的本體研究。所謂的本體研究是對“知己知彼”的客觀存在的影響比賽結果的分析和戰術安排。知己,是對己方綜合實力的認知和反省,知彼,是對他方綜合實力的認知和斟酌。古代軍事家時常采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侯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的方法,而達到由“不致于人”通向“致人”的效果。如何做到知己知彼,早在古代的武術家們早已把軍事戰術方的“侯之”“形之”“策之”“角之”等在武術技擊對抗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在現代散打戰術原則中,知己,是要清楚自己的體能備戰情況,訓練中加強自己的技術風格,完善技術體系,儲存更多的戰術策略,調整好比賽前的競技狀態。知彼,熟知對手的強項技術特點,是擅長單一技術或哪種技術還是組合技術或哪種功能組合技術;對方的弱項是什么,是防守能力較弱還是防守反擊能力差,對手主要靠什么戰術得分等。對方的運動素質也是考慮的因素,每個對手的運動素質存在著不同的差異,對于力量較好的對手,非以硬相克,貴在巧取豪奪,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面對耐力素質好的對手,應采取海盜式的打法,控制好擊打距離,以有效擊打動作抵制對方的連續進攻等;了解對手的攻防類型特點,主動進攻類型特點需采用游擊戰的戰術應對,防守反擊類型的對手需以強攻壓制性的戰術應對,攻守兼備類型的對手需佯攻戰術破壞其攻守平衡而擊之。
1.2 攻守詭道,戰術之法
“法”是方法、法則之意,完成一件事情所包含的思維活動、具體方案和操作程序的總稱。《墨子·天志》中最早提出方法之意,“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故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孟子集注》),有“法”可以遵循,做事才會條理清楚,快速高效。戰術之法是制勝的重要策略,攻受詭道是實現策略的方法和途徑。《孫子兵法》中說:“ 兵者,詭道也”。孫子所說的詭道并不只是詐術,是在作戰指導中視情況客觀衡量雙方的實力,用假象蒙蔽對方,借以非物質的力量將對方引向不利的境勢,造我方制勝的局面,乃為制勝的辯證法則。“詭道 ”之法在作戰中多以“佯攻”“利誘 ”為表現。孫子認為,“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固“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回顧中國武術史,武術起源于原始人類生產勞動的生存競爭,原始人經過無數次與野獸搏斗到與人搏斗的戰爭中,武術技擊對抗的經驗積累和生存環境的改變致使武術技擊中詭道內容逐漸形成。“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侯氣,與神俱往”,其中已暗示著武術技擊之詭道的性質。同軍事戰略相比,散打戰術的運用對于詭秘道之術更直接體現在“佯攻”和“利誘”的攻擊巧妙之中。散打實戰對峙中,雙方在技術和專業素質不分上下時,往往善用“佯攻”戰術的是判高水平方法之一,也是獲勝手段之一。散打戰術中常用誘攻和假動作相結合之法,通過 晃上擊下、晃左擊右、晃右擊左、佯前攻后、聲東擊西、指南打北手段以誘敵深入,避實擊虛,以假為真,攻之空檔,方能克敵制勝。佯攻戰術的運用需要明確目標目的性和針對性,真假結合,虛實莫測,靈活多變,避免單一假動作頻繁的使用,結合組合動作,隨著動作速度、節奏、幅度和面部表情的變化運用假動作。
1.3 奇正虛實,戰術之勢
“勢”在中國哲學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更多學者對“勢”的研究尚無準確的概述。但往往人們為了得到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藝術研究領域中的文學、兵法、建筑還是近代的戲曲、國畫、書法和武術都致力于追求一種高層藝術“勢”的境界。如在《孫子兵法》中提到的“勢”,曰:“勇怯,勢也;強弱,形也”。被認為形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而勢則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直接原因。《武編·拳》中記載:“拳有勢者,所以為變化也。橫邪側面,起立走伏,皆有墻戶,可以守,可以攻,故謂之勢。”此中“勢”包含著技術的進攻和防守的格斗本質和招術變化的特性。
在我國兵法戰術思想中,通過“勢”和“虛實”之理,結合武術攻防本質屬性,確立了奇正虛實的格斗戰術原則。《孫子· 勢篇》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兵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出奇制勝是戰術變化的啟動因子,是戰術發展的不竭動力。古代作戰中,常以正兵當敵,用“奇”制勝。正兵是按照符合正規邏輯或者進攻與防守動作能讓對方產生意料之中所采取的戰斗方法,反之,而采取的奇妙戰斗方法叫奇兵。虛實與奇正一樣是相對存在的概念。《孫子·虛實篇》中曰:“夫兵行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勝,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子貴在指明“避實而擊虛”“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因敵而勝”的重要性。軍事斗爭的勝利更多是避開敵人強勢的一面而攻擊敵人弱勢的一面,應戰場敵方情勢的瞬息變化而靈活運用進攻和防守的制敵戰術。奇正虛實之勢同樣在散打實戰中發揮得淋漓盡致。散打實戰中,奇正變化的戰術思想是常被使用,基本技術為正,高難度技術為奇,全面技術為正,特長技術為奇,常用戰術為正,特殊戰術為奇。奇正變換需要條件,比如,對手的備戰競技能力,賽前的競技狀態,比賽物理和自然環境等,以奇制勝是以正制勝的的制勝因子,以正制勝是以奇制勝的前提和基礎。正確處理奇正的轉換關系是散打戰術的重要思想。同時,散打戰術的安排應該根據對方在場上的變化采取相應作戰戰略,避其實,擊其虛,隨機應變,虛實轉換,方能做到戰術之“勢”。
2 影響散打“戰術原則”的發展因素
2.1 主觀因素
《孫子·九地篇》提出,“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孫子強調作戰之間的整體性和自我作戰的全面性。對于散打格斗對抗項目,其技戰術是競技能力的主導因素,在實戰中不僅要求運動員掌握全面的基本技術還應有特長技術,特別是要處理好運動員競技能力的因素整體性和各子能力之間的關系。戰術是散打實戰取勝的關鍵,靈活的戰術、豐富的比賽經驗和良好的心理素質對運動員自我發揮起重要作用。《孫子》云:“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進攻和防守軍事斗爭的組成部分,掌握主動權是取勝的關鍵。在散打比賽中,最好的防守就是進攻,要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預期,在于教練員給運動員指定的戰略部署和戰略決策,根據比賽對手的戰術特點應區別安排相應的戰術訓練。比賽中的雙方是相生相克不斷變化的過程,搶先掌握比賽的主動權,首先懂得知己知彼的戰術之理,發揮自身特長優勢,巧妙利用詭道的戰術之法克制對手的優勢,以奇正虛實之勢來整體控制比賽的節奏,方能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 而取得比賽的勝利。
2.2 客觀因素
《孫子· 形篇》中指出:“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孫子這一思想著重強調的善于用兵去創造客觀取勝的條件。這種客觀條件在散打實戰中就是創造時機,首先做好充分的備戰,致使對手不能戰勝自己,然后在比賽動態中根據對手戰術特點和技術發揮狀況,去創造能克制對手優勢而發揮自身優勢的時機,當客觀條件成熟,應當抓住時機,消弱對手或者直接取勝。
3 結語
散打比賽是擂臺上兩人的戰斗,知己知彼的戰術之理是比賽雙方相互認知的開始,是通向比賽終點的邏輯所在。詭道的戰術之法是比賽過程中取勝的重要策略。奇正虛實的戰術之勢是攻防戰術變化的啟動因子,是戰術發展的不竭動力。三者是構成散打戰術原則的核心因素。比賽的主動權、比賽時機的把握和自身競技能力的發揮是影響戰術原則的主要因素。散打比賽是雙方相生相克動態轉化的過程,掌握比賽的主動權是取勝的關鍵,進攻和防守是散打原則的本質特點。進攻和防守相互交替中,創造取勝時機是發揮自身優勢的客觀條件。比賽中自身參戰的整體競技能力因素和各子能力因素關系的處理是根據對手戰術情況和發揮程度去靈活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