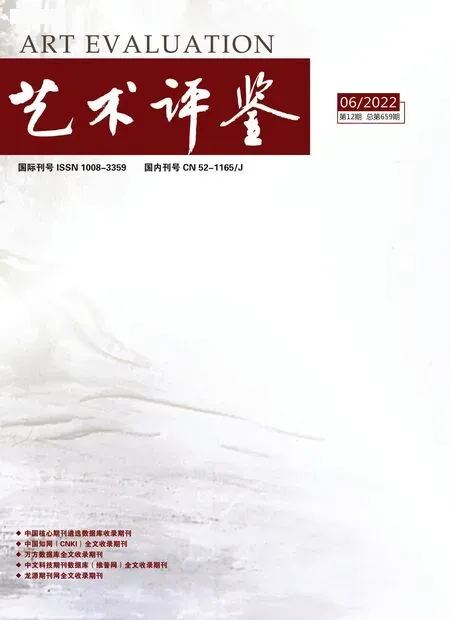試論楊仁愷書法
劉偉 山東藝術學院
楊仁愷(1915—2008),筆名易木,齋名沐雨樓,四川省岳池縣人。1915 年10 月生于四川省岳池縣,1980 年于沈陽籌備并主持了全國第一屆書法篆刻展,后又參與籌措在北京、沈陽、澳門、日本東京、南京的五次“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著有《國寶沉浮錄》《書畫鑒定學稿》《楊仁愷書畫鑒定集》《書畫真偽圖錄》等作品,其書畫的作品出版有《沐雨樓書法引玉集》《沐雨樓翰墨留真》等。
楊仁愷是新中國文博事業的拓荒者,對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的考鑒、拯救及中國文化的傳播作出卓越貢獻,海內外影響深遠。因其杰出貢獻,被授予了“人民鑒賞家”榮譽稱號,并被譽為“國眼”。楊仁愷雖不以書法而聞名于世,然置于當代書法史之上,亦可有一席之地。其書風古雅、蒼勁渾樸,深得帖學三眛。僅撰文就楊仁愷的書法進行研究,并從其中得以借鑒與啟示。
一、楊仁愷的書法
馮其庸言:“從書法的角度看,楊老當然是當代的書法大家。”楊仁愷于世所留書跡甚,多收錄于楊仁愷書法集《沐雨樓翰墨留真》《沐雨樓書法引玉集》等書中,大致歸納為行草、楷書、篆書。這些存世的大量書跡為我們研究楊仁愷的書法提供了最直接而寶貴的資料。
楊仁愷幼入私塾讀書,其書并不能脫清晚清書法的整體特征——習館閣楷體與帖學余緒。對于楊仁愷的習書歷程,雖對其詳細歷程今無法考證,然其自述:“青年時有過接近名家的緣分,如謝無量、沈尹默、于右任諸前輩;中年時經常拜會請益王蘧常、沙孟海、馬一浮先生,卻未在八法上求教;晚年精力不濟,只在鑒賞方面領略其中三昧。”楊仁愷生平之中多見書法大家,雖自謙未在八法上求教,然無意學書,書早已于胸中。王蘧常對于楊仁愷的書法評價:“于書,初嗜蘇長公,喜《西樓帖》,后及《石門頌》《龍門二十品》,復合漢碑晉帖為一冶,凡數十年,所造亦雄奇。”由此之中可窺得楊仁愷學書歷程一二,現對其存世所留書跡分類加以探討。
以現存資料來看,楊仁愷存世大量臨古作品,臨歐陽詢《千字文》《袁安碑》《張遷碑》《寶晉齋帖》《萬歲通天帖》《蘭亭序》《石門頌》《龍門二十品》等。《蘭亭序》臨摹是楊仁愷學古臨摹古人法帖的作品之一。臨此作之時已經67 歲,書者一氣呵成,整篇渾然一體,然用筆結字之上亦有己意,較原作更多幾分蒼茫渾厚。亦有《袁安碑等》對古代碑刻的臨習,所《臨袁安碑》婉轉厚重,時見飛白。對于書法的學習,楊仁愷可謂終身臨池不輟,后記曰“此碑文字用篆書,與一般流行小篆微異,運筆參以隸法。三國吳皇象所書《天發神讖碑》 正淵源于是”,此非深刻臨習不可得也。在教書育人之中,亦倡導傳統。20 世紀80 年代,遼寧書壇臨摹展上亦帶頭臨,做表率,正是楊仁愷對古代碑刻的臨習,積淀深厚的筆墨功夫,方為其后來書法風格的形成打下堅實的基礎。
楊仁愷的書法以行草書為主,馮其庸評其行書曰:“而他的行草,筆法之嫻熟,風度之瀟灑,一任自然,毫不著意而行云流水,自然天成,令人欽佩不已。”楊仁愷一生交游甚為廣泛,存世信札頗多。《沐雨樓來鴻集》中收錄楊仁愷收藏函扎百余通,由此可見楊仁愷的學術交往與交游概況。其中之人大致如下:王蘧常、陶北溟、沈尹默、謝無量等。致他人存世信札亦甚多,有《致錢君匋信札》《致羅繼祖信札》《致王連天信札》《致房果大信札》《致王連天信札》等,大量的手札書跡中均能體現出楊仁愷自然流暢的書風。《致錢君匋手札》筆墨流暢、結體緊湊、筆意連綿、字形欹側生姿,然優雅溫潤,文氣橫生,饒有古風。書風與明書家黃道周有頗多相似之處,黃道周與楊仁愷均有取法蘇字經歷,楊仁愷對黃道周書法亦有高度評價:“峭厲圓渾,緊勁連綿。楷書亦帶隸體,筆畫凝重,方勁峭厲,別具一格。”其書與黃道周書有同工之妙也。手札書為文人書法的代表,書家在寫的時候大多數是隨意的,沒有太多刻意的修飾,所以手札更能表現出一個書家的功底和修養,也是一個書家內心世界率真的流露。因其“功到天成”,這種書法往往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故楊仁愷手札書更具別樣意義。
除了手札行書外,楊仁愷亦有大字行書、楷書等。其書風雄渾,多以帖為主,參以魏碑的大氣與厚重,多為晚年所作。楊仁愷悼啟功所作詩軸,作品中有一印為:仁愷九十以后作。此時已九十高齡,然作品筆墨流暢,提按頓挫筆筆清晰明了。作品末“熱淚濕綸巾”五字,筆畫之中略帶飛白,此中正表達了楊仁愷悼念老友啟功的幾分哀愁。正如傳蔡邕《九勢》中言:“書者,散也。”此軸正是感情的真情流露。古之學書者無不于楷書之上深下功夫,除行草書外,楊仁愷亦善楷書,其楷書多受晚清館閣體影響,然多臨古帖,自出新意,大致以對聯、題額為主。楊仁愷于八十九歲作聯: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由落款可知為楊仁愷為西征所作。字勢整體略斂,然不失大氣。圓筆藏鋒入書,參以魏碑結體與厚重之氣,行筆遲澀,點畫厚峻,氣象渾穆。如“逸”“人”字捺收筆之處戛然而止,骨氣內藏,筆簡意深。作此聯時楊仁愷已八十九歲高齡,誠如孫過庭《書譜》中言:“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后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題額“黑白齋”三字,由落款知為八十五歲所作。觀此書貌豐骨勁,此中深得蘇軾的豐肥與顏字的渾厚,骨肉兼備、脈絡分明。“黑”上部略收且右上傾斜,“白”撇畫重長,下方日字與上方重長撇畫相配和諧,“齋”字自起至收筆意連綿,渾然一體。
于今所見楊仁愷書跡中亦有篆書,雖字數較少,然篆書亦能為也。存“竹西”二字與“陽關大道”四字,馮其庸言“其所作‘竹西’二字何等功力,真從李陽冰來,其挺拔秀勁又超逸又書卷氣,非胸中有詩書者,不可能由此。”
昔者古人云:“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于畫,載言莫善于書。故知書畫異名而一揆也。”對于楊仁愷的繪畫,存世者亦多,如《淺絳山水立軸》(早年)、《蘭譜》(早年臨南宋趙孟堅)、《墨竹手卷》(早年臨)、《寫生珍禽圖》(早年臨宋徽宗)。王蘧常亦曾評曰:“工繪事,初法宋元,繼悟故土靈秀,遂師造化,可謂山水純全已;更旁及花鳥草蟲,亦任于自然。既淖及書畫之理致,進而鑒定古書畫,尤于古畫,能以神遇。”
楊仁愷信札、詩軸、對聯、題額之中多古意,此與臨古人諸多法帖顯然是分不開的,然諸信札、詩軸中亦有自己面目。作書之時定不能對用筆、結字、章法……有諸多考慮,完全發于深厚的學識與修養。正如馮其庸言:“純是學者之字,無纖毫書法家習氣,是以更覺可貴。”楊仁愷于己評價亦是如此:“我不嫻于書法,只是年輕時下過一點功夫,50 年代以來由于搞文博業務,對古今書畫接觸較多,后來在國內外常有機會看到些珍品,只不過眼高手低,書法不能入流”“唯進入80 年代,受命辦理全國第一屆書展,受到一些熏陶,又掛上一點名義。于是有人錯覺地說我也是一個書法家,的確是大錯特錯的誤會!我只能承認為大家做過一些服務工作,不敢以書家自詡,所謂‘文如其人,書如其人’這是衡量每個人是否成為書法家的唯一標準,很慚愧我沒有信心作此妄想,由于水平有限,勉力以赴,還望書屆人士予諒解是幸。”楊仁愷雖未以書家自詡,然重學修身,筆下自有書家氣息。
二、楊仁愷的書學觀
(一)尚古觀念
古之學書者,臨古無疑是形成書法風格的主要途徑,古賢莫有無從此出著,楊仁愷亦是如此。楊仁愷對于繼承古人有著深刻的看法:“對于傳統筆墨應先求其似,后得其變,中間要有一個深刻的過程。如果學問和基本功夫達不到要求,想創新便無從談起,甚至可能走向反面,以至終身難脫粗俗之氣,宋代大書法家黃庭堅說:‘世上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指那些變不過來的人而言。從古人的碑帖中吸取精華,取法乎上。所謂的創新,便是在這日積月累的學習當中形成的,況且能不能成功,還要歷史來檢驗。”在書法創作上,楊仁愷如其所言,終身臨池,前文中所述其臨古書跡,足可見矣。教書育人中,亦是如此。趙有勤回憶楊仁愷的教誨亦是如此:“學書要從臨摹楷、隸入手,主要還是從唐楷入手。此外要特別認真臨習魏晉碑帖。王羲之是魏晉書風的主要代表……所以,對魏晉碑帖,要一個字一個字地去讀、去體會、去寫,要臨習千百遍,要先與古人和,再與離……”
楊仁愷對于中國古代書法的書體演進有著較清晰的認識,其中多有著述。在《試論魏晉書風與二王父子風貌》一文中,楊仁愷征引歷史遺留下來的第一手文字實物資料為考察依據,結合文獻,對魏晉時期的有關書法、書體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同時回顧殷商至西漢時期的書法、文字演進;論述了從金文大篆到秦朝的“書同文”以及由于用途、工具、書寫方法的不同形成了的“秦書八體”,再由秦至漢的“隸變”及書體新舊轉變成就王羲之成為書圣的等諸多書體演進問題。由此說明:“屬于藝術欣賞的書法,必定受到時代風格的限制,不能擺脫客觀現實另辟蹊徑,它只能在實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勞動推動了文字、書體和書法的演進,封建士大夫掌握了富裕的生活資料,他們竊奪了人民群眾辛勤培育出來的果實,在各種書體和書法原有基礎上,有條件地進行提煉與加工,從而獲得能書善寫的美名。這一歷史事實,一直被封建地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所顛倒,掩蓋了歷史的現象。”
(二)重學修身
從古至今,論書者無不以書家學識、修養與書家書法相結合而論。東漢趙壹著《非草書》一篇,其抨擊當時草書漸行,欲仍返于蒼頡、史籀,此事勢所不許。文中曰:“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在趙壹看來,書法乃“博學余暇,游手于斯”,只有達“博學”之境,方可為“后世慕焉”。至宋,東坡有詩“退筆成山足未珍,讀書萬卷始通神。”乃知筆墨之后學識為貴,至論矣。姜夔亦有言曰:“然而襟韻,記憶雖多,莫滌塵俗;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此乃與東坡之言合也。明清以降,論者頗多。王紱《論書》中曰:“書之為技,末之末也,胸無數百卷書,不能作筆。”又有“書雖手中技藝,然為心畫,觀其書而其人之學行畢見,不可掩飾,故雖堆筆冢,逼似古人,而不讀書則其氣味不稚馴,不修行則其骨格不堅正,書雖工亦不足貴也。”清道人李瑞清亦曰:“學書猶貴多讀書,讀書多則下筆自雅。”亦有論人品:“風神者,一須人品高……八須時出新意。”趙子昂有“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項穆“人品既殊……邪正自形”和“論書如論相,觀書如觀人”;朱和羹“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等等。
楊仁愷在《我對狂草書的膚淺認識》一文中提及自己對于書學的思想:“‘歷史上并沒有什么專業的書家’。許多大家,從李斯算起,到王羲之、顏筋柳骨、蘇黃米蔡,一直到近現代的毛澤東、于右任等,書法都是他們的‘余事’。而他們之能成為歷史留名的書法大家,很重要的就是依靠‘書外功夫’”。以及,聶成文回憶楊仁愷的教學理念時,有所述“書外之功”,此不贅言,下文有所詳述。誠然,楊仁愷的書法并未如當代書法教育經本、碩、博等教育培養模式。于而言書法乃一“余事”,更為重要的乃是“書外功夫”。
楊仁愷認為:“前人的著作,汗牛充棟,任憑自己去體驗,融匯貫通,自有心得。不過我還認為懂得一點唯物辯證法,對書法無不好處。如果能夠運用它,可以幫助我們少走許多彎路,而且加深認識能力。”楊仁愷對詩詞、古今書學理論、文物鑒定等諸多有研究,現存《書畫鑒定學稿》《楊仁愷書畫鑒定集》《書畫真偽圖錄》《國寶沉浮錄》等,更早于1951 年對《聊齋志異》的手稿深入研究。如此著述,可見其學養之深厚。楊仁愷亦于寄情詩中,有對老友啟功的悼念詩軸,其詩云:“相交六十載,情誼親且深。德藝眾所慕,楷模重古今。音容長相憶,熱淚濕綸巾。”楊仁愷雖存世詩文較少,然僅此一詩足見詩中多平淡之氣,儒雅之氣,少世俗之氣也。詩中多體現人之性情,此中性情亦可延伸至書法之中,與楊仁愷書法創作合而觀之,可窺其胸中修養。
凡此種種,古人論書家“學養”與“人品”,以二者為書家書法之內涵。與楊仁愷所言“書外功夫”乃一意也。楊仁愷作為一位書法家,亦是學者、書畫鑒定家、美術史家,于文字、書法與書體亦有較高的見解。其對書法的真偽,年代考訂等方面亦有較高成就,散見其著作《中國書畫》《楊仁愷書畫鑒定集》等中。在書法上,具有實踐與理論的雙重身份。于學術與書藝之間自由出入,以學養書下筆便脫世俗之氣、饒有文人趣味;以書踐學為鑒賞、鑒定之上得以運用。昔者傳衛夫人 《筆陣圖》 中云:“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時至今日,在書與學、鑒與寫斷然分離的當下書法環境中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三、楊仁愷的影響
(一)推動書法活動
1980 年于沈陽舉辦的全國第一屆書法篆刻展可以說是當代書法史上標志性的事件,《近現代書法史》 上亦有評價:“說此次展覽是全國書法屆力量的大檢閱、大顯示是并不為過的,無論是規模還是氣魄,在書法史上都是破天荒的。”此時“中國書法家協會”尚未成立,由遼寧一省獨自舉辦,楊仁愷負責了本次展覽的主持籌辦,并為此次展覽撰寫了前言,各省由副省長帶隊,各省市都派代表隊攜作品來沈陽,從兩千件作品中評選出兩百件作品展出。最終展覽順利開幕。如前言中所述:“可以相信,通過此次全國性展覽,必將對今后書法篆刻藝術產生深遠影響,對國內外文化交流和增進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具有更深遠意義。”
可以說,第一屆書法篆刻展為1981 年春“中國書法家協會”成立做了重要鋪墊,在楊仁愷為展覽給劉正成所書信札可讀出一二。信中談第二屆書法篆刻展的個別人以當時書協未成立為由,公開主張取消第一屆書法篆刻展等有關事宜。然正如信中所言:“殊知后有此次書展,就不可能很快成立書協,他們把歷史顛倒了。”楊仁愷在全國第一屆書法篆刻展中以及對后來的“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成立都起著重要作用。此后,楊仁愷亦積極參加籌措在北京、沈陽、澳門等地的“中國書法史國際研究會”,使中國的書法藝術走出國門,傳向世界。
(二)對遼沈書壇的影響
楊仁愷在遼沈書壇之中亦有重大影響。據現存資料檢索與從相關書家了解,可知在遼寧由楊仁愷所提攜的“九畹(郭子緒、聶成文、陳復澄、姚哲成等)”于70 年代末蜚聲書壇,且此時的遼寧地區為全國書壇三大焦點(上海、浙江、遼寧)之一,此與楊仁愷的書法教育是分不開的。除“九畹”外,依然活躍在當今書壇上的“十五人”“北園”“二十九人”等遼寧省推出的第二、三批書法人才群均得過楊仁愷的點撥,依舊對當今書壇具有深遠影響。
“九畹之一”的聶成文回憶:“(楊仁愷)注重傳統,1985 年在遼寧書協舉辦了第一屆書法臨帖展,楊仁愷親自臨寫了王羲之的手札,帶頭參展,給大家做表率、做示范。他還親臨遼寧書協舉辦的臨帖書法學習班,參與授課點評、傳藝布道,鼓勵學員要好好臨帖、好好學習傳統、好好加強基本功訓練、好好加強‘書外之功’,提高綜合素養。告誡大家不要急功近利,不要趕時髦。”
(三)文博鑒定
楊仁愷自述曰:“我不嫻于書法,只是年輕時下過一點功夫,50 年代以來由于搞文博業務,對古今書畫接觸較多,后來在國內外常有機會看到這些珍品,只不過眼高手低,書法不能入流。”自楊仁愷從事文博事業以來,經手文物數萬件,此與其書法上的成就有著莫大的關系。“楊仁愷的書畫作品中透露出一股文人學者的書卷氣,畫風樸質,詩畫交融,不尚奇,不求怪,竣整而含古韻,挺拔而俊媚,疏密有度,剛柔相濟。融諸家之長,雅俗共賞。這不僅來源于他的天資與功力,更重要的是半個多世紀的鑒定生涯對他的熏陶。”
牛克誠曾評:“楊仁愷在書畫鑒定中對于書法筆墨氣息間微妙差異的鑒定敏感,在很大的程度上即是仰仗他的書法修養。”楊仁愷于書壇名氣遠不及其于書畫鑒定界名氣,此如劉熙載言:“書者如也。如其才,如其學,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也。”清道人李瑞清有言:“書學先貴立品,右軍人品高,故書如神品。絕非胸懷卑污而書能佳,此可斷言者。”楊仁愷之書正合前賢所言也。
四、結語
自20 世紀90 年代,書壇亦有書法家文人化及學術與書藝相離之辯。尤在今日展覽盛行,展廳效應下的書法創作,使得書法藝術與傳統文化漸行漸遠。在楊仁先生的學書與書法創作中,我們可以不僅僅能看到筆墨技法,更為重要的是高學識、深厚的修養……可以說,楊仁愷先生的書學思想、教育觀念等在當代依然適用,依然是當代書法創作中所缺失的,依然為當代書家創作所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