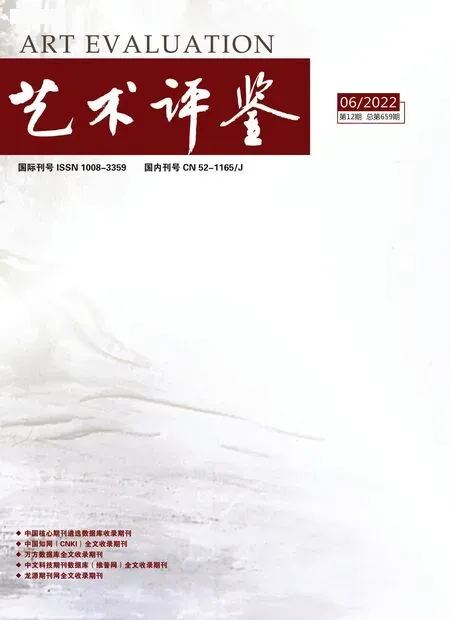劉熙載書法審美辯證思想中的問題意識
劉仲林 天津大學王學仲藝術研究所
劉熙載的書學思想是將古典文化既有的各類理論方法內(nèi)化為一個解釋書法藝術價值的美學體系,對古典書學觀念具有辯證總結(jié)式意義。劉熙載采用分條闡說的論述方式,使得其理論條理清晰,但通道必簡的表達手法使得其內(nèi)容言簡松散。本文將以厘清劉熙載書法審美辯證思想的問題意識為前提,從解釋中國哲學的理論中提煉出四個審美問題意識:本體意識、宇宙意識、工夫意識、境界意識,嘗試構建一個完整的劉熙載書學體系,并從四個方面展開討論,分別是劉熙載書論中以書法技法作為檢證其審美思想體系的形式構成;以書品、書家與書法審美層次論體現(xiàn)出倫理道德觀的價值傾向;以書法風格類型角度論述其審美意識的超越性;劉熙載審美辯證思想中的儒道佛價值意識。
一、以書法技法作為檢證其審美思想體系的形式構成
問題意識是探究劉熙載書法審美辯證思想觀理論的分析基礎,他對書法技法的約定體現(xiàn)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中對實現(xiàn)理想人格目標的操作實踐工夫的具體要求。劉熙載對書法形式美感構成中的技法作用有深刻理解,《書概》總結(jié)云:“凡書,筆畫要堅而渾,體勢要奇而穩(wěn),章法要變而貫。”以下通過關注筆法、結(jié)構、章法布白等問題,進而分析劉熙載書法形式美感反映的審美問題意識。
“筆畫要堅而渾”,劉熙載將提按、振攝、遲速、疾澀、完筆與破筆等多組對立關系進行討論,其中關于中鋒與側(cè)鋒的運用,“書用中鋒,如師直為壯”以兵家用兵來比喻中鋒,強調(diào)中鋒用筆的飽滿、力量,這個觀點反映出明確的主體意識。用“正鋒取勁,側(cè)筆取妍”概括中鋒、側(cè)鋒用筆的審美特征。對中鋒、側(cè)鋒的審美要求是以中正求穩(wěn)的力量感為主,以妍美多變的變化感為輔,正如他在《藝概·文概》中說:“兩物相對待故有文”,單一無法產(chǎn)生美,對立矛盾而又相輔相成的法則是構成美的核心。
“體勢要奇而穩(wěn)”,關于主筆與余筆,“作字者必有主筆,為余筆所拱向”“善書者必爭此一筆”,可見劉熙載在處理字形結(jié)構中“一與多”關系時,有意識的注意到主次安排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作用。在談及內(nèi)抱與外抱結(jié)字規(guī)律特征時,“抱”字體現(xiàn)出書寫的蘊藉之力,含蓄內(nèi)斂的“力”反映出對形成理想人格境界的本體價值意識的主體要求。
“章法要變而貫”,將章法分為大章法和小章法,對字與字、行與行、篇幅與篇幅之間的關系予以細分,“皆須有相避相形、相呼相應之妙”,提升章法形式美感的完整性、創(chuàng)作意識的自覺性。“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書者,尤以書脈為要”“分形而同氣”“要變而貫”“流通照應”“書脈”都強調(diào)的是變化萬千的技法形式要形成渾然一體的美感,與王羲之《記白云先生書訣》所云:“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的“氣”之理一致,是鏈接“技”與“道”的力量,一種造乎自然的混元。
總之,對修煉技法的要求是熟悉美的創(chuàng)造規(guī)律,為達到自由創(chuàng)造的境界提供基礎條件,劉熙載所說“由人復天”就是此意,“學書者始由不工求工,繼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極也。”并借用《莊子·山木》篇曰:“既雕既琢,復歸于樸”說明創(chuàng)作主體要進行刻苦的“鍛煉之工”,達到真正的美的自由創(chuàng)造境界,即人之“獵微窮至精”的工夫?qū)嵺`達至妙造自然的境界,對書法的形式構造說明以及在個人的書法實踐中也追求古雅審美思想所傳達的“無一物而不化之筆”的超然境界。可見,劉熙載將技法的實踐鍛煉問題提升到天、人關系的哲學高度。而技法的鍛煉就是運用主體“做工夫”的工夫意識,天、人關系就是圍繞主體創(chuàng)作活動與找到人生努力方向之間的聯(lián)系來論述,說明人存有通過本體意識追求具有理想境界的經(jīng)驗現(xiàn)象的宇宙世界觀,這個過程就是工夫意識與宇宙意識、境界意識的交融。
二、以書品、書家與書法審美層次論體現(xiàn)出倫理道德觀的價值傾向
在“書如其人”論中,劉熙載將書法家人格的完善與書法審美境界直接關聯(lián),他在評價王羲之書法風格時用“中和誠可經(jīng)”形容其陰陽調(diào)和的審美感受,體現(xiàn)出與“盡善盡美”相符的藝術品格。舉例“東床坦腹”的典故論說個人氣量與“書之靜而多妙也”之間的關系,以及規(guī)勸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的個人政治態(tài)度與“書之實而求是也”之間關系,可見劉熙載對書法作品所反映的學、才、志的個人品質(zhì)非常重視。在比較王羲之與王獻之的審美層次時,云:“子敬書高致逸氣,視諸右軍,其如胡威之于父質(zhì)乎”,借用父胡質(zhì)“清恐人知”高于子胡威“清恐人不知”的典故,類比小王“高致逸氣”但大王的“簪裾禮樂”合乎禮樂文化的中和之韻質(zhì);并用“筆法勁正”形容王獻之的用筆,可見骨力、勁質(zhì)依舊是他品評書法水平層次的重要條件。劉熙載“尊王”“崇顏”都具有以上審美共性,強調(diào)顏書的“紆馀蘊藉”以及“胸中具旁礴之氣,腕間贍真實之力”是學習其書的關鍵。劉熙載對書家人品風骨等精神因素外化,并結(jié)合“法則”“工夫”將其概括為“書如其人”,從創(chuàng)作主體角度思考書法的本質(zhì),這是工夫意識與本體價值意識與選擇之間的結(jié)合,對學養(yǎng)、才氣和志趣的重視是對倫理道德的皈依。
在論神、氣、形的書法美感層次時,按照“學書通于修仙,煉神最上,練氣次之,煉形又次之”排序,神依舊屬于精神層面的,體現(xiàn)在心性、才情、志趣等方面,“氣”屬于作品形質(zhì)中生命力的范疇;“形”包括對形勢、骨力等形式美感類別。在品評書法審美層次時也反映了劉熙載將“學書”與“學仙”相類比,以修煉自身的精神境界、人格品質(zhì)為主導,在此基礎上兼顧“氣”與“形”。劉熙載提出“書之要,統(tǒng)于‘骨氣’二字”,又進一步論述了“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和“骨力”統(tǒng)領“形勢”的重要性,體現(xiàn)了工夫意識可以以實踐活動的階段性差異進行區(qū)分,“骨力”要以工夫入手,進而達到“形式”的整體特性。神、氣、形則反映了工夫?qū)嵺`中的主次問題,即要有工夫次第意識,最終進入“學書同于修仙”的境界。
總之,強調(diào)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運用修養(yǎng)的方法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本體意識價值取向上的觀念建構以及宇宙意識下的知識建構之間,找尋宇宙人生的終極真象以及人生意義的形上學問題。宇宙意識體現(xiàn)在劉熙載書論中創(chuàng)作者與實踐、空間、材料之間的交融互動。本體意識則體現(xiàn)在“道體”本身終極意義與價值意識的存在原理下的創(chuàng)作主體的意義攝取,為工夫修養(yǎng)的價值目標提供理論根據(jù)。劉熙載的人品與書品論觀點體現(xiàn)出儒家的德性本位特點,是“道德的形上學”。在宇宙意識的基礎上所展開的工夫?qū)嵺`活動,對主體心性、身體能力變化會產(chǎn)生明確的歷程層次要求。
三、以書法風格類型角度論述其審美意識的超越性
包括陽剛與陰柔、“北書”與“南書”“金石氣”與“書卷氣”,所反映的是人與世界、天、人在境界領域中的交融關系。將陽剛、陰柔與動、靜關系關聯(lián),“文章書法。皆是乾坤之別,乾變化,坤安貞也”“正書居靜以治動,草書居動以治靜”,在討論書體的性質(zhì)中加入動、靜討論。以宇宙萬物的陰陽觀作為宇宙意識的出發(fā)點,陽剛、陰柔與動靜觀的聯(lián)系是建立在人心與天地萬物的“一氣流通”之上的,是人與世界的交融,而不是主客二分意識下的認識論模式。
在討論南北書派論的問題上,他一方面認同整體上“北書以骨勝,南書以韻勝”,另外一方面表示“北自有北之韻,南自有南之骨”,書家可以通過學習實踐歷代優(yōu)秀書跡以達到超越時風自成風格的成就,即“若母群物而眾腹才,風氣故不足以限之”,統(tǒng)一“南北書派論”的觀點是建立在對有限的人的生存與無限整體之間的關系而言的。阮元“南北書派論”關注的是有限的個人從自身出發(fā)向外探索后的整體結(jié)果,是有限的自我融于無限的整體中、參與到無限的整體中,形成一體性的書風特征,強調(diào)有限個體實現(xiàn)價值離不開無限整體的環(huán)境支持。而劉熙載討論南書與北書時則關注到了人與物、人與人融于并參與到無限整體的結(jié)果的同時,又不忽視有限個人自我實現(xiàn)的過程,從自身出發(fā),關注向外探索的本體價值的特殊性。
“金石氣”與“書卷氣”是建立主體創(chuàng)作境界的體現(xiàn),“金石氣”是對自然萬物、風雨歲月的宇宙、境界融合,“書卷氣”是對文人清新儒家氣質(zhì)的本體工夫、價值意識的熔煉。既有抽象的理性、精神文明、個人情感,又保持在萬物一體的本體論基礎上,達至超越道德意識的審美意識領域。劉熙載的辯證審美思想是物與物一體、人與物一體、人與人一體的萬物一體的境界,超出主體與客體之二分,超道德意義但又是自然合乎道德的。由陽剛陰柔、南書與北書,到金石氣與書卷氣,始終圍繞天地萬物與我為一體的核心審美意識,將“應然”式的道德價值意識與人與世界的關系及態(tài)度相融,達到超越二者的天人合一境界,這個過程是本體意識進行自然的、直接的驅(qū)使,而非刻意停留于道德意識之下,本體工夫的實踐是以超越的、圓融的長期磨煉過程深化為審美觀的境界意識。
總之,劉熙載在討論書法風格的三方面,陽剛與陰柔、“南書”與“北書”“金石氣”與“書卷氣”,雖然面向的是書法風格審美的不同方面,但都體現(xiàn)出人與自然融合為一的超越之路,認識到自然規(guī)律與人是一體相通的,因此在劉熙載討論書法風格問題時,自然現(xiàn)象的陽剛與陰柔、動與靜的客觀規(guī)律與書法形式美構成的主觀意識得到同一,實現(xiàn)了以無限的觀點看待自然規(guī)律并在書法創(chuàng)作實踐理論中形成能夠反映存有者存在情狀變化歷程的宇宙意識。“南書”與“北書”“金石氣”與“書卷氣”都結(jié)合了對文人精神氣質(zhì)素養(yǎng)的內(nèi)涵要求,即需要書家經(jīng)過艱苦的、長期的磨煉以達到“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境界。工夫活動是書家需要從中掙扎出來的,掙扎的過程就是工夫?qū)嵺`活動中痛苦與磨煉的過程,而看到的不在場的東西就是超越有限而達到的高遠境界。“氣”的審美概念范疇與宋儒張載所講的“天地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以及“變化氣質(zhì)”的內(nèi)涵一脈相承,都是以主體道德意識的價值意識判斷作為本體工夫的同時,借由人存有者的宇宙知識,說明這個工夫進程的意義。
四、劉熙載審美辯證思想中的儒道佛價值意識
劉熙載的書論研究反映出中國古典辯證思想中對人生、價值意識問題的思考,他以書寫本體為中心展開的討論生發(fā)于儒道佛的價值系統(tǒng),下面以價值意識的差異為核心,從儒家工夫修養(yǎng)理論、道家宇宙修煉理論、佛家本體修行理論三個方面分析本體意識、宇宙意識、工夫意識、境界意識之間的關系性問題。
(一)儒家的工夫修養(yǎng)
從事心理意志的培養(yǎng)鍛煉活動主要是以心理狀態(tài)的涵養(yǎng)、察識而進行的,劉熙載的書法審美意識中的工夫意識包括本體工夫、工夫次第、工夫境界的形式。劉熙載以為書家不能違背廉立寬敦的儒家價值觀,與儒家心理修養(yǎng)意義上的本體價值觀念一致,且與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一并形成包含本體價值認知的工夫意識,即本體工夫。關于工夫次第,劉熙載論學書要“先師夷、惠,不然則頑儒鄙薄之書”,學書也不能違背圣人教訓,要合于《虞書》九徳。以及凡書“性情為本”中他強調(diào)書寫者的首要任務是對自己的性情進行認真內(nèi)省、升華,“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要求書家調(diào)理正確的價值意識為首要工夫任務。關于工夫境界,就是說明書家如何維持最高級的狀態(tài)境界,例如劉熙載云:“凡論書氣,以士氣為上”強調(diào)“士氣”是書氣境界中的最高類別,結(jié)合孟子“養(yǎng)氣”說,即要求書家將德行器識養(yǎng)成為浩然之氣,以形成情之順此本心本性而行時之精神昂揚的書法境界。以及劉熙載其他“氣”說的其他類別:金石氣、書卷氣、士氣、骨氣、浩氣等以心理修養(yǎng)的工夫觀念作為宇宙意識的進路。除此之外,建立在工夫意識之上的工夫次第、工夫境界形式同時運行著工夫?qū)嵺`的要求、工夫?qū)嵺`的記錄。對筆法“骨力”的強調(diào),就是將儒家理想人格轉(zhuǎn)化為書法活動中的對工夫?qū)嵺`的要求,甚至劉熙載《書概》本身就是工夫?qū)嵺`的記錄。
(二)道家的宇宙修煉
主要涉及身體鍛煉的活動,同時也伴隨著一定的心理修養(yǎng)工夫內(nèi)容。劉熙載書法審美意識與道家修煉理論的鏈接建立在尋找宇宙人生的終極真象以及人生意義的形上學的哲學觀之上,關于終極真象的哲學問題反映在書法審美思想上,表現(xiàn)在對連接天與人關系的宇宙意識知識論以及本體價值觀念兩種道路。老子的身體修煉工夫有“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第一項表明人的精神會破應該收斂凝聚,類似于劉熙載的“內(nèi)抱、外抱”結(jié)字強調(diào)收斂動作蘊含的力量感。第二項形容人的身體氣場應該像新生嬰兒一般純潔柔軟,劉熙載在《游藝約言》中將其類比“道家養(yǎng)嬰兒,書亦應爾。嬰兒養(yǎng)成,則入乎形內(nèi),出乎形外,”呈現(xiàn)無我部分、人書兩忘的境界。第三項人的心理狀態(tài)應該不隱藏私心雜念,與劉熙載重自然本真的本體價值觀相符。樸、靜、真的道家境界、重“本色”與“個性”的道家觀念、反對“書家自老其筆”的刻意造作、“大家貴真,名家貴精”,便是審美主體精神的工夫修煉路徑以達至天人合一的境界體現(xiàn)。
《藝概·書概》中重要的“由人復天”思想是一套以心理修養(yǎng)的本體工夫出發(fā)而達至最高身心境界的修煉工夫,他認為“無為之境,書家最不易到,如到便是達天”“書要有為,又要無為”,創(chuàng)作之前先要有構思,“有為”就是工夫意識形式是后天人為的努力;最終達到天然境界,“無為”就是境界意識是自然的本性,符合老子“無為”本體工夫的解釋。他也進一步解釋“無為者,性也,天也;有為者,學也,人也。學以復性,人以復天,是有為仍蘄至于無為者”。此中,即是個人修煉工夫與境界意識在宇宙觀中的實現(xiàn),個人的修養(yǎng)活動與宇宙觀的知識有直接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三)禪宗的本體修行
劉熙載研究過《楞嚴》《圓覺》《凈名》三經(jīng),他的審美思想也蘊含著禪宗的修行觀念。《楞伽經(jīng)》最重要的哲學概念“自證圣智境界”,要求修正者通過自證的工夫活動,入成佛的圣智境界。圣智境界在主體自證的心識意境之中,而不在概念義理的知識性認識。可見禪宗為實相、為法的本體修行涉及身體與心理兩路并進的修行工夫。劉熙載在《游藝約言》中將學書與禪宗“悟有頓、漸”相聯(lián)系,概說“摹古人得”是漸悟,“觀物得者”是頓悟,并說明頓悟的修行方式“觀物以類情,觀我以通德。”“觀物”從天地萬物的不同情狀中獲得創(chuàng)作啟發(fā),是整體的存在原理的存有情狀的客體化,具有抽象性涵義。“觀我”從主體經(jīng)驗、感悟中反觀自身,是主體所傾向的價值意識選擇而產(chǎn)生情興、生意的工夫活動,具有藝術實踐的實證意義。從漸悟的修行方式來說,劉熙載進一步說明“古,當觀于其變”,摹古重在理解其中的變化,工夫意識明顯。學書“頓悟”“漸悟”以通天地神明之性,直覺關照、凝思寂慮都是要在創(chuàng)作中實現(xiàn)的。主體自證心境的境界狀態(tài),以主體的實踐來呈現(xiàn)本體意識與宇宙世界觀、理想人格境界之間的交互。
劉熙載在《藝概·書概》中論述“意”與“象”關系,“意,先天,書之本也;象,后天,書之用也”說明書寫者的思想情感之“意”是書法的根本,即本體意識,“象”是人為的工夫作用,即工夫意識。意與法的“體用”關系是本體宇宙意識與本體工夫意識的結(jié)合,體現(xiàn)的是眾生心中的真如自體(宇宙意識),又是眾生自性中的真如相用(工夫意識)。論述“意”與“法”關系,說“意乃法之所受命”認為“意”是“法”的主宰。在論述蘇軾之書時,將其與詩文一起論說,形容其書頗得“華嚴法界”,將“我書意造本無法”的蘇軾書法形容為一種類于華嚴宗義的圓通無礙的最高境界。“蓋無法者,法之至”,前一個“法”是規(guī)矩格式,后一個“法”是現(xiàn)象界終極意義本身的存有特性,書寫者自身的生命追求。對“意”的提倡,與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內(nèi)涵一致,特別強調(diào)心性上真實修養(yǎng)型態(tài)的本體工夫意識與工夫境界意識之間的轉(zhuǎn)換。
五、結(jié)語
四個審美問題意識是獨立存在且互相關聯(lián)的,宇宙意識是以時間、空間、材質(zhì)、宇宙發(fā)生、基本元素、生命觀、此在世界與它在世界等知識性問題在內(nèi)的審美意識。本體意識生發(fā)于價值意識、整體存在界的存在意義、生命追求的理想、個人追求的目標與原則。工夫意識來自于改善生命現(xiàn)象的實踐,包括與本體意識相聯(lián)系的心理修養(yǎng)論、與宇宙意識相聯(lián)系的身體修煉論,以及工夫?qū)嵺`、工夫次第、工夫境界等問題。本文力圖實現(xiàn)藝術哲學與書法審美的結(jié)合,建立起良好的問題意識、完整的視野框架,以問題意識來建構劉熙載審美思想的解讀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