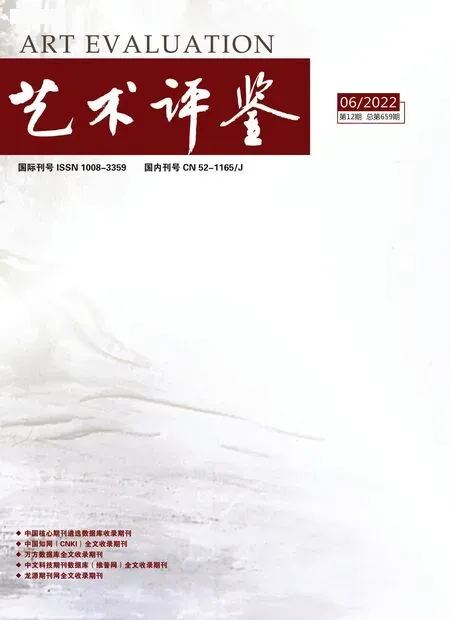探析盧西安·弗洛伊德的架上繪畫
張琳悅 遼寧師范大學
繪畫藝術作為人類的精神性產物一直在隨著人類的發展而發展。從最初的洞穴壁畫開始,繪畫就不以獨立的姿態而存在,它如明鏡一般,時刻反映著某一時代的人或社會風氣。如若細談繪畫藝術的發展歷程,非三言兩語可以交代清楚,因此本文主要以弗洛伊德為代表,淺談其所處時代的繪畫表現形式發展,以及其繪畫造型和審美思想等內容。
一、架上繪畫的復歸
(一)20 世紀繪畫語境的轉變
弗洛伊德所處的20 世紀藝術似乎延續了19 世紀藝壇動蕩的余波,西方傳統寫實主義繪畫在發展到印象派時期好似畫上了句號。后啟的藝術家們以新的觀察視角和表達方式反叛著西方幾個世紀以來的創作模式——后印象派時期以梵高為代表的主觀傾向到后期的野獸派消解了傳統繪畫的色彩程式;以塞尚為代表的理性傾向到立體主義則消解了傳統繪畫空間形體的邏輯體系。由此,繪畫就像是被這些新銳的藝術家們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誠如貢布里希所言:“20 世紀的西方前衛藝術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實驗性”。
藝術家們都希望尋找到獨立的語言來表現自身的價值與精神觀念。他們渴望獨出心裁,但這不代表“獨出心裁”是藝術家需要具備的最高的或最本質的要素,可若是連這種想法都沒有的畫家,就不能稱其為藝術家。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人們開始變得惶恐不安,反叛情緒逐漸加深,這種情緒無疑延伸到了藝術領域。藝術的表達逐步向著脫離架上這種形式載體的方向發展,繪畫的故事性與敘述性開始被消解。畫家逐步搭建起藝術與生活的橋梁,二者的界限開始被打破。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們開始重視創作的過程而非作品的結果,藝術開始被簡化為表達一種理念,或是一種獨特的觀念。
(二)架上繪畫復歸的必然性
與此同時,也有部分人認為,藝術已陷入了窘迫的地步,因而“繪畫已死”的口號也時有出現。我們不能否認現代藝術提供了新的觀看視角和理解方式,但從一方面有所得,都必然要在另一方面有所失。因創作者思想的改變而在創作中產生新的繪畫形式并不代表它就是絕對進步的,也存在一定的逆發展。與傳統割裂,追求有意味的形式,標榜藝術自身的獨立價值,在藝術一味求新的形式下,弊端也因此產生——圖像時代的到來雖拓寬了視覺廣度,但也出現了淺視、荒蕪化、庸俗化的趨勢,直至心靈層面的缺失。
法國藝術家艾爾威·菲舍爾說:“如果藝術活動必須保持生機,那么就必須放棄追求不切實際的新奇,藝術本身沒有死亡,結束的只是一種作為不斷求新的進步過程的藝術史。”此時,藝術需要回歸“架上”,它是一種超越。在當時的情況下,似乎繪畫只有回歸到“畫布”這個最終的戰場上才能真正成為一門學科。英國畫家盧西安·弗洛伊德運用傳統寫實的手法回歸架上繪畫,以宗教般的信仰與熱情成為架上繪畫的捍衛者和圣徒。
二、盧西安·弗洛伊德筆下真實的生命語言
二戰給當時的人們普遍帶來了精神上的不安及更深層次的憂郁與冷漠。盧西安·弗洛伊德以犀利的目光捕捉到時代的痛點,他筆下的寫實肖像畫或裸體畫對觀者有著侵略性的視覺沖擊,如同存在著某種更反叛的情緒。他用傳統的寫實精神把握現實生活,將人們潛在內心的“人性”展現出來。正如他自己所強調的:“畫家不想表現生活,而將他的語言禁錮在純粹的抽象形式里,就使他們無法激起美學情緒以外的任何可能。”盧西安·弗洛伊德畫作的模特是活生生存在于他生活周圍的,因為在他看來,如果模特與畫家互不熟悉,那他們對于畫家來說僅僅是走馬觀花,像是僅僅閱讀了一本旅游書籍,并沒有去過這些景點。在創作中,他通過對模特的凝視獲得了與其自身情感特質相一致的表現元素,他將這些元素運用在畫布上,無論是從宏觀位置的經營,還是微觀抽象意味的筆觸表現,或是畫面中凝聚著團塊力量感的色彩,無不觸動著每一位觀者的眼膜和心弦,其特有的繪畫語言所塑造的藝術造型已遠超于普通圖像或單純的模特給觀者帶來的心靈震撼。
(一)富有張力的形式感
觀看弗洛伊德的作品,生命的真實感迎面而來,愈演愈烈。他以飽滿的構圖拉近了人物與觀者的視覺距離,猶如特寫般真實,使觀者深刻感受到了畫中人物的氣息,盡顯畫中人物的驚悸、憂郁與冷漠。弗洛伊德常使用仰視或俯視的角度,這與古典主義穩定、和諧的美感不同,它營造的是一種非均衡性、非對稱性的不安和壓迫感,這恰恰是畫家對物象觀察與表現的獨特視角,更是自己真實內心的映照。在《和兩個孩子在一起的映像》 這個仰視角度的畫作中,畫家本人與兩個小孩在大小上有著鮮明的懸殊,呈現出一種失衡的狀態。畫外仰視者與畫中俯視者猶如對視一般,給人造成了視覺上的壓迫感,觀者看畫亦如畫中人觀己,“畫里”與“畫外”的界限好似被打破,營造出了一種壓抑不安和略帶恐懼的氛圍。值得一提的是畫中的成年男子正是畫家本人,這種帶有自畫像性質的作品正是弗洛伊德與自我的對話和表達,這和他其它畫作中所流露出來的不安的壓迫感甚至是某種荒誕的情緒有異曲同工之處。
此外,在他的大幅人物畫中,模特的姿勢給人一種特別難受的感覺,如在《在床上的裸男》一畫中,模特人物蜷縮,臉側枕在床上,臀部翹起,腿部卷曲并攏……這個姿勢異常怪誕。即便是再正常的睡姿,在弗洛伊德的筆下,也會被成斜線動勢的肢體所分割。弗洛伊德常用變形的手法處理他筆下的人物,雖然這種變形是微妙的,但足以體現出他在繪畫的空間中運用了現代主義的藝術語言。“人物是以逼真的形態出現,是一種現實再現,但是你再看頭被他畫扁了,腿也被他拉長了,鼻子也被他處理歪了。”因畫家對模特的細致觀察,在他眼中的模特是全方位顯露,或許模特本人第一次見自己“像”時會詫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愈發覺得這幅作品與自身之“像”非形象之“像”,而是更深層次的“像”。弗洛伊德在學習現代藝術強有力的表現手法后又回歸到傳統寫實主義語言,彌補了先前寫實手法表現力的不足,這是一種批判式的繼承,為寫實繪畫在新語境中注入了活力。并非只有抽象性才能表達對形式上的探索,具象的表現手法也同樣可以駕馭形式上的探索,這些只是一種表現的手段,最終都要服務于作品之中。我們能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看到最真切的詮釋,這是他畫面中富有張力感的重要因素。
(二)飽滿激情的筆觸感
繪畫藝術的筆觸經歷的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從原始時期的無意識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抑制階段,從印象派畫家的半自覺到現代主義的自覺階段。而在后現代主義時期,畫家們則更重視對筆觸的探索。雷諾阿曾說:“如果這幅畫能引誘他的手去撫摸它,那么這幅畫在視覺刺激效果上一定是感人至深的。”
縱觀弗洛伊德不同時期的作品,就會明顯地感受到筆觸在他這里經歷了一個從工細到寫意的發展過程。贊賞安格爾藝術的弗洛伊德早期是以柔軟的貂毛筆進行創作的,試圖消解筆觸感,側重畫面造型的把握和線的運用,力圖更純粹地傳達出自己的意思。其之后的筆觸則受到了好友培根的影響,培根無拘無束的用筆風格給予他很大的啟發,使他原本柔和綿軟的貂毛筆換成了富有彈性的豬鬃筆。60 年代后,“畫家的筆觸變化豐富多樣,楔形、環狀型、‘工’字型、‘之’字型等等”,筆觸隨著畫家對人體解剖的深刻把握“充滿了內斂的凝聚力量”。而其晚期的筆觸則趨向老辣,恣意縱橫,揮灑自如。若靠近觀察,便可發現他那帶有某種抽象之美的筆觸肌理效果與形體和色彩三者相得益彰,頗具“庖丁解牛”之快感。事實上有無筆觸感并不能成為區分作品好壞的標準,一幅作品的好與壞主要在于畫面上最終呈現出來的效果是否與畫家所要表達的情感或主題相一致——對真實生命的探索與表現存在于弗洛伊德繪畫生命的始終。
除筆觸外,他的畫面還有著浮雕般的肌理效果。作品《站在碎布旁》從人物面部的刻畫可以明顯地看到畫家用豬鬃筆蘸滿顏料,依據面部結構、筆觸厚重,層層疊加。多次調整后,“使畫面產生了如浮雕般的肌理和砂巖般的質感”。弗洛伊德通過這種處理使畫面視覺中心自然而然地轉向清晰的、有立體感的筆觸肌理之上,更有利于空間的營造。他的畫面筆觸與畫中人物形象統一,與畫家所展現的精神氣質相統一。“使人無法相信人力可以塑造出來,也使人無法懷疑他們的客觀存在”,這是視覺的,更是心靈的。
(三)沉穩含蓄的色彩
“我不需要任何引人注重的色彩,我需要的是色彩的生命,因為無論你注意到它怎樣改變,它都同樣存在,我不需要現代派畫家的色彩感覺,有些東西是獨立的,我不愿聽人們去說:‘哦,你畫中的藍色是什么?紅色是什么?’我已經忘記那是什么了,我寧愿回避強烈飽和的色彩在情感的意義。”這是弗洛伊德本人對色彩的觀點。他強調的不是顏色,而是顏色內在反映出來的生命情感。因為蘊藏在作品中的生命情感永遠不會隨著顏色的變化而產生或消失、強調或減弱,它一直存在。弗洛伊德并不喜歡對他每塊顏色都賦予解釋,也從不考慮作畫技巧,在筆者看來,他更在乎的是所有色塊混合在一起后的隱喻效果。
正如他所說的追求“色彩的生命”,在他的畫作中,多以灰色調為主來表現人物皮膚固有色,因其長期在室內創作使用的多為自然天光或燈光,因此環境色對畫面影響不大,即使存在,也處在一個較含蓄的狀態。畫家沉穩含蓄的色彩與他所要表達人物的冷漠憂郁與神秘色彩呈高度契合狀態。他的肖像作品《貝拉》以固有色肉色為主,統一于不透明的灰色系中,人物的耳朵、鼻梁和眼角處泛朱紅色,并以冷灰色相襯托。臉的暗部、唇底等這些地方的冷灰色相對較重,這使得畫家在試圖表現面部特點的同時也能更好地和諧受光部分的暖色調,從而呈現出一種含蓄的、沉穩的色彩關系。畫中人物下垂的眼皮泛冷紫色,人物憂郁凝重的氣質盡顯于畫布之上,青年的臉龐流露出不符合他年齡的惆悵與不安。而最讓人驚異的是畫中的人物后來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讓我們不得不感嘆弗洛伊德對于人物內心深處的洞察力,他的色彩并非似印象派畫家那般絢麗紛呈,但卻能剖析出最真實的個體,進而感染觀眾,這是一種真實的生命色彩。
三、真實層面上的審“丑”思想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西方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在藝術領域里,代表普世的理性、優美、和諧、神圣、崇高這些藝術典范受到漠視,非理性的個體欲望急需表達,繼而出現了一種“不崇高也不神圣的、反而還帶有拒絕崇高,褻瀆神圣的藝術意味”。現代美學的藝術特征與傳統古典理性的“美”相對立,有一種顛覆古典美學傳統的強勁勢頭。
(一)“丑”似乎有著比“美”更加直接的表達
“自然中認為丑的,往往要比那認為美的更顯露出它的性格,因為內在真實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皺蹙穢惡的瘦臉上,在各種畸形與殘缺上,比在各種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顯地呈現出來,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藝術的美,所以常有這樣的事情,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藝術中越是美的。”這是羅丹對“丑”的理解,在愁苦、消瘦、褶皺、畸形、殘缺中,往往更加凸顯美。可這并不是一種真的“丑”,在藝術家的眼中,這是一種“美”的體現,現實自然中的“丑”反而在藝術中展現了“美”。即便是處在當前這個時代,都有很多人欣賞美而摒棄丑,認為丑不可取。但真正的“美”應該是一種真實的,應該是每個物體、個人所特有的內容。
因此,羅丹對于“丑”的論述有利于啟發我們對盧西安·弗洛伊德作品的思考。弗洛伊德將現實中的“丑”與人性中的“真”通過人物畫坦蕩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他對個體精神的關注,就像他的祖父西蒙德·弗洛伊德對人的精神剖析一樣,是精神分析學說在藝術層面的延伸。畫家如同給每個人物寫自傳的狀態一般,把生活中的人最真實的狀態帶入繪畫中,與傳統的積極、健康、優美、崇高不同,這種真實的狀態往往是“丑”的,是消極、病態與頹廢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它是荒誕的。弗洛伊德用他的畫筆、用他的作品向觀者真實而強烈地反映了西方現代人的精神危機,在他的畫布上,那些過度肥胖或過度瘦弱的形象,似乎在暗示著現代社會給人精神和肉體帶來的雙重損害。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即便是再瘦弱的形象,在他的畫筆下卻有如鐵鑄一般結實有力,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在筆者看來,未嘗不是在受到內在和外在的雙重壓迫后,內心尚未泯滅存藏深處的一股“美”的力量。
(二)弗洛伊德審“丑”思想的運用
在弗洛伊德的《靠著獅子圖掛毯的酣夢》 一畫中,過度肥胖的裸體女子昏睡在皮椅上,左手放在肥碩的左腿上,右手支撐著因昏睡而低下的面龐,與后側的警覺的獅子形成了鮮明對比,臉上的五官因擠壓而變形,兩個碩大的乳房癱軟在已被脂肪填充到變形的肚皮之上,視點前方兩條粗壯的大腿異乎尋常地占據了畫中人物體量感的1/2 以上。在弗洛伊德以前的畫作中,從未出現過與此畫作相類似的處理方式。弗洛伊德的畫面雖有“性”的表達,但卻無性欲之感,這不禁讓人想到了舊石器時代維倫多夫的維納斯雕像。但與原始女性生殖崇拜思想不同,藝術家通過這種病態的“丑”反映出個體真實的狀態——即物欲橫流之后個體身軀與精神的頹廢,這是畫家通過作品對世人的一種警示。
弗洛伊德稱自己的創作為“靈魂的自傳”,即使畫作模特是高貴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他也未因其身份高貴而對畫面做特殊處理,依舊畫出了他眼中女王真實的形象——光鮮靚麗背后的真實。不同于其他恭維女王的畫作,弗洛伊德筆下的女王雖沒有被美化,但也與普通英國民眾眼中那個女王形象判若兩人:冰冷的臉上流露出倦怠之情,仿佛只有頭頂上的王冠暗示著她尊貴的身份。弗羅伊德筆下的女王也只是一個有著血肉之軀、人到晚年的老婦人,并不對稱的眼睛、松弛的皮膚和那張欲言又止的嘴,似乎想訴說自己為國事的操勞。盡管英國輿論對這張女王肖像畫一片嘩然,但又有誰能否認這不是他們的女王呢?
在弗洛伊德這里,視覺不光是感知系統,更是一種直覺,他的那些作品中的人物外部特征正是他們與世界溝通的一種再現。他的那些作品若觀者留心觀察,便能看到畫作里如床底下伸出來的頭或雙腳、人物手中莫名其妙的耗子等等,這些雖荒誕卻又與他創作習慣相符的細節。畫中人物臃腫的身體傷疤、粗糙的皮膚、男人身上的體毛等等,這些在現實自然中使人“厭惡”的視覺上的“丑”,在畫家手里恰恰成為了其隱喻的一種手法,而這種隱喻的表象所要昭示的正是畫家一直想要追求和探尋的“真實”。這是一種真實的生命本質狀態,在這真實的生命狀態下,藝術的“丑”才更加具備張力。
四、結語
盧西安·弗洛伊德將繪畫這件事堅持到了他生命的盡頭,在收入較少為了誰結算飯錢而與好友發生爭執的時期,他也仍未放棄作畫,始終將創作放在生活的首位。弗洛伊德的那些創作動搖了當時的審美觀,拓展了寫實主義繪畫在造型、審美心理及畫家精神內涵方面的內容,他剖析人的生命狀態,在令人眼花繚亂的20 世紀藝苑中精準定位。他對畫畫的熱愛,對創作的嚴謹,對人物內心精神世界的捕捉,對真實生命的關注與表現,對藝術語言的開拓,捍衛了架上繪畫的尊嚴與生命。弗洛伊德在抽象主義橫行的時代,卻仍堅持表現主義繪畫,他的這些風格、觀念對20 世紀西方寫實主義風格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他的畫體現著以人為本,畫筆描繪著人性,是當代繪畫領域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