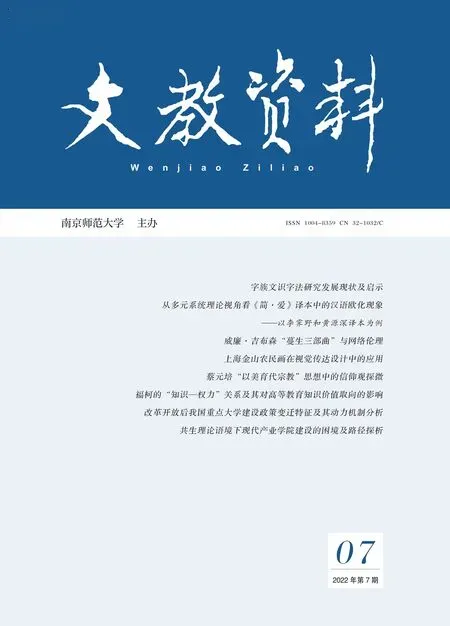紅色影視中的視聽、敘事元素與高校思政教育融合探析
——以電影《長津湖》為例
李萬軍
(煙臺大學 建筑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3)
在2018年的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全面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堅持立德樹人,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強調教育中要堅定學生理想信念、厚植愛國主義情懷、加強品德修養、培養奮斗精神,教育引導學生熱愛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立志聽黨話、跟黨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獻國家,教育引導學生樹立高遠志向,歷練敢于擔當、不懈奮斗的精神狀態、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高校作為培養人才、發展科技、服務社會的主陣地,解決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尤為重要。在當前做好思政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世界胸懷尤其重要,紅色影視藝術作為當下圖文時代的重要代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理解、用好紅色資源,也有助于思政教育質量的提升。2021年國內上映的《長津湖》電影以其關鍵的故事背景、恢宏的敘事手法、精準的視聽語言完成了對歷史和愛國主義情懷的表達,用獨特的中國式審美元素吸引了廣大學生的目光,是高校思政教育的一個成功案例。
一、紅色影視的界定與意義
(一)紅色影視的定義
紅色影視因其呈現的角度和承擔的使命,在中國普遍具有意識形態引導的功能。它主要是指具有革命實踐、國家符號、人民畫像的,具有政治性、時代性、先進性、教育性的,能夠反映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國家奮斗歷程、黨的卓越領導的電影、紀錄片等影視作品。
(二)紅色影視的階段性發展
電影藝術傳入中國,最初的功能是滿足大眾精神需求,借鑒傳統戲劇表現方式,反映當時社會條件下的某種思想觀念。而紅色影視作品自其發生,便從實用性和服務性出發,最早可追溯到1938年抗戰時期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該片主要記錄的是革命領袖帶領人民斗爭生活的革命實踐;緊接著便是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新兒女英雄傳》《白毛女》《中華兒女》《團結起來到明天》等一批具有工農形象、強烈時代氣息的作品;隨后便是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創作的《紅旗譜》《楊門女將》《紅色娘子軍》等體現共產黨領導人民艱苦奮斗、國家獨立繁榮的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至20世紀70年代“新時期”中國電影創作的《從奴隸到將軍》《一個和八個》《小花》《紅高粱》等一系列關注個體情感與國家情感探索的作品;20世紀90年代至今創作的《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焦裕祿》《橫空出世》《周總理回延安》《金剛川》《長津湖》等突出國家富強、人民團結、歷史轉折的作品。紅色影視始終在人民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宣傳和精神指引作用。
二、紅色影視作品的創作意義解讀
(一)背景闡釋和意義解讀
影視作品的背景闡釋和意義解讀是做好育人工作的重要一環,正確理解革命年代、社會主義發展時期的宏大背景,精確闡釋作品中的臺詞及心理、行為產生的深刻意義,是影視藝術在思政教育中產生無窮可能的基本點。從紅色影視發展的各個階段可以窺得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以及各個階段人民生活的現狀,如《延安與八路軍》中體現的抗戰時期軍民魚水情,《白毛女》中體現的社會動蕩下共產黨的人民情懷,《橫空出世》中表現的個人與集體利益的共融,《長津湖》中體現的無畏利他的革命群像。只有在深入了解了“四史”之后,才能講好中國故事;只有將作品中的關鍵意義解讀出來,才能激發廣大學生的愛國情感。
(二)《長津湖》文本解讀
《長津湖》影片表現的是中國人民志愿軍為保家衛國而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第二階段的故事。這場歷時28天的殘酷戰爭,被稱為朝鮮戰爭史上最為殘酷的會戰之一,它直接導致在美軍歷史上極其少見的長津湖大撤退,美陸軍第7步兵師31團“北極熊團”徹底覆滅。毛澤東主席曾親自為此戰撰文兩次全國播發,并創作了“顏斶齊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無邊,而今一掃紀新元。最喜詩人高唱至,正和前線捷音聯,妙香山上戰旗妍”的詩詞。在這場戰爭的背后是新中國剛成立的民族骨氣、謀求和平的有力宣言、國家團結的直觀體現、人民信仰的熾熱之心,這場戰役也直接激發了民族自信心,為新中國的國際發聲打下了基礎。“我女兒問我,為什么我要去打仗。這場仗我們不打,就是我們的下一代要打。我們出生入死,就是為了讓他們不打仗;有些槍必須開,有些槍不可以開;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務,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不相信有戰勝不了的敵人。”臺詞體現的內容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的承諾。和平年代少了硝煙,多了選擇,但不能缺失信仰、少了情懷。沒有一位戰士臨陣脫逃,他們選擇的是堅守陣地,哪怕只剩最后一名。影片反映的是一段歷史,但體現的是一種精神,是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
三、紅色影視視聽元素分析
(一)電影中的視聽語言
影視作品中的視聽語言指的是作品的構圖、景別、聲音、色彩、場面調度等各方面元素,相似于常規寫作中的場景、對話等推進敘事發展和組成空間意境的詞語。電影在發展初期就宣稱其是繼繪畫、雕塑、建筑、音樂、文學、舞蹈、戲劇之后的第八類藝術,電影應當是流動的詩的語言。因此,電影的發展始終在于各個類型的藝術相互交織,也正是這個緣故,電影作為視覺表現的藝術形式,視聽語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電影的特點,這也直接促成了諸如現實主義、新浪潮、新歷史主義等充滿各個時期流派特點的產生。紅色影視的視聽語言更是在塑造英雄人物、表現大好河山、引起觀眾共情、突出現實生活方面形成了獨特的語言符號。
(二)各個時期的紅色影視作品視聽發展與創新
電影經過長時間發展,在表現形式上跟隨大眾審美亦有所演進,紅色影視在傳統演變的基礎上,根據意識形態和宣傳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影視的發展。例如,蘇聯電影工作者通過蒙太奇的方式進行電影創作,《戰艦波將金號》《敖德賽》均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情懷和國家主題。在抗戰時期由于政治形勢和經濟條件需要,主要以紀錄片的形式為主,采用長鏡頭的方式真實記錄。新中國成立后,受國家獨立自主、經濟生活好轉和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方針的鼓舞,越來越多的作品開始關注現實題材和個人情感,在視聽語言上運用特寫、大全景,聲音、色彩方面也開始確立特點,例如《南征北戰》中大全景的運用,《小花》《白毛女》中特寫以及蒙太奇剪輯的運用,就直接構成了觀眾親臨現場、直擊內心情感的視聽特點。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產生了“三突出”原則,從意識形態角度說這是一種政治傾向服務,但從藝術角度講,這也是繼前一時期藝術表達的部分跟進。由于過于形式化的“三突出”原則對電影形式的限制,至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作品逐漸回歸影視創作基本原則,開始向有“政治藝術片”性質的藝術電影、宣傳電影、商業電影、實驗性電影演進,在這個時期,作品以內容帶動形式,在色彩、聲音、場面調度等方面進行了多維度的探索。例如《黃土地》《紅高粱》著重利用音樂、色彩體現生命本身不屈的精神。《天云山傳奇》通過燈光、主觀鏡頭、場面調度等方面,精彩呈現了作品中人物的內心情緒,表現了一個時代的人物群像。
(三)《長津湖》視聽語言解讀
視聽語言的發展離不開整體電影工業的發展,脫離不開整個社會的大眾審美。在紅色影視中若能夠合理利用中國特色的藝術創作方法,對于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長津湖》便具備了這一傳播意義。
鏡頭的特點在于普遍的平視鏡頭、大全景、特寫,平視代表的是一種客觀和尊重,大全景傳達的是冷靜的審視,特寫提供的是感情的共鳴。影片沒有局限于表現英雄主義,而是冷靜、客觀地展現了事實,無論是對美軍,還是對中國人民志愿軍,均如實展現了敵我差距,客觀的對比自然體現出情懷的可貴和信仰的真誠。在表現戰爭場面中巧妙地利用散點透視藝術創作方法,將美軍裝備的優良、戰場的慘烈、奮勇殺敵的現場、美軍撤退的狼狽表現得淋漓盡致,再加上特效的巧妙運用和色調冷暖的交替,呼喚出了一段真實歷史,同時也展現了中國傳統美學,將歷史賦予民族的壯烈徐徐鋪陳開來。
四、紅色影視敘事方法分析
(一)根植于中國傳統的敘事脈絡
敘事是中國電影形成特色的重要元素。自電影傳入中國,中國電影便對戲劇與電影結合進行了探索,并結合中華文化進行了創作。紅色影視作為中國電影發展的一部分,在關鍵時期做出了關鍵探索。
新中國成立前的紅色影視記錄性、服務性較強,較為突出的探索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后,在這期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真實、樸素,充滿時代氣息和生活氣息,主要的敘事方式依舊是戲劇式結構,即特別注重矛盾沖突,特別注重故事結局,特別注重人物個體。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紅色影視開始融入世界眼光,在敘事上依托中國傳統文化逐漸淡化戲劇性和英雄情結,注重體現出散文性、現實性和主體性,例如《高山下的花環》體現了優缺點并存的人物形象;《天云山傳奇》突破線性敘事,體現了個人在時代背景下的悲哀;《紅高粱》不再追求戲劇沖突,而表現歷史背景下個人的情感。
(二)《長津湖》敘事結構解讀
《長津湖》整體采用了線性敘事方法,以連長伍千里作為主線進行串聯,故事體現的依舊是中國傳統戲劇的沖突,但只是將這一沖突作為線索,而未做重點突出,在最后通過家國情懷進行了消解。影片的突出點在于不書寫單一個體,而是注重多個個體,這與視聽表現呼應。影片敘事節奏緩慢,用以刻畫抗美援朝戰爭的艱辛;設置重要戰斗任務,用以表現精彩視覺和情感感受;設置平衡的兩軍推進線索,用以表現戰斗懸殊對比出赤誠信仰。影片在不露痕跡的敘述中,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學的語言特點,兼顧了現實性和表現性色彩。和2021年上映的《金剛川》比較,影片去除了過于密集的革命群像,而是將多個個體結合現實環境組成了真實的人物特點,這對于紅色影視的敘事發展是一種探索。但過于宏大的表現,將影片作為了中國傳統山水畫進行表現,對于立體的人物和矛盾塑造,仍有所欠缺,例如對伍千里和老班長的刻畫,對戰斗任務突然的來臨,難免有平面化和不連貫之感。
五、紅色影視創作融入思政教育策略
(一)引入創作實踐,發展個人理想
短視頻是當下大學生尤為喜愛的獲取知識的媒介形式,但短視頻的發展存在博人眼球的個人主義、惹人共情的異類價值、膚淺直白的欲望窺視、斷章取義的即時滿足四個特點。這使得大部分學生沉迷于滿足欲望,而得不到個人思想認知的提升。國家鼓勵思政教育的提升,在短視頻制作方面亦有多種比賽,在引入紅色影視過程中,若將專業的視聽語言的敘事方法講授給學生,鼓勵學生以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原型進行創作,參與比賽,一方面可避免學生對于不良內容的沉迷;另一方面讓學生在專業的創作實踐中體會到個人技術與藝術的價值,從而對創作產生敬畏,同時發展了學生的綜合素質,也能帶動一大批學生參與到創作的表演和研究中,促使學生在實踐中尊重歷史,在實踐中收獲成長。
(二)開設紅色影視研讀班,引入本地紅色資源
設立專門的紅色影視觀影沙龍,結合影視創作原則進行背景和內涵解讀,結合當下社會發展實際,不生硬、不刻板、不虛構,融入最新時事政策,讓學生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做出自我判斷,鼓勵學生針對自我群體進行解讀,及時獲取學生思想動態,在專業學習中知曉學生的價值觀念。帶領學生了解身邊的紅色人物榜樣和歷史真相,邀請本地區老兵進行專題講述,讓學生參與到事件的采訪和創作之中,同時積極和學生深入到紅色革命場館之中,利用歷史符號和實物,營造直觀的視覺感受。
(三)專業融入思政,講好紅色故事
國家取得民族獨立,是無數可歌可泣的先輩浴血奮戰、勤勉奉獻的結果,在大學的學科體系中,基本上每門課程都有引領性的人物,例如藝術領域的張大千、梅蘭芳,物理領域的鄧稼先、郭永懷,文學領域的李大釗、陳望道等,不勝枚舉,在專業學習中引入紅色主題專題片、紀錄片,既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又增強了教育意義。在此基礎上,與學生進行專業社會實踐,前往具有代表意義的革命老區,例如建筑設計類的去山東膠東紅色文化展館,美術類的走“一帶一路”沿線城市,讓學生在專業的實踐中,體會國家發展史、革命奮斗史,在堅定學生的“四個自信”的同時,提升學生對于專業的熱愛。
紅色影視的發展是基于中國電影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形成了特殊的表達語言和個性符號,但總體是對國家發展的記錄和對優秀文化的傳承,不能只注重單一發展紅色影視,而忽略了對于個體藝術情感的輸出。在國家提倡思政教育的背景下,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學生是最終的目的,落腳點依然是以人為本。利用紅色影視藝術提高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提升專業技能,豐富人生情趣,正向確立價值,樹立理想信念,拓展思政教育渠道,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