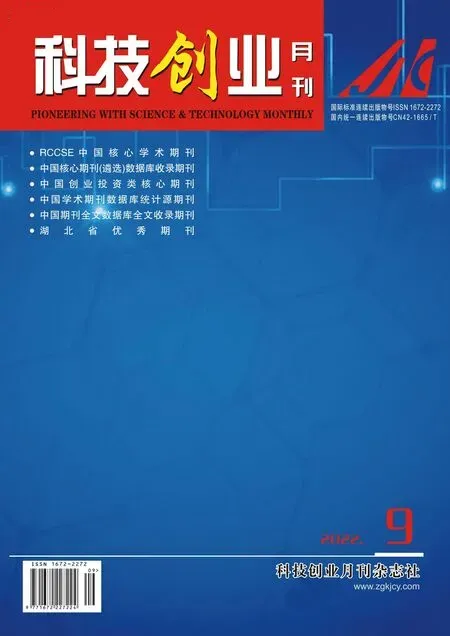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下鄉村環境治理問題及路徑優化的案例探析
王舒樂
(海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海南 海口 570100)
0 引言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十四五”時期我國尚需加強鄉村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實施鄉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構建美麗村莊。2022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鄉村振興是三農工作的重心,鄉村治理是其重點工作之一。農民是鄉村振興工作和鄉村人居環境治理的主體,是推進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基礎[1],發揮農民自主性,對我國鄉村環境改善和美麗鄉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國內許多學者圍繞“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整治”的要求對農村生態環境治理進行了多方面探討,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主要關注如下4個方面:①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的功能。②農民參與鄉村人居環境治理的困境。學者研究發現參與滯后是指農民在環境污染威脅自身利益時才選擇監督、抗爭等參與行為[2]。參與“漠視”則表現在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的意愿不強、治理能力和動員能力不足[3]。另一種是農民參與流于形式僅參與卻無共同合作[4]。③農民參與鄉村人居環境治理困境的成因。學者從主體參與[5]和制度設計[6]與非制度角度[7]將成因分為內部成因和外部成因。外因是受政府過度主導和動員不足[8]、社會資本融資難[9]和勞動力因素[10]、權益保障制度缺位[11]和快速城鎮化影響[12],導致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的能力薄弱。內因則是受“搭便車”思想[13]影響,使得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時更多考慮自身直接利益得失,參與積極性不高。④促進農民參與鄉村人居環境治理的具體路徑。根據參與困境的成因也可將治理路徑分為外部路徑和內部路徑。外部路徑是通過政策支持[14]和制度約束[15]來提高農戶環境治理的支付意愿,如通過支持開展鄉村旅游來提升農民收益,由農民主動治理環境,降低治理成本。內部路徑是從農民內生角度入手,利用鄉村社會形成的鄉村非正式制度[16],如習慣習俗、生態意識和生態文化和村規民約[17]等非正式制度來建立生活共同體觀念,提升農民對村莊權威的認同度,從而提高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參與度[18]。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關于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整治的理論研究較多,案例研究少。基于此,本文結合案例和自主治理理論,分析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合適的鄉村環境治理方式,從而更好推進鄉村振興和鄉村生態文明建設。
1 案例分析
1.1 案例引入
X村地處H省Z鎮西南部,交通便利。該村村民居住分散,年輕勞動力大規模外出務工,村里老人、婦女和孩子居多,于2019年實現脫貧摘帽,處在鞏固脫貧成果的階段。既要防返貧,又要實現“美麗鄉村”的目標。
據介紹,由于地形原因和歷史規劃問題,當年土地規劃不整齊,空間利用不合理,私搭亂建許多棚子和豬欄,有的甚至蔓延至村路邊,影響村容村貌。因此村委會決定聘用保潔員負責環境衛生清理工作。但所聘請的保潔員隊伍疏于管理,保潔員工作態度消極、偷工減料、消極怠工的現象屢見不鮮,此外還有村民不愿參與整治村內衛生,衛生意識差,處理垃圾基本采取隨意傾倒、簡易填埋、臨時堆放、露天焚燒等方式,既影響了村容村貌,又造成環境污染。沒有太多工程資金投入建設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對上述問題都無法做出有效處理,因此環境整治任務繁重且艱難。
對于此現象,本文認為,村內環境整潔屬于集體利益,可以產生環境經濟效應的附加值,是出于對美好生活向往和美麗鄉村建設的整體性考量,但是村民并不認為村內的公共衛生是需要整理的衛生對象,出現“村委埋頭干、村民不想干”的現象。為何會出現村民對村內環境治理參與不足?如何有效破解村民環境治理參與中的缺位難題?本文擬分析厘清疑問。
1.2 自主治理的理論意義
在新時代下,廣大農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逐漸提高,這是激發廣大農民共同積極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的現實基礎。自主治理注重從農民和村莊角度出發來構建合理有效的環境治理方式。自主治理相較于政府主導型治理、多元主體合作治理,有其優勢所在。政府主導型治理中,并未挖掘掘政府開展農村環境治理的實際行為特征,缺乏靈活性,也缺乏對多元治理主體參與的回應,很難避免政府在農村環境治理場域的失靈[19]。多元主體合作治理是政府、社會組織和農民共同治理,但是實踐起來仍然有市場主體介入農村環境治理動力不足和行政主導色彩強烈,導致農民環保參與明顯不足的問題[20]。而自主治理可以避免農民搭便車行為,有助于降低鄉村環境治理成本。當前引入自主治理能夠讓農民主動參與環境治理,提高組織認同度,借助生活共同體的觀念來監督、解決鄉村環境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讓農民發揮主體性作用,更好地激發出農民參與村莊環境治理的積極性。鄉村人居環境存在村莊內的各個方面,由農民和村莊自主治理可以及時發現環境問題,并進行相應治理。自主治理推動農民開展鄉村環境治理和保護,及時糾偏環境治理行為,并且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提升村民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2 分析框架
本文將借鑒已有研究的觀點,從系統和整體性思維出發,基于村莊和農民并加入扶貧干部來構建整合性分析框架來分析治理困境。
2.1 村莊治理困境
當前農村變遷最明顯的特征是人口流動性大和撤村并居帶來的村莊規模擴大,這一特征帶來最明顯和直接的影響就是勞動力的外流和對村委會治理能力的挑戰。首先青壯年和勞動精英的大量流失,使村內人力資本不足,農村空心化嚴重,人才治理懸浮使得參與環境治理的效率低下。其次村莊規模擴大意味著對村委的供給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由于人口流失和戶籍狀態的改變帶來民與村之間的利益聯結和歸屬感變化,農民參與農村公共事務的意愿日益降低。
2.2 農民參與困境
首先,農民對鄉村人居環境治理內容的了解程度較低,對治理方式和要求不夠熟悉,致使農民參與鄉村人居環境治理的態度不積極。其次,村內勞動力的流失會使得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出現差序結構,人才懸浮無法為鄉村環境治理起到帶動作用,影響了村委會對鄉村環境治理的協調和連接。另外,由于鄉村環境的公共屬性,農民認為無論參與與否都不會影響其利益,利益懸浮導致出現“搭便車”行為。最后,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會考慮成本收益問題,農民參與的知識懸浮和利益聯結不足帶來了鄉村環境治理實踐的困境。
2.3 鄉村振興組的治理困境
一方面鄉村振興組不僅要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同時還要完成參與、監督鄉村環境的治理任務,會出現為了應付上級政府規定的任務,以求得完成壓力型體制下的任務邏輯和“對上負責”的實踐邏輯[21],難以動員農民和村委一同參與治理鄉村環境。另一方面,鄉村振興組并無村內的社會性權威,因此治理權威缺乏。
為此,本文分別從村莊、農民和鄉村振興組3個層面來分析鄉村環境治理。
3 農民自主參與治理鄉村環境的整合性分析
3.1 農民自治鄉村環境治理的表現
結合本文分析,農民參與環境治理行為分為兩個階段:該村從鄉村環境整治開始,由村委出資聘請保潔員等方面的投入,但收效不佳。而在現階段,加入了農民自主參與鄉村環境治理后,環境治理效果顯著,從建立獎懲機制激勵農民參與到農民主動相互監督,并由村委設立農戶考評小組,每季度考核評選衛生家庭并頒發流動紅旗和獎金,將農戶的參與感提升到大家齊心協力,一同守護家鄉凈土。
3.2 農民自治鄉村環境治理的邏輯分析
3.2.1 村莊治理方式的轉變
根據案例可知,由于農民進城帶來了治理的空心化和勞動力缺失,某種層面上也削弱了治理領導力。
(1)“1+N”模式。村委組織了17人的保潔團隊,創新推行“1+N”模式,建立以村委會為主導、鄉村振興工作隊監管、村民小組帶頭、保潔員全覆蓋的“四級”防控網絡工作機制,扎實推進人居環境綜合整治工作。
分別以期望值與最低要求值為參考點,確定決策人員的主觀感知價值與然后借助決策人員權重,確定群體主觀感知價值(ppvmn)4×4與(npvmn)4×4,如表7所示。由(npvmn)4×4可知,應急方案ep4在指標c1的群體主觀感知價值為負值,即該方案的時效性并不能滿足應對該突發事件的基本要求,應將其剔除,對應急方案{ep1,ep2,ep3}進一步擇優。
(2)約束機制和利益導向。村委配套建立了獎懲機制,對于不積極參與鄉村環境治理人員,將在村委會和鄉村振興組共同商議后,扣除補貼,這樣確保了有問題能夠及時處理,也讓保潔員能夠按時到崗、出工出力,保障村環境衛生整潔。
(3)激發主體意識。村委會主動搭建協商平臺,農民可以在平等基礎上商討治理中的重難點問題和措施,激勵村民在規則框架內自主參與環境治理。
(4)重視婦女地位。外出務工勞動力多為男性青壯年,留守農村女性在農業生產和生活中的角色發生轉變,當地村委注重提升農村女性參與農村社區環境治理的地位,發揮女性在農村協商治理的主體地位。
3.2.2 農民個體行動的轉變
(1)鄉土認同。需要動員留守群體參與農村環境治理,增強群體歸屬感和地方依戀感,進而促進農村環境治理利益共同體的形成。X村村委立足實際情況,建立利益聯結機制,收取每月十元的清潔費,用于聘請村內保潔員的補助。對于治理到位的個人通過評比后發放獎金,強調其作為環境利益相關者而主動參與并監督鄉村環境治理的全過程。
(2)共識認同。村落共識是村民生活行為的約束機制。重塑村莊內的共識,需要重塑治理鄉村環境的共識,構建非制度層面的農民利益關聯機制,調動農民參與鄉村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農民自治水平。
3.2.3 鄉村振興組治理的轉變
(1)明確角色定位。農村環境治理面臨村級權威不足問題,以及花費成本過高等問題。對此,鄉村振興組應當明確自身的角色,是監督和引導,而不是主導和控制。鄉村振興組應鼓勵農民對鄉村環境治理過程進行監督。將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與每個農民的利益關聯起來,將環境治理變為 “農民的事”,激發農民的積極性。
(2)賦權與協調。鄉村振興組需發揮賦權和協調的作用,由農民按照民主協商程序制定和執行治理規則,由農民決定治理成本的均攤和公共利益的分配等。農民在鄉村振興組的的動員和組織下進行收益分配和協調工作,能夠有效化解公共設施建設過程中因占用土地、拆除建筑物以及其他利益等引發的矛盾糾紛。
鼓勵村民積極參與村莊環境治理,提升村民自覺維護村莊生態環境的意識(農民參與對環境治理轉向分析如表1)。

表1 農民參與對環境治理轉向分析
4 鄉村治理優化策略
通過案例分析可以發現,一方面,鄉村環境治理需要通過激發農民這一自治主體,將鄉村人居環境整治從政策性事務轉化為農民內生性事務。對于鄉村振興組這一基礎行政主體,以新定位共筑一個互相支撐的治理結構,推動鄉村環境治理以低成本、高成效的方式得到解決。另一方面,尋求家庭主體和婦女主體與自治主體間的身份轉換,是將家庭主體轉換為自治主體的重要途徑。
具體而言,有效推進鄉村人居環境治理實踐需要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自治需要政策公共性和村莊內生治理動力的共同推動。讓村民積極參與,村民在持續性參與中,不僅體現了治理的民主價值,同時促進了生態環境改善,最終塑造了良好的村容村貌。
(2)創新治理方式,提升主體意識。農民對本地情況更了解,參與治理時可以發揮優勢。建立責任共識就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治理方式,明確界定不同利益主體作用的邊界,以及參與、協作的途徑,借助農民濃厚的鄉土情結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得農民積極主動地參與鄉村環境治理。
(3)培育和發掘本地精英。首先,重視女性地位和作用。其次,以鄉村振興為抓手,注重治村能人的培育,建立和健全農村人才培養機制,提高農民環境治理建設與監督的參與度。
(4)重塑村干部責任意識和明確鄉村振興組的角色定位。村干部需要持續和村民溝通,通過宣傳教育、文化活動激勵等方式,使村民認同鄉村環境治理的價值,領會鄉村環境治理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