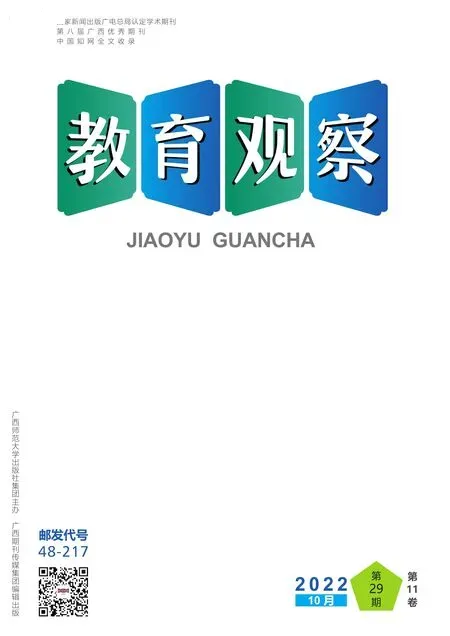中小學學習動機的潛在剖面分析
馮玉祥,范會勇
(渤海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遼寧錦州,045116)
一、引言
學習動機是指能夠引發(fā)并維持學生學習活動,并使之指向一定學業(yè)目標的一種動力傾向。[1]對學生而言,學習動機決定著其學習方向、學習進程和學習效果,影響著學生的學業(yè)成績,同時影響著其個性及心理的發(fā)展。因此,通過研究學習動機來提升學生的學業(yè)成績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關于動機結構的研究有兩類:一類是以變量為中心的,一類是以個體為中心的。[1-2]以變量為中心的研究大多考察學習動機總體水平或學習動機某一維度的現(xiàn)狀及其與學業(yè)成績、家庭作業(yè)行為或其他變量的關系。該類研究能同時考慮的維度較少,學習動機結構構成差異與家庭作業(yè)努力的關系研究較少。以個體為中心的研究探討不同動機的組合結構如何激發(fā)個體的行為。例如,Regueiro等人調查了西班牙714名高中生的學習動機水平,發(fā)現(xiàn)了不同維度的學習動機水平。[3]Trautwein等人針對德國五年級、七年級和九年級學生的研究表明,學生在課堂作業(yè)努力的主觀動機比在家庭作業(yè)努力的主觀動機更高。[4]現(xiàn)有個體研究在分析學生學習動機類型時考慮的維度較少,關于學習動機的具體分類并不明確。
對此,本研究采用潛在剖面分析(latentprofile analysis)探究不同類型學習動機的構成要素。潛在剖面分析能夠對所有個體屬于哪類群體的概率做出估計,相比于傳統(tǒng)的以個體為中心的分析技術,其保留類別數(shù)量的標準更嚴格,具有更好的分類效果。[5]潛在剖面分析是潛在類別模型在連續(xù)外顯變量上的延伸,同時能表現(xiàn)出個體間多維的質化和量化差異。[6]相較于以往的研究,潛在剖面分析納入了更多學習動機的子維度,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小學生學習動機的了解,探究了中小學生學習動機構成的具體模式,更契合我國學生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對了解學習動機的作用機制、完善學習動機的相關研究都有著重要意義。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潛剖面分析技術探究中小學生的學習動機潛類別。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測試對象選取某市及周邊地區(qū)4所小學、5所初中、2所高中的中小學生,共發(fā)放問卷2120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回收有效問卷1995份,有效回收率為92.2%。其中,小學生(3—6年級)547人,初中生1001人,高中生407人。被試年齡在8—19歲(M=13.54,SD=2.41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編的中小學學習動機問卷,分為挑戰(zhàn)取向、獎懲取向、收獲—發(fā)展取向、興趣取向、表現(xiàn)取向、尊重需求取向六個維度,共28個項目,采用Likert-4點計分法,無反向計分項。該問卷的一致性系數(shù)為0.800。
(三)施測程序
在開學兩周后開始正式施測,全部測試在一周內完成。問卷由心理健康教育專業(yè)研究生或委托測試學校心理健康教師發(fā)放,在發(fā)問卷前與被委托的教師確認了每題的含義。學生在填寫問卷時若有不理解的問題,發(fā)放者予以解答。回收問卷后,先對全部問卷進行編碼,對問卷數(shù)據(jù)進行清洗,剔除空白超過三分之一、大量選擇同一選項和明顯亂選的問卷。
(四)數(shù)據(jù)處理
本研究使用SPSS 25.0和Mplus 7.4對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對學習動機類型進行潛在剖面分析,探究不同動機類型下學生的家庭作業(yè)努力情況。本研究分別抽取1至10個類別,并根據(jù)AIC、BIC、SSABIC、Entropy、LMRT和BLRT等相對擬合指數(shù)指標綜合判斷模型擬合優(yōu)度。根據(jù)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赤池信息準則,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貝葉斯信息準則和SSA-BIC(samplesize-adjustedBIC)樣本校正的BIC反映模型擬合情況,在估計時其統(tǒng)計值越小表示擬合度越好,通常選取值最小的模型。Entropy即信息熵,用于評價分類精確性,值越接近1分類越精確。當Entropy=0.80時,分類準確率超過90%。[7]Lo-mendell-rubintest(LMRT)和Bootstrapped Likelihood Ratio(BLRT),二者用于比較k-1和k個類別模型間的擬合差異,若二者的p值顯著,說明k個類別的模型擬合度優(yōu)于k-1個類別的模型擬合度。除了以上指標,在確定類別數(shù)時,本研究還綜合選取了各潛類別中各指標的差異程度作為確定標準。
三、結果
(一)中小學生學習動機的潛在剖面分析
根據(jù)自編的中小學生學習動機量表的六個維度,本研究依次對1至10個潛類別進行分析,3至7個類別數(shù)的相關模型擬合度指標如表1所示。當模型的AIC、BIC、SSA-BIC更小,Entropy更大,且LMRT和BLRT達到顯著(p<0.05)時,該模型的擬合度較高,模型更優(yōu)。擬合指標結果表明,LMR值的顯著程度在5類別后有所下降;當潛類別數(shù)大于5后,p值均大于0.05,Entropy值雖有所增加,但整體增幅較小,且各類別對應的潛類別概率均大于0.05。綜合考慮,將中小學生學習動機劃分為五類較為適合,此時各潛類別對應的潛類別概率和后驗概率如表2和表3所示。

表1 中小學生學習動機潛在剖面分析模型擬合指數(shù)

表2 各動機潛類別所對應的潛類別概率

表3 各潛變量后驗概率均值
根據(jù)后驗概率,分到該組的平均概率都在0.8以上,分到其他組的概率均在0.1以下,辨別力較強,表明潛在剖面分析獲得最優(yōu)模型的結果較為可靠。
為探究5個類別動機在中小學生學習動機六個維度上呈現(xiàn)出的分布特征和類別特點,本研究先對學習動機六個維度進行Z分數(shù)轉換,然后計算5個類別動機在各個維度上Z分數(shù)的均值。為繼續(xù)探究動機各維度在5個亞類上的分布是否有差異,本研究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潛類別1的Z分數(shù)值均低于均值,除在獎懲這一維度與潛類別5相近且高于潛類別2外,其余各維度均明顯低于其他類別,因而可命名為“低動機組”。整體而言,潛類別2在挑戰(zhàn)和收獲發(fā)展兩維度上處于主導地位,表現(xiàn)出更多的自主性,而獎懲、表現(xiàn)和社會價值這些更依賴外界評價的維度則較低,整體處于中等水平,因而可命名為“自主型中等動機組”。潛類別3的Z值多低于平均水平,僅獎懲和社會價值維度高于均值,動機構成更依賴外部評判甚至是直接的獎懲措施,因而可命名為“獎懲敏感型中等動機組”。潛類別4的Z分數(shù)值多高于均值,除挑戰(zhàn)維度略低于潛類別2和潛類別5外,其他各維度均處于較高水平,因而可命名為“高動機組”。潛類別5除獎懲這一維度低于平均水平外,其余各項均高于平均水平,動機構成相對主動、均衡,因而可命名為“均衡型次高動機組”。

表4 動機類型與各動機維度的Z分數(shù)、均值及差異
(二)學生動機類型的預測變量研究
由以往的研究結果可知,學生年級和性別可能會對學習動機造成影響。卡方檢驗結果發(fā)現(xiàn),只有年級這一變量在不同動機類型上分布存在顯著差異(χ2=161.832,df=36,p<0.005),而性別對動機類型并無影響(χ2=6.114,df=4,p>0.005)。將年級作為預測變量納入回歸混合模型,使用穩(wěn)健三步法[8]進行多元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在0.05的級別上,年級分布差異明顯的有類別1和2,類別1和類別3,類別1和類別4,類別1和類別5,類別2和類別3,類別3和類別4,類別3和類別5。其中,高年級學生更易成為獎懲敏感性中等動機組,而年級越低越易成為自主型中等動機組。

表5 年級作為預測變量對動機類型的影響
四、討論
(一)學習動機潛類別的分類
本研究通過潛在剖面分析探索了中小學生動機的潛類別,即低動機組、自主型中等動機組、獎懲敏感型中等動機組、高動機組、均衡型次高動機組,各類別動機各子維度分布差異明顯。在各類別動機具體分布情況上,占比第一的為獎懲敏感型中等動機組(34.2%),第二是均衡型次高動機組(29.7%),第三是自主型中等動機組(21%)。在這三種類別動機中,自主型中等動機組與均衡型次高動機組的挑戰(zhàn)和收獲發(fā)展維度均高于平均值,區(qū)別在于自主型中等動機僅關注個人,而均衡型次高動機組還關注他人給予的反饋和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等,且動機構成水平顯得更社會化。在動機構成要素方面,獎懲敏感型中等動機組雖然各維度也處于中等水平,但相對以上兩組,其獎懲維度顯著高于其他各維度,使該組動機更多依賴外部的直接反饋,顯得更被動。低動機組和高動機組人數(shù)占比最小。
學習動機總體水平和挑戰(zhàn)維度不存在性別差異,其他維度有顯著差異,部分支持了已有研究成果。學習動機總體水平及各維度在年級上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表現(xiàn)為:年級升高,學習動機總體水平下降,面對學業(yè)問題時,個體努力挑戰(zhàn)克服困難的傾向減少,這與以往的結論相符。[9]下降的原因可能是隨著年級的升高,學習任務和難度及科目增加,學習困難增多,導致學習效能感減少,學習動機水平下降。興趣與社會取向這兩個維度則隨著學生年級的升高而有所增長,這與高年級學生的自我認知和自我意識隨年齡而逐漸增長,自我認同的需求增加有關。學習表現(xiàn)優(yōu)秀會為高年級學生帶來更多的尊重和他人對自己的認可。
(二)教育和干預啟示
教師了解學生動機類型,能有針對性地、更高效地進行教學,在注重達成客觀目標的同時更多關注個體的差異。從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類型和班級的動機類型組成入手,教師可以嘗試更多元化、更有針對性的多維動機提升模式和方法,激勵和促進學生積極學習行為的產(chǎn)生與保持。此外,教師在教學中應多關注低動機群體,幫助其找到學習的動力和意義,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水平。要想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教師應從適當提升學習動機水平、轉變學習動機類型入手,更多地發(fā)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激發(fā)和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和獲得感。
(三)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的全部被試來自同一城市及其周邊地區(qū),存在研究對象代表性不足、研究結果對其他地區(qū)適應性不強的問題。今后的研究在地域的選擇上可以更廣泛,探索其他地區(qū)中小學生學習動機是否也存在相同或類似的關系。本研究調查的小學、初中、高中的學校類型并不相等,各年級分布也不同,可能存在人數(shù)較多的年級對分類結果的影響較大的情況。另外,本研究為橫斷面設計,僅能說明當下學生的學習動機分類模式。對此,未來的研究可采取縱向追蹤設計,關注學生整個中小學學習階段的動機類型。
五、結論
通過潛在剖面分析對中小學生學習動機進行分類,結果表明學習動機結構特征存在五種潛類別,即低動機組、自主型中等動機組、獎懲敏感型中等動機組、高動機組、均衡型次高動機組。其中,占比較大的為獎懲敏感型中等動機組、均衡型次高動機組和自主型中等動機組,低動機組和高動機組人數(shù)占比較小。各學習動機類型的性別分布差異不顯著,但年級分布差異顯著,表現(xiàn)為年級越高,中小學家庭作業(yè)努力程度越低。總之,本研究結果對改善學習動機、提高學業(yè)成績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