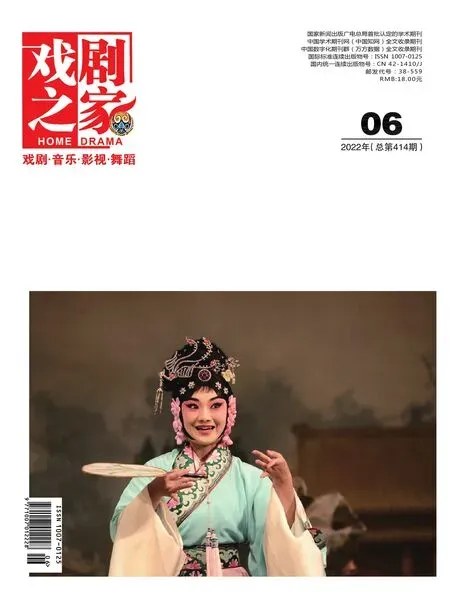影視人類學視域下的女性主義紀錄片文化意義探究
徐忱卓
(四川大學 四川 成都 610225)
近幾年,隨著女性主義的獨立紀錄片與紀實作品頻頻上線,有關于女性主義的爭論也隨之而來。揆諸當下,女性主義運動作為一個跨越階級與種族界線的社會運動,雖不屬于社會主流運動,但因其特殊的跨歷史乃至跨文化的對社會結構所產生影響的獨特性,在中國乃至世界仍造成了較大影響。可以說,許多以女性為主題的獨立紀錄片都對此積累了豐富的素材,但同時也飽受爭議。
一、對女性弱勢群體的深切人文關懷
影視人類學是借助影視藝術手段表現人類歷史的發展足跡、人類文化存在形態以及人的社會化行為方式的一門學科,從影視人類學視角探究人文紀錄片的敘事是影視研究的新視角。隨著時代變遷,女性紀錄片作品也逐漸走向成熟,雖缺乏一定的女性主義理論支撐,但總體來看,仍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與其他紀錄片不同的是,女性題材的出現為紀錄片創作提供了新角度,它不同于傳統的宏觀敘事,也不同于一般的直觀展現,女性題材紀錄片在情感的細膩度和豐沛度上是非常突出的,這與其拍攝對象和基于對象采取的拍攝手法、創作特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紀錄片《麥收》將鏡頭聚焦到一些特殊女性群體之中,拍攝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幾位女性特殊工作者的日常生活。該片展現了處于社會邊緣與底層的女性困苦艱難的生活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將那些未被人們看見的角落中的柔弱女性身上所迸發出的人性的堅強樂觀展現給受眾,不僅帶動受眾對女性意識進行探索思考,也抒發了導演對女性弱勢群體的深切人文關懷。可以說,《麥收》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價值已儼然超越了片子本身,深入到了人類學、社會學乃至倫理學的廣闊視野。
與之相似主題的紀錄片《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ls:Calcutta’s Red Light Kids》)是一部導演試圖改變當地生活在紅燈區的兒童生存狀態的紀實影片。該紀錄片講述了一位新聞記者帶領一群在加爾各答紅燈區生活的孩子們學習平面攝影的故事。《生于妓院》不僅給受眾展示了這些生活在紅燈區的孩子們生活的艱苦,更令人唏噓的是他們這個年齡不應該承受的命運的無奈與壓力。在片中,本來應該是處在最單純最純凈的環境里的孩子們,由于過早地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和疾苦,說話的語氣仿佛都如出一轍,是超乎常人的冷靜與成熟。在拍攝過程中,導演組在物質上給予了孩子們幫助,拍攝結束后,紀錄片的播出更是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無價的東西,即社會對這些特殊群體的關注與思考。該紀錄片的播出使得這群在特殊環境下成長的孩子獲得了社會的關注,給予了孩子們來之不易的改變命運的希望與機會,充滿了溫情的人文關懷。
二、“他位視角”與“本位視角”相得益彰
在人類學研究中,“他位視角”指:研究者站在被研究者的高度,在對被研究的事物深入觀察基礎上,運用研究者所持的理論進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認識,按照自己的觀點加以詮釋。而“本位視角”指:站在被研究人群的角度,用他們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研究者不加入自己的理念,不進行干擾,任其行為及觀念自然地表露,研究者則努力站在被研究者的角度去把握、去體驗。
基于人類學的研究范疇與研究方法,傳統意義上的人類學更注重對弱勢群體、底層人群予以人文關切。在英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電影制作人勞拉·穆爾維“看的實踐”中涉及了有關影像倫理問題的三個維度,其中最為敏感的問題便是制作者與被拍攝對象的位置關系——制作者“必須讓自己處于和研究對象完全對等的層面上,任何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的輕視或者怠慢,都可能給視覺成果留下恥辱的印記。”因此,影視人類學視域下對調查對象的研究更多的是從平等的視角出發,對其文化形態、風俗習慣、發展目標等都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麥收》與同類題材的紀錄片不同的是,導演徐童以一種虔誠、敬畏的創作態度,用平視、仰視的“他位”視角在受眾面前將底層社會以江湖般的場景展現出來。該片沒有刻意煽情,沒有故意刻畫,自然的剪輯與情節的過渡,帶給了觀眾最為真實和直接的視覺沖擊。底層人物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會令受眾明顯感受到一種恐懼,這種恐懼源自于內心,也源自于此部紀錄片的真實。正如林達所言:“刺破平靜水面的銳利冰峰,它也許只露出一角。”如果片中所表現的女性人物生活狀態的“原貌暴露”是冰山一角,那么其背后有如冰山之重的本質便是當今社會在文化主題上對于倫理問題的態度,及其延伸出來的社會倫理意識與倫理責任。《麥收》令觀眾了解到“真實的中國”邊緣者被主流視野遮蔽的生存狀況,因此應該受到充分的肯定,而一些觀眾“震撼”“感動”的感受就是其價值的證明。
紀錄片《生于妓院》則使用了大量的本位視角鏡頭語言,導演羅斯·考夫曼等站在孩子們的立場上感受生活、把握分寸,充滿人道主義的底層關懷。兒童,是人類社會最特殊的群體之一,他們天真爛漫、單純可愛,導演正是將鏡頭對準了“孩子”這一特殊群體,才能使整部紀錄片沒有一開始就利用大量的“灰色”鏡頭將觀眾引入傳統紅燈區悲慘狀態的主題上,而是通過孩子們的“童言童語”與拍攝的充滿童真與力量的照片來映襯整個紅燈區的迷亂不堪生活狀態與慘白的未來。整部紀錄片敘事流暢,沒有拖泥帶水之感,也正是看似格格不入的對比和冷靜的旁白令人感慨。
三、獨立紀錄片中女性意識的表達
獨立紀錄片在滿足反映社會客觀真實的現實的訴求上,又有自己的獨特的選擇傾向。例如,《麥收》《生于妓院》《秉愛》等作品在拍攝題材和對象的選擇上都將鏡頭對準了處在社會邊緣的女性人物,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橫向映射了社會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對女性造成的影響。這些獨立紀錄片將尊重與保護女性展現為當前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在宏觀層面對女性意識進行了普及,提升了社會對于處于特殊“邊緣性”群體的女性的重視程度。從其敘事線索來看,此類紀錄片都摒棄了傳統紀錄片常用的宏大敘事,更注重對個體或者某一特殊群體的生命體驗,其有關個體、生命、情感等看似支離破碎與凌亂的畫面背后展現的是關乎女性成長和愛情、女性尊嚴等更具有普適性的話題。
觀照目前我國的女性紀錄片,鮮少有將鏡頭聚焦在城市女性、職業女性、邊緣群體中的女性等具有和普通男性相同境遇的這些群體中。在現代社會中的女性,雖然已很少面臨生存危機,但諸如“容貌焦慮”“唯外貌主義”“大齡剩女”等女性文化歧視等觀點仍廣泛存在,社會偏見或是女性自身的舊有觀念仍有待打破。女性主義紀錄片不應該只是女性顧影自憐的作品,更不應該是滿足社會“窺探”的話題,它應該成為女性甚至男性的當頭棒喝,讓社會的目光更多的放在喚醒女性自我的力量和自我尊嚴,更多的放在推動女性的自我覺醒和集體解放上。
因此,中國現時代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在拍攝女性題材紀錄片時,可以多從女性的視角去觀察、體驗、理解這個世界,更多地將目光關注于生活在社會底層“邊緣性”的女性,去鼓勵她們保護自己的權益,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帶動社會對女性意識和女性話語的思考,促進社會結構不斷優化及良性轉變。
四、結語
19 世紀末,以西方女性主義者為代表的女性毅然高舉社會性別視角的旗幟努力通過一系列社會行動擴大群體影響力、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隨著時代發展進步,在當下,人們的思想意識也有所開放與提高,許多女性的性別意識也開始覺醒與獨立。《麥收》《生在妓院》等以女性主義為主題的紀錄片,從“他位”和“本位”視角將鏡頭著眼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性,展現了獨特的視野與人文關懷,鏡頭下的女性在遭受了現實生活的種種歧視和壓迫后仍能保持頑強的自尊與對生活的憧憬,令人感慨與深思。同樣,紀錄片背后所折射出的對于女性的思考更是起到了“影片有盡,含義無窮”的藝術與思想啟迪的效果,達到了直指人心的震撼力度,也直白地道出了一些現實社會的有關女性權利問題。
在當今社會中,仍有部分社會底層的女性群體生活在“水火之中”。如何幫助她們培養一種保護自身權益的敏感度,如何讓一些生活在社會底層“邊緣性”的特殊群體有尊嚴、有理想地生活在陽光下,如何讓其從心理和生活上真正地獨立起來,如何讓女性紀錄片作品更加完善,仍然是亟待思考與解決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