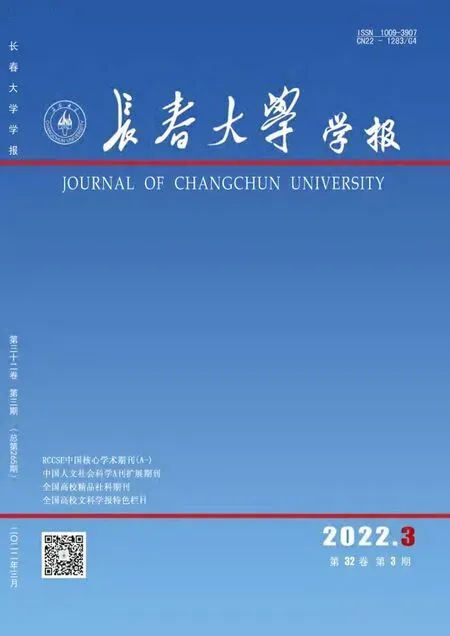設計造物視域下產品形態共性與個性的認知
左鐵峰
(滁州學院 美術與設計學院,安徽 滁州 239000)
一、產品形態共性與個性的意涵界定
基于唯物辯證法,共性與個性是表征事物辯證聯系特性的一對哲學范疇。共性揭示的是不同事物的統一性、普遍性;個性闡釋的是一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多樣性與特殊性。共性決定事物的基本性質,個性標明事物之間的差異性[1]69。就產品形態而言,共性與個性的內涵和表征既指向產品形態作為人工造物比較于其他物類形態相對一致和獨有的性質,也包括某類產品形態相較于它類產品表現出的共有與特有屬性。而就產品形態設計而言,則著重指向某一產品與同類產品具有相似和迥異形態表征的特質。其中,針對產品形態共性的設計呈現的是其工作的多數、群體價值效應,產品形態的個性設計昭示的則是少數或單體訴求的滿足與回應。
首先,根據美國心理學家赫伯特·A·蒙教授的觀點,作為人工設計造物的產品形態與自然物相對,二者的共性在于其構成的基本物質及內在品質都可追根溯源于自然,均可視為自然界某種物質的一種存在與顯現形式,具有相近或相似的外部表征及本質屬性應有其客觀必然性。同時,產品形態與自然物都為人類生存、生活所必需,是人類生存與社會發展必要和重要的組成部分。例如,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木材與家具的價值可謂不言而喻。相較于二者的共性,產品形態的個性(二者的本質區別)突出表現于其“人工性”,即產品形態是經人工綜合而成,而非大自然的直接“恩賜”,是人類憑借一定的材料和手段,為實現特定目的制成物品的物態化表現,是人類創建的“第二自然”重要的物質對象,更是生活、勞作和發展等人類活動樣態的主要物質化表象。其次,就產品形態的本體而言,李硯祖教授將其定義為具有藝術質的技術性人工造物,既可通過增加其審美要素的比重而“提升”為藝術品,亦可以其實用功能為價值核心而“降格”為非藝術質的技術造物。如司空見慣的座椅,不但可如洛克希德椅(Lockheed Lounge)一般現身于“藝博會”,也可以是我們身邊一把尋常的快餐椅。游離、搖擺于藝術對象與技術對象之間,不但可品評其審美意涵,而且可以實用功效予以考量,是大多數產品形態普遍具有的一種相對一致、共通且基本的屬性。這種跨界、復合、兼具藝術與技術的特性是大多數產品形態的共性所在,亦是產品形態區別于眾多其他人工造物的重要個性之一。而產品形態這種共性與個性的存在,在令其創設具備了更多可能性與可行性的同時,亦令其價值確認和成效品評充滿了些許的爭議性和不確定性。
需要明確的是,在我們的經驗體系中,作為人工設計造物的產品形態屬于能夠被實際看到、觸到與感知的形態,即所謂的“現實形態”[2]61。誠如馬克思所言,人的五官感覺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產物[1]13。對“現實形態”全面、有效的認知是需要調動與依托人體一切感官的綜合介入和參與。基于此,產品形態應是一種具有多視角、多維度與多層次效應的復合性、綜合性形態,不僅應指向點、線、面、體、色、質等產品視覺要素構成的視覺形態,還需包括產品形態能夠給予使用者的觸覺形態、聽覺形態與動作形態、程序形態等[3]。這種復合性、綜合性產品形態的意涵與內容認知既符合形態的哲學屬性訴求(有特征的形式),更契合其憑借“設計”達成的目的需要(建立多方面品質)。根據美國哈佛商學院有關研究人員的分析,人類獲取信息的83%來自視覺、1.5%出自觸覺、11%源于聽覺,因此,產品的視覺形態是產品形態的主要構成內容,亦是產品形態共性與個性重要的顯現形式,更是剖析產品形態共性與個性屬性與構建其含義的首要目標對象及核心要素。同時,基于產品形態“現實形態”屬性的認知,產品形態共性與個性的特質應涵蓋與彰顯于產品能夠給予人類感知的各個對象及其要件。其中,共性是某類產品區別于他類的基礎性與界定性要素,也是某一產品形態從屬于某類產品的重要指標和關鍵依據,亦是某類產品形態具有“同類似形”設計現象的主要因由之一。就產品用戶而言,根據類比推理的思維方法,某類產品形態具有的共性表征既是其基本屬性能夠被有效識別、認知的重要觀測點與參照物,也是該類產品能夠被正常使用、達成效能的必要條件保障;就設計造物而言,某類產品形態具有的共性特質在為其設計工作的開啟、實施確立相對明晰的目標及基本屬性訴求的同時,亦能夠為后續工作的展開、深入給予與界定相對可行的路徑和可期的畛域,進而令設計行為有的放矢、有章可循,設計結果有據可依、有法可據。與之相對,產品形態的個性則是指某一(類)產品在滿足其“類別”共性訴求基礎上呈現出的獨特或差異性形態表征,既可表現為產品視覺、觸覺、聽覺、動作及程序等形態的“部分性改觀”,更指向產品各形態構成要素的“整體性顛覆”。譬如在手機形態領域,更換彩殼、設置鈴聲、指紋解鎖等達成的個性便屬于“部分性改觀”,而按鍵手機、觸屏手機與折疊手機之間的形態變更則可稱之為“整體性顛覆”取得的個性。在設計造物視域下,某一(類)產品形態的個性需構建于該類別產品基本屬性的要義訴求基礎上,可發端于設計者獨具匠心的思想或觀念,也可表現為用戶、環境等要素對某種特定需求的回應,亦可為某項既有科技成果的重裝上陣或最新理論的初顯身手,是產品形態設計領域“同類異形”現象的重要成因和推手之一。不同于以共性特質及其價值取向為創設主旨的產品形態常常表現出的理性嚴謹、中規中矩與應然性,及其“帶給”人和相關系統的平淡、和緩和普適,具有個性表征的產品形態時常因展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寫意隨性、玩世不恭與或然性,而散發著較強的多元性、思想性和感召力,更多契合的是人、環境及其相關系統的專享、專向與專為性需求。
二、產品形態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剖析
產品形態的共性與個性作為一對彼此矛盾的對象和現象,既是產品形態一種必需的屬性,也是一項必要的表征,二者以互異、互聯及互為轉化的態勢、關系存在并彰顯于一切產品形態之中,這揭示與表明,完整意義上的產品形態應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統一的“復合體”本質與特征。
(1)基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關系,產品形態的共性與個性不但是其固有、不可或缺的客觀存在,而且是以相互區別、彼此關聯的內容及形式呈現的。其一,產品形態的共性是以其個性為條件,并在與該個性的比較、對比中得以達成和顯現的,是一種絕對、無條件的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及相關環境等要素為轉移的。根據現象與本質的辯證關系,產品形態的共性不是某幾個或某類產品形態表征簡單、合集式的“共有”,而是以產品形態諸多個體化表征為條件,求同存異、萃取凝練后形成一致的本質與相通表象。如形態萬千的各類椅子,或直或曲、或硬或軟、或黑或白……似乎毫無共性可言,然而透過表象的“紛亂”不難發現,大多數的椅子都會包括椅面、椅背和椅腿,均可滿足人類某種坐姿的需要,并能將人體重心置于椅腿有效支撐的范圍之內……這些必要與必需的要素為椅子這類人造物所共有,而這種“共性”正是椅子被稱作椅子的“形態底線”。產品形態共性的存在既與其作為獨立個體的客觀性有關,更關聯于其架構及效應面中相對確定和穩定的因素。作為一個由人工創造且具有特定價值屬性的物類,產品形態的客觀獨立性賦予了其能夠“自成一類”的系統性。而依循系統的哲學釋義,系統各要素需具備某種一致或共有的結構、功能等特性,方能令其架構為一個有機整體,即物以類聚。同時,根據產品形態的“成形”機制與價值達成的機理,產品形態能夠成為一種“現實物類”,相應的科學原理、技術手段是其得以“成形”的必要基礎和必備條件,其價值則是該“物類”與其他物類及相關人、環境等對象在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過程中達成的[4]。而無論是科學原理、技術手段,還是與其共存并形成關系的其他物類、人和環境等,均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與既定性,都是該類產品形態創設及形成效應必須面向與應對的相對一致且確定的“共通”要素,而這種必需要素的“一致、共通”必然昭示并訴求產品形態某種相同或相似表征的具備與呈現,即產品形態共性的存在。其二,產品形態的個性是以其共性為基礎,并在與其共性的關聯中得以架構和表現的,具有相對、有條件、動態性等屬性,昭示的既是產品形態作為一個客觀獨立系統應具有的屬性,亦是產品形態需與具體人、物及環境等達成特定價值的使然和應然,可表現為產品形態各個具體構成要素關聯性的對比和區別。如視覺形態的曲與直、觸覺形態的光滑與粗糙、動作形態的平動與轉動、程序形態的依次與隨性等。依循產品形態系統的哲學意涵,作為從屬于一個產品形態系統內的共性和個性應是相互關聯的,而根據系統發展性的本質特征,產品形態系統還應處于隨時的演變之中,其動力不僅源于產品形態自身需要持續前行的內因,更關聯于其構建、服務和存在等各項客體要件,而這種“演變”必然訴諸系統各構成要素既有共性的適時嬗變,并“連帶”其個性的時時更迭[2]51。變則通,通則久。循證于“科技能動+需求注入+環境界定”的設計造物維度及策略,對于一個特定類別的產品,依托不同科學原理和采用相異技術工藝,均會令相應的產品形態呈現出區別于既往某種相對共性的個性化表征。在特定的時空語境下,產品形態的共性關注的多是整體、群體與全局的宏觀價值需求,是以普適、共享為其價值效應的出發點與落腳點,以相關科技運用的合理、功能發揮的優化及形態適應性的提升為其價值達成的著眼點和方式手段,回應的是產品形態構建的合理性、合情性與相關用戶的認知及從眾心理需要,更是維護、確保相關環境系統穩定性、賡續性的重要加持。反觀產品形態的個性,則傾向于將部分、個體及本位等微觀對象作為其價值的要義和取向,以定向、專享為價值意涵的開篇與結尾,滿足的是人類求新、求變、好奇與自我實現等心理及其相關系統的動態性、發展性訴求,相關科技的突破重構、功能的全新演繹、適應性的另類視角是其價值達成慣常的思維脈絡與途徑策略。
(2)作為彼此互異、互聯的矛盾對象,共性與個性雖是產品形態固有與客觀的存在,但其界定卻非是一成不變與一以貫之的,二者的相對性“身份”可以實現某種特定條件下的互為轉化,而且這種互為轉化是推進與促動產品形態不斷更換、迭代所需的重要力源和成因之一。以事物變化與發展的質量互變規律度之,產品形態的共性經由整體的漸進性“量變”或局部的飛躍性“質變”均可引發和促成其個性的實現,而產品形態個性的“質變”屬性也可通過解析、驗證及適應等途徑、手段和過程“演化”為產品形態的“新共性”,進而達成二者滾動式推進、更替式發展與螺旋式上升。
第一,根據產品形態復合性、綜合性的內涵與表征特質,某類產品形態的共性是指該類產品形態在要件構成、條件依托及價值取向等方面表現出的相對穩定、一致的“部分”。依據產品形態系統的開放性與發展性特征,這種相對“穩定與一致”的認知和界定是富于時效性的,持續的演化、變更是其應有的“常態”。因此,作為物質對象的產品形態,其共性表征應是一種動態的共性,而正是這種動態屬性使產品形態具備了整體漸進性量變或局部飛躍性質變的條件和因由,并令其轉化為某種個性的可能與可行成為應然和必然。究其原因,一則,某類產品形態共性中的科技、人及環境等要素自身的發展、變動與更換,均可實現其共性的個性轉化。例如,CRT與液晶成像科技迭代給予的電視形態“由體到面”的更替。二則,為達成某類產品形態的指定性價值需求,在科技、人及環境等條件相對確定的前提下,形態自身各構成要素的重組、借用、添加、嫁接、重構等關系的變更亦可實現產品形態的個性化。
第二,產品形態的個性是在與其共性的“沖突、對抗”中形成的,是對既有認知、規則、界限的翻轉、更新與突破,另類、突兀、存疑等是其常見的感官反應與價值評價。然而“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依循認知心理學,時間、數量與成效等可以平復、和緩和慰藉產品形態個性引發的“不適”,而適應、共識與感悟之后,便意味著“新共性”的萌發和啟動。根據貝勃定律,第一次刺激能沖淡第二次刺激。習慣成自然,熟視才會無睹。時間與數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降低”產品形態個性“破局”帶來的沖擊,“累時、累量”地實現其“新共性”達成。值得關注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單純地憑借時間與數量的累計,累加尚不足以驗證和確認產品形態的某種“個性”具備轉化為“新共性”的潛質時,一定程序、標準和范圍的成效評估是給予這種“認定”的必要途徑與有效方法之一。如個性十足的IKEA設計,其“民主設計”理念有效地平衡了產品造型、功能、品質、可持續、低價等五項要素,為IKEA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的同時,儼然成為一種指導與衡量產品形態是否具有“親民性”的共性理論標桿。大相徑庭的是,給美國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中的人民帶來希望和解脫的“流線型”設計,以一種象征速度和時代精神的造型語言,曾一度被視為代表時尚的個性美學與“成功共性”,被大量應用于電熨斗、面包機等許多產品的形態設計。然而,忽視具體對象實用功效的“泛濫化”,最終導致了家庭主婦的怨聲連連——“流線型的冰箱上,什么東西也不能放”。
三、總結
產品形態是與人類關系最為密切的設計造物,某類產品形態的共性是該類產品能夠從屬于某個“類別”的重要物象因由和感官依據,滿足的是該類產品能夠作為“一類”而必要與必需的相對確定性要素和一致性準則,而某一產品形態的個性則是其能夠區別于“同類”其他產品主要的表征憑據與要件構成,給予的是該類產品能夠賡續發展、不斷前行應有的條件和動力。需要明確的是,產品形態的共性與個性表征是以產品用戶(人)為基點和視角的感官意象,人既是這種表征屬性認知與判定的緣起,亦是該屬性面向與形成價值的主要對象。根據美國心理學家赫伯特·A·西蒙對于人工物基本特征的界定,產品形態可以通過功能、目標、適應性三個方面來表征[5]。因此,產品形態的共性主要源于功與形、人與機、機與境等關聯要素間匹配、契合與協調等的慣常認知與做法使然,而產品形態的個性則是對上述“慣常認知與做法”的變更、調整和重設。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設計造物視域下,產品形態的共性與個性是“并育”“并行”于產品形態的一處,并有機、合力地貫穿于設計造物活動的始終,相得益彰地顯現于“完整”的產品形態。就該意涵而言,產品形態是共性與個性的“復合體”,不存在嚴格意義上只有共性,亦稀見唯個性的產品形態。作為一項以構建“新事物”形態為核心內容與主要形式的活動,在具體的產品形態創設中,針對某個產品形態的共性設計,可視作是令該產品形態具備某種類別屬性的“確立性”工作,而旨在架構某個產品形態個性的設計中,其工作則可認知為該類別產品既有形態共性的“突破”。有道是欲立先破,破而后立,曉瑜新生。在如此的“新事物”創設中,產品形態的共性與個性非但不是一種互為掣肘、排他的關系,反而分別以各自的內涵要義及價值取向,界定、規劃著設計活動的具體內容、方式策略與行為結果,進而達成創造一個更好世界的設計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