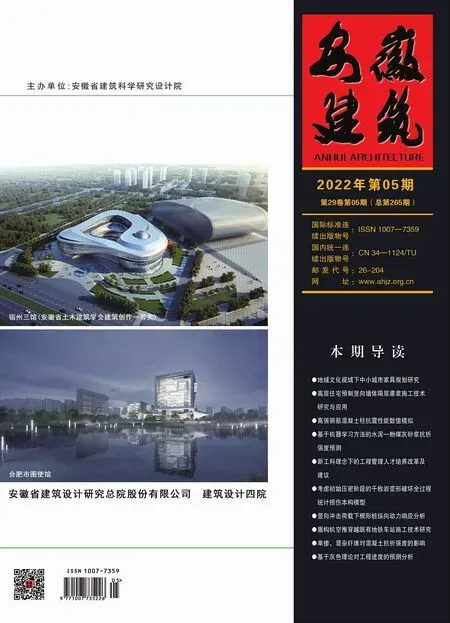影響“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教學效果的源性問題探析
張吉,馮騁,陶美竹
(貴州民族大學建筑工程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0 前言
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是一個交織多門課程、多個領域的綜合課程,學生畢業后在工作崗位中經常會使用該門課程的知識與技能,是學生硬技能構建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評估工程結構通常會使用結構可靠度這一詞語,其指的是在規定的時間和條件下,工程結構完成預定功能的概率,是工程結構可靠性的概率度量[1]。工程結構需要滿足預期的安全性、適用性和耐久性等功能的能力。工程結構是否可以順利建成并完成預定功能,荷載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荷載是建筑結構設計的重要方面,也是工程設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但由于影響可靠性的各種因素存在著不確定性,如荷載、材料性能等的變異,計算模型的不完善,制作質量的差異等,而且這些影響因素是隨機的[2-4],因而工程結構完成預定功能的能力只能用概率度量。結構能夠完成預定功能的概率,稱為可靠概率。由此可見本課程涉及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與數理統計、材料力學、結構力學等多門課程[5]。
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教學平臺建立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后疫情時代為疫情突發狀況做好充分的教學準備。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自 2019 年爆發,我國境內在2020年上半年出現不同時長停課現象,從世界范圍來講,其已具備大流行的特點。目前雖然國內疫情控制處于穩定狀態,但不斷出現變異的病毒變異株,讓疫情走向變得更難以預測[6-8],局部地區仍有小范圍的疫情反復,在后疫情時代為課程做好充分準備是每個教師的職責。其次,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教學效果與預期值差距較大。目前貴州民族大學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采用的為傳統教學模式,在疫情期間啟動了應急模式完成了線上教學,但并未建立完整的適合本校學情的教學線上課程,最后使課程適合線上、線下教學模式。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是一門房屋與橋梁工程專業課程,涉及的前導課程和后續課程較多,學生需要通過平臺解決本課程與前導課程交織的基本概念及知識點之間的邏輯關系,線下需要教師對高頻疑難問題做出統計并給出專業解答,上傳至線上平臺的服務器。
本文針對這一現象進行調研,并為后續平臺設計目標——聚焦問題、激活舊知識、求證新知識、應用新領域、融會貫通做好準備。根據教學活動進行解析,參與人包括:教師、學生;任務:講師通過一系列的方式和手段,將知識傳遞給學生。因此,調查問卷設計為兩種,一種調查主體為教師,另一種調查主體為學生,分別從教學過程兩個參與主體不同角度來解析評價問題。
本研究將問題從教師源性問題、學生源性問題、課程源性分析歸納。
1 教師源性的問題
教師源性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具體如下。
1.1 教師知識高精尖但廣度不足
該課程團隊共6人,碩士3人,博士3人,學歷層次較高,但知識廣度欠缺。教師自己在本科學習時,會學習儲備大量土木專業必修課程、選修課程,進入碩士研究生學習時,開始分為不同研究方向,出現側重,隨著博士研究生的學習,教師開始從事更為具體化的科學研究方向,整個過程教師雖然知識深度增加,但知識廣度逐漸變小。
1.2 教學方法單調
教師團隊成員針對教學方法、教學心理學等知識了解不夠深入。教師團隊成員絕大部分是土木工程學校碩士、博士畢業后直接擔任了教師的角色,課上大部分時間以教師為中心,以講授法作為主要教學方法。本課程中“以教師為中心”的問題,與多數教學調查發現的現象存在一致性[9]。滿堂灌的模式,使得學生參與度比較低,學生的注意力集中時間會明顯縮短[10]。
1.3 教師對課程難度認識與學生存在差異
通過對訪談與微信對話開放平臺收集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教師對于知識點給予的難度系數與學生給出的難度系數存在較大差距,由于教師的知識結構體系與學生不同,其知識體系搭建得更加扎實、豐富,可以利用不同的知識對難點進行輔助理解,這也是師生難度系數差異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難度認識不同會導致教師以自己定義出的難度系數授課,以致學生學習起來存在理解困難。
2 學生源性問題
學生源性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具體如下。
2.1 學習任務較重
學生需扎實學習掌握大學英語、思想政治公共課,以及貴州省情等地域、學校特色課程。除課堂學習外,還需要進行認識實習等現場實踐環節的學習。課外時間被壓縮得比較緊張。教師進行翻轉課堂式教學時,布置的前導課程復習和基本概念的學習沒有充足的時間去很好的執行。
2.2 主觀能動性不足
學生大部分關于課前預習多是被迫式,教師沒有布置,只有很少比例的同學愿意主動花時間去看,更多的同學是在等教師課堂上講解。但是,由于涉及前導課程內容,同學們并不是很熟悉,教師授課時限制,在課堂并沒有辦法深入復習前導課程知識。
2.3 隱形逃課比例高時間長
由于智能手機的普及和4G、5G網絡費用為絕大多數學生可承受范圍,教師為提升效率,多采用教學平臺、通訊軟件等替代傳統的點名。通常情況下,教師會建議購買一本教材,而教輔資料如《建筑結構荷載規范》[11]、《建筑結構可靠性設計統一標準》[12]與建筑構造做法相關的圖集等,一般不再要求學生購買,直接推薦采用建標庫APP或電子書進行查看。因此,學生常常可隨身攜帶手機,為學生在課堂看視頻、網絡購物、打游戲提供了便利條件。根據調查,部分同學反映,課前預習不足,課程晦澀難懂時更容易造成隱形逃課[13-14]。若在課堂學習受阻,很大可能會導致學生轉投虛擬世界,這也間接印證為什么更多是成績不甚理想的同學喜歡在課堂打游戲,看視頻、聊天等[15]。
3 課程源性問題
課程源性問題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具體如下。
3.1 本課程涉及交叉學科目較多
本課程涉及高等數學、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數學課程,以及理論力學、材料力學、結構力學、土力學、流體力學等力學課程。在講授土體對建筑物的荷載作用時,需用到主動、靜止、被動土壓力理論等土力學知識。在講授風荷載時需利用流體力學伯努利方程理解風速與風壓的關系。在講授地震作用時,結合理論力學達朗伯原理與結構動力學知識,建立單自由度體系的平衡方程,采用高等數學中常系數非齊次二階微分方程求解方法,結合杜哈梅(Duhamel)積分獲得單自由度體系的地震響應。在講解多自由度體系地震作用時,需采用線性代數知識,通過求矩陣特征值與特征向量,求得結構的周期與振型,利用振型矩陣的正交性可將多自由度體系剛度矩陣對角化,以實現耦合方程組的解耦,與最終通過結構力學與材料力學知識,得到結構的傾覆彎矩與構件內力等。獲得單一工況的荷載效應后,設計時需與其他荷載進行組合,如地震作用與恒活組合,此時需采用概率與數理統計知識,根據既定失效概率pf(或可靠度指標β)等,確定基于結構概率可靠度設計的實用表達式,獲得各工況效應的分項系數[16-17]。
除此之外,恒荷載計算時,需查閱建筑施工圖中標注的圖集構造做法,逐步分層計算各組成層的恒載值。地震作用計算時,是否考慮樓梯等,因地震作用與房屋建筑的剛度有關,而是否應考慮樓梯的剛度,又與樓梯是否設置滑動支座相關聯,若能采用國家建筑標準設計圖集(16G101-2)中滑動樓梯構造[18],在地震作用計算中,可僅考慮樓梯的重力荷載代表值。
3.2 前導課程知識掌握程度欠缺
前導課程知識掌握欠缺第一體現在學生的成績上。通過調取學生相關前導課程成績發現,接近10%的學生成績超過85分,30%~40%處于75分~85分之間,30%~40%處于65分~75分之間甚至有5%~10%的學生成績低于60分。除此之外,通過試卷分析和任教課程教師訪談發現,試卷難度系數在近些年不斷下調,盡管從成績分布上沒有顯示學生知識掌握程度下滑,其本質是因為下調了難度系數。但工作崗位難度系數并未下調,也導致用工單位滿意度調查并不是非常理想。
3.3 課程資源不足
教學視頻多源于網絡資源,視頻數量不足,且并未根據本校學情進行修改,與本校學生的學情契合度不夠。教學視頻多為動畫,非動畫設計等專業的教師對于動畫制作軟件操作不熟,導致很多教師不愿制作教學視頻,即使制作了教學視頻多是PPT錄制,而非真正地將抽象知識具體化,微觀知識宏觀化[19-20]。
考慮活荷載的隨機性應做的不利布置設計,荷載組合時的互斥性,活荷載的折減等問題,對于在校的學生而言,均顯得比較抽象,看書時所有的字都認識,但就是不能深入理解掌握。遇到特殊的荷載情形,學生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風荷載大小是與結構周期相關,如果在初始階段設計的結構,經方案調整后,周期改變,應該再次反填周期通過迭代完成風荷載計算與后續設計,但大部分學生會忽略此問題,這也是作者在多年教學與畢業設計指導過程中,發現頻次最多的問題之一。
3.4 課程學習監督機制較弱
首先大學多數課程沒有課前預習任務,也幾乎沒有把課前預習完成情況納入課程成績考核的范圍。其次課程參與度也幾乎不納入考核成績,即使納入比例很低,學生參與一兩次提問就可以獲得對應的分數,并沒有顯著提升學生的參與度。最后,教師很少布置任務,即使部分教師布置一些任務,但比例遠低于50%,課后復習基本依賴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通過本次調查和訪談清晰地了解教師、學生、課程資源三個方面問題所在,為后續工程結構荷載與可靠度設計原理課程WEB端平臺建立、線上課程設計、課程整改、課程運行、監督等方面提供理論依據。從課前—課中—課后建立敦促機制,同時利用平臺共享前沿知識,充分利用碎片時間,讓學習減少受時間、空間限制[21-22],學習過程遵循艾賓浩斯記憶遺忘曲線,真正地實現“以教師為中心”轉變為在教師有效指導和監管下的“以學生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