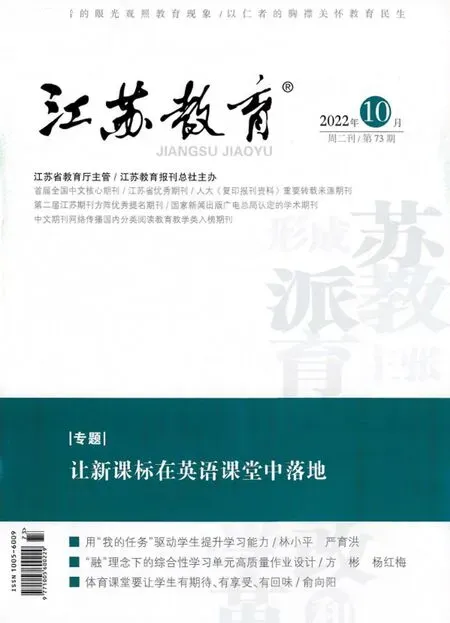以創美活動推進低幼銜接*
邱洪艷
兒童在幼兒園時愛游戲、愛唱歌、愛創造,而上小學后,受制于學習時間和學習任務,加之很多教師忽視了兒童對教學氛圍、教學情境、教學活動等方面的需求,兒童的游戲時間銳減、歌唱欲望降低、動手機會變少,導致其對學習的理解漸漸狹隘化、學科化。為打通低幼銜接的堵點,教師應堅持兒童本位的原則,尊重兒童身心發展的節律,為兒童提供兼具美感與創意的語文教育。
1.玩:順應游戲之心,行走游戲路徑
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任何形式的心理活動最初總是在游戲中進行。”當游戲成為兒童精神的一種表達,引領兒童的精神成長,兒童的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就是游戲的精神,游戲就成了兒童精神發展的重要營養。因此,教學時,教師就要充分尊重兒童身心發展的自然規律,讓他們在自主的活動、自得的嬉戲中獲得成長。教師可以通過創設情境的方式來推動教學活動的游戲化,使學生在具身式體驗中實現經驗、行為與情意的轉化。如教學一上《小蝸牛》一課時,筆者扮演蝸牛媽媽的角色,利用音樂、美術等元素讓兒童化身課文中的那只小蝸牛,通過師生對話、共同活動,使其較為準確地理解了文章的主旨內容。此外,兒童對小蝸牛角色的演繹也激發了筆者對文本內容的再思考,并生成了重要的教學資源。如筆者在觀察兒童演繹小蝸牛的一次次失望而歸時,萌生了以下衍生問題:“小蝸牛們,既然我們每一次都完不成任務,接下來我們就不再出發了吧?”出人意料的是,兒童紛紛回答:“一定要再出發,一路上能看到很多不一樣的風景”“要再出發,只有出發了才有成功的可能”……由此,教師在教學中滲透了德育因素,更好地發揮了語文學科的育人價值,而這也是教學活動游戲化過程中“意外的驚喜”。
2.唱:激蕩藝術之思,巧妙轉化文本
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引導兒童站在審美欣賞的角度,用哼唱的方式與文本對話。童話與音樂相結合,有助于引發兒童的藝術之思,激發兒童的表達欲望。如一上語文園地五“和大人一起讀”中的《拔蘿卜》一文涉及多個人物的對話。于是,筆者鼓勵兒童想象“老公公喊老奶奶,老奶奶喊小姑娘,小姑娘喊……”的情形,用對唱的方式將故事演繹出來。他們的哼唱雖不成旋律,但從中完全可以聽出“大家團結一致拔蘿卜”的快樂心情。這不僅是兒童用個性化的腔調去和童話里的“他”對話,更是一種蘊含著自身理解的最本真表達。
此外,教師還可以巧妙地抓住模仿和歌唱的契合點,引導兒童以配樂演唱的方式將自己創編的文本歌唱出來。如教學一上《比尾巴》時,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在掌握文本句式的基礎上,進一步仿寫“比耳朵”“比眼睛”“比鼻子”等,在文本創編完成后,用熟悉的曲調配上自己根據課文創編出來的歌詞。這時,音樂課上學唱的《小螞蟻》《小樹葉》等旋律就成了學生的首選,這不僅能帶給兒童學習的成就感,還可使其在無形中提升藝術素養。
3.創:活躍創美之手,催發綠色制作
蘇霍姆林斯基說:“兒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尖上。”教師帶領兒童活躍雙手,可以讓他們在享受學習樂趣的同時提升創造力。
對于一年級的兒童而言,識字是重點也是難點,但如果教師將識字與兒童的生活和實踐聯系起來,難點便會不攻自破。如教師引導兒童以剪貼的方式將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漢字做成精美的識字小報,或自行制作主題識字卡,再將生活中看到的與該主題相關的漢字從包裝上剪下來貼在識字卡上。這樣的教學是對陶行知“做中學”理念的生動實踐,既能激發兒童創作的熱情,又能讓兒童在輕松愉快的狀態下識記大量的漢字。
綜上,適合兒童身心節律的創美語文教學項目與活動方式可以讓兒童獲得更多的具身體驗,發出更多有個性的聲音,更好地完成從幼兒到小學生的身份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