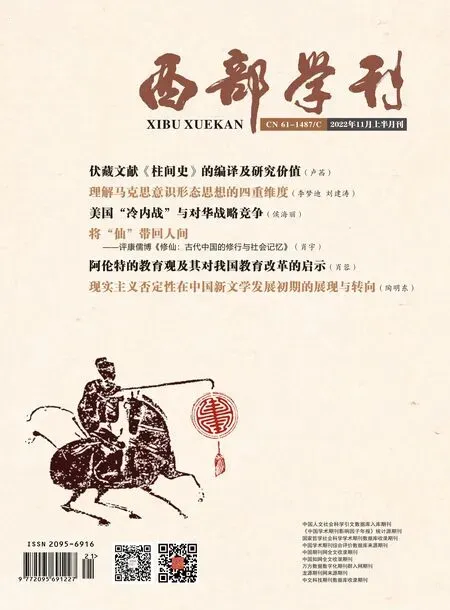淺析泛義動詞“搞”和“整”
劉宇航
一、泛義動詞研究現狀和定義
在現代漢語中,泛義動詞作為一類具有特殊性的動詞的統稱,指代這樣一種語言現象:一個動詞的使用超出了其原義的范圍,模糊了與其他動詞的使用界限,可以作為多個具體動詞的替代使用。隨著語境色彩的變化,泛義動詞的語義可以延伸出極具彈性和豐富性的表述空間,在語言的實際應用中,泛義動詞的使用場景靈活多變。漢語中衍生出了許多極具語言張力的泛義動詞,如“做”“弄”“打”等,都擁有重要的語言地位。方言中更是有許多生動有趣的泛義動詞,如東北方言中的“整”,源于西南官話的“搞”,等等。
知網上搜索“泛義動詞”這一研究主題,共有146篇文章,主要體現出四個研究方向。一是有關漢語本體的研究,尤其對諸泛義動詞語義語用方面的研究文章居多,有60篇以上,占據總數量近一半;二是有關泛義動詞對外漢語教學方面母語為非漢語學習者的二語習得偏誤分析類文章,約40篇,數量也較多;三是外語泛義動詞尤其是日語中的泛義動詞與漢語泛義動詞的對比類文章,數量在10篇以上;四是有關泛義動詞常用構式的研究類或與泛義動詞研究無甚關系的文章。在諸多文章中,“整”是最受研究者關注與青睞的泛義動詞,有關研究文章可占總量的三分之一;“弄”“造”“做”“干”“打”各有千秋;以“搞”為研究對象的文章數量不多,僅有9篇。“搞”作為近年來使用頻率越來越高且廣為人知的泛義動詞,卻鮮有人關注研究,現有的關于泛義動詞研究的文章多為語義語用方面的分析和對比,有些意猶未盡之意,對泛義動詞內在機理的聯系性方面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筆者借此契機,淺析“整”和“搞”這兩個泛義動詞,以期為泛義動詞研究提供自己的思考。
泛義動詞是由劉瑞明[1]先生提出的概念:他稱其為一類有著寬泛和浮泛特點的動詞,并與表意準確具體而范圍固定的一般動作動詞相區分。需要注意的是,泛義動詞不同于多義詞,其含義數量遠遠大于一般多義詞的數量。經金鵬在《泛義動詞“整”的語義探析》[2]中統計,“整”的義項高達50個,這種龐大的數量和極其寬泛的語義空間是多義詞所不能企及的。多義詞雖然一詞多義,但其語義比較明確穩定,而泛義動詞有著“浮泛游移”的特點,伴隨著不同的語境,往往有相當大的變化。泛義動詞也不同于適量、少許、暖和等模糊詞語,模糊詞語傳遞的信息雖然具有不確定性,但每種不確定性所歸屬的詞義是單一的,并不能寬泛;泛義動詞的義項雖然寬泛眾多,但其每個義項的內容都是精確的,所表述的并不是一個范圍不確定的事物。因此,莫嬌與李明[3]認為:泛義動詞更傾向為一種具有指稱能力,詞義寬泛且意義確定依賴語境的選擇的動詞。
二、泛義動詞的語言地位
泛義動詞雖然因其模糊、靈活、多變的特性,讓許多非母語學習者感到頭痛,難以辨別其適用范圍,但其在語言交流中具有獨特的功用價值,是漢語動詞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首先,泛義動詞對單詞儲備構成了靈活的補充。不是每個動作都能找到獨一無二的專屬動詞進行指代,尤其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舊有的詞匯將很難用于直接描述新出現的現象。如“打電話”“打字”“打游戲”等動作的語境,是漢語字詞生成時期所不可想象的。由于語言的經濟性制約,盡管漢語具有相當的靈活性,但為每個動作生成一個新詞,也是不現實、沒必要而且極其浪費的。因此,漢語更傾向于運用已有的動詞泛化其詞義,以達到擴充語言、描述新現象的目的。這實際上把一部分動詞變成了一種靈活的類似“詞根”的狀態,從而與其他字詞尤其是名詞排列組合,進行語言的生成創造。
其次,泛義動詞讓信息的交流更為便捷。盡管泛義動詞有時會因為過于泛義而產生歧義語句,如“整兩瓶”到底是拿兩瓶酒來,還是喝兩瓶酒?但是總體來看,瑕不掩瑜。語言的本質是交流工具,詞匯是信息交換的載體。崔蕾在《小議東北方言泛義動詞“整”》[4]中曾言:泛義動詞“整”其實是無義動詞,只有在一定構式中才能產生意義。泛義動詞盡管以一詞涵蓋多義,但是其信息傳遞不受影響,只是傳遞信息的方式發生了改變,不是通過詞匯本身的語義傳遞,而是利用上下文語境傳遞信息,這一現象與漢語的時態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如果一個特定動詞雙方并不都明確其含義,反而不能起到流暢傳遞信息的效果,而在特定的明確語境下,動詞是什么并不太重要,交流雙方都能理解,此時動詞只是一個符號,表示這里發生了動作,具體是什么,借助語境去直觀理解,反而更加精確。東北方言中的“整”幾乎無不可用,但是不管是不是東北人,聽眾往往都能理解具體語境下“整”這個詞的含義。這說明泛義動詞是一種簡潔高效的表達。
三、泛義動詞“搞”和“整”的語言學價值
在所有的泛義動詞之中,“搞”和“整”無疑是最具特殊性的兩個,與干、弄、做、打等動詞不同,這兩個詞本來源于方言,保留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語言色彩,并且高度口語化,因此在泛義中又保留了自身的語言特色,產生了獨特的魅力。
首先,“搞”和“整”具有更強烈的情感表達和更生動的文字張力。二者經常在各類文學作品尤其是喜劇作品和方言作品中出現,豐富了文學形式,產生了夸張、詼諧、幽默等多種文學色彩,讓作品語氣變得活靈活現,通俗幽默接地氣。
其次,“搞”和“整”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種亞文化現象的語言文化。“整”成為東北方言的代名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東北人的性格特點,成為東北方言文化的象征符號和幽默標簽。“整活兒”一詞更是把“整”帶入了網絡空間,打上了網絡直播文化的烙印。“搞”所代表的“惡搞”文化和“搞笑”風格,代表了一種民間的、和主流的陽春白雪式的“雅文化”不同的、難登大雅之堂卻如野草一般發揮著自身生命力的、下里巴人式的俗文化。這兩個特別的泛義動詞之間,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截然不同的區分,構成了一對值得研究的詞匯。因此,本文以“搞”和“整”為例,對這兩個泛義動詞進行對比分析,并探究其背后的語言規律。
四、泛義動詞“搞”和“整”的對比分析及其探源
(一)泛義動詞“搞”和“整”在語義上的聯系與區別
作為泛義動詞,“搞”和“整”之間既相似相近又有著微妙差異的特性,早已被國內研究者注意到,蔣明在《泛義動詞“整”與“搞”的語義語用對比》[5]中將它們總結為以下幾點:
“搞”和“整”的語義重疊:在以下情況中,可以表示相同的含義,甚至可以相互替換。如1.獲得;2.制作;3.懲治;4.修理/破壞的處置義。
“搞”和“整”的語義差異:1.“搞”有從事進行義,并可與正式用語相連進而融入書面語語境,如“搞研究”,“整”則不可;2.“搞”可以表達戀愛和發生性關系,“整”則不可;3.“整”的總體范圍更為寬泛,可以表達表演、扛過去、拍照等“搞”不具備的含義;4.“整”的詼諧感和生動性更強。
但遺憾的是,之前的研究僅停留在現象的歸納總結階段,未能深入挖掘其現象背后的語言規律。這紛亂的現象背后,實際上有著明確的邏輯成因,即是兩個動詞本義對其發展變化的制約。本文將從詞源學和語詞流變的角度對“整”和“搞”進行分析,在透過諸多“整”與“搞”的語義語用異同現象中展開思考。
(二)“搞”和“整”語義相似性的內在成因
如前文所述,“搞”本義為“攪”,也就是“打亂”,“整”作為動詞的原意則是“使之整齊”。二者作為泛義動詞有著廣泛的語義重疊,原意卻恰好相反,這并不是一個巧合。在語言傳播中,原本的詞義逐漸延伸出相反的詞義,以至于一詞兼具兩個相反的含義,甚至詞義完全倒轉的現象也是普遍存在的。二者本義的相反性,恰恰是二者發展為同義詞的語義基礎。“相反”恰恰說明兩個詞語在描述同一概念,否則就無法“相反”了。回到“搞”和“整”的詞義,無論“使之亂”還是“使之整”,本質上都是一個施事者對另一受事者的狀態的處置,因此“搞”和“整”都可以引申為處置義,進而變成所有處置動詞的普遍代替。觀察可知,幾乎所有“搞”和“整”通用的句式,都可以轉化為處置句,這正說明二者的動詞泛義現象與處置式這一語言結構的緊密聯系。正是本義上天然具有的共通性——表達“處置”的語言色彩,令二者能夠共同躋身泛義動詞并產生廣泛的語義重疊。因此,二者相似性的根本原因是其詞源本義的互通性。
(三)“搞”和“整”語義差異性的內在成因
由于“搞”和“整”二者的本義不同,就使二者在語義延伸時,所帶有的情感色彩發生變化,進而限制了其泛用范圍,構成了雙方的差異。
1.本義差異導致語氣和情感色彩不同
“搞”本義是攪亂,由此延伸了兩種色彩,一種是貶義色彩,暗示行為不正當、不光彩,另一種是非正式色彩,表示行為的隨意性、非正式性,用于消解嚴肅氣氛,達到自謙和拉近距離的效果。如“我是搞研究的”就比“我是做研究的”要少了許多正經、嚴肅的情感色彩,暗示研究也只是很平常的,并非特殊重大的工作,有種“隨便玩玩,算不得正經”的暗示語氣。
之前的研究者敏銳地發現了這點,但由于缺乏內在的分析,得出了錯誤的歸因。并非搞具有“正式”“嚴肅”的色彩,而正是由于“搞”具有不嚴肅、不正式的色彩,才會在日常用語中和嚴肅正式的事項頻繁使用,以此起到折中效果。
“整”的形容詞性本身就有全部的含義,因此,書面語中“整”本身帶有一種嚴肅的語氣色彩,并多用于形容程度較劇烈、規模較大的改變。例如,修容、美容、美體和整容、整形相比,顯然后者的規模和程度都要高上許多。因此,帶有嚴肅、大規模性質的“整”進入口語,去形容平常小事時,就形成了“大動干戈”的夸張效果,這種反差感就構成喜劇性,產生了詼諧色彩。這也符合東北方言善于用豐富甚至過量的詞語和過于夸張的語氣去描述生活小事的幽默氣質,如喝酒干了說“掫”(掀起義),吃飯說“造”等,都是用高度夸張的動詞去修飾事物而產生笑果。這種詼諧的色彩,恰恰是由其本義的嚴肅性、正式性帶來的。
情感色彩的差別也導致“搞”和“整”在接人和表述性關系時產生語義差異。“整”本就有“整治,懲處”的含義,此時是高位者對下位者的撥亂反正。因此“整人”中包含一種居高臨下,任意給予痛苦和懲罰的霸道色彩,這導致其詞義趨向貶義。“搞”本就有貶義色彩,因此“搞人”一詞更多強調其手法的不正當、陰損性質,此時“整”更接近于“修理”,而“搞”更接近于“陷害、暗算”。二者的詞義雖然十分接近,卻是分野陰陽。在描述性關系時,更能體現這種區別。由于長期以來傳統文化渲染,性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男性和女性發生性關系,本身就被認為是對女性的損害。因此發生不正當的性關系,都可以用“搞”一言以蔽之。“整”一旦接人,就體現出其“懲罰,整治”的語義,于此處便和“搞”產生了分歧。
2.本義差異導致泛用范圍不同
一方面,“整”的含義接近于“處置,處理”,因此其作為處置動詞的泛用范圍也較“搞”更大。“整”強調的是狀態的變化,因此,不僅可以表示獲得,也可以表示消費,而“搞”更強調一個做出的動作,因此更偏向于獲得,而沒有消費、完成之義。比如“整兩瓶酒”就有消費的喝酒之義,而“搞兩瓶酒”就只有獲取的含義。另一方面,“搞”的本義是“攪”,本質上是一物進入另一物之內,并使后者的狀態發生變化。因此“搞”除了和“整”接近的作為處置動詞的含義,還有另一種泛義是“參與、從事”。例如常見詞“搞笑”,就不能替換為“整笑”,因為“整”只能作為處置動詞泛義,而笑作為處置對象無意義。只有當笑作為處置結果,如“給爺整笑了”時,“整”才能和笑連用。
同時,也正因如此,“整”在面對一些不是很具體的名詞,例如一些語義接近一種關系的動賓結構短語時,造詞能力要遠遜于“搞”。這一差異可以在用法上體現,一般來說,“整”所修飾的對象總是能接甚至必須接量詞,例如“我想整酒”就是一個不合理的說法,而“我想整兩瓶酒”就是可行的說法,又比如“整個節目”“整張相片”“整點買賣”,如果把中間的量詞刪去,就會很生硬別扭,而“搞”就沒有這樣的限制。準確來說,漢語中的大部分動詞尤其是泛義動詞都沒有這樣的限制。“我想做菜”和“我想做兩個菜”,都是合法的表述,但是“整”卻是高度受量詞制約的。對此,沈家煊《“有界”與“無界”》[6]與陸儉明《關于“有界/無界”理論及其應用》[7]中的觀點認為,量詞實際上把名詞進一步“有界化”了。量詞把名詞從一種普遍的指稱里面捕捉出來,變成一個具體的對象。“酒”可以是具體的眼前的這瓶酒,也可以是全體酒的泛指,是一個非特定的對象,但“兩瓶酒”就是非常具體的一組指向,必然是指代特定的某兩瓶酒。因此,這更符合“整”作為處置動作對于一個名詞性的處置對象的高度依賴。“我想做菜”這一句子中,“做菜”的目的是明確的,做菜就是為了要吃的;“我想整菜”這一句中由于“整”過于泛義,反倒表意不明,讓人不明所以,聽者不知道到底怎么“整菜”,也不知道“整菜”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自然就被會話雙方淘汰掉了;而“我想整兩個菜”這一句中,“兩個菜”從原來的“無界的菜”變成了實實在在的有界的“兩盤菜”,此時,句意便明朗了。“我想做菜”或“我想整兩個菜”這兩句表意明確的句子因遵守會話的質量原則被會話雙方保留了下來。所以很多時候,如果要用“整”去完成一些會話,需要借助一個量詞將后接名詞有界化才能形成一個合法的、足以支撐其某種具體的處置義來發揮作用的語法結構,而“有界化”的目的也是通過改變原本“無界”的事物的狀態或性質的手段來框定語義范圍,明確語境含義。此外,量詞的使用也讓整個句子更口語化,與“整”的語言氣氛更為適合。
五、結語
泛義動詞作為語言發展中產生的一個特殊現象,一方面,豐富了語言的文學性和創造性,為漢語尤其是方言增添了活潑性和特色性,另一方面,也讓其他語言環境下的學習者感到無所適從,既不理解其內在邏輯,也難確定其使用界限,構成了學習和交流上的障礙。因此,明確泛義動詞的語用特點及其成因,挖掘其背后深層次的語言規律,充分掌握其語用、語義和語法結構,是極有必要的。本文的分析表明,看似邊界模糊、含義不定的泛義動詞,其寬泛性背后其實有著嚴格的有限性,其無規律的表象背后有著深刻的語言規律。準確把握泛義動詞這一語言學現象,對方言研究和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都大有裨益。當然,本文仍有不足之處,僅僅深入分析了兩個源于方言的泛義動詞,對于更多的泛義動詞的探討,仍有待廣大研究者繼續求索。相信隨著對泛義動詞的進一步挖掘,我們能越來越明確泛義動詞背后的規律,更好地把握這一語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