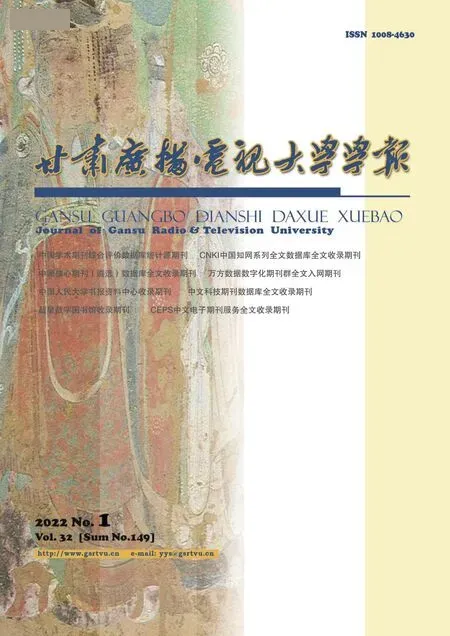晚清民國時期的蘭州旅館
——以西行文獻為中心
于方方,劉全波
(1.蘭州文理學院 外語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2.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西行文獻是指歷史上各個時代的人們自內地到西北出使、考察、旅游或任職時所留下的紀行文字,西行文獻記載了不同時期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道路交通、山川景色、氣候物產等內容,多側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區的社會風貌,是深入了解西北的極為珍貴的史料[1]。歷代保留下來的西行文獻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利用西行文獻不僅可以開拓西北區域史研究的新境界,還可以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帶來新視野。
廣義來說,只要能夠為遠行的人們提供食宿,特別是住宿功能的場所都可稱之為旅館。近代旅館業的興起與發展是中國旅游業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現象。近年來,學術界對近代旅館業的整體發展狀況、發展歷程、經營管理等具體領域都進行了諸多研究,同時,針對近代旅館業較為發達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也產出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侯艷興《銷金窟與競技場:民國時期的上海旅館》言:“上海的一些大中型旅館是市民除了家之外可以‘擁有’的另一個空間,對他們而言,已經把旅館這種經濟單位當成了一種消費的對象,在里面消費成了上海市民某種時尚和身份的象征。”[2]王京傳《民國時期的北京旅館業》言:“民國時期,北京旅館主要有西式旅館、中西式旅館、舊式旅館、招待所和公寓。當時北京旅館特別是西式旅館和中西式旅館普遍采用現代的管理體制和經營策略,并注重員工的選拔、培訓與管理。”[3]馮賢亮《民國時期江南旅館業與城市生活的現代化》言:“當現代化的發展態勢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時,人們對處于公共服務業關鍵地位的旅館,已不再懷有新奇的認識,而是成為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日常。”[4]潘雅芳《民國時期杭州旅館業的轉型及其社會根源探析》言:“民國時期也為旅館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反之,旅館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一個門類,其繁榮興盛也推進了杭州的城市現代化進程。”[5]
晚清民國時期是蘭州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一方面,明清以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積累,為蘭州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較為厚實的基礎;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西北同內地的經濟聯系,也超過了任何歷史階段,在此背景之下的蘭州,雖然不可避免的,仍帶有落后與狹隘的歷史印記,但這畢竟是一個具有承上啟下關鍵作用的發展階段[6]。蘭州的旅館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了起來,作為隴右襟喉、三秦屏蔽的重要城市,蘭州是有特殊性的,更是具有代表性的,本文以西行文獻為主,分析西行之人眼中的晚清民國時期的蘭州旅館,力圖還原一幅晚清民國時期的蘭州旅館風貌圖,從而對研究相對薄弱的西北旅館和社會生活史形成有益的補充。
一、晚清民國時期蘭州的舊式會館
1.浙江會館
陶保廉(1862—1938),字拙存,浙江嘉興人。陶保廉是清末民初的名人,曾任《清史稿》纂修。1891年,其父陶模調任新疆巡撫,陶保廉隨父至烏魯木齊赴任,《辛卯侍行記》就是其長途旅行的日記。陶保廉著,劉滿點校《辛卯侍行記》載:“(十月)初二日……住南府街浙江會館。”[7]214“(十月)十一日,壬寅,發蘭州浙館。”[7]247因陶模是浙江人,故陶模父子一行,在蘭州居住的是浙江會館。
侯鴻鑒(1872—1961),字葆三,號夢獅、病理,江蘇無錫人,《西北漫游記》是其在1935年旅行考察陜、甘、青、寧的一部實錄。侯鴻鑒著,陶雪玲點校《西北漫游記》載:“午正,往浙江會館。”[8]85“往浙江會館魏君處,午餐,晤四川天君,談話久之。見會館中一碑,為浙江張勤果公曜所撰書,有跋語,其銘文為篆者,曰:‘天山三十有二盤,伐石棚木樹扶蘭。誰其化險夷之安,嵩武上將唯桓桓。利有攸往萬口歡,恪靖銘石字龍蟠。戕毋扼損毋鉆邧,光緒二年四月刊。’讀此知天山三十二盤,勤果所銘也。”[8]97-98侯鴻鑒三入蘭州,兩入浙江會館會客,并記載了浙江會館中的碑刻。從1891年至1935年,從陶保廉到侯鴻鑒,浙江會館多次被記載,可見其狀況。
2.八旗會館
闊普通武,字安甫,蒙古族,生卒不詳,光緒二十四年(1898)以禮部左侍郎加副都統銜,出任西寧辦事大臣,《湟中行記》記述了作者由京師赴任,及罷官后返京之沿途所見。闊普通武著,王晶波點校《湟中行記》載:“三月初一日……制軍派全隊郊迎,率闔城文武官跪請圣安畢,入城,至皋蘭縣八旗會館宿。”[9]晚清至民國,皋蘭縣是甘肅首縣和省會重鎮,故皋蘭縣八旗會館即是蘭州八旗會館。
3.江西會館、鐵柱宮
裴景福(1855—1926)字伯謙,安徽人,光緒三十一年(1905)三月二十七日,由廣州啟程,經江西、安徽、河南、陜西、甘肅,于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到達烏魯木齊,行程11 720余里,起訖370余天。裴景福著,楊曉靄點校《河海昆侖錄》載:“二十二日,晴暖……午后,同海秋、潘志言往看江西會館。房可住,言定月租四千,押租十金,擬二十四移居。”[10]116“二十三日,晴暖。昨訂江西館,屋未成。”[10]117可見,蘭州有江西會館,江西會館位于今蘭州市博物館附近,但是不知何故,裴景福未能入住江西會館。“二十六日,晴。午,海秋來。午后,移居鐵柱宮,賃金照前議。”[10]119由“移居鐵柱宮”可知,裴景福在蘭州的住宿之所是鐵柱宮。
4.黃華館(皇華館)
《北草地旅行記》是李德貽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從鎮江由海路上北京,經內蒙古到新疆伊犁,復自伊犁經河西至蘭州的所歷所事。李德貽著,達浚、張科點校《北草地旅行記》載:“翌晨隨節起行,十月初一日抵蘭,駐黃華館。”[11]
袁大化(1851—1935),字行南,安徽人,宣統二年(1910)調任新疆巡撫,《撫新記程》是其在宣統三年(1911)赴任新疆巡撫時的紀行之作。袁大化著,王志鵬點校《撫新記程》載:“二十里至省城,入東門,長少白制府率同現任司道等在官廳相迎慰勞,甚歡,住皇華館。”[12]李德貽與袁大化皆曾入住皇華館,雖然李德貽情況不甚明了,但由袁大化的身份可知,此館應是非同一般,當是當時極好的住宿之所。
5.皖江會館
林競(1894—1962年),字烈敷,浙江人,畢業于日本東京政法大學,后曾任青海、甘肅民政廳廳長。1918年至1919年,他開始了第二次西北之行,從北京出發,經河北、內蒙、寧夏、甘肅到新疆,在蘭州時,與當時名流多有交接。林競著,劉滿點校《蒙新甘寧考察記》載:“二月十日。晴。華氏二十八度。……十二時返寓,而張督催往皖江會館聽戲,蓋今日為省會各機關團拜,在此宴會,并演戲助興。今早張督已命江知事敬封來邀也。一時前往,軍政各界均已到齊,只候余一人入座矣。是日所演戲目為《鐵公雞》《四杰村》《胭脂虎》《關王廟》《四郎探母》《八蠟廟》,各演員藝雖不高,卻異常出力,邊地睹此,亦異數也。”[13]91-92
程先甲(1874—1932),字一夔,又字鼎丞,江蘇人,舉人,著名文字學家和《文選》學家。1919年程先甲曾有隴上之行,是年3月由北平到包頭,溯黃河經寧夏(今銀川市)到達蘭州,供職于省署,至1922年冬,復自原路返北平。《游隴叢記》是記述這兩次旅途及在蘭州見聞的集結,《游隴集》則是這期間所作的詩詞集。程先甲著,達浚、張科點校《游隴叢記》載:“皖江會館——江蘇舊會館原甚湫隘,勛帥于石子山創建皖江會館,安徽、江蘇兩省寓公從而贊助之,規模宏敞,內有劇院,凡團拜及公燕、喜慶諸事,多于是館。余嘗代仙帥撰一楹聯,又自撰二聯,均載《千一齋小品》中。又嘗偕同僚公燕孔華清,華清好風雅,均載《菩薩蠻》一闋,蘭人盛傳之,詞載《百仙集》。”[14]52民國時期的皖江會館是新建筑,安徽、江蘇兩省的士紳捐資贊助,故得名,并且此皖江會館有戲樓、劇院,故凡團拜及公宴、喜慶諸事,多于此館舉辦。
6.山陜會館
馬鶴天,山西人,從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一日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二十八日,走走停停前后歷時三年整,先后職務由行署參贊而代專使,復為參贊而變為護靈專使。正是在如此漫長的時程和緩慢曲折的行程中,作者才得以深入接觸廣大藏區政教軍民各色人等,多方考察邊區藏蒙回土諸民族、各部落的生產生活、民情習俗、歷史文化,以至邊區的山川林藪、物產氣候等。馬鶴天著,胡大浚點校《甘青藏邊區考察記》載:“(九月)七日。至距城數里處,參謀本部張明德諸君,交通部穆逢欣君等,先后乘車馬迎于郊外,詢知高參軍、徐參謀等,剛覓定山陜會館為寓址,正在忙于布置,未能出城。至西城門,戒備甚嚴,見大批人馬頗驚疑,用電話請示綏靖公署,始許入。旋即至山陜會館,一部分屋宇尚為兵士住居,明日始可移出,暫屈居于后院內,一切物品,堆積院中,騾馬暫喂各店。”[15]1936年9月7日,馬鶴天再來蘭州,因蘭州戒嚴,故派前導入城尋找寓所,計劃寓于山陜會館,因山陜會館有兵士居住,故暫屈居于山陜會館后院之內。
二、民國時期蘭州的新式旅館
1.華興旅館、豫盛店
陳萬里(1892—1969年),江蘇人。1925年春天,美國哈佛大學考古隊華爾納等將赴敦煌考察,邀請北京大學派人參加,北京大學派陳萬里同往調查,2月16日從北京出發,7月31日回到北京,共歷時五個半月。陳萬里著,楊曉斌點校《西行日記》載:“十五里東關門,經東關大街,進南門至馬坊街華興旅館住。”[16]50“(六月)二十八日……尖后四十里到蘭州,寓東下關豫盛店;略坐,即進城在華興用飯。”[16]97“七月一日……十二時往華興飯,得蠶豆及小青椒,時天已放晴,惟道路極泥濘耳。”[16]98陳萬里兩次到達蘭州,一次住在華興旅館,一次住在豫盛店,但卻記載了兩次在華興吃飯,可見此華興旅館不僅提供住宿,并有餐飲。
2.中西旅館
林鵬俠,旅居新加坡的華僑,祖籍福建莆田,林鵬俠奉母命,于1931年11月24日從上海出發,30日至西安,開始了她對西北陜、甘、青、寧各省的考察。林鵬俠著,王福成點校《西北行》載:“二十三日……自平涼西來,每日均登峰越嶺,履險趨艱,刻刻有顛復之虞,處處無平易之徑,懸心忍氣,寸晷難安。今幸已達康莊,回憶過去,殊有苦盡回甘之樂。近省垣之道路,尤寬敞平治,聞為民十二年國民軍所修者。車行其間,遂若風馳電掣。九時,即抵皋蘭。城內商業之盛,殆過西安,惟馬路較狹。入城,倉卒莫知所往,乃依康君邀約,暫寓現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先生之宅。粉壁丹墻,規模雄壯,其間布置,頗能寓雅致于宏敞。”[17]45-46“二十三日……下午,田副官已代覓妥城南中西旅館,驅車往視。房雖小,然尚清潔。遂囑茶役更事灑掃,約以翌日遷來。歸途本擬瀏覽街頭,一窮社會生活情況。忽頭痛殊劇,急乘車回寓。夜餐略進,即行收拾就寢;此處雖亦系土炕,然構造甚精,頗似南方舊式之木床,髹以丹黃,鋪以厚氈,且整理妥貼。室中溫暖,較之途間棲止,誠若天堂矣。”[17]45-46林鵬俠旅途多有勞累,故至蘭州后,深感安樂,對蘭州亦是多有溢美之詞。“(四月)八日……既而抵金城關,渡黃河鐵橋,入城,仍駐足中西旅館。”[17]177林鵬俠兩次入住中西旅館,可見中西旅館還是比較符合好旅館的標準,雖然房間比較小,但是干凈整潔,雖是土炕,但整理妥帖,溫暖溫馨。
3.江蘇旅社、金城旅社
侯鴻鑒著、陶雪玲點校《西北漫游記》載:“一時入城,寓南大街綢鋪街江蘇旅社二號,武、周、陳、倪、竇諸君均同寓此。”[8]50“二十五里,約四點鐘,始到蘭州,入城抵綢布街江蘇旅社。卸裝后,晤武、陳、周三君,快甚,握談青海狀況,為之粲然。”[8]78“仍寓江蘇旅館。”[8]94“往金城旅社應武君等邀。”[8]96可見,侯鴻鑒三次入住江蘇旅社,并曾往金城旅社訪客。
4.中華旅館
陳賡雅(1905—1995年),筆名任安、石英,云南人,《申報》記者,《西北視察記》一書是其于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對西北各省作考察采訪的通訊集。陳賡雅著,甄暾點校《西北視察記》載:“十五里抵蘭州,時已入夜,電燈火光,交燦如晝;黃河流聲甚大,反覺人間默不一語。城門已閉,宿金城關,是日計行程一百四十里。翌晨入城,卜居中華旅館。”[18]108“鴿子魚。產于靖遠河口,冬季鑿冰捕得,其形似鴿,故名。俗謂真鴿投水所變,乃附會之說也。惟味甚佳,當地人常用以餉客,別具風味。”[18]117陳賡雅對蘭州的物產多有記載,其中,特別提及鴿子魚。張恨水《西游小記》亦載:“此外,還有一種黃河鴿子魚,也是請客的上品。魚不過筷子長,大頭扁嘴,嘴上有兩根肉須,酒席上照例每盤一對。每一對魚,卻要值洋兩元。”[19]93
5.勵志社
莊澤宣(1895—1976),祖籍常州。其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于杭州任教時,受當時教育部之聘,到西北視察教育。莊澤宣著,達浚、宗華點校《西北視察記》載:“四月二十二早六時半,余等再抵機場,七時二十分登十七號機,二十五分起飛,同機者有甘省一、二、五區專員張績忱、盧廣績、王向山三先生,寧夏航空站發電員沈同柏先生及其妻女,計共七人,占六座,全機實可坐十四人。起飛不久,即過渭河,關中平原開展如畫,未幾經鳳翔、隴州入六盤山脈區域,機漸升高,達三千二百公尺,蓋山高近二千五百公尺也。機上設有熱氣管,故不覺寒,過六盤山后,機仍高飛。靜寧、會寧二城,在腳下經過,宛如地理模型。過會寧后始降至二千公尺,旋見黃河蜿蜒如蛇,九時三十五分即達蘭州機場。省府及教廳方面,均派人來迎。余等乘小汽車,行李則交歐亞大汽車運入城內。省府招待余等至新落成之勵志社下榻,勵志杜在省府署之西北隅,另有大門,原為署后花園之一部分。”[20]莊澤宣是乘坐飛機到達蘭州的,這與此前諸人多有不同,免去了長時間的旅途奔波,而作為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代表,視察西北教育,省府招待亦是殷勤,故其住宿之所為省府署西北隅的勵志社。
6.齊魯大旅社、南關大旅社、隴秦旅社
顧頡剛(1893—1980),字誠吾,號銘堅,江蘇蘇州人,著名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西北考察日記》是1937年至1938年顧頡剛先生率員在甘肅、青海調查教育的生動記錄。顧頡剛著,達浚、張科點校《西北考察日記》載:“(九月)三十日:聞西北考察團團員白亮誠、白壽彝兩君俱住此間齊魯大旅社,因訪之,知其自北平出發,游綏遠、寧夏后抵蘭,近又至青海歸矣;此吾團中之后頸也。”[21]180-181可見,齊魯大旅社是白亮誠、白壽彝當時的住所。“(十月)十四日:三時二十分抵蘭州南關大旅社,雇車向舊教廳。”[21]186可見,南關大旅社是顧頡剛在蘭州的暫住之所。“(十月)二十二日:八時與孟和先生及渭珍、貽澤同到東關隴秦旅社,晤陸軍運輸處汽車總隊長,辦手續訖。”[21]187又可見,隴秦旅社則是陸軍運輸處汽車總隊長的臨時寓所。
三、晚清民國時期蘭州的餐館
祁韻士的戍途于嘉慶十年(1805)二月十八日自京師始,歷時170余日,于七月十七日抵達伊犁惠遠城。根據戍途所見,祁韻士創作了長達一萬兩千余字的紀行散文,因路途一萬七百余里,故名《萬里行程記》。祁韻士著,李正宇點校《萬里行程記》載:“西行二十里至蘭州府。城東衢路蕩平,直至坡下。目擊園畦叢薄,點綴道旁,心為一暢。府城雄據黃河南岸,五泉山在城南二里許,稱名勝,游人不絕。城北黃流浩渺,自西而東,有二十四舟為浮橋,束水若帶,兩岸鐵索系之,復用集吉草為巨綆,維舟屬橋,渡者如履平地。北岸多酒樓,開窗臨水,南望城郭,林樹如畫。惟岸上山楛,草木不生,僅有番僧寺宇耳。”[22]祁韻士是較早的經行蘭州的晚清文人,其言北岸多酒樓,且鄰水望山,可見,蘭州的旅館、餐館環境較佳,祁韻士對蘭州的評價總體還是較好的。程先甲《游隴叢記》言:“木料局——在蘭州北門外,其后客座極軒敞,略似河廳;面臨黃河,水聲浩浩甚大,別有意致。余有聯載小品。”[14]52木料局坐落于蘭州北門外,其后面有用來招待客人的后座,極其寬敞,類似于面向河的廳堂,可以看見河水浩浩蕩蕩而去,別有一番風味。此處看起來,不像是餐館,更像是喝茶之所,與祁韻士所記有異曲同工之妙。
1.金谷園
裴景福著,楊曉靄點校《河海昆侖錄》言:“晚至金谷園,赴伯庸之招,同坐九客,杯勺皆銀,為東南酒館所無。”[10]119此外,裴景福對蘭州的餐飲也有評論。“蘭州無時鮮,酒筵多用海味。黃河白魚最美,大者一頭千余錢,鴨雙掌四五百錢。”[10]121
2.榮慶園
林競著,劉滿點校《蒙新甘寧考察記》載:“下午一時許,同鄉潘詠侯招飲于縣前榮慶園。同坐多鄉親,異地相逢,情意倍殷。此間吾浙人最少,統計不過數十人。大半系前清仕宦或幕友,失業之后,因道遠天遙,無力回家,流寓此間有已經二三代者。其分發來甘,及在各機關服務者,居極少數,其從事商業者,不過一二人而已。是日肴饌頗豐,每席僅費十五六兩,廉于新疆遠矣。”[13]87-88林競對1919年2月5日蘭州同鄉聚會的餐飲價格做了記載,每席僅費十五六兩,“兩”應是“元”的意思,且與新疆之餐飲價格做了對比。
3.東關花園別墅、東方春羊肉館
林鵬俠《西北行》兩次記載了東方春羊肉館:“二十七日。晨間,民政廳秘書主任翁木圣先生來訪。……午間,至東方春羊肉館,應林夫人餐會。”[17]51“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午后,木圣先生約赴東方春食羊肉鍋。此北方冬令號稱最美之食品,以其味厚而清腴爽口,雖不善肉食者,亦可盡數碟也。”[17]56
林鵬俠《西北行》還記載了東關別墅花園:“(四月)十五日……午赴徐兆筌先生之約,驅車至東關花園別墅,客己齊集。墅臨黃河而筑,人望風景絕佳。園內樓閣亭榭,布置殊修潔。翠蔭中遍植名卉,色香沁人心目。”[17]179東關別墅花園臨河而建,目及之處風景絕佳,內部不僅亭臺樓榭疏落有致,而且樹影花香令人沉醉。
4.慕蘭居、金城飯店、北平飯店、榷運局、名勝園
侯鴻鑒三入蘭州,且在蘭州停留時間長,故其所記載的蘭州餐館亦多。《西北漫游記》載:“二時往慕蘭居午餐。”[8]50“武君來約往金城飯店晚餐,座客有江蘇同鄉萬秀岳,字幼璞,儀征人,任電局一科科長,山西馬蔚奇中央銀行營業主任,甘肅車南軒電局科員。”[8]78“又訪張委員維于甘肅通志館,久談,即出,往金城旅社應武君等邀,陪孟君等于北平飯店晚餐,餐罷,即返寓。”[8]96“是晚張九如邀往榷運局,晚餐,大烹羊肉,座客十一人。此種羊肉,名手抓羊肉,蓋始自番人所食者,故名。”[8]98“往貢院巷樂善書局訪楊顯澤先生,楊先生贈余詩六首,偕李行之、魏振華三人作東道,邀余至名勝園晚餐,座客有王子豐、高德生兩君,均楊先生之門下,且與江蘇教育有關系者。”[8]101
5.金城食堂、慶春園、福華軒
1937年至1938年,顧頡剛在西北考察教育,蘭州是大本營,故在蘭州逗留時間亦久,參與的聚會、宴會亦多。《西北考察日記》載:“(十月)十四日:貽澤由西蘭公路至,同赴金城食堂進食。”[21]186可以想見,侯鴻鑒所記金城飯店與顧頡剛所記金城食堂應是一處,只是二人所說的名字略有不同而已。“(十月)二十二日:六時半起束裝,上街吃羊肉泡饃。”[21]187此處的羊肉泡饃雖沒有記載下店鋪名字,亦可見蘭州餐飲之一斑。“(八月)二日:今日為陰歷七夕,雷壇有香會,順道往觀之。定邦等邀至新關慶春園晚餐,看天上雙星。園中小有花木,且在河堤之旁,水車聲隆隆,對面細談為之禁遏;蘭州最勝處也。”[21]254“(八月)三日:下午與謹載雇騾車至小西湖,又下黃河,乘皮筏至慶春園——此一新經驗也;筏身過輕,洪濤駭浪之中亦自驚心怵目——應毅之夫婦之宴而回。”[21]254-255“(八月)四日至十六日:予返蘭消息既傳出,賓客群集,遂不勝其酬酢之忙。最使予感興趣者,為十三日新疆旅蘭同鄉會之招待,主人為哈的爾、阿海麥提、文伯都拉阿吉、買和信諸君,所進為新疆之手抓飯,猶內地之什錦炒飯然,洗手而攫食之。”[21]2551938年,8月上旬,顧頡剛再次回到蘭州,如他自己所言,賓客群集,遂不勝其酬酢之忙。“(九月)八日:上午六時至飛機站,待至七時許,以陰雨無機退出。楊向奎、孫元征、史念海諸君邀至福華軒食‘高三肉’,游大佛寺藏經樓及鐘樓。”[21]258高三肉為蘭州傳統名食,以肉質新鮮、色澤光亮、不肥不膩而聞名,始由高彬吾精心研究而成,因高氏行三而得名。
四、結語
1934年5月,張恨水離開北京,前往西北考查,將沿途所見所聞編輯成《西游小記》。《西游小記》載:“旅館。蘭州城里,比較像樣一點的旅館,共有國民飯店等八家。其中只有兩家預備有被褥出租,好在向蘭州來的人,都是帶有鋪蓋的,這倒沒有多大問題。最貴的房間,一元錢上下,不帶伙食。其次幾毛錢的,也勉強可住。房間里除床或炕而外,只有木頭桌椅,并無別的陳設,但多數有電燈。旅館都在城里省府附近,容易打聽。西北人樸實,蘭州人尤其干脆,旅館商人沒有什么訛詐人的事情,旅客可以放心。”[19]93“酒館。蘭州城里,并沒有像西安那樣大的酒飯館,不過設下七八副座位,便是上中等的了。有一家最有名的菜館,還是附設在旅館里的,可以想見其余。”[19]93通過張恨水的文字,我們對蘭州旅館、酒館的真實情況,抑或是總體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概言之,蘭州人是干脆的,而旅館、酒館之情況則需要客觀評價,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林競著,劉滿點校《蒙新甘寧考察記》載:“二月二日。晴。十一時,實業廳司徒君招飲,筵為西式,材料多自京、津用郵政寄來,聞蘭州近來此風頗盛。”[13]87“三時應勛伯督軍之招,席設督署節園,亦西餐。聞蘭州一隅,香檳酒一項,歲入四十余萬元,奢哉!”[13]87通過林競的記載,1919年的蘭州,西餐的風氣業已展開,由此亦可見蘭州的另一面。
西行文獻是一批非常特殊的文獻,他們的重要性還沒有被認識到,尤其是晚清民國時期的西行文獻,學界多認為他們是淺薄的、主觀的,不足為憑、不足為據,其實,我們以前就說過,對于一個個所謂的小地方而言,他們是很少有機會被正史所記載的,而文人墨客的不經意間的游記、雜記,恰恰是記錄一個地方歷史文化的最為珍貴的材料,且是多姿多彩的珍貴材料。通過對西行文獻的梳理,我們得到了一些晚清民國時期蘭州旅館、餐館的認知,這個認知無疑是淺顯的、初步的,甚至于只是得到了一些旅館、餐館的名字而已,對于諸多旅館、餐館的經營理念、基礎設施、社會影響等的認知則是欠缺的,還有待新的考察、新的資料來補充。
對比晚清民國時代北京、上海、杭州的旅館、餐館,我們也能感覺到明顯的不同。以上海為例,上海的旅館已經被認為是家之外的另一個空間,旅館成了上海市民某種時尚和身份的象征,而在蘭州,在諸多的西行文獻中,普遍沒有這種感覺,僅僅是提供住宿的場所而已,可見蘭州旅館與上海旅館之間的重大差別,亦可見經濟發展狀況、文化面貌、文化觀念的差異。當然,換一個角度來看,蘭州永遠只能是蘭州,不會變成其他,盲目地對比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就是蘭州的獨特性、特殊性。最后,我們所做的聊勝無于的初步的、淺顯的關于蘭州旅館、餐館的考察,還是讓我們重溫了一些漸漸被遺忘的蘭州故事,手抓羊肉、羊肉泡饃、鴿子魚、高三肉,等等,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這對于我們認識晚清民國時期的蘭州還是有建設意義。蘭州從來不是一個缺少歷史與文化的城市,蘭州也從來不是一個自甘邊緣、自甘寂寞的地方,只有當我們對她的認知越來越豐富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她獨特的歷史與鮮明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