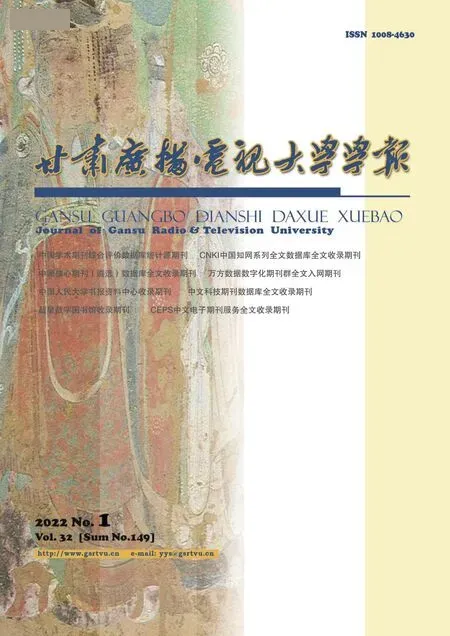漸進式政治發(fā)展模式的人性基礎(chǔ)探微
葉長茂
(廣東第二師范學(xué)院 政法系,廣東 廣州 510303)
在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過程中,各國政治發(fā)展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激進式,一種是漸進式,其他政治發(fā)展模式要么是二者結(jié)合,要么是其變種。激進式政治發(fā)展可以推動社會進步,但往往需要付出比較大的代價。選擇漸進式政治發(fā)展模式的國家雖然進步緩慢,卻能通過長期的制度改進以較小成本取得突出成就。在近代頑固的專制勢力比較強大的時候,選擇激進式政治發(fā)展模式有其合理性,激進式政治發(fā)展所追求的理想、價值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但在和平與發(fā)展成為人類主旋律的時代,在人民主權(quán)已得到憲法確認(rèn)的國家,漸進式政治發(fā)展模式顯然是一種更優(yōu)的選擇。漸進式政治發(fā)展之所以能持續(xù)推動人類進步,是因為其植根于人類的本性。深入探討漸進式政治發(fā)展模式的人性基礎(chǔ),有助于后發(fā)展國家的精英與民眾樹立漸進主義信念,自覺選擇通過和平、協(xié)商、非暴力方式推動政治進步。
一、人性發(fā)展的兩種可能性
人的自然本性不適合用善、惡來評價,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已指出,人的潛能是自然生成的,美德和邪惡不是人的潛能,“我們不能說一個人天生是善的或惡的”[1]。善、惡不是人性固有的本質(zhì),只是人性中潛在的傾向[2]。人們一般所說的善、惡是用特定的社會道德標(biāo)準(zhǔn)對人的行為所作的價值判斷。
人的基本特性可以概括為道德上中立的自利性,也就是人所共有的趨利避害的自然天性。政治思想史上關(guān)于人的自利特性有許多深刻的論述。休謨指出,在自然性情方面,每個人愛自己都會超過愛其他任何一個人,所以我們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自私在其中是最重大的[3]527-528。沒有一種激情是能夠完全無私的,即使是最慷慨的友誼,也只是自愛的另一種形式[4]。斯密也認(rèn)為:“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guān)心自己;……每個人更加深切地關(guān)心同自己直接有關(guān)的、而不是對任何其他人有關(guān)的事情。”[5]101-102馬克思主義人性論承認(rèn)人既是一定社會關(guān)系中的社會存在物,也是一種具有物質(zhì)利益需求的“自然存在物”[6]。人追求利益的天性來源于人的動物性本能。恩格斯指出:“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jīng)決定人永遠(yuǎn)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yuǎn)只能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于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7]人要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生活與發(fā)展,首先必須努力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就像馬克思所說:“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就是人們?yōu)榱四軌颉畡?chuàng)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8]生存理所當(dāng)然是人類的第一需要,所以人的行為取向自然傾向于自我保存,逃避危險,追求能夠滿足自身需要的利益、榮譽和權(quán)力。
自利是人的自然本性,人先天具有的這種自利傾向不能用善惡來進行評價。人的自利行為只要不傷害他人及公共利益,便是正當(dāng)?shù)摹H诵园l(fā)展實際上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向善,一種是作惡。一個人向善還是作惡,關(guān)鍵取決于外在的制度環(huán)境。人的行為是個體選擇與制度環(huán)境互動的產(chǎn)物。外在的制度環(huán)境如果崇善抑惡,大多數(shù)人就會成為良善的公民。外在的制度環(huán)境如果不能保護善良,懲罰惡行,即使有少數(shù)人選擇行善,但大多數(shù)人只能變成茍且冷漠的小人。
鼓勵人們抑惡從善需要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和制度環(huán)境。在一個秩序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人性中的作惡傾向通常被嚴(yán)格限制在社會可容許的范圍之內(nèi)。一旦制度和環(huán)境突然產(chǎn)生變化,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個體作惡的可能性則會大大增加。雖然有少數(shù)人在惡劣環(huán)境中也能行善,但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無約束易為惡則是常態(tài),這是由人的生存本能決定的。正是人性中存在的這種自保與自利的傾向使人在缺乏外在規(guī)范和約束的條件下很容易傷害他人,謀取私利。斯密曾形象地描述了這種侵害他人的傾向:人們很容易接受誘惑,去恃強傷害一個人,如果沒有在人們中間確立正義的原則,如果沒有使人們懾服而敬畏的力量,人們就會隨時準(zhǔn)備向他人發(fā)起攻擊[5]106-107。
人性的制度約束一旦松懈,就會產(chǎn)生大量惡行。正因如此,對人性的理性態(tài)度是不能過于樂觀,不能寄予過高期望,而是應(yīng)該保持警惕和防范。張灝曾用幽暗意識來概括這種對人性較為謹(jǐn)慎的看法。幽暗意識是一種低調(diào)的人性觀。所謂幽暗意識是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正是由于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人的生命才有各種丑惡,世界才不會圓滿。這種幽暗意識珍視人類的個體尊嚴(yán),正視人的罪惡性和墮落性,但是其在價值上否定人的私利和私欲,然后在此前提下防堵和疏導(dǎo)人們?yōu)閻褐疂撃躘9]2。這種對人性的審慎態(tài)度不能等同于性惡論,而是承認(rèn)每個人都有墮落趨勢與罪惡潛能,必須用制度化的東西加以約束[10]。人的自利性以及潛藏的作惡傾向?qū)τ谌说暮筇煨袨榫哂猩钸h(yuǎn)的影響。防范人性中的作惡傾向膨脹進而規(guī)范人的自利行為成為文明社會道德與制度建構(gòu)的第一要務(wù)。對待人性較為客觀的態(tài)度,是構(gòu)建人性良性發(fā)展的制度條件,防范人性可能為惡的一面,同時鼓勵人性中積極向善的一面。
二、從人性視角看政治發(fā)展的模式選擇
政治發(fā)展是世界各國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所發(fā)生的趨向進步的政治變遷,通常會對社會政治環(huán)境產(chǎn)生較大影響。如果一個國家選擇激進式政治發(fā)展道路,就會急劇改變社會個體的生存環(huán)境,很容易造就制度真空,使人性失去基本的約束,從而改變?nèi)藗兊膬r值取向和行為模式,對道德規(guī)范和社會秩序產(chǎn)生嚴(yán)重沖擊。法國思想家勒龐認(rèn)為,一旦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例如突然發(fā)生嚴(yán)重的動亂,那么個體人格與社會環(huán)境的平衡就會被打破,對人性的束縛就會全然解除。在擺脫了所有傳統(tǒng)和法律的約束之后,人的本能就失去了羈絆,留在人們身上的就只有原始的獸性了[11]195-208。同一個個體的人格將發(fā)生驚人變化,前后判若兩人。一個在平時溫文爾雅的人可能變得殘忍好殺[11]51-52。休謨在《人性論》中也表達(dá)過同樣看法,他認(rèn)為人類的貪心和偏私如果不受某種一般的、不變的原則所約束,世界就會混亂不堪。當(dāng)約束民眾原始野性的規(guī)范體系被輕率地打破之后,在人類社會中就會產(chǎn)生無限紛擾,爆發(fā)激烈的沖突[3]572-573。
在社會失范狀態(tài)下,不僅個體的性格特征和行為模式會發(fā)生嚴(yán)重變異,而且平時沉默的群體也會行動起來,參與各種政治與社會沖突。動蕩時期,當(dāng)民眾大規(guī)模參與政治生活時,政府可能會喪失部分或全部權(quán)力,一部分權(quán)力轉(zhuǎn)移到臨時組織起來的民眾手中,難以受到有效約束。不完善的人性和不受制約的權(quán)力相結(jié)合,很容易沖破各種制度規(guī)范。人性中潛藏的惡的因素會在失去約束的群體中急劇膨脹,人的性格會畸形發(fā)展,失去理性、判斷力和責(zé)任感,對社會造成嚴(yán)重的危害。孤立的個人因為擔(dān)心受到懲罰,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fù)責(zé),能夠自覺抵制各種犯罪的誘惑和沖動。當(dāng)個人集聚在一個龐大的群體中時,就會出現(xiàn)完全不同的情形。恰如勒龐所指出,當(dāng)個人加入一個不負(fù)責(zé)任的群體時,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所以約束個人的責(zé)任感會徹底消失,人多勢眾使個人感覺到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他們很容易放縱自己的本能,犯下各種罪行[12]。柏克也認(rèn)為在民眾普遍參與的政治狀態(tài)下,沒有人會害怕自己可能要受懲罰,因為民眾整體不能成為懲罰對象[13]。
從人性的視角看待政治發(fā)展問題,后發(fā)展國家的最佳方略是選擇漸進式政治發(fā)展模式,通過漸進改革的方式推動政治體系的演進和更新。后發(fā)展國家的政治發(fā)展面臨不利的國際環(huán)境,很容易受到外部勢力的干預(yù)和影響,國內(nèi)民族、宗教、地區(qū)、階層矛盾比較突出,如果選擇激進式政治發(fā)展道路會對社會秩序造成顛覆性破壞,政府權(quán)威弱化,法律和制度失去約束力,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的危害極大。人性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沒有法律和制度的約束,在政治發(fā)展過程中更是如此。為阻止人性向惡的方向發(fā)展,需要延續(xù)道德傳統(tǒng)來訓(xùn)導(dǎo)人的精神,保持法律的穩(wěn)定性以規(guī)范人的行為,才能在變動社會中使人們的權(quán)力濫用和貪婪的權(quán)力欲求有所收斂[14]。政治變遷本來就對現(xiàn)存的法律秩序構(gòu)成威脅,如果選擇激進式政治發(fā)展道路,摧毀制約人們行為的規(guī)范體系,就會導(dǎo)致各種惡行泛濫。在政治發(fā)展的過程中需要對人性中所隱藏的作惡可能性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終保持制度和規(guī)范的穩(wěn)定性,確保政府的權(quán)威和基本的法律體系能夠約束人性的弱點。政治發(fā)展不能借助全面改造人性與制度來實現(xiàn),不能輕易地拋棄社會原有的制度體系,而是要通過審慎的改革消除舊制度的弊端,使新制度在舊制度基礎(chǔ)上逐步生長,在避免社會動蕩的前提下實現(xiàn)新制度取代舊制度的目標(biāo)。
三、漸進式政治發(fā)展模式的制度設(shè)計
因為人性發(fā)展有兩種可能性,所以思想史上出現(xiàn)了性本善與性本惡兩種對立的人性預(yù)設(shè),并且對政治制度設(shè)計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這兩種人性理論都是片面強調(diào)了人性在某一方向發(fā)展的可能性,誤把后天生成的德性當(dāng)作人的原初本性,以此為據(jù)推導(dǎo)出的制度設(shè)計必然存在重大缺陷。例如,中國古代的儒家對人性的主流看法是性本善[15]。人性善的假定應(yīng)用于私人領(lǐng)域和一般社會生活領(lǐng)域,有其可取之處。但若根據(jù)儒家的人性假定設(shè)計政治制度,則難免會失效。儒家的政治設(shè)計是由圣人掌握最高權(quán)力或者寄希望于掌權(quán)者自覺提升德性以實現(xiàn)良治,卻未對掌權(quán)者濫用權(quán)力設(shè)置有效的制度性防范措施。這種性善假定與絕對權(quán)力的結(jié)合在實踐中只能導(dǎo)致披著道德外衣的專制統(tǒng)治。中國古代的法家認(rèn)為人性本惡,并且推崇絕對“性惡論”,主張以嚴(yán)格的法律與統(tǒng)治權(quán)術(shù)控制官員和百姓。但是法家式的性惡論有兩大缺陷,一是在社會生活與私人生活領(lǐng)域也貫徹絕對的性惡論,對百姓實施嚴(yán)刑峻法,不能為人性向善、自由選擇提供充分的空間,摧毀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失去了創(chuàng)造良好生活的可能性;二是在公共政治領(lǐng)域,性惡論的假定不包括最高統(tǒng)治者,最高統(tǒng)治者掌握了絕對權(quán)力,又不加以系統(tǒng)性的制度約束,必然為暴政打開大門。馬基雅維利是西方近代性惡論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所主張的性惡論和中國古代的法家有相似之處,都把君主排除在外,只強調(diào)君主可不擇手段控制臣民,卻忽視了對掌權(quán)者的制約。顯然,在政治生活領(lǐng)域,片面的性善論或者性惡論都不能構(gòu)建良好的政治制度,創(chuàng)造良好的政治生活。
一個國家若要成功推進漸進式政治發(fā)展,國家的制度設(shè)計必須充分考慮人性的兩重性。在私人領(lǐng)域及一般社會生活領(lǐng)域,除以法律防止個人侵犯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外,制度設(shè)計應(yīng)相信人性具有向善的可能,側(cè)重以道德教育、榜樣示范引導(dǎo)人向善,政府權(quán)力恪守界限,不過分干涉私人生活及社會交往。在公共政治領(lǐng)域,制度設(shè)計應(yīng)重點關(guān)注人性趨惡的一面,始終著眼于對人性蛻變與權(quán)力濫用的防范和制約。在體制轉(zhuǎn)型過程中防范掌權(quán)的政治人物或群體人性蛻變尤為重要,不能因為政治體制的新舊交替而對權(quán)力的制約稍有松懈。在人性中潛藏著作惡的可能性面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政治人物也不例外。“當(dāng)個人由市場中的買者或賣者轉(zhuǎn)變?yōu)檎芜^程中的投票者、納稅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員時,他們的品性不會發(fā)生變化。”[16]341制定法律和掌握政府權(quán)力的人也和普通人一樣,同樣是被難以控制的情感和直接的利益所驅(qū)使,并且因為掌握著強制性的公共權(quán)力,政治人物更容易受到人類弱點和情感的支配,更容易濫用手中的權(quán)力。不僅位高權(quán)重的個人有受權(quán)力腐化的趨勢,特殊時期掌握了政治權(quán)力的民眾也容易受到權(quán)力的腐蝕,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欺凌其他群體[9]10-11。普通人大規(guī)模直接進入政治生活領(lǐng)域,成為活躍的政治行動主體,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政治權(quán)力時,其人性中所潛藏的惡的可能性也會集中爆發(fā)。多數(shù)人掌權(quán)如果不受制約同樣有濫用權(quán)力的危險,并不會因為人數(shù)眾多而改變?nèi)诵酝懽兣c權(quán)力變質(zhì)的基本規(guī)律。
推進政治發(fā)展的政治主體,無論是少數(shù)人抑或多數(shù)人,都有可能濫用政治權(quán)力,因此防止任何政治力量濫用權(quán)力應(yīng)是漸進式政治發(fā)展過程中政治制度設(shè)計的首要任務(wù)。雖然人性本身并非注定為惡,但政治制度設(shè)計的邏輯必須著眼于人性的約束,對惡的發(fā)生預(yù)先防范,必須從假定人人皆可濫用權(quán)力的角度進行制度設(shè)計。休謨對此曾提出著名的“無賴假定”,即“在設(shè)計任何政府體制和確定該體制中的若干制約、監(jiān)控機構(gòu)時,必須把每個成員都設(shè)想為無賴之徒,并設(shè)想他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謀求私利,別無其他目標(biāo)。我們必須利用這種個人利害來控制他,并使他與公益合作,盡管他本來貪得無厭,野心很大”[17]。經(jīng)濟學(xué)家布坎南也得出了同樣的結(jié)論:“立憲政治的一個重要的原理是要作如下的假定——掌權(quán)者將濫用政治權(quán)力去促進特殊的利益;這不是因為情形常常是如此,而是因為這是事物的自然趨勢,這是自由制度特別要加以防止的。”[16]342
這種邏輯前設(shè)并非是指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壞人,必然要做壞事,而是尋求一種制度上的防范和控制,其目的是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最壞結(jié)果的出現(xiàn)。控制權(quán)力濫用的手段是在民主與法治基礎(chǔ)上建立有效的權(quán)力制衡體系。麥迪遜指出,正是由于人性總是不完善的,所以人類社會才需要政府以及對政府的控制,才需要遏制政府專權(quán)之企圖,而“防止把某些權(quán)力逐漸集中于同一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18]。建立權(quán)力制衡機制的政治體系不僅在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上是穩(wěn)定的,能夠使政治權(quán)力恪守適當(dāng)?shù)慕缦蓿揖哂泻軓姷倪m應(yīng)性,能夠滿足政治發(fā)展過程中劇增的各種利益表達(dá)和政治參與的要求。當(dāng)政治體系面臨多重挑戰(zhàn)時,各個政治機構(gòu)可以相互配合,都在維持政治體系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方面發(fā)揮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只有通過基于法治的制衡機制使政治權(quán)力受到嚴(yán)格制約,遏制任何個人或者集團濫用權(quán)力的企圖,向民主政體過渡的過程才能以和平的漸進的方式進行。
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類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通過激進變革完全消除政治生活中的弊端。政治發(fā)展的合理目標(biāo)不是基于人性本善去追求一個完美的理想國,也不是依據(jù)人性本惡去構(gòu)建一個法家式絕對專制的權(quán)力體系,而是通過持續(xù)的制度創(chuàng)新糾正現(xiàn)有制度體系的缺陷。致力于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后發(fā)展國家政治上的最佳選擇是走漸進式政治發(fā)展道路,通過合理的制度設(shè)計懲惡揚善,更好地約束人性,控制權(quán)力,減少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動蕩和破壞,為國家發(fā)展提供穩(wěn)定安全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