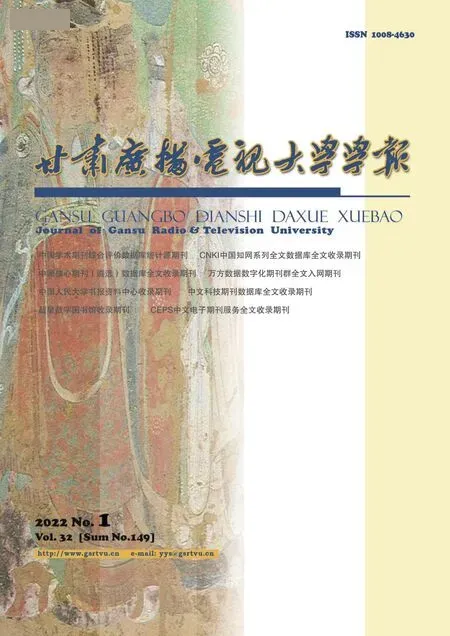知識與權力共生中的知識分子
——齊格蒙特·鮑曼思想中的立法者角色研究
李 娟
(重慶醫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400016)
一、知識與權力共生的歷史基礎
鮑曼認為知識分子的誕生與“啟蒙”有著緊密的聯系,知識分子是為了重申其在啟蒙時期在知識的產生和傳播中處于重要地位而誕生的。鮑曼在《立法者與闡釋者》一書中詳細闡述了權力與知識的共生并不是憑空想象,而是發生在啟蒙時代,兩者的關系隨著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不斷變化。在16、17世紀的法國,這種知識與權力的共生作用表現最為突出,與當時法國的歷史時期有著必然的聯系,法國的知識分子與國家的聯合成為現代社會知識與權力共生的歷史基礎。
哲學家是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鮑曼對啟蒙時代的哲學家進行了深入研究。啟蒙時代的哲學家群體并不是一個思想流派,在許多國家,由于主客觀各個方面的差異,哲學家們相互分離的力量遠遠超過他們相互統一的力量。那么,為什么在法國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們會聯合在一起呢?是什么力量使他們聯合?鮑曼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就回答了知識與權力共生的歷史基礎,揭示了支撐起知識分子觀念的基本形態。這種聯合的力量蘊含于話語活動的意圖和價值中,換言之,不應該到哲學家的話語中或者是某個觀點中去尋找這種使其聯合的堅強有利的因素。正如鮑曼自己所言:“把某種意圖與價值賦予這種話語活動,一方面出身philosoghers(哲學家們),但是從根本上說,是出于他們在政治史上的一段短暫而壯麗得令人難以忘記的遭遇。”[1]32
首先,專制主義的興起。由于土地所有權和政府行政權力之間的聯系逐漸衰落,政治權力重新分配,從而使專制主義得以發展。專制主義國家開始了富有野心的計劃,將秩序和高標準強加在它所統治的民眾身上,他們身上所承擔的極其龐大的聽證事務,反而使得國家所擁有的權力出現了驚人膨脹,專制主義的統治也出現令人震驚的脆弱。對于富有創造性的計劃者來說,這正好為統治、組織和管理社會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啟蒙哲學家為這一角色武裝自己,成為了不將自己拘泥于社會某個特殊機構的利益(如教會或合法的行業)——“獨立的知識分子”,他們來自于生活的不同階層,將自己的身份與整個社會相認同。
其次,舊的貴族階層及其封建價值的衰落。這意味著貴族們很難再通過官職與職位的聯系來占據大量的行政職位,但是貴族們所具有的貴族性,作為一種影響政治的合法形式,并沒有放棄對權力的訴求。當他們的這種血緣世襲不再起作用的時候,他們就需要尋找一種新的方式即政治權威合法化,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啟蒙哲學家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他們通過教育的方式來解決,因為教育是使人卓越和通往美德之路的關鍵環節。貴族們在公眾面前呈現出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角色正是通過教育的方式來實現的。
再次,法國哲學家們自身所具有的特點。鮑曼從當時一位具有獨道眼光的法國革命史的史學家奧古斯坦·科尚關于雅各賓派短暫統治的研究中,找到解釋哲學家之謎的鑰匙。啟蒙哲學家們相互寫信、拜訪、交流思想,建立了緊密網絡,創辦了一個不是由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所控制的,而是由基于經驗所作的觀念控制的“共和文人社團”。“這是一個自治的團體,這一團體引介觀點、寫作、演講和普遍的信仰。”[2]鮑曼認為這些文人是今天知識分子的原型,代表公眾與政治權力談判溝通,最后達成共識,在創造公共輿論方面具有權威性。鮑曼認為這些社會條件雖然不夠全面,但足以用來證明知識與權力的融合是諸多要素共同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遺產。這些條件同時發生在法國,在同時代的其它國家是“獨一無二的,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1]64。
二、知識與權力如何共生
福柯認為:“權力制造知識;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3]鮑曼正是受到福柯權力觀的啟迪,在《立法者與闡釋者》一書中提出了“權力需要真理,絕對權力需要絕對真理”[1]64。可見,知識與權力的運作是緊密關聯相互依存的。鮑曼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在啟蒙時期知識與權力共生關系的形成過程,一方面從國家層面來看,對社會系統的控制需要建立什么樣的秩序模式;另一方面從知識分子的層面來看,在協調社會秩序與管理對象的關系過程中,知識分子如何獲得這種支配話語權。
(一)全景監視的發明
在16世紀,前現代世界遭受到巨大壓力,由于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土地所有權重新分配,農業及耕地效率的提高,造成了大量的人口過剩(鮑曼把他們稱之為“無主者”和“流浪者”正罹受著絕癥)。這些被分離出來的流浪者,被定義為不確定的危險人群,他們四處游蕩,居無定所,成為了引起當地居民焦慮和驚恐的焦點。這充分反映了當時傳統的社會維持機制已經陳腐不堪和社會控制手段的嚴重不足。換句話說,現代國家正是在原有的君主專制政治形態和行政手段難以融合的情況下孕育而生,擔當起維護社會秩序的使命。那么國家如何使“流浪漢”們再重新獲得從屬于某一個主人,或擁有自己的財產,作為可以不受懲罰的行為正常的條件呢?如何把他們重新置于法律的監視下?傳統手段的局限性暴露無疑,共同體的那套單調的秩序系統無法實現對現有秩序的維護。在16、17世紀的英國,法國開始了瘋狂的立法活動,并且發明了新的懲罰和改造技術。一種最簡便易行的方法就是打烙印,這源自于飼養牲畜的實踐過程。用烙上標記把流浪漢和普通人區分開來,以便關注他們的動向。隨著共同體控制機制的逐漸瓦解,社會各界做出了各種回應。鮑曼認為強制性監禁的發明是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強制性監禁的主體是國家,方式是通過設計監獄、勞動場所、貧民院等來對流浪者們的行動、生活等進行監控,從而維護國家統治的社會秩序。換言之,當原有的監控手段無法滿足國家統治的需要,新的監控方式將會取而代之。可見,現代國家的根本任務其實就是通過重組社會權力,重新安排控制的機制,從而維持自己統治的社會秩序。
鮑曼否認把控制和維護秩序理解為一種監視,他認為監視從古至今都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革,其最重要的變革就是建立在控制的不均衡性之基礎上的新機制。但在前現代不均衡權力所涉及的就是對物的占有程度,主要表現在統治者采取高壓的政策對剩余產品的再分配,他們通過展示自己的權力,即暴力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鮑曼把這稱之為一種“散點的監視”,這種監視是建立在人類學家所謂的“沒有分化的相互性”基礎之上的。在這個監視的共同體中成員具有永久性和相互性,正是因為成員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監視的行為得以合法化。
在現代社會中,邊沁的“全景式監獄”被廣泛運用,這種監視方式充分體現了社會的權力技術。鮑曼認為這種“全景式監獄”是為解決監視這個問題而設計的技術。“全景監獄”也是福柯最常用的一個典型事例。“全景監獄”的建筑是一個環形狀態,內環即環形的中間是監視者所在的塔樓,外環則是被監視者的房間,外環每間房間上的窗戶正對著中間的塔樓,這便于監視者了解被監視者的行為。這種監視是監視者對被監視者的一種單向行為,并非雙向行為。也就是說“監管人知道被監禁者的一切,而被監禁者對監管人卻一無所知”[4]。事實上,被監視者因為看不見監視者,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監視者的自我監督,而被監視者實際上也是處在一種無形的監視機制中。
鮑曼認為這種“全景式監獄”使得體制內的權力發生了變化,與“散點監視”不同,有了創新之處。首先,從監視者的層面分析,“全景式監獄”中表現出的連續性的單向監視,不僅使得監視者的行為有了更多的約束和改善,同時為社會控制的完善創造了條件和可能。其次,從被監視者的層面分析,單向監視使得被監視者因受到權力關系的規定,出現了社會同一化的特征。單向監視傾向于消除其對象的個體間差異,傾向于用能夠在數目上進行管理的千篇一律性取代質的多樣性[1]62-63。這種監視方式的重要任務就是通過監視來改變個人多種多樣的現實活動,使被監視的人們形成一種千篇一律的行為方式。
“古代希臘和羅馬”屬于世界古代史的范疇,雖然古希臘和古羅馬早已滅亡,但是作為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希臘的民主制度、人文精神,羅馬的法律制度卻是后世重要的財富。高中必修教材中共有兩個專題涉及這方面內容,教材一共涉及以下問題:古希臘的地理環境及其影響;古希臘的城邦和公民;梭倫、克利斯提尼、伯里克利改革;雅典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影響;羅馬法的發展、特點與作用;人文精神起源。但縱觀近幾年高考題,考查這一方面的知識點可謂是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
全景監視的發明是維護國家統治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在現代民族國家政治統治中,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霸權是統治者用來維護其統治的重要工具,知識分子作為文化霸權的主體,一方面,逐漸凝練出支撐統治者維護社會秩序的“國家意識”,這種“國家意識”是超越本地、階級、種族的共同利益的體現;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在人們行為規范的活動中承擔著教化的作用。
(二)教育家——全景式監獄的監視者
為了維持現代國家中的這種不均衡監控,就必須將專家置于監控者的位置上。不均衡監視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運用強行的手段使得被監禁者的人類行為方式具有普遍性的特征,這種強行的手段包括暴力方式和具有專業實踐知識的人采取的教化方式,兩種手段相輔相成,保證了監視措施的有效實施,進而達到改造全社會人類普遍行為的模式。這種監視者的身份便成為了一種專門性的工作。鮑曼認為與其說他們是施行高壓政治的行家里手,還不如給他們冠以“教育家”的稱號。
制度化的不均衡監視導致了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的出現,“教育家”角色正是在這種現代社會權力的重新分配中形成的,教育者進入權力領地,他們行使教化功能使個人行為中的各種缺陷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不斷完善。這種至善是社會秩序所必需的,因此可以恰如其分地把它稱之為“共同利益”[1]64,也就是說,鮑曼認為人是有缺陷的動物,但教育者取代牧師的角色重新塑造了對這種缺陷的認識,并視之為可以完美和教化的。因而教育者成為了這個權力結構中的重要因素,他們必須運用自己特有的知識來分析“共同利益”,從而制定出最適合這種共同利益的行為模式。因此,教育者為全景監控的合理化和合法化提供了保障。權力和知識的關系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應用而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權力迫切需要知識,知識賦予權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
不均衡監視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種典型的結構,產生于這一社會結構的新型權力具有兩個顯著特征:牧人式權力(pastoral power)、改造思想的權力(proselytizing power)[1]64。這兩種權力是在基督教會的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并不是新創造出來的。牧人式權力的目的是突出個人的自主作用,有決定個人行為的權力,旨在完善每一個個人,而不是為了權力自身的利益,它通過制定一套獎懲體系,使得個人集權力與義務于一身。后者則是為了使個人承認這種權力所創造的生活方式的優越性并加以服從,個人并沒有能力去創造更理想的生活方式,他們只是這種生活方式的認知者和實踐者。鮑曼認為在現代權力結構中,兩種權力的世俗化才是真正新產生的東西,他們開始根據國家需要進行全新的分配,兩種權力方式是在控制人們信仰的基礎上,使國家得到人們的認同,而被統治者們自身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無知,他們只有通過那些知識淵博人的幫助、監督才可以真正幸福地生活。
鮑曼在對知識與權力共生的分析中,對啟蒙運動有了一種新的理解,認為啟蒙運動是一場實踐,分為密不可分卻各具特色的部分。“第一,國家權力逐漸擴大,其核心是行使規劃安排、管理與維持社會秩序相關的職能。第二,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有意設計的訓導人們行為的社會機制,目的在于規范和調整作為這個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國家和臣民的社會生活。”[1]64換言之,正是國家希望通過約束來訓導人們的行為建立社會秩序的意愿,使得啟蒙思想家在維護國家秩序時通過設計監獄、貧民院、勞動場所等機構來進行社會改革。因此,“權力需要知識,知識賦予權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擁有權力就是擁有知識”[1]64。因此,知識與權力的共生成為現代性最顯著的特征。
三、立法者身份的確立
在現代民族國家中,政治統治的鞏固離不開文化的支撐,知識分子作為文化的主體,其地位也逐漸地突顯出來,他們既扮演著啟蒙教化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國家權力的有效性和合法化。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在知識與權力共生之后,其職責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由對現實的批判上升為為統治階級服務。
(一)“立法者”的功能
1.民眾意識形態的教化者
2.國家控制策略的設計者
知識分子作為國家控制策略的設計者,為維護國家統治和國家權力設計有效的控制策略。這對知識分子自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需要具備一定的理論知識,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相關技能。知識分子集知識與技能于一體,保證了國家制度規范的有效發揮。國家的政治家們正是在知識分子所設計的監控藍圖的引導下建構社會秩序和控制策略,知識和權力正是在秩序設計和執行的流程中順利融合。
現代國家為了維護國家秩序追求的是一種統一的全社會模式,是以共同體為基礎的生活方式,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消除地方的差異性。知識分子立法者地位的鞏固,就是在統一的全社會模式中逐漸形成。一方面,國家為了維護統治把知識分子中的精英納入國家制度建設中來;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們發揮其基礎功能,把對大眾的教化改造運動發揮到最大程度。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實踐活動與特定的歷史時期有緊密的聯系。立法者們對于世界和社會生活領域的理解形成了自身所獨有的世界觀,鮑曼把它稱之為“典型的現代型世界觀”。這種世界觀認為,世界本質上是有序的,而不是無序的總體,人只有掌握了充足的正確的知識,就能擁有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因此,人必須掌握正確的知識才能保證實踐活動的有效性。無法被客觀檢驗的實踐活動(如只有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才具有合法性的實踐),是比較低劣的。因為它們曲解了知識界,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這種實踐等級(這種等級是由“控制/知識”的共生系統來進行評判的)的提高,意味著使實踐逐漸遠離“狹隘性”“地方性”和“特殊性”而大步地邁向了普遍性。
(二)“立法者”的特點
在鮑曼看來,“立法者”的角色是對當時國家中知識分子的最佳描述。作為“立法者”的知識分子的特點和國家權力與知識共生有著緊密的聯系,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作用。這些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立法者”角色具有合法性。這種合法性主要表現在擁有從事仲裁的合法權威,是由他們在國家統治中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一方面他們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獲得知識的機會和權力。另一方面,他們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知識引導這種角色的定位存在于權威性話語構建活動中。被賦予合法權威的“立法者”角色的知識分子具有仲裁和抉擇的權力,他們告知民眾哪些意見是正確是應該被遵守的,哪些意見是錯誤是應該被摒棄的。換言之,他們具有從事仲裁的合法權威與他們所擁有的至上的知識是分不開的,這種權威就是對意見的差異性進行仲裁,同時對人們在進行知識的選擇時起到引導作用。
2.“立法者”角色與程序性規則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立法者”角色的知識分子是程序性規則的解釋者,也是程序性規則得以正確運用的保障者。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是凌駕于一種職業之上的職業,被賦予了對社會各界所持信念之有效性進行判斷的權利和責任,這種職業成為了“知識分子”所獨有的特權。程序性規則對“立法者”角色作用的發揮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程序性規則的普遍有效性,使得國家在運用這些規則所導致的結果也具有了普遍有效性,這是一對因果關系。知識分子正是在對錯是非的決定中發揮其“立法者”角色的作用。
3.“立法者”角色對國家秩序的維護起著決定的作用。知識分子是一個知識的集體所有者,通過運用這種程序性規則而組成。鮑曼認為并不是所有擁有知識的人都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只有有利于維護國家統治的那一部分人才是“立法者”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知識的集體所有者群體是由科學家、道德哲學家和美學家組成,他們對國家的統治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4.“立法者”角色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特征。“立法者”角色知識分子及其所擁有的知識不受地方性共同體傳統的約束,因而對地方性知識的判斷具有客觀性。
總之,鮑曼對知識分子“立法者”角色的研究具有歷史時代性,擁有至上知識的“立法者”滿足當時國家發展的需要,知識分子與國家的融合是知識與權力共生的歷史基礎。國家賦予了“立法者”角色的合法性,“立法者”角色的確立對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隨著國家社會的發展,“立法者”角色的危機凸顯出來,其角色地位也將實現轉化,被一種新的角色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