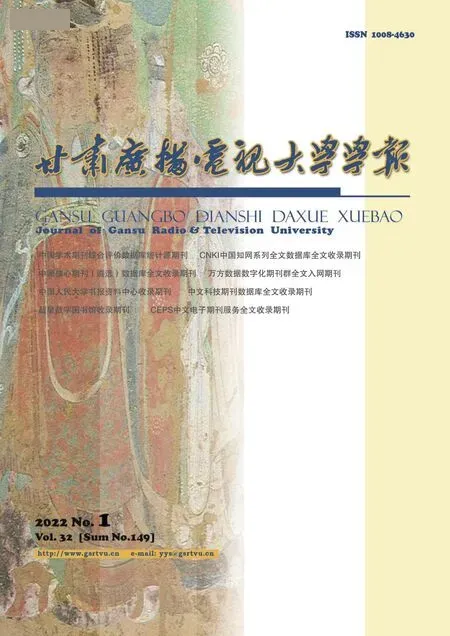拜倫創作與“浪漫主義的根源”
倪正芳
(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文學院,湖南 婁底 417000)
詩人拜倫的創作實踐所體現出的高高飛翔的想象、澎湃洶涌的激情以及無與倫比的創造性才能,還有他的文學作品與社會活動在那個革命熱情空前高漲時代所發揮的鼓舞作用和戰斗意義,都印證了他不愧為浪漫主義文學代表性人物。在借用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書名(《浪漫主義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作標題的本文里,我們希望著重探討的則是,拜倫浪漫主義創作傾向受到過那些因素的影響,他那鮮明的浪漫主義創作風格是如何形成的。
一
我們首先必須看到,英國本土文化傳統特別是早期浪漫主義文學傳統對拜倫的影響是直接的,這可以從蘇格蘭“農民詩人”彭斯說起。彭斯是英國浪漫主義的前驅,他收集、整理了約三百首蘇格蘭民歌并通過加工賦予其新生命,正是這種對民歌傳統的復興后來成為英國浪漫主義的特征之一。除了歌唱自由和愛情的民歌型抒情詩,彭斯還擅長諷刺詩、敘事詩等。彭斯的詩,“不是廟堂、學院和客廳的產物,而是法國大革命風云激蕩的歷史時刻由幾種從不同方面要求解放人性的思想趨勢形成的”,他“使得這個新的詩歌運動不至于過分理智化、抽象化,不至于輕飄飄,而是有堅實性、強韌性,同時又有樸素、生動而持久的美”[1]220。他的詩學主張是:“我只求大自然給我一星火種,我所求的學問便全在此中!縱使我駕著大車和木犁,渾身是汗水和泥土,縱使我的詩神穿得樸素,她可打進心靈深處!”[1]219他的這種對民間風味與本土屬性的主張及其創作實踐,猶如一股清風,攪動了陷入沉悶、刻板的偽古典主義盤踞的文壇,特別是給英國詩歌創作注入了生機和活力。
作為曾在蘇格蘭山地度過一段童年時光的拜倫,對這個蘇格蘭平民出身的浪漫主義文學開路人充滿了理解與敬仰,對他的詩歌風格也是認同的。葉利斯特拉托娃說:“(拜倫)這位未來的詩人從童年起就非常熱愛蘇格蘭的大自然,他常常把蘇格蘭當作自己的故鄉。多山的蘇格蘭一向為彭斯所歌頌,在那里,農民當時的生活還保留著資產階級形成前的宗法氏族關系的一些習俗,因此,在拜倫的記憶中它永遠是自由的象征。”[2]13早在1806年,拜倫在編自己的詩集《即興詩集》及后來正式出版的《閑散的時光》時,就按照彭斯的風格寫了若干首詩,如《勒欽伊蓋》《我愿做無憂無慮的小孩》《我曾是一個年輕的高地流浪者》等。18世紀的一些詩人們喜用古典主義的抽象詞藻,以華麗、浮夸、冷漠的哀詩和書信表達所謂“崇高”的熱情;而世俗愛情的喜悅則多半成為“滑稽的”、輕浮的、自然主義的粗野詩歌的主題。是彭斯首次成功地克服了這種分離,并在詩歌中恢復了民間創作所固有的靈與肉的統一性,因而他才能寫出像《我的愛人像朵紅紅的玫瑰》這樣清新溫柔而極富地域特色的愛情詩。拜倫對彭斯的熱愛,還表現在以他為榜樣,使抒情詩的情感得到自然的表達,比如《她走在美的光彩中》就是一篇這樣的范例。此外,彭斯富于社會熱情,在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社會思想感召下,再加上固有的蘇格蘭民族主義情緒,使得詩人創作了不少帶有“顛覆”性和叛逆性的政治詩及諷刺詩。如《不管那一套》:“國王可以封官,公侯伯子男一大套。光明正大的人不受他管——他也別想夢想弄圈套!管他們這一套那一套,什么貴人的威儀那一套,實實在在的真理,頂天立地的品格,才比什么爵位都高!……”[1]212而我們已經知道拜倫的《路德分子之歌》等也是表現下層民眾反叛情緒的力作。
成名比拜倫早的司各特,在很長時期里都是英國文壇的領袖之一,他還是拜倫尊敬的朋友。從司各特作品寶貴的民間風格因素中,拜倫受到了很大啟發。他從不諱言自己對這種風格的借鑒,如他在《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第一、二章序言中申明:“第一章開頭部分的那首《晚安歌》則是受了司各特所編的《邊區歌謠集》中的《麥克斯威勛爵的晚安歌》的啟發而寫成的。”[3]拜倫在《貝波》中對那些“比下流更差”的在貴族沙龍里無病呻吟的作家們表示厭惡時,也表達了自己對司各特等人的好感:“此外也還有通達世情的詩人,例如司各特,羅杰斯,摩爾,以及較好的作家,除了耍筆桿,也還能想到其他;……”[4]339(《貝波》第76節)司各特給拜倫摸索中的早期創作以方向性影響,及至拜倫成名后,司各特又以寬廣的胸襟甘愿為之騰出浪漫主義抒情詩人的王座,并對其后期創作給予一如既往地支持和鼓勵。如在《唐璜》第一、二章剛出版就受到各方攻擊時,司各特卻這樣說:“(《唐璜》)像莎士比亞一樣地包羅萬象,它囊括了人生的每個題目,撥動了神圣的琴上的每一根弦,彈出最細小以至最強烈最震動心靈的調子。”[4]8
曾被稱作消極浪漫主義代表的“湖畔派”與拜倫雖然在政治觀點上有很大分歧,但同為浪漫主義的詩人,他們在創作主張進而在實際文學風格上有不少相通之處。如作為浪漫主義基本特征的想象、天才和情感便都是他們共同強調并竭力追求的。實際上,作為“后生”的拜倫在與湖畔派交往的過程中,并未對湖畔派尤其是對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的藝術成就視而不見,相反,他贊賞他們的才華,甚至在自己的創作中借鑒過其中的長處。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就承認華茲華斯“偶爾”也對拜倫發生過影響。莫洛亞《拜倫傳》也記載,1816年在日內瓦的時候,雪萊曾讓拜倫欣賞“一小段一小段華茲華斯的詩”[5]239。華茲華斯被剛出道時的拜倫在《英格蘭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中責罵過,而且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拜倫一直拒絕讀這位詩人的詩。可是在1816年日內瓦湖畔這樣難得的寧靜而優美的環境中,在知心的朋友身邊,他對華茲華斯的詩漸漸產生一定的興趣。在飽嘗了世道辛酸之后,在這幽靜的湖光山色中,接觸到華茲華斯的高雅溫柔的作品,他也許一度體會到了內心的平和,而這種情感變化又可能在作者當時的創作中反映出來。所以我們看到在《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第三章中,那位孤獨傲世的旅行者的情緒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澄澈、透明、鏡面似的萊蒙湖!你同我曾居住的茫茫人世相異迥然,你似乎在靜靜地告誡我,向我叮囑:應拋棄塵世的煩惱水,尋求潔白的泉。好像無聲的翅翼;我曾經愛過,曾經愛過那翻騰吼嘯著的波瀾,但湖水的溫柔耳語像姐姐在責怪我:究竟是為了什么要那樣喜愛危險的風波。(《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第三章第85節)
對另一位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拜倫也并非總是抱著厭棄態度。他不僅在社交場合與柯勒律治保持著交往,還與其有過書信往來。1815年3月31日,在一封致柯勒律治的信中,拜倫表達了對后者的敬意及自己過去在作品中可能對他造成的粗暴傷害的悔意:“很多年來我們還沒有寫出能與您的《悔恨》相提并論的作品,我應該認為那部戲的接受程度是足夠能鼓舞起作者與觀眾的最高的希望的。我們堅信您所從事的一項大業必定會獲得成功,……您提到我的‘諷刺的’諷刺詩文,或無論您或其他人高興稱它什么。我只能說它寫于我十分年輕氣盛的時候,……涉及您的那部分太冒失、太粗魯、也太膚淺了。”拜倫甚至有時還贊揚柯勒律治的作品,針對別人的批評還主動替他作辯護:“我聽說《愛丁堡評論》對柯勒律治的《克利斯塔貝爾》進行了抨擊,并攻擊我對它的贊揚(‘狂熱的和有獨創性的美妙的詩’)。我贊揚它首先是因為我認為它好;……我為杰弗里對他的攻擊深感遺憾,因為,可憐的伙伴,那會使他的心靈受到創傷,經濟上受到損失。至于我,我是歡迎他的——我決不會因為將來他會說什么反對我的著作的話而對他有更低的評價。”[6]出發點可能復雜了一些,但還是能看出拜倫對柯勒律治詩歌某些方面的認同。拜倫還很欣賞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并親自勸其發表它。
其實,即使是拜倫的老對頭騷塞,也并非對拜倫的詩學思想沒有任何影響。比如騷塞的東方題材的作品比拜倫寫得早,(騷塞的《薩拉巴》出版于1801年,《克哈馬的詛咒》出版于1810年)盡管拜倫看來那不過是一種“疑似”東方題材的作品,但它們畢竟和穆爾等人的作品一道引發了民間的閱讀興趣。之后拜倫才以自己的優勢和特點通過《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和“東方故事詩”等作品遠遠地超越了他。拜倫對吸血鬼題材很有興趣,而這也與騷塞較早涉及并影響了拜倫有關。“東方故事詩”之《異教徒》中有這樣的詩句:“當吸血鬼被遣送到人世間來,他首先會把你的尸體從墳墓里朝外硬拽……”接著詩人在這里特地作了個注,介紹他對騷塞引用同一故事的關注:“騷塞先生在他的《薩拉巴》的注釋中引用了這個故事。”[7]43類似的情形還有拜倫戲仿騷塞《審判的幻景》寫出了他精彩的同名諷刺詩,以致勃蘭兌斯這樣調侃:“我們感謝騷塞寫的《審判的幻景》引出了拜倫的那篇同名作品——而且為了他的這項‘功勞’,我們愿意寬容他的《克哈馬的詛咒》和《薩拉巴》這兩部作品。”[8]115無疑,這也表明,騷塞與拜倫之間多少存在一個題材啟發、靈感觸動的事實。
二
當時歐洲的社會變革及文學傳統也對拜倫浪漫主義傾向產生了非常明顯而積極的影響。
就英國浪漫主義發生發展的社會背景與時代契機而言,英國的浪漫主義是在受到法國革命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點我們在談論歐洲浪漫主義對拜倫的影響時不能不首先指出。羅鋼說:“英國浪漫主義運動緊接著法國大革命爆發,絕對不是時間上的偶合,沒有法國革命中對人的尊嚴權力和精神價值的充分肯定,沒有法國革命觸發的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沒有法國革命帶來的人的主觀精神的蹈厲發揚,就不可能有縱情抒發個人懷抱,自由地馳騁想象,徹底打破新古典主義清規戒律的浪漫主義文藝的誕生。”連一向被稱為“消極浪漫主義”領袖的華茲華斯尚且聲稱法國革命是“高貴的雙親——自由和慈善的愛的孩子”[9],那些被稱為“法國革命的產兒”的所謂“積極浪漫主義”詩人如拜倫、雪萊們,其身上法國革命的思想烙印就更加深刻了。
歐洲大陸啟蒙主義時期的文學對包括拜倫創作在內的浪漫主義文學也產生了顯著影響。這種影響首先應該是思想觀念上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一些作家創作中的情感傾向、題材內容、具體技法等與后來浪漫主義氣質相同或相近的要素的積極作用。當時法國、德國等一批作家們就以自己敏銳的感受和超越時代的眼光,奮筆疾書,大聲吶喊,他們的思想遺產與創作成果從許多方面都起到了催生不久之后將橫掃歐洲的浪漫主義滾滾洪流的作用。
盧梭,這位“返回自然”的倡導者、人性解放的先驅和敏感的思想家,曾給拜倫、雪萊等人以豐富的思想資源、熱烈的情感鼓舞、強大的精神支撐和創作動力。他的《新愛洛綺絲》等作品體現了新的時代資產階級乃至整個第三等級爭取個性解放的民主主義思潮,表明一批文藝家們開始格外迫切地要求從封建的“理性”精神束縛下徹底解放出來,獲得心靈的自由舒張,而且他們已把這種訴求通過對人類情感、本能的描寫傳達出來。拜倫不僅在作品中經常引用盧梭作品,還不止一次地直接表達對這位精神導師的敬意。在瑞士日內瓦一帶游歷時,這個盧梭的誕生地和伏爾泰的避難地引起了拜倫對法國啟蒙主義者的回憶。觸景生情,拜倫在《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第三章描繪了他們的形象。在第77節他專門寫到盧梭,這仿佛也是拜倫自己的寫照:
狂放的盧梭,那作繭自縛的哲人,就從這地方開始他那不幸的生涯;他用魔力美化了那種痛苦的熱情,從悲苦中涌迸出無敵的辯才,……他所用的語言就好像眩眼的日光,人的眼睛立刻流下同情的淚,一讀他的文章。
拜倫還將其中的第81—82節獻給盧梭和他的同志們,宣稱盧梭的預言“讓全世界燃起了熊熊的火焰,直到所有的王國全都化為灰燼”。1816年6月27日,拜倫在致默里的信中說:“我已詳細考察了盧梭的地方,《新愛洛綺絲》就在我的眼前,在某種程度上,我驚異于他描繪的準確與其現實中的美麗所產生的那種力量。”在晚期的一部悲劇性長詩《島》中,拜倫所描寫的太平洋小島上那種烏托邦式的社會生活,映射出人類的黃金童年時代,也正是以前盧梭所憧憬的。
歌德是拜倫心目中整整一個時代的文壇上的君王。在去希臘參戰途中收到歌德的《論拜倫》、一些給拜倫的短詩及其感謝拜倫將悲劇《沃納》題獻給他的一封信后,拜倫于1823年7月24日回信,表示對歌德的由衷敬意與崇拜,稱歌德“50年來一直是歐洲文學無可爭議的君王”,還虛心地說“能得到歌德先生親筆寫的一個字,都是我無可比擬的好兆頭與驚喜。”其興奮激動之情,溢于言表。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作品,拜倫不僅閱讀,還在作品中引用。維特的煩惱,是一種渴望沖破舊世界舊觀念的牢籠、釋放青春的激情而暫時不可得的煩惱。他對周圍環境的窒息感,對庸俗的社會秩序的絕望感,何嘗不是拜倫同樣遭遇著的呢?所不同的是,維特的時代,革命的精神還未成氣候,他看不到個性解放的前途,所以只能絕望地自殺,而拜倫生活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后、拿破侖在歷史的舞臺縱橫捭闔之際,人類歷史正因此上演著一幕幕驚天動地的大活劇。人們獲得了有力的精神鼓舞、廣闊的情感空間和相當程度的表達自由。加上拜倫身為貴族,擁有一般人所無法比擬的行動特權,他可以更加大膽地、并相對安全地抒發自己的理想,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批判,開展自己對未來的追求(盡管如此,拜倫在社會上還是碰了不少壁,受了不少傷)。《浮士德》中的浪漫因素給予拜倫的影響也是明顯的。莫洛亞《拜倫傳》這樣介紹拜倫與《浮士德》的相遇:
(1816年)8月里,《修道士》的作者馬修·路易斯來到狄沃達蒂拜訪他。馬修·路易斯為他翻譯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些片段。它的主題打動了他的心!浮士德提出的關于宇宙的這些古老的問題,與魔鬼訂的契約,失去瑪格麗特——這些難道不是他自己的問題嗎?但是,假如拜倫自己創作了浮士德,他會將他描繪得更大膽,更悲慘。為什么在幽靈面前發抖呢?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蔑視幽靈,蔑視死神。
這樣,“《浮士德》的閱讀和阿爾卑斯山脈的風景震動了他,于是從中產生了一部偉大的詩劇《曼弗雷德》”[5]249。確實,當我們看到作品第二場,魔女提出幫助曼弗雷德的條件是要求后者發誓服從其意志方可實現自己的愿望,我們會馬上聯想到魔鬼靡菲斯特與浮士德的賭約。所不同的是,曼弗雷德拒絕了魔女的要求,因為他還有強大的魔術去求助于阿里曼(伊朗神話中的罪惡與黑暗之神)。甚至歌德本人也從拜倫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作品的影子,并為他構思作品時對《浮士德》的借鑒表示理解和支持。他說:“拜倫筆下的變了形的魔鬼(指拜倫的《變形的畸形人》中的主角——筆者注)也是我寫的靡非斯特的續編,運用得也很正確。如果他獨出心裁想要偏離藍本,就一定弄得很糟。所以,我的靡非斯特也唱了莎士比亞的一首歌。他為什么不應該唱?如果莎士比亞的歌很切題,說了應該說的話,我為什么要費力來另做一首呢?我的《浮士德》的引子也有些像《舊約》中的《約伯記》的引子,這也是很恰當的,因此我不該受到譴責,而應該受到贊揚。”“拜倫只有在寫作的時候才是偉大的,一旦他進行思考時,卻是—個孩子。所以當他的同胞對他進行類似的無理攻擊時,他就顯得束手無策。他本來應該向他的論敵們表現得更強硬些,應該說,‘我的作品中的東西都是我自己的,至于我的作品是來自生活還是來自書本,這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于我是否運用得恰當!’”[10]
三
在歐洲浪漫主義文學中,異域背景是一個極具特色的創作興奮點,而“東方”更是幾乎成為“異域”的同義詞。對拜倫而言,“東方”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那片神奇土地上的文學遺產也給了他創作上的諸多教益和啟發,尤其是對形成其個性化的浪漫主義風格發揮了作用。
薩義德說:“‘東方的’(Oriental)一詞由來已久;它曾出現在喬叟……和拜倫等人的筆下。從地域、道德和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指的都是亞洲或廣義的東方(the East)。”[11]作為與拜倫生活經歷和創作密切相關的“東方”概念,從地理意義上說,它當然是指歐洲大陸以東的廣大亞細亞地區,包括拜倫詩歌中東方元素的重要體現地、跨越歐亞兩大洲、曾影響廣大歐洲地區的伊斯蘭國家土耳其。如果從歷史文化淵源講,北非的埃及等地也應被納入“東方”的范疇。我們要探討的對拜倫浪漫主義創作風格發生了影響的東方及其文學主要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
拜倫6歲就由母親聘請了家庭教師指導閱讀。“《舊約》,史書,各種旅行記給了他無窮的愉悅,并激發起他對東方的興趣。”[12]18拜倫在中學和大學時更是廣泛接觸了東方歷史、宗教、文學與文化。求學時期的拜倫曾開列過一份所讀書籍的清單,其中有關東方文學與文化的作家和作品有:
阿拉伯:穆罕默德,其《可蘭經》包含了最莊嚴的詩性段落,遠勝于歐洲的詩歌。
波斯:菲爾多西,創作了波斯的《伊里亞特》——《王書》。薩迪。哈菲茲,不朽的哈菲茲,是東方的阿拉克瑞翁……
緬甸帝國:這個國家的人民狂熱地喜愛詩歌,不過他們的詩人還不夠著名。
中國:除了乾隆皇帝和他的《茶頌》,我還沒有了解其他任何詩人。……
非洲:非洲有些地方的歌曲,音調悲涼,歌詞樸素而動人……[12]25
看得出,在杰出的具有世界意義的東方詩人當中,拜倫推崇菲爾多西(941—1020)、薩迪(約1203—1292)和哈菲茲(1300—1389)。令人吃驚的是,他居然關注到緬甸詩歌和中國歷史上的詩歌“冠軍”(指產量意義上)乾隆皇帝的作品。此外,“他感到惋惜的是,由于對梵文了解不深,以致不能使歐洲人對印度古代的詩歌創作有所領略”[2]17。這是青年拜倫對“世界文學”視野內的東方文學的感想。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這些詩人的創作(乾隆皇帝作為一個特殊“詩人”可以不列入討論),也并非完全是浪漫主義風格,也有反映現實、同情民眾、批判暴政、揭露丑惡等現實主義內容,但拜倫所主要關注的無疑既不是浪漫的抒情,也不是嚴肅的批判,而是因為“他們”和“它們”來自遙遠陌生的東方,詩人借助于這些東方要素進行創作可以產生新奇感、神秘性和吸引力。在實際創作中,拜倫在題材、背景及情調、構思等方面浪漫特色的形成均得益于東方文學很多,東方元素的實際作用也基本在于此。
雖然英國早就擁有東方大片的殖民地,但對這個島國的多數民眾來說,那片遙遠而遼闊的土地一直是神秘而令人向往的。19世紀初期,“東方”在英國尤其是在社會上層的閱讀圈里曾成為一個時髦的概念。在文學創作界,作家們也以表現東方題材為時尚。其實“喜歡描繪東方題材是各國浪漫主義作家的一個共同點”[8]110。由于求學時期對東方及東方文學的接觸,還由于1809—1811年的“東方”(此處還包括了東南歐一些山地國家)之行,拜倫在這個潮流中后來居上,占領了制高點。可以說正是以神秘、新奇甚至怪異等浪漫情調為特征的“東方”書寫對鑄就拜倫最輝煌的詩名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813—1815年,拜倫創作出了轟動一時的所謂“東方故事詩”。當然,他的東方故事的背景實際上還是伊斯蘭教文化與希臘、阿爾巴尼亞等東南歐地理環境結合的產物,以致他自己給《異教徒》和《阿比多斯的新娘》加的副標題就是《土耳其的故事》,而他的同時代人,在“東方”行走期間與拜倫結識的英國文學家約翰·高爾特則把這兩篇及《海盜》叫做《希臘的故事》。然而,盡管“東方故事詩”很大程度上是詩人對東方的一種想象,但畢竟詩人還是到過像土耳其這樣的伊斯蘭國家,而且當時歐洲有的國家還處在伊斯蘭世界的統治下,有的國家還殘留有伊斯蘭勢力統治過的痕跡,更何況還有詩人天才的想象和對真正東方文學的間接經驗呢。因而,詩人的“東方”固然有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但對英國多數讀者而言,東方味兒(或不如說是非英國文化味兒、異國情調味兒)已足夠濃了。比如在《異教徒》里他用一些有東方特色的典故、比喻及習俗描寫來增添作品的“東方”氣息:蕾拉的雙眸“烏黑迷人”,“像杰姆希德的寶石那樣明亮耀眼”——這里就用了一個中古波斯的傳說。相傳中古波斯杰姆希德蘇丹有顆著名的紅寶石,光芒四射,人們還叫它“夜之炬”“日之杯”。詩人還把玫瑰稱作“夜鶯的公主”,理由是他知道,“夜鶯對玫瑰的戀情在波斯語言中是人所熟知的”[7]9。在這篇作品中,拜倫還充分顯示了他對阿拉伯世界或伊斯蘭教經典的了解。安拉、宗師之類形象,石榴花的隱喻,《古蘭經》的教義,土耳其人的喪葬習俗,阿拉伯世界傳說中的魔鬼,等等,似乎足以予取予求了。詩人為了西方讀者的閱讀方便,還不厭其煩地(大概也在炫耀自己作品東方題材的正宗與地道吧)作了許多關于東方的注釋。
其他作品中,他也努力地營造著一種盡可能濃厚的“東方”語境。《恰爾德·哈洛爾德游記》中的“一個人的頷下有了灰白的長須,并不妨礙他心中有青年似的熱忱;愛能戰勝老,哈菲茲說得有根據,……”(第二章第63節)詩句表明拜倫對波斯詩人哈菲茲的熱愛不是一時的沖動。從《曼弗雷德》第二幕第四場以伊朗(波斯)神話中罪惡與黑暗之神阿里曼為中心的構思我們可知拜倫對波斯神話的借重。拜倫在中學就熟讀《天方夜譚》,“《天方夜譚》對拜倫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重大的”,它“不僅喚醒了兒時拜倫的想象而且拓寬了他想象的空間,并促使他閱讀和了解更多的東方”[12]20-21。后來,《天方夜譚》之類的東方元素也成為他作品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如“阿拉伯故事所傳說或夢想的/財寶”(《海盜》第三章第5節),“現洋本來是阿拉丁的燈燭”(《唐璜》第十二章第12節)等詩句,表明作者對這類阿拉伯民間故事熟悉到了隨手拈來的程度。如此等等異域的情調和文化特征,既是拜倫作品浪漫主義風格的體現,也表明了這種風格所具有的相當的東方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