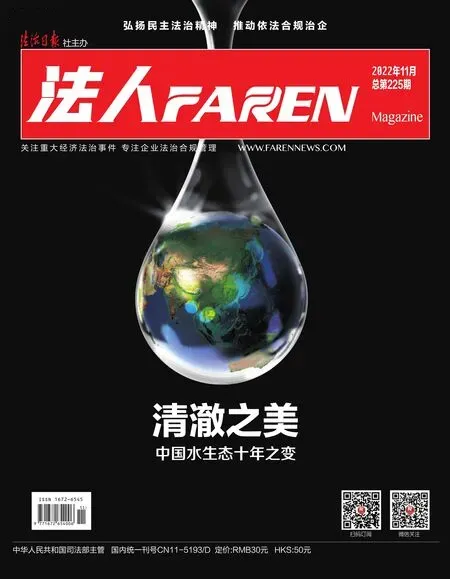分級管理“精準制導”涉稅風險
《法人》特約撰稿 董剛
近年來,行業(yè)業(yè)務(wù)轉(zhuǎn)型與平臺經(jīng)濟增長使經(jīng)營活動呈現(xiàn)“領(lǐng)域化”交叉與融合的特點。一方面,傳統(tǒng)領(lǐng)域受到商業(yè)模式發(fā)展、監(jiān)管方式調(diào)整與外部形勢變化的影響,陸續(xù)謀求產(chǎn)業(yè)升級和嘗試“跨圈”經(jīng)營,使傳統(tǒng)經(jīng)濟領(lǐng)域煥發(fā)新活力;另一方面,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促進了以共享經(jīng)濟、平臺經(jīng)濟、靈活用工經(jīng)濟等為代表的新興領(lǐng)域發(fā)展,業(yè)務(wù)整合與供需適配加速為經(jīng)濟活動注入新生機。
中國在稅收法律領(lǐng)域?qū)η笆鼋?jīng)濟發(fā)展的回應(yīng)主要體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經(jīng)濟活動領(lǐng)域化給服務(wù)于傳統(tǒng)民商事交易的稅收法律制度及其治理帶來了挑戰(zhàn),出現(xiàn)部分經(jīng)濟活動無法與現(xiàn)行稅法評價良好匹配的現(xiàn)實問題;二是隨著稅務(wù)征管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不斷深化,稅收工作得以更加深入地通向社會方方面面。新舊稅收違法現(xiàn)象疊加顯現(xiàn),稅收風險指數(shù)躍升,對企業(yè)涉稅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上述兩方面的碰撞、交匯促成了稅收政策口徑、征管技術(shù)手段及治稅監(jiān)管理念不斷革新和日益科學化、精細化。
本文從行業(yè)與平臺為代表的領(lǐng)域經(jīng)濟發(fā)展及其稅收實務(wù)問題入手,結(jié)合稅收大數(shù)據(jù)支持的中國稅收監(jiān)管模式特征,對新形勢下的企業(yè)納稅風險管理和應(yīng)對提出建議。
逃避稅問題多發(fā)
就傳統(tǒng)行業(yè)而言,首要的問題是經(jīng)濟形勢變化對傳統(tǒng)行業(yè)的沖擊導致逃避稅問題多發(fā)。在全球經(jīng)濟下行和政策調(diào)整的雙重影響下,建筑業(yè)、房地產(chǎn)業(yè)、批發(fā)零售業(yè)和教育業(yè)等行業(yè)利潤率整體下滑,企業(yè)資金流相較過去更為緊張,催生了部分企業(yè)規(guī)避稅收的心理。為規(guī)避繳納稅款,有企業(yè)通過提前或延遲確認收入等方式,實現(xiàn)少繳企業(yè)所得稅的目的;還有一些企業(yè)采取更為激進的逃稅手段,通過虛構(gòu)交易等方式,從其他行業(yè)取得增值稅發(fā)票虛列進項成本或費用。
其次,傳統(tǒng)經(jīng)營方式向電子平臺化經(jīng)營模式的轉(zhuǎn)變,使企業(yè)可以輕易地跨域從事交易和運營,更容易規(guī)避稅收監(jiān)管。比如,批發(fā)和零售業(yè)、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yè)等行業(yè)本就具有現(xiàn)金結(jié)算、與自然人交易和“兩頭在外”等經(jīng)營特點,在電子化經(jīng)營轉(zhuǎn)型趨勢下,一些企業(yè)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虛開發(fā)票等違法現(xiàn)象日益猖獗。
最后,由于監(jiān)管部門對特定行業(yè)的監(jiān)管方式進行了調(diào)整,部分企業(yè)為維持原有銷售模式,通過特殊途徑套取發(fā)票,進一步加大了涉稅風險。例如,在“營改增”和“兩票制”的雙重改革下,以往在藥品銷售中端發(fā)生的銷售傭金和回扣等,前移至醫(yī)藥制造環(huán)節(jié)。醫(yī)藥制造企業(yè)將傳統(tǒng)的藥品分銷商轉(zhuǎn)變?yōu)楹贤N售組織,通過接收推廣、營銷和咨詢等服務(wù)取得各種名目的服務(wù)費發(fā)票。除了有可能被稅務(wù)部門認定為虛開增值稅發(fā)票以外,有關(guān)費用在稅前列支的情況下,還有可能被認為構(gòu)成偷稅。
就新興行業(yè)而言,以平臺為基礎(chǔ)的業(yè)務(wù)體系構(gòu)建具有業(yè)務(wù)融合性強、支付渠道眾多和信息追溯困難等特點,實踐中隱瞞收入、轉(zhuǎn)移利潤、虛開增值稅發(fā)票、地方財政罰沒款返還、利用“稅收洼地”從事逃避稅行為等違法事項不斷涌現(xiàn),呈現(xiàn)出一種新型商業(yè)模式的“野蠻生長”。比如,不少平臺設(shè)立在可以享受地方財政返還的地區(qū),但其勞務(wù)人員和服務(wù)接收方均在其設(shè)立地外。由于平臺用工和業(yè)務(wù)活動數(shù)量龐雜,其真實性往往難以核實,企業(yè)所得稅虛列成本和虛開發(fā)票的風險較大。
在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方面,主播的收入來源和形式包括來自各平臺的底薪、打賞分成、銷售提成、廣告收入、坑位費和電商銷售業(yè)績分成等。由于主播的稅收待遇由其收入性質(zhì)決定,因此主播往往以工作室名義和平臺進行合作,將工資薪金或勞務(wù)報酬等所得轉(zhuǎn)換為經(jīng)營所得。更有甚者,通過虛構(gòu)業(yè)務(wù)、隱匿收入等方式,虛假申報偷逃稅款,或采取違法稅收核定等其他性質(zhì)更惡劣的偷逃稅手段。
在網(wǎng)絡(luò)物流平臺方面,有些物流公司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整合和調(diào)配物流資源,與托運人訂立運輸合約,并將其委托給個體或自然人性質(zhì)的承運人。由于許多平臺無法跟蹤物流全過程,且基于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影響,使得稅務(wù)部門很難辨別出貨運業(yè)務(wù)的真?zhèn)危瑥亩鵀橐恍┢脚_虛構(gòu)業(yè)務(wù)和虛開發(fā)票等違法行為創(chuàng)造條件。
監(jiān)管思路轉(zhuǎn)型和優(yōu)化
近年來,我國持續(xù)推進稅收改革,一方面,依法拓展稅務(wù)部門職責,強化稅務(wù)部門職能,優(yōu)化稅務(wù)執(zhí)法方式,推行有柔性、有溫度的執(zhí)法;另一方面,不斷深化稅務(wù)信息化建設(shè),通過“金稅三期”基本實現(xiàn)對企業(yè)端的稅收管理系統(tǒng)工程建設(shè),并于近期開展以“金稅四期”建設(shè)為主要內(nèi)容的智慧稅務(wù)建設(shè)。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關(guān)于進一步深化稅收征管改革的意見》,提出全面推進稅收征管數(shù)字化升級和智能化改造,精確實施稅務(wù)監(jiān)管工作。以下為分級和分類管理的基本特點:
一是對輕微違法行為實行“首違不罰”。近年來,我國在稅務(wù)執(zhí)法領(lǐng)域研究推廣“首違不罰”清單制度,對于首次發(fā)生清單中所列事項且危害后果輕微,在稅務(wù)機關(guān)發(fā)現(xiàn)前主動改正或者在稅務(wù)機關(guān)責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內(nèi)改正的,不予行政處罰。
二是對一般涉稅違法行為實施“信用+風險”監(jiān)管機制。在信用方面,我國已建立起納稅繳費信用評價制度,根據(jù)評價結(jié)果由高到低分別為A、B、M、C、D五個等級,對信用等級不同的納稅人實現(xiàn)分類管理,對高信用低風險的納稅人不打擾、少打擾;對低信用高風險的納稅人嚴管理、嚴監(jiān)督。在風險方面,我國稅務(wù)機關(guān)通過建立風險預(yù)警機制,實現(xiàn)對納稅人涉稅風險的快速預(yù)警和實時監(jiān)管。一方面,稅務(wù)機關(guān)通過對其獲取的海量數(shù)據(jù)進行篩選,可以全面了解企業(yè)納稅人稅務(wù)登記、申報、開票和涉稅信息,分析其涉嫌違規(guī)享受稅收優(yōu)惠、違法適用稅收政策和未依法進行納稅申報的情況;另一方面,稅務(wù)機關(guān)還會對其所歸集的數(shù)據(jù)予以加工,結(jié)合特定產(chǎn)業(yè)、行業(yè)和企業(yè)的常見經(jīng)營風險點,制定風險預(yù)警指標。一旦企業(yè)的納稅數(shù)據(jù)達到已設(shè)定的風險指標值,稅務(wù)系統(tǒng)就會實時進行預(yù)警提示。此外,稅務(wù)機關(guān)還依托稅收大數(shù)據(jù)自動對納稅人的各類數(shù)據(jù)進行稽核比對,實現(xiàn)對同一企業(yè)不同時期、不同稅種、不同費種之間,以及同規(guī)模同類型企業(yè)相互之間稅費匹配等情況的自動分析監(jiān)控。
三是對重點行業(yè)和重大稅收違法行為進行嚴格查處和嚴厲打擊。一方面,對于稅種特征突出、生產(chǎn)經(jīng)營結(jié)構(gòu)復雜、管理難度較大的重點行業(yè),通過“雙隨機、一公開”適當提高稅收監(jiān)管抽查比例,圍繞社會問題,嚴格查處當期重點行業(yè)和領(lǐng)域所涉惡意籌劃和利用新型經(jīng)營模式逃稅等涉稅違法行為。2021年,國家稅務(wù)總局公布的稅務(wù)稽查重點領(lǐng)域名單中,農(nóng)副產(chǎn)品生產(chǎn)加工、廢舊物資收購利用、大宗商品(如煤炭、鋼材、電解銅、黃金)購銷、營利性教育機構(gòu)、醫(yī)療美容、直播平臺、中介機構(gòu)、高收入人群股權(quán)轉(zhuǎn)讓等“榜上有名”;另一方面,我國還建立重大稅收違法失信主體信息公布管理制度,對重大稅收違法失信主體實施監(jiān)管和聯(lián)合懲戒。
重塑稅務(wù)合規(guī)管理機制
無論是傳統(tǒng)還是新興行業(yè),回應(yīng)新形勢下的納稅風險、重塑稅務(wù)合規(guī)管理機制,是企業(yè)繞不開的課題之一。針對分級化的涉稅風險與稅務(wù)管理,企業(yè)可結(jié)合自身特點,以防范風險為導向,建立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補救的分級管理體系,具體而言如下:
一是重視建設(shè)企業(yè)稅務(wù)合規(guī)體系,及時糾正輕微違法行為。一方面,企業(yè)應(yīng)根據(jù)所在領(lǐng)域的共性稅務(wù)問題和本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實際情況,開展稅務(wù)合規(guī)建設(shè),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和完善內(nèi)部稅務(wù)合規(guī)管理組織架構(gòu)、涉稅業(yè)務(wù)、納稅申報、發(fā)票管理、外部稅收協(xié)作與配合以及審計監(jiān)督等內(nèi)部管理規(guī)章制度;另一方面,對于經(jīng)營過程中常見的輕微違法問題,企業(yè)應(yīng)充分運用“首違不罰”原則,與主管稅務(wù)機關(guān)積極溝通,在法定稅收執(zhí)法裁量權(quán)范疇內(nèi)盡可能爭取免予行政處罰。
二是嚴格防范一般涉稅違法行為,規(guī)范落實納稅信用管理。一方面,稅收信用在招投標、融資授信和進出口等領(lǐng)域已成為部分企業(yè)的“市場準入”門檻。對于納入納稅信用管理的企業(yè)納稅人,應(yīng)主動糾正自身涉稅違法行為,在規(guī)定期限內(nèi)向主管稅務(wù)機關(guān)申請納稅信用修復。另一方面,我國多區(qū)域發(fā)布地方性稅務(wù)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對稅收政策和征管差異事項予以統(tǒng)一。企業(yè)應(yīng)充分了解所在地的裁量規(guī)則,區(qū)分稅務(wù)登記、賬簿憑證管理、納稅申報、稅款征收、稅務(wù)檢查、發(fā)票及票證管理和納稅擔保等事項可能引發(fā)的行政處罰風險,并據(jù)此細化企業(yè)合規(guī)建設(shè)內(nèi)部章程。同時,了解稅收處罰的裁量規(guī)則也有助于企業(yè)防范潛在涉稅法律風險,并在出現(xiàn)稅企爭議時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quán)益。
三是堅決杜絕重大稅收違法行為,積極整改爭取從寬處理。自2020年起試點的企業(yè)合規(guī)改革(“合規(guī)不起訴”)穩(wěn)步推進,并于今年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開。根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企業(yè)合規(guī)典型案例,以虛開發(fā)票為代表的涉稅刑事犯罪案件數(shù)量可觀,對企業(yè)著手解決類似重大稅收違法行為具有示范意義。合規(guī)不起訴適用案件類型及范圍較廣,既包括企業(yè)在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涉及的各類單位犯罪案件,也包括企業(yè)實際控制人、經(jīng)營管理人員、關(guān)鍵技術(shù)人員等實施的與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密切相關(guān)的犯罪案件。在貫徹少捕慎訴、落實認罪認罰、加強行刑銜接等一系列改革的驅(qū)動下,企業(yè)應(yīng)盡快將合規(guī)體系構(gòu)建和評估工作提上計劃,以合規(guī)規(guī)范企業(yè)治理,以合規(guī)創(chuàng)造企業(y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