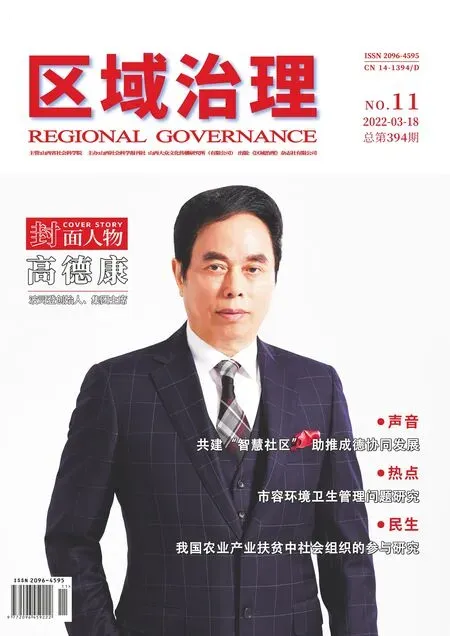區域發展視角下的內蒙古縣域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徑研究*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黨校 歐陽麗娜
我國縣域治理研究隨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內蒙古自治區地域廣闊狹長,地區差距、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比較明顯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其縣域社會治理能力是內蒙古基層社會治理水平的關鍵。本文就內蒙古縣域社會治理能力提升所提出的一些實踐探索,有利于推進內蒙古自治區高質量發展。
一、內蒙古縣域社會治理能力存在的問題
內蒙古自治區現有101個旗縣市區,76個縣域經濟范疇的旗縣市,其中大致劃分為農業主導型、牧業主導型、工業主導型、林業主導型、效勞業主導型等幾個經濟類別。各旗縣經濟發展差距較大,縣域社會治理能力不均衡,對各縣級政府的社會治理要求和標準無法統一,部分縣級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一)價值引領能力不足
近些年,內蒙古充分利用其資源優勢,發展迅速,但其基層社會治理理念還不配套。大部分縣級政府價值引領能力不足、法治化治理理念不深、公平正義理念不夠、注重效率的思維欠缺。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政府“服務本位”理念的轉變落實不到位,仍存在辦事程序煩瑣、事項辦結時限長、“跑腿多”的現象。另一方面,縣域社會治理中群眾參與深度不夠、廣度不夠深,充分表明民眾參與治理意識缺失、參與治理的能力較差。
(二)政策執行能力不實
政策執行力直接關系社會治理的成效和人民群眾的滿意度。內蒙古地區各類區域基層社會治理的特點完全不一樣,因此,各地區政策的制定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這就要求縣級政府在政策的執行中要注意區域的差異性特征。當前縣域社會治理中存在著一些制度規章“寫在紙上、貼在墻上、鎖在柜里”的形式主義色彩,“三分鐘熱度”“雨過地皮濕”等落實不實的現象,執行過于僵化教條,不能結合本地區實際情況具體分析的現象。
(三)組織協同能力不到位
社會治理注重協同能力凸顯系統性。縣級政府在社會治理中,要求各部門組織協調運作,形成社會治理綜合運行體系。內蒙古地區的部分縣級政府存著“多頭管理”“無主管部門管理”等現象,尤其是在矛盾糾紛的化解中,信訪、政法委、司法、法院、公安、檢察院等部門之間的協同對接不順暢,對于社會資源、市場資源、政府資源的整合不到位,人力資源、財政投入、物質保障的整合不完善,未能使政府、市場、社會本來的效用發揮到位。
(四)共建共享能力不充分
社會治理凸顯“社會”二字,治理主體強調社會化、多元化。縣級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共建共享能力是實現治理社會化的重要指標。
內蒙古地區各類企業發展水平不高、社會組織發展較弱、民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不強,導致在縣級政府的引導下,很難建立起高效暢通、充滿活力的政社互動、政企互動、政民互動的聯動機制。部分縣域的社會治理實踐中,沒有更好地構建起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
(五)風險防控能力不高
社會風險防控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政府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水平。內蒙古地區部分縣級政府的風險防控能力不高,沒有形成系統的風險研判、風險評估、防控協同等機制。2021年國慶期間的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對新冠疫情的防控與處置充分暴露出了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可見,對于發展相對緩慢的地區,其縣級政府尚未形成符合縣域水平的應急管理基本模式。除此之外,縣級政府應對風險防控的科技支撐相對薄弱,很多地區沒有建立社會治理綜合信息系統,無法實現社會治理的“智能化”,這也是導致風險防控能力不高的重要原因。
二、制約內蒙古縣域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
準確的歸因是解決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大體可從客觀和主觀兩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制約內蒙古縣級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原因。
(一)客觀因素
1.縣域經濟基礎薄弱,發展具有局限性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縣域社會治理的水平。內蒙古自治區各地區經濟發展基礎不同,自治區內多數旗縣的產業結構以單一產業為主,甚至產業內部缺乏多種經營模式。占相當比例的旗縣區,一產產業化程度較低,三產發展緩慢,甚至有部分盟市相鄰旗縣的二產結構出現趨同現象,資源配置極度不合理。這些都導致內蒙古地區縣域經濟發展整體上與全國比較呈現出基礎薄弱、發展不均衡的特點。同時,嚴重制約著自治區各盟市的縣級政府社會治理的能力具有差異性。如內蒙古的興安盟科右中旗、科右前旗、扎賚特旗、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赤峰市巴林左旗等10個旗縣被列入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這些旗縣不僅在經濟發展中需要大踏步地“追趕超”,而且需要加強縣域社會治理的能力,提升社會治理水平。
2.深化改革意識較弱,忽視治理能力的提升
20世紀60年代,浙江省楓橋鎮形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成為國家基層社會治理的寶貴經驗和推廣模式,并在全國各地探索、創新與發展。內蒙古自治區探索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同時,不斷推進社會治理方面的深化改革,但仍存在遵照“頂層設計”而忽略基層探索的問題,沒有真正做好“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不同穿法,根源在于縣級政府各職能部門在推進改革方面意識較弱,無法真正認識到縣域社會治理水平有待提升,沒有深入研究如何提升縣級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有效路徑,容易造成各種問題,由于“權責不明確”而推卸責任、“自掃門前雪”導致程序繁雜,甚至出現“公權力的分配不合理、不科學”以及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出現“責任分享的困境”等問題。
3.治理手段單一粗放,多種治理能力低下
社會治理手段單一和缺乏精細化就是典型的社會發展不充分的表現。內蒙古縣級政府社會治理手段單一,以網格為主搭建治理框架,沒有充分發揮各要素的功能,志愿服務水平較低,專業化的社會工作者隊伍薄弱,單純的治理居多,人性化的治理較少。同時,沒有充分運用現代科技進行社會治理,網格化治理和服務不夠精準,基層治理信息平臺建設不完善,農村地區與城市相比,其信息基礎設施和信息資源的占有量相差甚遠,存在較為明顯的“數字鴻溝”,甚至認為“不出事、不出聲”就是治理的目標,導致治理能力的全方位提升存在困難。
(二)主觀因素
1.縣級政府對縣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求的認識不夠
當前內蒙古部分縣級政府對推進縣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認識不夠,有些停留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推進中,認為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求就照做,沒有涉及的內容就沒必要做,沒有真正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沒有真正思考人民群眾需要什么、社會需要什么,這必將導致對“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認識不到位、方法不多、效果不好。在化解社會矛盾時,不能很好地動員全社會力量,也不會形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的良好氛圍。
2.縣級社會治理人才隊伍建設相對滯后
內蒙古縣級政府社會治理人才隊伍建設相對滯后,社會工作領域的人才總量明顯與治理任務不匹配,尤其是受地方政府財力及人才流動偏好的影響,縣域社會治理領域的人才數量缺少。從人才隊伍的專業、學歷、年齡等結構看,呈現出極為不均衡的狀況,專業人才少、非專業人才多,專職網格員少、非專職網格員多,人才積聚在常態維護的領域少、解決問題的領域多,專業人才從事農村社會治理少、城鎮社會治理多,人才流動愿意去落后的旗縣少、發達旗縣多。
3.社會治理各主體參與度不高、積極性較低
縣級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建設需要多主體參與,當前內蒙古縣級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偏弱的根源恰恰是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困難。一是基層黨組織不能很好地發動群眾,不能很好地處理社會活力和社會秩序的關系,要么管得太死,要么放得太開,缺乏強大的動員和組織能力。二是政府把“政府負責”直接等同于政府主導,對全面落實各治理主體的責任不到位,一些領域多頭管理、分散管理的問題解決不徹底。三是無法匯聚起各類社會組織的合力,社會組織要么規模小、實力弱,要么存在利益分歧,要么行政化傾向明顯。四是群眾參與度不高,認為社會治理是政府和社區工作人員的事,與自己毫無關系。
三、提升內蒙古縣域社會治理能力的路徑探索
政府治理能力就是政府在治理地方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時所具有的潛在的或顯示的能量和力量的綜合反映。縣域范圍內的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要求,因地區不同而能力偏重也不同。新階段,內蒙古縣域社會治理能力在不斷提升中應更加具有地區特色、時代特色。
(一)建立“全領域清單”制度,明確職責權限,提升政策執行能力
明確縣級政府各部門的責任,并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建立“全領域清單”,在涉及社會治理各領域的組織和部門中,要求建立任務清單、負面清單、考核清單、評價清單。首先,確定縣級政府的責任邊界,進一步明確政府的職能職責,該管的事項堅決管到位,不該管的事情一定要以機構改革、簡政放權為契機,把社會組織、市場主體可以辦、能辦好的職能下放,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其作用。
內蒙古烏海市海勃灣區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理念,統籌推進治理權責“大清單”,在各部門積極建立“一辦法三清單”制度規范,落實各部門建立相關“三清單”的政務公開制度,報同級黨委、政府,上級政法委和上級指導部門審核。呼和浩特市新城區為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提高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建立民生實事項目清單,圍繞市民關注的教育、養老、出行等熱點問題票選出了每年的民生清單,2021年共涉及8項民生實事項目。以8項民生項目為類別,按照涉及的部門和單位進行任務分解,并制定整改時間。這種“全領域清單”的具體實施路徑,有利于政府、部門權責明確,使政策執行能力不斷提升。
(二)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加強部門溝通,提升組織協調能力
縣級政府應以建立聯席會議制度為抓手,完善內部協調溝通。要在縣域范圍內建立以黨委領導政府牽頭的跨部門協調機構,加強各部門之間橫向業務的協調,使原有的部門分割格局被打破。在縣域、鄉鎮、社區(嘎查)范圍內建立不同類別的聯席會議制度,推進相關單位部門協調和事項處置能力的提高。
內蒙古興安盟烏蘭浩特市(縣級市)創新實踐“1+3+x”工作模式,“1”是以信訪局為牽頭單位,“3”是區域內常駐單位、輪駐單位和隨駐單位三類單位,“x”是指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參與力量。常駐單位、輪駐單位、隨駐單位通過多部門聯合會議處置復雜事項,實現解決群眾反映問題“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
(三)發揮“綜治中心”的作用,化解矛盾風險,提升風險防控能力
充分發揮“綜治中心”的輻射牽引作用來化解矛盾風險。“綜治中心”是平安建設的重要平臺,是社會治理的“大腦中樞”,充分利用這個平臺,進行各種調節矛盾力量的介入和協調。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堅持以綜治中心實體化建設為載體,積極打造“綜治中心分派吹哨、相關部門依責銷號”的工作格局,深入推進調解組織和網絡向下延伸,壓實蘇木鎮、村兩級以及職能單位的公共服務、矛盾化解、社會治理等職能,促進綜治中心與各相關部門協作聯動、資源整合、信息共享,實現一體化運作、實體化運行,實現了“1+1>2”的綜合效能,變單科門診為專家會診,變單打獨斗為兵團作戰,真正實現“最多跑一地”。同時,在“綜治中心”設置群眾接待大廳,將網格化服務管理中心、綜治網絡信息指揮中心(監控研判室)、矛盾調解中心(訴調對接矛盾多元化解)、法律援助中心、涉法涉訴中心、信訪訴求中心、行政仲裁中心和交通事故調解中心等10個功能室全部納入該中心進行綜合運行。
(四)全社會治理互動機制,多元主體參與,提升共建共享能力
建立健全社會治理互動機制,有利于積極調動社會多元主體的參與熱情,參與到社會治理中。
建立各種平臺和參與渠道,培養社會大眾主體意識,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的良好氛圍,努力促進各類社會組織建設,社會服務能力有所提升,讓社會主體有更多機會和平臺參與治理。縣級政府要構架互動橋梁,推動各主體之間的信息和資源共享,幫助市場主體和社會主體積極領會政府政策,同時縣級政府也要了解市場和社會的客觀需要,創新社會治理的多種互動模式,如網絡問政、調查問卷、座談會等公眾參與治理方式,探索行之有效的公眾參與途徑。
赤峰市紅山區以建設智慧社區為中心,通過微信、網站等多媒體方式實現社區、社會組織、社工和居民在線互動與資源對接,形成了一個閉環式的互動機制。十分注重對社會組織培育,要求每個街道注冊和構建一個社會組織服務中心或社區社會組織聯合會,在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實踐中實現了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五)加強法治政府建設,做好普法宣傳,提升依法治理能力
法治政府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縣級政府首先要做好依法決策,明確重大行政決策事項、主體、權限、程序和責任,切實提高決策質量,控制決策風險最小化。提升縣級社會治理能力,更加強調縣級政府運用法治工具的能力,不僅要加快地方性法律制度的建立與完善,還要提升縣級政府工作人員的依法行政能力。壯大普法隊伍,塑造和培養一支精干的隊伍,建立從上而下的普法隊伍網絡,抓好落實,做好每一階段的工作規劃和實施方案,建立一種領導干部有效、基層群眾歡迎的法治宣傳教育機制,豐富普法方式,有側重地加強宣傳工作。
(六)完善縣級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提升治理創新能力
基層社會治理中,基層政府作為治理主體的引導者,在推動其他參與主體參與公共事務、化解社會等問題時,不可避免要運用大量的專業化知識和手段,這就要求完善縣級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機制,在專業化人才的培養和引進上下功夫。
縣級政府在組織內部應提高現有基層工作人員的專業水平,提高縣級政府關于社會治理的專業化知識、方法。其次,加大對專業人才培養、引進的財政投入,多層次、多角度制定吸引人才和培養人才的制度和辦法。第三,注重引進多領域人才。社會治理專業化推進過程中,要求不斷豐富社會治理專業知識體系,不斷提升創新能力,來實現高質量、高水平的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