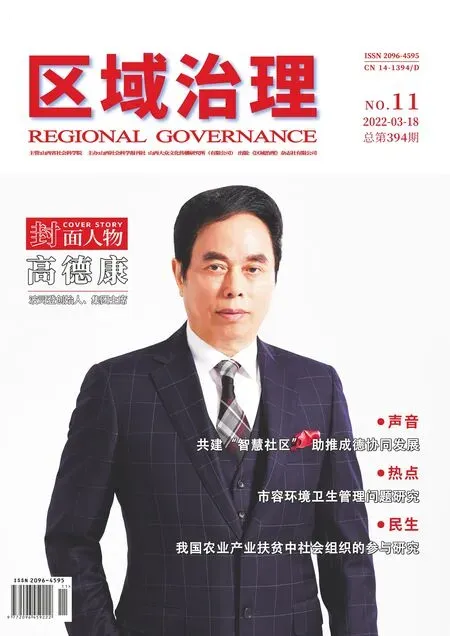中國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法治化探究*
東北林業大學 吳辰昱,鐘琦
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法制概述
(一)立法概況
立法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三部法律法規成為我國應對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的中流砥柱。
機構設置層面,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構的體系化建設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衛生應急管理制度形成人民政府統一指揮、衛生部門協調工作、有關單位通力協助的基本框架。根據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根據本級衛生部門的建議以及實際需要,擁有決定是否成立應急指揮部門的權力,應急指揮部門的構建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我國面對突發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時,在事前預警、事中監督、事后保障三個方面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進,形成了全方位、全流程、全覆蓋的保護屏障,進一步提升了我國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二)現存問題
我國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已經具有維持衛生緊急狀態時的社會安定功能,正朝著更加完備、科學的方向發展,其中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法治化亟待進一步推動。法是治國之利器,發揮著懲惡揚善的作用,也是人民之盾,保護著人們不受非法侵害。緊急狀態下,非法行為者抓住漏洞,尋求逃脫之機時,法律將成為人民手中的自衛利器,保證自我權利的實現。此外,信息傳遞工作與應急手段發生了實施上的錯位,在跟緊工作部署的步伐上有所欠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天然具備時間屬性,爭分奪秒進行信息傳遞將為挽救無數生命創造前提條件,現階段的信息傳遞工作較為滯后,需加強重視。最后,是應急工作人員職權行使問題。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明確權責一致要求,同時這也是行政法所立之基本原則。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發生以后,公職人員依法辦事、權責一致,而由于客觀原因,許多非公職人員秉承服務人民的信念加入了應急隊伍中,這就面臨少有完備法規指導工作的困境。職權不定且公信力不夠,難以展開工作,職權模糊,工作中可能出現超越限度的行為,引發不滿。因此,需加大力度解決非公職人員的職權問題。
二、古代傳染病防治法律的經驗
(一)應對機制多元化、科學化
雖然早在殷商時期就出現了相關的記載,但是正式作為立法出現的傳染病防治法最早見于秦朝。《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爰書,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五(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即疏書甲等名事關諜(牒)北(背)”。說明秦朝時期官府會及時記錄疑似病例以便更好地控制流行病蔓延,提高防治效率。“里節(即)有祠,丙與里人及甲等會飲食,皆莫肯與丙共桮(杯)器”。說明立法對周邊人群進行了切斷傳播途徑的行為規范。在《法律問答》寫道,“城旦、鬼薪癘,可(何)論?當(遷)癘(遷)所”。說明秦朝設立了集中隔離地——癘遷所,此時的隔離所僅收容已經確診的病患,對于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觸者并沒有相關的隔離辦法。
(二)優化信息傳遞機制
受限于客觀環境,中國古代地方醫療發展相當有限,如貞元九年任職黔中的張侍郎上表談到當地“絕無醫人,素乏醫藥”,唐代地方的醫學生在未正式成為醫師之時,便被政府征調投入救治工作,可見地方醫療人才資源嚴重缺乏,因此政府援助便顯得尤為重要。除了隔離,及時發現疫病,然后迅速組織管理,可以降低傳播風險并提高病患存活率。古代通信技術落后,這便需要另辟蹊徑,從立法入手建立健全報告制度,打通從地方到地方、地方到中央的信息高效傳遞渠道。宋朝皇祐四年,仁宗發出了“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的疑問,后規定“凡是有關州縣疫病的公文及臣僚奏疏,閤門司、通進司、銀臺司、登聞理檢院、進奏院等,一概不得阻留,直達于上”。此外,宋代將“翰林醫官院”派駐到地方,稱為“駐泊醫官”,進一步將地方與中央之間的醫療信息、資源打通,要求地方政府將本地疫病暴發的信息公布于交通要道之中,加速地方之間的信息流通。《大明律》的《戶律》中對瞞報、漏報行為予以懲戒,從官員入手,提高信息傳遞效率。
(三)立法統籌中央與地方應對機制
唐《天圣·疾醫令》中立法確定了巡患制度。《疾醫令》唐16:“諸醫、針師等巡患之處,所療損與不損,患處官司錄醫人姓名案記,扔錄牒太常寺,據為黜陟。”唐代設太醫署,太醫署醫師的巡患之地主要限于京師地區,主要負責京師地區爆發疾疫時的救治工作,只有在地方疾疫爆發時才會被派遣前往救助。但是信息往來的滯后性必將延誤救治工作,因此《疾醫令》唐16規定:“諸州醫師亦如此。”說明地方依照中央設立巡患制度。然而史料研究發現,唐代地方并無醫師編制,實際上參與救治工作的是醫學生。據史料考察,醫學生在提早完成學業并具有救助能力后,便被要求前往各州進行“巡患”,并且記錄在冊,作為考校辦法之一,因此實際上,此時他們已經具備《疾醫令》唐16中所言“醫師”的身份。《唐六典·三府都護州縣官吏》記載,“京兆河南太原三府:醫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開元初置醫學生二十人”。據此可知,地方官府在醫療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仍啟用經驗不足的醫學生應對突發疾疫時也有所考量,因而以帶教醫師為領隊設置醫療小組,以此來提高救治成功率。
(四)集中社會力量協助機制
1.利用慈善性質的組織
在古代,受限于社會發展水平,系統學習醫學知識并接受專業培訓的醫師尚在少數。突發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發生后,人手不足的問題便凸顯了出來。除了號召民間醫師,國家還注意到了慈善機構等非政府機構的社會組織力量。慈善機構性質的組織如北宋范仲淹首創設立的義莊,其發揮著重要的救濟作用。淮北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李學如研究發現,義莊的救濟與福利不局限于本宗族人員,而是擴展到了鄉鄰,逐漸成為社會救濟中的重要組織力量,同時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對義莊進行備案予以保護,按律懲處危害義莊正常運轉的成員,對建莊者予以政府名義的褒獎等。
2.規范基層民間組織
早在西周時期便出現了憑借道德準則調和鄉里關系的鄉里組織,直到秦漢時期,鄉里組織才正式形成,并且成為統治者治理基層社會的重要手段。但是鄉里組織中的教化人員卻不是官僚體制中的一員,漢代的三老制中,“三老”由道德威望極高的人擔任,其承擔勸導鄉里、助成風化的責任。三老制、老人制中的管理者被賦予了相當于官員的地位,“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一言說明了這樣的事實。到宋代,保甲制替代了鄉里制,并制定有《畿縣保甲條例》,條例中諸如編制、輪差、連坐以及要求保丁習武的規定,體現出宋代保甲制的治安管理目的,其對于鄉村治安以外的事件管理職能有所弱化。但此時出現了鄉約制度,講約之人亦由德高望重者擔任,維護著鄉村社會秩序。到了明代,政府將鄉約與保甲制度相結合,加強了對鄉村的控制。清朝時期的鄉紳制度雖然表面上看似乎脫離了政府的管控,以其天然的權威對鄉村進行管控,但是其參與國家治理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與政府打交道,而從史料記載來看,政府對鄉紳所產生對抗力量的態度模糊,將此放在處于皇權集中頂峰時期的清朝來看似乎不可思議,筆者認為這可能也是政府對于基層自治的另類規范。
(五)嚴格管理人口流動機制
嚴格管控人口流動是對傳染病防治迅速作出反應的重要環節。人口流動數據管理在古代表現為戶籍管理,戶籍管理制度的完善尤為關鍵。《大明律》的《戶律》中規定:“凡一戶全不附籍,有賦役者,家長杖一百,無賦役者,杖八十。若將他人隱蔽在戶不報,及相冒合戶附籍,有賦役者,亦杖一百。無賦役者,亦杖八十。”由此可知,明代嚴懲逃戶即幫助他人逃戶的行為,若里長在戶籍管理方面失職,也將受到嚴懲。記錄成冊的戶籍信息有利于進行篩查密切接觸者的工作,對于公共衛生安全起著重要作用。
(六)其他保障制度
古代統治階級除了用法律手段進行傳染病的防控,還會通過綜合運用城鄉規劃、醫師考核制度等手段輔助管控傳染病暴發。
1.城鄉規劃
西周時期,不論是王朝都城還是諸侯國郡,域內領土都分為城邑與鄉野。“城”強調聚落具有城防設施,“邑”說明此處為居民聚居之地。按照人類聚居的規律來看,有山澤、田地與放牧的草地就意味著可以進行生產,從而生存下去,所以,可以判斷邑外之地雖為鄉野之地,也存在小規模的、零散的住戶集聚。那么從整體來看,西周時期居民集聚呈現出大塊團狀為中心、小點松散分布在周圍的形態,各個小點之間往往有大量山川田地、牧野相隔。古代傳染病暴發主要來源于公共衛生管理較差的鄉野以及外來人口流動,都城與鄉野之間遙遠的距離、鄉野各居民點間呈現的松散狀對突發傳染病的傳染鏈條切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2.醫師考核制度
據《唐研究》一書分析,唐代實際上負責醫療救助一線工作的人員可能主要是醫、針師,而非太醫署中的醫監醫正等醫官或醫學教育體系中的醫學博士即助教等人,更不是未通過醫、針生晉升醫、針師考核而為下一等級的醫工。成為醫、針師后,他們要不定時接受“遣醫救療”的考核,即到地方患疾疫之處進行醫療救治,這便是唐代“巡患制度”的核心所在。《天圣·醫疾令》唐16記載:“諸醫、針師等巡患之處,所療損與不損,患處官司錄醫人姓名案記,扔錄牒太常寺,據為黜陟。”該條律令表明醫、針師在“巡患”中的所作所為是年終考核的重要依據。唐代特別的醫師考核制度大大彌補了地方醫療資源缺乏的漏洞,獎懲機制也提高了醫師的積極性,有利于地方傳染病的控制。
三、古代傳染病防治法律經驗對當代的啟示
(一)重視應急管理法治化
公共衛生安全突發事件中,隔離法在其中的重大意義未曾改變過,縱觀整部中國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史,我們不難發現國家總是基于緊急時期適當管控人們的部分自主權以達到管理目的,其結果也是十分有效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隔離法雖是無奈的,卻也是十分有效的,要堅持以隔離為主的管理辦法。現代意義中的隔離固然不可能像古代那樣單純地將病人隔離起來,還要考慮諸多事項,在人權保障意識覺醒的時代,應該注意協調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人權保障。
(二)高度重視信息傳遞問題
古代尤為重視信息傳遞的作用,在緊急狀態下,信息傳遞環節漏洞以及法律規范的疏忽導致了許多現實問題。如實行封閉管理時,若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保障民生,將出現嚴重后果遺因此,需立法明確規定此類行為,學習古代立法具體形成此類罪名或由行政法調整的相關處罰,比如細化并納入年度考核標準中,或者處以降級處罰等相關措施。
(三)明確規范非公職人員的具體權責
中國古代的宗族、鄉里、鄉約是現代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雛形,這些民間組織在國家組織應急管理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封建帝制的中央政府雖手握高度集中的權力進行國家治理,但是受限于客觀技術條件,對于地方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應對機制,在面臨地方緊急狀態時的處境了,于是便有了對民間組織具體如何進行基層自治的法律規制,但是古代政府對基層自治的管理或有法律進行規制,更多散見于統治者實施的具體手段中,對于其中的細則沒有深入考量。而處于現代社會中的我們,或許可以得到關于管理非公職人員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啟發。突發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爆發后,參與社區這一基層自治組織活動的有許多如志愿者、社區工作人員的非公職人員,他們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從事相關活動,執行著強制力度非常大的“職權”,此時不可避免會與公民所擁有的權利產生沖突,他們行使“職權”的權力邊界應該明晰,執行過程中應有合理的規范程序。
四、結語
本文對中國古代統治者在面臨傳染病突發時的應對措施進行了陳述,其中不僅包括統治者、政府官員的積極主動行為,還包括時代背景下各種因素催生而出的消極被動行為,二者在不同層面、不同力度上都對古代傳染病的有效控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回顧歷史不僅是為了吸納其中的精華,還在于總結其警醒功能。盡管古時候的管控手段在現代看來已經不再新鮮甚至過時,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其立法原意中得到現代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法治建設的相關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