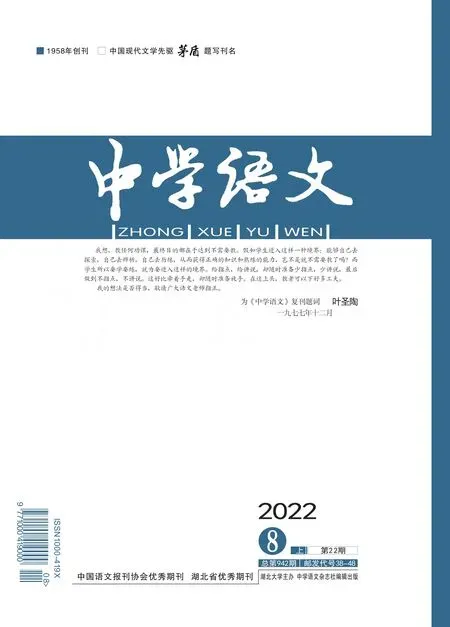從破“解”悟“道”讀《庖丁解牛》
趙文建
《庖丁解牛》節選自《莊子·養生主》,題目是后世讀者從文章首句“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中截取的。這一截獨具眼光,直接把文章的文眼給擇取了出來。全文緊扣“庖丁解牛”這四字展開,描繪了解牛的場面、闡述了解牛的境界、解牛的理念、解牛的態度、解牛的切入點、解牛的方法。可以說,“解”字是窺探本文主旨的一扇窗戶,庖丁因解牛悟道,文惠君聽庖丁談解牛獲得養生之道。
但也有不少人因此質疑:生活中常說“殺豬宰牛”,為什么莊子卻用“解牛”?文惠君究竟獲得了怎樣的養生之道?今天我們讀《庖丁解牛》該汲取什么為人處世的智慧。
特級教師薛法根說文本內涵有三個層次:表層(第一層)是字面所寫的意思,即文本所寫的“人事景物”。里層(第二層)是字面背后的含義,即文本隱含的“思想感情”。深層(第三層)是字面之外的風格,即文本體現的“表達藝術”。解讀文本需要找到一個打開文本的切入口,由此進入,從而領略文本內在的、表達的奧妙。據此,本文試以“解”字作為切口去打開文本,走進“庖丁解牛”的世界。
一、用漢字六書理論剖析“解”字的字形字義,由此進入文本
許慎《說文解字》中說:“解,判也。從刀判牛角。”“判”字,意思是分,分開。這是個會意字,可見“解”的本義就是用刀從牛頭下手拆分牛的軀體。牛軀體龐大,必須用刀化整為零、化大為小地拆分才能物盡其用。先民們用“解”字標示殺牛的過程,足見其表達的形象精準。文中“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每至于族”“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從這些語句來看,庖丁也正是輕巧地用刀像拆解一個大的結構復雜的物件那樣,把牛的龐大軀體分解成一個個小零件。“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不像良庖那樣用刀“割”,更不像族庖那樣用刀“折”。這里“解”與“割”“折”的區別在于:首先,“解”是“依乎天理”(牛體的自然結構),刀游走在“彼節者有間”的牛關節縫隙,必須非常熟悉牛身體的“天理”結構,看準縫隙下刀。“割”與“折”就沒這個講究,尤其是“折”,課本中注釋是“斫、砍”,只要用力掄刀就可以了。其次,動刀用力的方式不同,順著關節縫隙“解”用的是巧勁,“動刀甚微”,所以他手上的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割”“折”就不太需要顧及牛的身體結構,只要刀刃鋒利,有蠻力就可以了。固然,刀刃鋒利可以割肉,但牛肉柔軟有韌勁,也會鈍刀,更不必說用刀砍斫了,牛骨粗壯堅硬,常常把刀刃磕出豁口,所以“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就不足為怪了。至于“殺”“宰”和“屠”等字只是表示一個事實,遠不及“解”字內涵具體豐富,能突出表現庖丁的眼光精準獨到、手法靈巧、力道靈活、技藝高超。
二、與平常生活中常見的殺豬殺雞場景對比,分析庖丁解牛場面的不同
孫紹振教授提出用“還原比較”法解讀經典文本,具體說就是把文本中描述的藝術形象恢復到平常生活中本來的樣子,凸顯差異、揭示矛盾,在研究矛盾的基礎上解讀文本。平常生活中一般人都看過殺豬殺雞,那是一個怎樣的景象:被殺的豬或雞拼命掙扎、慘叫,特別是殺豬,屠夫一刀子下去鮮血飛濺,場面血腥,往往讓人感覺屠夫下手殘忍。挨刀的豬也很可憐,被幾個人合力摁著,只能拼命掙扎、慘叫。如果豬是自家養大的,還真讓人有點不忍心,所以古有“君子遠庖廚”之說。屠夫與幫忙的一干人手忙腳亂,仍弄得渾身血水,氣喘吁吁。本文第一段描述庖丁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庖丁手腳肩膝并用,動作嫻熟,節奏流暢,伴著刀在手中揮動得呼呼作響,合乎古曲的節拍韻律,完全沒有平常宰殺所見的鮮血與掙扎,聽不到慘叫,感覺不到血腥與殘忍,似乎被殺的牛也不曉得自己是怎么死的。從旁觀人看來,庖丁不像是在殺牛,而像是在街頭廣場上跳舞,給人一種美的享受。如果換作“殺牛”“宰牛”“屠牛”,這些在今人眼里飽蘸血腥的字眼,豈不毀了庖丁解牛創造的美感!
三、從寓言的藝術表達角度揣摩庖丁解牛蘊含的“道”
莊子的文章天馬行空,變幻莫測,善于運用藝術形象來闡明哲學道理,而這些藝術形象就包含在莊子編造的一個個寓言之中。寓言在藝術表達上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用比喻說理。其比喻的喻體就是寓言中的人、事、物,本體則是寓言的寓意,由比喻本體與喻體之間的相似性啟發人們聯想,從而領悟寓意。《庖丁解牛》這則著名寓言節選自《莊子·養生主》,一般認為,篇名“養生主”意思是養生的關鍵、要領。“養生”的意思是保身、全生、盡年。通俗地講就是保全生命怡養心性、活得長久、活盡天年,不同于今天人們常說的“養生”。如若揣摩庖丁解牛寓言蘊含的“養生之道”,或者對今人為人處世的啟發意義,就得從寓言善于運用比喻說理這個特點出發。文惠君講養生,就是想“保全生命,活得長久”,在本文中與“生命”有相似性的喻體就是庖丁手中的“刀刃”。庖丁說“良庖歲更刀,族庖月更刀”,“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相比之下,庖丁的刀刃生命最長久。庖丁的刀刃所以耐久,是因為庖丁解牛講究用刀、養刀的結果。庖丁面對的是軀體龐大、結構復雜的牛,文惠君養生、今人為人處世面對的是復雜迷幻的世道社會,那么文本中與牛對應的本體就是世道社會,可以說庖丁不僅解牛,還解世道社會。分析庖丁解牛用刀、養刀及其技藝精進的經驗,就可以獲得養生之道和為人處世的智慧,也就是庖丁所說“臣之所好者道也”的“道”。
首先,庖丁說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一切操作順著牛的天生結構。這是莊子借庖丁之口明確告訴我們,凡事須尊重現實(“固然”),處世須遵循客觀實在的規律法則(“天理”),根據規律法則行事,養生必須順應生命的自然節律。
其次,庖丁解牛從“大郤大窾”下刀切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因為刀刃沒有厚度,關節縫隙就顯得寬綽有余,切入精準,刀刃游走,就能有效避免磕碰損傷。“刀刃者無厚”啟示我們養生要清心寡欲,為人應虛懷若谷。世道社會盡管矛盾復雜、斗爭激烈,但總有間隙可尋,只要像庖丁那樣,把準時機,“以無厚入有間”,切入精準,就能在夾縫中求生存,保全性命,養護精神;回避矛盾,人就能在社會中游刃有余了。
第三,刀刃鋒利解牛可以割肉斫骨頭,但牛肉會鈍刀,牛骨能豁刀刃,這是互害關系,所以“良庖歲更刀,族庖月更刀”。庖丁的刀使用了十九年卻能“刀刃若新發于硎”,是因為不割“技經肯綮”,不斫“大軱”。這就啟示我們:不蠻干、不糾纏、不碰硬、不做無謂的消耗。
第四,解牛“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可以啟發我們:面對糾結難解復雜問題,心存敬畏,認真對待,設法四兩撥千斤,以簡御繁,以易化難。
第五,解牛結束,庖丁“善刀而藏之”,又提醒我們:養生須注意及時保養身體,處世就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自如。
第六,庖丁也不是天生神技,他技藝精進,得益于學藝時“所見無非牛者”“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用心專一,也驗證了實踐出真知的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