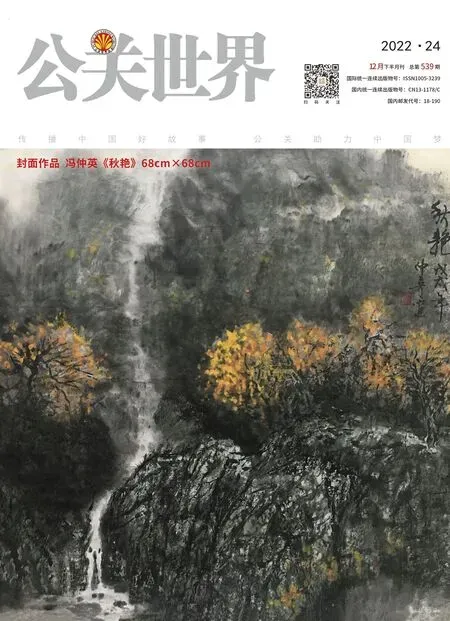高校輔導員分析處理大學生抑郁情緒問題研究
文/玉佩鐘
引言
大學生處于心理尚未完全成熟的發展階段,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關鍵時期,應對環境變化、生活困境與人生挑戰的經驗不足,容易產生心理問題。[1]抑郁癥是當代大學生最為常見的心理問題,而抑郁癥的前期體現的是抑郁情緒等不良情緒體驗的堆積。我國大學生抑郁情緒檢出率為29.3%,[2]抑郁是一種心境低落、悲觀的消極情緒狀態,若長期處于此種狀態會引發各種心理疾病。[3]抑郁癥狀包括自我評價低、精神遲滯、無愉悅感、精力減退等,嚴重的會伴隨出現自殺念頭、存在自殘行為、易失眠或睡眠過多等情況。[4]抑郁不利于大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是造成大學生退學、休學的主要原因。目前治療抑郁癥的方式比較簡單,吃藥或者做心理咨詢就可以解決,但大家對抑郁癥存在偏見,拖延或害怕導致抑郁癥最佳治療時間被延誤。大學生輔導員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職責和崗位要求輔導員深入學生群體,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而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一環,關系到學生三觀的培養質量與立德樹人的目標實現,因此,發現和研判大學生抑郁情緒并做好疏導,防止大學生抑郁情緒堆積與惡化是高校輔導員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大學生抑郁情緒成因分析
1.自我發展與人際關系焦慮
大學生常見的焦慮源包括以下兩項:學業與就業壓力、人際關系危機,當焦慮無法調節時伴生抑郁情緒。焦慮從行為上可以引起社會功能退縮和生活方式改變,產生回避行為,社會支持系統范圍減少,增加抑郁風險。[5][6]學業與就業壓力屬于由自我發展矛盾引發的焦慮源,在大一適應階段與大四就業擇業階段尤為突出。其次,人際關系失調是引發大學生焦慮與抑郁的重要因素。[7]人際關系的本質,是人們滿足馬斯洛需求層次中的底層需求,即生理和安全需求后所追求的歸屬、愛和尊重的需要,或可稱后者為社會的需要。人際關系的優劣決定社會需要滿足的程度,焦慮和抑郁情緒會在人際關系出現危機時產生。大學生焦慮來源是進一步研究抑郁情緒的線索與突破,高校輔導員可以通過相關線索判斷更深層次原因并有針對性開展心理疏導。
2.原生家庭因素
原生家庭是大學生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課題,家庭功能低的大學生抑郁檢出率高。早期負性教養方式會引起個體的適應不良圖式和負性認知,而后者與抑郁的關系極為密切。[8]大學生抑郁成因為父母的忽視、冷暴力及極端做法讓其產生負性童年體驗,遇到應激性事件容易內歸因及自我否定,陷入消極情緒,若大學生心理資本水平較低,出現抑郁癥狀概率較高。心理資本指個體在成長發展過程中呈現的積極心理狀態,有利于緩沖應激性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9]其他研究指出,受身心虐待兒童比在正常環境下成長的兒童在生活中更容易產生消極情緒偏向,較高概率形成神經質人格。[10][11]神經質人格屬過于敏感人格,會促使個體在情緒調節過程中采用不適當的調節策略,阻礙情緒調節的進度與質量。[12]由于構成早期情緒調節刺激的不適應性加工奠定了日后情緒調節困難的基礎。[13]簡而言之,童年時若長時間遭受情感忽視及極端對待,長期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情感支持能量弱會導致個體的無助感和消極情緒體驗感強烈。長大后在受到應激事件時,如同學、同事的忽視,會讓學生聯想到自己小時候的遭遇,出現應激障礙。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體生活在特定的環境系統之中,個體行為與社會環境系統的交互促成了個體心理行為的發展。家庭是與個體聯系最為密切的微觀系統,對個體的影響是直接且持久的,家庭環境被指出是影響大學生抑郁的重要因素。[14]高校輔導員在研判大學生主要抑郁情緒源于原生家庭問題的前提下,可采用充分調度及發揮個體社會支持系統作用的方式開展疏導工作。
二、輔導員處理抑郁情緒辦法
1.加強問題分析研判能力
大學生心理素質不同,對外界刺激的承受能力也存在差異,采取的應對方式就存在差異。[15]大量研究指出,大學輔導員在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應注重問題導向,即將重心放在大學生患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產生自殺行為等問題的解決和處理預案方面。輔導員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從職責及工作性質的角度的確需要注重問題的解決,但該導向將輔導員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高校特殊人群上,從而忽視了其他“普通”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狀態。加強高校輔導員的問題分析與研判能力,要求輔導員在聚焦問題學生的同時排查“普通”學生的潛在隱患,遏制或消除抑郁等心理問題在萌芽狀態。輔導員在日常工作中通過學生課堂、課外活動、學習生活的方面搜集信息加以處理,發現及判斷大學生抑郁情緒等不良心理體驗來源并根據來源特點及時且有針對性地做出反應,可阻斷大學生抑郁風險加深的可能性。分析研判學生的問題所在后,解決問題有兩個思路,一是通過人為減少外部刺激的方式降低對大學生的心理沖擊和傷害。由于外部刺激形式內容多樣,且學生接受刺激的維度和標準不一致,因此需要消除的外部刺激無法被精準鎖定,該方法不具備操作性和可行性。作為高校輔導員,可采用第二種解決問題的思路,即通過提高大學生的心理資本水平提高學生抗逆力,降低抑郁情緒堆積的風險。[16][17]
2.關注學生不同階段焦慮源
輔導員需掌握不同學生在不同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焦慮源,有針對性地制定預防及疏導機制,從而有針對性地阻斷抑郁情緒堆積。研究指出,大學生焦慮的根源可歸結于兩個方面,自我發展矛盾與人際關系危機,焦慮源的影響程度在大學生所處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一是自我發展矛盾。一年級到三年級主要表現為學習焦慮。一年級學生從高中跨越式進入新的學習生活環境,容易適應困難;二年級課程量與課程難度加深,學習強度與深度水平提升;三年級大學生處于自我實現與現實矛盾沖突的關鍵時期,該時期各類競爭結果相對定型且影響學生考研就業等職業生涯發展方向,反向促使學生提升學習效率和時間精力的投入。因此,一年級到三年級學習壓力是學生焦慮、抑郁的主要原因。四年級學生主要焦慮源是就業與升學的壓力。四年級學生處于步入社會前的適應階段,就業升學選擇迫切,且當今外部社會環境的崗位稀缺、就業率低迷等情況反向強化四年級大學生就業升學壓力,增加大學生不良情緒調節的挑戰性。二是人際關系焦慮。人際關系焦慮貫穿大學生學習生活的始終,其內容也緊緊圍繞親情、愛情、友情展開,隨著年級和學習工作內容的變化,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出現由校園內轉向校園外、學校轉向社會的變化趨勢,學生面對的人、事、物呈數量級增長,人際關系壓力隨時間推移不斷增加[6]。高校輔導員應在大學生不同階段,針對不同焦慮源制定分析和應對策略,及時且有指向性地消解大學生不良情緒。
3.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
研究表明,社會支持系統的完備與高質量的社會支持領悟可緩釋個體抑郁情緒體驗,[18]降低無助感和社會隔離感。[19][20]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個體領悟社會支持水平,大學生自尊與領悟社會支持呈顯著正相關,領悟社會支持對自尊有正向預測作用,自尊對抑郁有顯著負相關且能負向預測抑郁水平,而低自尊是抑郁最重要的易感因素之一,自尊與抑郁、焦慮等呈高度負相關。[2]因此,如何幫助和引導學生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提高學生領悟社會支持是輔導員處理學生抑郁問題的關鍵,同時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高校輔導員應充分運用第二課堂,強化大學生家、校、社會聯系,為大學生建設和完善社會支持系統提供良好外部環境。高校第二課堂為學生提供鍛煉的條件和平臺,高質量的第二課堂活動可引導學生正確處理與他人、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培養學生的認知意識與行為能力,從而提高學生建立高質量社會支持系統的能力。同時,高校輔導員通過學生在第二課堂的表現,分析研判學生心理狀態及其社會支持系統問題,分析結果作為幫扶指導依據。建立大學生社會支持系統與提高大學生領悟社會支持系統是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的重點課題,理論與實施途徑需要進一步探究。
4.積極心理干預
大學生心理和諧水平可折射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大學生積極心理干預的加強可以促進大學生心理和諧水平的提升。研究表明,大學生心理和諧包括兩個層面,個體對內的與自己的和諧與個體對外的與他人、環境及其他外部事物的和諧。大學生面臨的壓力與焦慮會破壞心理和諧的平衡,在面對困境時,若對內無法悅納自己,對外無法調整由外部刺激引起的情緒行為反應,造成知情意的失衡會陷入抑郁情緒之中。使用“優勢積極心理品質練習”等積極心理品質干預方式,可以將大學生的注意力引導至自身所擅長的部分并加以強化,使自己的優勢得到增強與拓展,從而提升自己抵抗風險與挫折的能力,更容易達到心理和諧的狀態。根據吳九君研究[20],大學生學會與各種逆境和平相處的能力可稱之為抗逆力,指個體在實現目標活動時受到阻力所表現出來的情緒狀態和行為表現。積極心理干預可培養個體的積極情感、行為和認知,所積累的積極心理資本為大學生提供積極心理能量,能有效緩解逆境刺激下個體產生的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從而提高個體的抗逆力水平和心理和諧水平。大學生積極心理干預實踐的拓展與延伸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