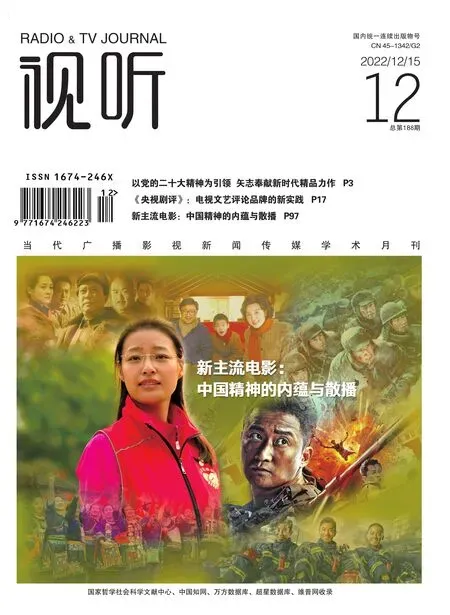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文化紀(jì)錄片發(fā)展新樣態(tài)
蔡秋川
文化紀(jì)錄片早期是一種重要的電視節(jié)目類型,是電視媒體傳播區(qū)域文化、發(fā)揮對外傳播功能的重要載體。如今,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主體、傳播渠道和話語方式等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文化紀(jì)錄片也呈現(xiàn)出多元發(fā)展樣態(tài)。
一、文化“富礦”造就文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優(yōu)勢
文化紀(jì)錄片是以“文化”為表現(xiàn)主題,以文化傳播為目的的紀(jì)錄片品類,兼具文獻(xiàn)意義和審美價值。傳播是文化的重要存在方式。①一種文化,如果不能被看到、聽到,不能被接觸、了解,就難有較強(qiáng)的生命力。文化只有被傳播、被了解、被消費,才能被傳承。而文化紀(jì)錄片便承擔(dān)了重要的文化傳播與傳承之責(zé)。文化紀(jì)錄片往往聚焦一種文化事項、文化品類或文化現(xiàn)象,對其進(jìn)行全面系統(tǒng)的呈現(xiàn)和“易于傳播”的包裝。經(jīng)由紀(jì)錄片這一受眾普遍接受的節(jié)目樣式,不少重要卻又容易被忽視的文化議題被帶入大眾視野。反過來,文化本身也為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提供了重要素材和啟發(fā)。“文化即人化”,廣義的文化包含了人類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其結(jié)果。狹義的文化則是剝離物質(zhì)創(chuàng)造活動及其結(jié)果后的精神創(chuàng)造部分,包括知識、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習(xí)俗等。②中國文化源遠(yuǎn)流長,積淀深厚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成為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和題材“富礦”。也正因為題材的豐富性,文化類紀(jì)錄片更易于實現(xiàn)欄目化、系列化,更能夠做出體量,做出厚度和深度。
文化紀(jì)錄片自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便在電視熒屏上大放異彩③,如今在文化影視產(chǎn)業(yè)大發(fā)展的背景下,更是成為具有文化標(biāo)桿意義的影視藝術(shù)品類。近年來,習(xí)近平總書記多次強(qiáng)調(diào)要“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各級廣播電視媒體、各領(lǐng)域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者積極探索,不斷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資源,對之進(jìn)行再創(chuàng)造、轉(zhuǎn)化和發(fā)展,形成了文化紀(jì)錄片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的熱潮,催生了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這些作品的問世,在增進(jìn)國人對所處文化環(huán)境的認(rèn)知和認(rèn)同的同時,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國人的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信反過來又激勵了創(chuàng)作者的創(chuàng)作自信。
當(dāng)前,紀(jì)錄片的質(zhì)量和獨家資源依舊是各媒體平臺之間競爭的制高點。在此背景下,作為文化傳播載體的紀(jì)錄片需要在強(qiáng)調(diào)紀(jì)實性的同時,加強(qiáng)歷史觀和文化審美的引導(dǎo),豐富敘事技巧,突出個性化與差異化,從而實現(xiàn)節(jié)目品質(zhì)和品位的升級,滿足受眾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網(wǎng)絡(luò)傳播助推文化紀(jì)錄片發(fā)展
早期的文化紀(jì)錄片一般由各級電視媒體制作,往往聚焦媒體覆蓋地域的歷史、民俗、藝術(shù)等精神文化成果,公信力較強(qiáng),且具有一定的欄目化特征。電視媒體人向來有著親近文化的偏好、傳播文化的擔(dān)當(dāng)以及對文化品質(zhì)的堅守,因此我國的電視風(fēng)格一度被稱為“文人電視”。④
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不僅帶來了新的傳播渠道,也對傳播者、受眾、話語方式等產(chǎn)生巨大影響。對于文化紀(jì)錄片發(fā)展來說,這些影響更多是正向的。一個市場是否繁榮,往往要考量這個市場的需求是否旺盛,供給是否活躍。互聯(lián)網(wǎng)對文化紀(jì)錄片供給和需求的拉動是同步的。在供給端,當(dāng)前,優(yōu)酷、愛奇藝、騰訊等主流視頻平臺都開辟了“紀(jì)錄”版塊,紀(jì)錄片作品有了更多的傳播平臺,一些電視媒體長久以來積累的紀(jì)錄片版權(quán)資源也得以在網(wǎng)絡(luò)平臺繼續(xù)發(fā)揮價值。傳播平臺的多元化也造就了制作主體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機(jī)構(gòu)、個人從事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而這種“草根化”的創(chuàng)作趨勢并沒有拉低紀(jì)錄片的質(zhì)量,這是因為流量競爭倒逼創(chuàng)作者加強(qiáng)內(nèi)容創(chuàng)新,提高內(nèi)容品質(zhì),否則就會被市場淘汰。在需求端,平臺化的傳播方式滿足了受眾對紀(jì)錄片的多元化需求。隨著國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文化紀(jì)錄片因其知識性和觀賞性,受到越來越多高知受眾的青睞。網(wǎng)絡(luò)端收視的互動性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紀(jì)錄片的傳播。有的紀(jì)錄片在電視上播出未能獲得較好的收視效果,在網(wǎng)絡(luò)平臺上線后卻能成為“爆款”,這得益于社交媒體的“病毒式”傳播。例如,文化類紀(jì)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紀(jì)錄頻道播出時,未能獲得較大反響,其后在彈幕網(wǎng)站Bilibili上進(jìn)行次輪播出后,實現(xiàn)流量逆襲,快速火爆網(wǎng)絡(luò)。⑤精英用戶聚集的豆瓣網(wǎng)對該作品也打出了高分,更是難能可貴。《我在故宮修文物》共3集,每集50多分鐘。這樣的長篇紀(jì)錄片能夠走紅網(wǎng)絡(luò),足以說明網(wǎng)絡(luò)受眾對文化紀(jì)錄片的認(rèn)可。在網(wǎng)絡(luò)傳播環(huán)境下,視頻平臺增加了紀(jì)錄片的曝光度,為受眾提供了收看紀(jì)錄片的便利,為紀(jì)錄片這一內(nèi)容品類匯聚了人氣,進(jìn)而帶動了創(chuàng)作者和資本的加入。網(wǎng)絡(luò)平臺對供給端的促進(jìn)還在于用戶行為大數(shù)據(jù)對內(nèi)容創(chuàng)作的指引,有助于內(nèi)容創(chuàng)作者拍攝出更加“適銷對路”的紀(jì)錄片作品,進(jìn)而實現(xiàn)供需相長的良好局面。一些小眾文化的需求也能被識別和積聚,并吸引有相關(guān)興趣的創(chuàng)作者進(jìn)行創(chuàng)作,這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紀(jì)錄片文化主題的多元化。
三、新傳播環(huán)境下文化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的多種樣態(tài)
互聯(lián)網(wǎng)改變了紀(jì)錄片的傳播方式,也對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多重影響。在新的傳播環(huán)境下,文化紀(jì)錄片的創(chuàng)作題材更加廣泛,表現(xiàn)手段、話語方式更趨多樣化,呈現(xiàn)出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
(一)“非遺”選題偏好凸顯文化紀(jì)錄片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
“非遺”是近些年文化紀(jì)錄片的選題偏好。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俗稱“非遺”,是一個國家優(yōu)秀歷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標(biāo)志,更是一個民族在代代存續(xù)中留下的集體記憶和活態(tài)文化基因。中國“非遺”文化項目多姿多彩,諸如西安鼓樂、蘇州評彈、江浙地區(qū)的昆曲、浙江龍泉青瓷工藝、安徽宣紙工藝……這些珍貴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祖先傳承給今人的精神文化財富。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和經(jīng)濟(jì)文化生態(tài)的變化,不少傳統(tǒng)藝術(shù)、技藝、習(xí)俗等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如果保護(hù)意識落后或資金、技術(shù)匱缺,這些文化成果可能就會面臨后繼無人、斷代失傳的風(fēng)險。聚焦“非遺”主題,傳播“非遺”文化,推動“非遺”保護(hù),凸顯了當(dāng)下文化紀(jì)錄片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
電視文化紀(jì)錄片能否助力“非遺”傳承?答案是肯定的。紀(jì)錄片能夠以其“藝術(shù)地展現(xiàn)真實”的優(yōu)勢,從不同的視角展示“非遺”的非凡與珍貴,以及其“脆弱”的一面——沒有傳承,就會斷代。《關(guān)于加強(qiáng)我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工作的意見》指出:“鼎力支持新聞出版、廣播電視、互聯(lián)網(wǎng)等媒體對‘非遺’實施保護(hù)舉措,普及知識、培育意識,盡力在全社會引發(fā)共鳴,營造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良好氛圍。”可以說,文化紀(jì)錄片是傳播“非遺”文化最適宜的內(nèi)容品類,對推動“非遺”保護(hù)和傳承,保障我國民族文化多樣性,責(zé)無旁貸。文化紀(jì)錄片依托豐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段,有助于加速受眾對“非遺”文化的理解,激發(fā)受眾對“非遺”文化保護(hù)的共情,進(jìn)而引導(dǎo)更多的人消費“非遺”文化,投身“非遺”事業(yè)。近年來,一批具有藝術(shù)特色、思想深度的非遺文化紀(jì)錄片廣受好評。比如,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文國際頻道攝制的《傳承》,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紀(jì)錄頻道推出的《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國手作》,上海廣播電視臺打造的《非遺來了》,愛奇藝播出的《指尖上的中國》,優(yōu)酷播出的《了不起的匠人》,Bilibili播出的《百年巨匠·非遺篇》等,從不同角度、以不同風(fēng)格展現(xiàn)“非遺”文化,弘揚(yáng)匠人精神。越來越多的“非遺”文化紀(jì)錄片以接地氣的表達(dá)語境和個性化的敘事風(fēng)格吸引著觀眾的眼球,其中不乏現(xiàn)象級的“爆款”。在媒體融合背景下,不少電視媒體出品的紀(jì)錄片作品從營銷到播出也跳出了電視,實現(xiàn)了全媒體多端覆蓋。例如,上海廣播電視臺推出的《非遺來了》,實現(xiàn)廣播、電視、網(wǎng)絡(luò)和線下活動等全媒體滲透,擴(kuò)大了電視文化紀(jì)錄片的覆蓋面。其“非遺來了”同名抖音號還進(jìn)行了100多場視頻直播⑥,其傳播力和影響力不可小覷。
(二)“小而精”成為文化紀(jì)錄片的重要轉(zhuǎn)型方向
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受眾的消費場景變得愈加多樣化,閱讀習(xí)慣趨向碎片化、即時化。“小而精”的短視頻正契合了這樣的內(nèi)容消費需求,“微紀(jì)錄片”也應(yīng)運而生。如中國紀(jì)錄片網(wǎng)負(fù)責(zé)人張延利所言:“微紀(jì)錄片回應(yīng)著新媒體時代觀眾對于精簡影像的需求。”⑦關(guān)于微紀(jì)錄片的界定,時長是重要考量因素。國外學(xué)者通常以4~10分鐘的時長來劃定,國內(nèi)學(xué)者則普遍認(rèn)為其時長可在5~25分鐘。⑧如果按后者劃分,目前諸多文化紀(jì)錄片都可算是微紀(jì)錄片,如《如果國寶會說話》《國寶100》《中國手作》《了不起的匠人》等都屬于微紀(jì)錄片。
2019年,廣東廣播電視臺珠江頻道重點打造的《廣東名片》進(jìn)行了微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嘗試。該系列紀(jì)錄片介紹了民俗活動、戲曲表演和手藝制作等廣東本土“非遺”文化,共105集,分為兩個版本——“高清版”每集3分半鐘,“4K版”每集5分鐘。微紀(jì)錄片“短”的特質(zhì)決定了其敘事上的“精”——精于選題、精選細(xì)節(jié)、精簡敘事。例如,在《揭陽青獅》一集中,鏡頭通過諸多細(xì)節(jié)捕捉,用幾分鐘時間還原了制作“非遺”青獅的全過程。師傅訓(xùn)練弟子們舞青獅的畫面現(xiàn)場感十足,節(jié)目中還適時穿插師傅與弟子的采訪,節(jié)目架構(gòu)頗為豐滿。《廣東名片》篇幅雖短,但給出了足夠多的信息量。微紀(jì)錄片的“微”,除了體現(xiàn)在時長上,還體現(xiàn)在選題與敘事上的“以小見大”:一是關(guān)注大主題、大事件中的平凡個體,二是從民生視角、平民視角審視大主題、大事件。⑨《廣東名片》系列紀(jì)錄片在策劃之初就注入了互聯(lián)網(wǎng)基因:從拍攝、制作到播出,都著意凸顯傳統(tǒng)文化的新媒體表達(dá)和新時代內(nèi)涵,力求以“見人、見物、見生活”的理念,充分展現(xiàn)廣東“非遺”文化的歷史底蘊(yùn)、地域特色以及其中蘊(yùn)含的匠心精神、東方美學(xué)、民族智慧,彰顯廣東百姓作為文化主體的能動性。該作品再造了“非遺”“亙古亙今、日新又新”的當(dāng)代時空,通過通俗活泛的話語方式吸引年輕人,通過“非遺”傳承人的故事、“非遺”文化的魅力激勵年輕人參與“非遺”保護(hù)和傳承,凸顯了節(jié)目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廣東名片》這部“小而精”的系列微紀(jì)錄片,在傳統(tǒng)電視熒屏和廣東廣播電視臺旗下新媒體平臺“觸電新聞”上播出,實現(xiàn)了大屏和小屏聯(lián)動,達(dá)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三)聚焦當(dāng)下個體凸顯文化紀(jì)錄片的人文關(guān)懷和文化自信
傳統(tǒng)的文化紀(jì)錄片更多關(guān)注文化現(xiàn)象、文化器物、文化事件,如《話說長江》《故宮》《新絲綢之路》等,或者某種文化品類,如《瓷路》《錦繡記》《園林》《中國節(jié)日》等,甚少直接關(guān)注人,或者人的“面目”相對模糊。隨著紀(jì)錄片創(chuàng)作主體的泛化,特別是草根化,不少拋卻宏大敘事,關(guān)注普通個體,特別是聚焦當(dāng)下人物典型的紀(jì)錄片作品涌現(xiàn)出來,如《外灘老人》《最帥上海交警》《西單女孩》《侶行》等。這樣的創(chuàng)作偏好在文化紀(jì)錄片領(lǐng)域也有升溫跡象。例如,央視推出的紀(jì)錄片《文學(xué)的故鄉(xiāng)》集結(jié)了6位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家,導(dǎo)演張同道帶領(lǐng)攝制團(tuán)隊回到文學(xué)家的故鄉(xiāng),一路探尋他們的文學(xué)起點:和莫言一起在山東高密感受天開地闊,隨著賈平凹下商州,跟著阿來去四川嘉絨藏區(qū),與遲子建回到東北漠河,看劉震云如何走中原,找畢飛宇記憶中的蘇北水鄉(xiāng)……通過觀看這一系列尋訪過程,觀眾了解了幾位文學(xué)家的出生、成長、性格,甚至一些不為人知的嗜好、習(xí)慣,還看到了一個完整的“人”及其背后的文化土壤。這種充滿未知的人物跟拍和諸多細(xì)節(jié)展現(xiàn)具有一定的“真人秀”性質(zhì),增添了紀(jì)錄片的感染力。
又如浙江衛(wèi)視推出的6集電視文化紀(jì)錄片《西泠印社》,該片打破了慣常的時間線敘述方式,采用人物的共生關(guān)系構(gòu)建出紀(jì)錄片的邏輯結(jié)構(gòu)。攝制組在利用實地尋訪、口述歷史等表現(xiàn)手段的基礎(chǔ)上,在視覺傳達(dá)方面做了新的嘗試:將“創(chuàng)社四君子”——丁輔之、葉為銘、吳石潛、王福庵的后人請到了攝影棚內(nèi),并讓他們在一個特殊的空間里與先人“相遇”。例如,鏡頭跟隨著手捧花束的丁輔之孫女丁如霞拜謁孤山,重訪丁家遺址。該片以多元的視覺表達(dá)形式,圍繞杭州孤山,重現(xiàn)當(dāng)年西泠印社創(chuàng)始人及其家族的一些珍貴影像,設(shè)置了古今對話的場景,使片子富有真實性與感染力。將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個體生命的境遇交織敘述,是電視文化紀(jì)錄片一種特別出彩的表現(xiàn)手法。如果說聚焦文化,傳播文化,滿足社會大眾的文化需要,凸顯了文化紀(jì)錄片的一種文化擔(dān)當(dāng),那么聚焦文化中的人,還原文化個體的本來面目,則體現(xiàn)了對拍攝對象、對普通受眾的尊重,凸顯了一種人文關(guān)懷。
另外,關(guān)注當(dāng)下的人以及當(dāng)下的文化,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新一代創(chuàng)作者的文化自信。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題材,打造文化節(jié)目,開展對內(nèi)對外傳播,有助于激發(fā)國內(nèi)受眾的文化自豪感,同時獲取國外受眾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認(rèn)可,反過來又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國內(nèi)大眾的文化認(rèn)同。這是許多主流媒體及相關(guān)創(chuàng)作者樹立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然而,優(yōu)秀的文化并不只在“故紙堆”里,在當(dāng)下,同樣有著值得記錄的文化和文化人。聚焦現(xiàn)當(dāng)代的文化和文化人,更深層次地折射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
四、結(jié)語
在網(wǎng)絡(luò)傳播環(huán)境下,文化紀(jì)錄片具有了更突出的傳播屬性。繼微博、微信、微視頻、微電影等之后,微紀(jì)錄片誕生,它繼承了網(wǎng)絡(luò)傳播的“微”特征,主要表現(xiàn)為即時性、互動性、社交性等。文化紀(jì)錄片的既有創(chuàng)作主體——電視媒體從業(yè)者需因應(yīng)網(wǎng)絡(luò)傳播特點做出轉(zhuǎn)型,在保持嚴(yán)謹(jǐn)性與公信力優(yōu)勢的同時,主動進(jìn)行傳播方式創(chuàng)新和話語方式創(chuàng)新,從而在“新陣地”占據(jù)一席之地。
注釋:
①何華湘.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播研究——以女書為例[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2010.
②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9:2-4.
③孟建,黃燦.當(dāng)代廣播電視概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16:101-103.
④孟建,黃燦.當(dāng)代廣播電視概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xué)出版社,2016:101-103.
⑤劉博.《我在故宮修文物》:互聯(lián)網(wǎng)語境下紀(jì)錄片發(fā)展新形態(tài)[J].中國廣播電視學(xué)刊,2021(08):77-79.
⑥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家廣電智庫。
⑦牛夢笛.歷史文化紀(jì)錄片大有看頭[N].光明日報,2022-05-08(004).
⑧何志武,馬曉亮.融媒體時代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微紀(jì)錄片傳播[J].中國編輯,2022(09):42-47.
⑨譚馨語.微視角下的微紀(jì)錄片敘事策略——微紀(jì)錄片《故宮100》敘事策略分析[J].新聞研究導(dǎo)刊,2020(15):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