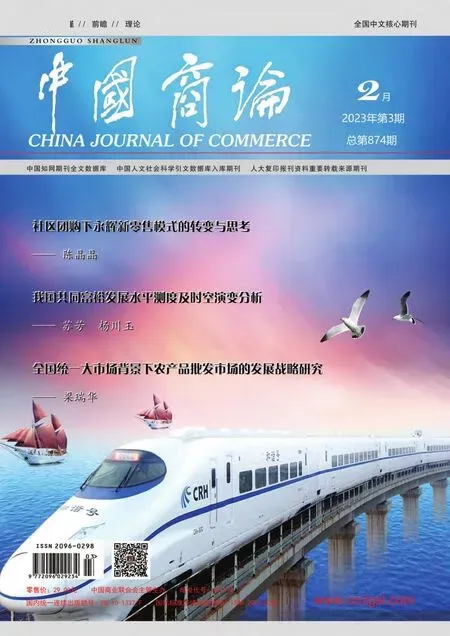基于GRA模型的我國城鎮失業規模影響因素分析
馬琦峰 劉尹新宇 周楊健馨
(1.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北京 100872;2.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上海 200234;3.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 華盛頓)
改革開放之初,大批知識青年返城、城市勞動力和其他社會待業者劇增,伴隨著就業政策的調整,我國迎來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兩次失業高峰。為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失業保障空缺帶來的負面影響,國務院于1986年7月和1999年1月相繼發布《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和《失業保險條例》,標志著我國失業保險制度從創建走向確立。截至2020年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同比2000年增長35.48%,可見21世紀以來我國城鎮失業問題未獲得實質性改善。
目前,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尚未達到4%的充分就業水平,且由于我國“失業登記率”相較國際通用的“調查失業率”存在著統計年齡限定嚴格、統計指標不全面性及大量的城鎮隱性失業未納入統計范疇等缺陷,因而導致統計結果低于真實的失業水平(王玉潔,2014)。龐大的勞動力人口基數使得中國較同等失業率的發達國家而言,面臨著更為嚴重的規模失業問題(閆濤,2011)。此外,結構性失業逐漸成為當下長期失業問題產生的重要來源(汪戎和薛軍,2013)。凱恩斯主義的工資黏性理論提出由于工資水平對勞動供需變動的反映存在滯后性,因而產生了大批的非自愿結構性失業者(郭春良和呂心陽,2016)。同時,伴隨勞動主體日趨多元化,性別、年齡、教育、產業等結構差異加劇了勞動供需不匹配現象,同樣產生了大量結構性失業者(蔡禾和曹薇娜,2019;楊紫薇和邢春冰,2019;陳明生,2019)。另外,勞動力市場雙方信息流動受阻及不對稱產生的自愿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經濟周期波動產生的周期性失業及某些部門的間歇性生產特征導致的季節性失業大大加重了社會失業問題(田靜,2015;Lawrence J等,2020)。從上述角度來看,當今我國城鎮就業情況不容樂觀,城鎮失業規模對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產生了消極影響,正因如此,相關研究一直是我國社會保障及勞動經濟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張車偉和蔡翼飛,2016)。
本文應用改進后的GRA模型探究我國失業規模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不僅能夠豐富現有的失業研究,還能為我國失業控制及就業促進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數據來源及變量選擇
1.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中國統計年鑒》,其中包括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國內生產總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數據來源可靠、時間序列數據跨度較大、數據指標的選擇均與失業規模有直接的關聯性,為后續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數據基礎。
1.2 變量選擇
本文解釋變量包括人口變量、經濟變量與社會變量三個方面,選取男性人口數量、65歲及以上人數、GDP、CPI、第三產業從業人數、高校畢業生數及參加失業保險人數共7項測量指標,被解釋變量是失業變量,選取城鎮登記失業人數作為測量指標。各變量指標選擇及依據詳情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指標選擇及依據
2 方法選擇
灰色關聯度分析模型(GRA)最早是由鄧聚龍(1990)教授創立的,該模型本質上提供一種度量兩個向量之間距離的方法,即通過觀察度量序列曲線的形態、走勢及所構成的幾何圖形面積是否相近來判斷兩個序列間的關聯程度。應用模型前需要明確參考、比較兩組序列,在此基礎上將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置于鄧氏關聯度系數模型中,但該方法存在兩個弊端:其一,在采用不同的標準化處理方式(初始化、均值化、區間化、逆化、倒數化)或取不同的調整系數時,可能會改變原始序列的相對位置,產生序數效應,故不具有保序性。其二,由于在關聯系數計算中采用截距計算方式,因而使得關聯系數取值始終介于(0,1],僅能反映關聯強弱程度,但無法反映兩者之間究竟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這種性質不利于對失業規模的影響因素研究。對此,單聯宏(2010)對傳統GRA模型進行改進,棄用原有鄧氏關聯度的面積與形狀擬合,進而采用斜率作為關聯度的衡量指標,提出利用序列平均相對變化率的構成差與構成比來定義新的關聯系數,并引入一個符號函數來反映序列的正負相關關系,即對應時段平均變化率方向一致時關聯系數為正,相反則為負,進而得到新的關聯系數計算模型為:

其中,k=∈[2,n);sgn為符號函數,用于判斷關聯系數的正負;ξi(k)為斜率關聯系數,在改進后的模型中取值為[-1,1];x0與xi分別為剔除量綱后(本文采用初值化方式)的參考序列與比較序列數據。分別為參考序列與比較序列中時點k-1到時間k的斜率,min與max分別為最小取值函數與最大取值函數,即在兩序列比較中所有斜率中的極值。同樣,在對斜率關聯系數計算完成后需要對特定時間區間[a,b]的各序列關聯系數絕對值進行均值計算。改進后的公式擺脫了原模型中的兩大弊端,統計性質優良。
3 統計分析
將城鎮登記失業人數指標數據作為參考序列,將人口、經濟及社會變量中各指標數據依次作為比較序列,運用Excel 2010軟件,利用SGN、ABS等組合函數對兩序列間進行灰度斜率計算,以求得各序列關聯系數。在此基礎上,對各序列關聯系數絕對值進行均值計算,以獲取序列關聯度,并利用RANK函數對各關聯度進行排列形成關聯序,關聯序如表2所示。

表2 GRA關聯序
由表2可以看出,各組關聯度均處于60%~70%水平,受數據、模型精度等因素影響,真實情況可能更高。一般而言,GRA關聯度高于70%為重要因素,處于50%~70%的為比較重要因素,低于50%則為不重要因素,據此可知本文所選各指標均為影響我國城鎮失業規模的比較重要因素,能夠較好地解釋我國城鎮失業規模變化。其中,各組關聯度從高至低排序依次為:通貨膨脹關聯、產業結構關聯、年齡結構關聯、性別結構關聯、社會保障關聯、經濟總量關聯與高等教育關聯。基于此,本文依次對經濟、人口與社會變量進行逐一分析如下:
首先,經濟變量對我國城鎮失業規模的影響最大,具體表現為通貨膨脹、產業結構與城鎮失業規模的關聯度分別為66.195%與66.101%,位列關聯序前兩位。一方面,通貨膨脹關聯再次印證了菲利普斯曲線揭示出通脹與失業率間存在的短期負相關關系,符合勞動經濟學相關原理。另一方面,伴隨著第一二產業的“機器換人”趨勢加速,在以服務為核心的第三產業中人的不可替代性相對更強,同時新業態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并吸納了更多的勞動者,因而產業結構與城鎮失業規模密不可分。此外,雖然經濟總量關聯位列第六,但其關聯度仍接近65%水平,說明經濟總量發展對促進就業是有顯著影響的,但弱于經濟結構優化帶來的影響。
其次,人口變量對城鎮失業規模的影響弱于經濟變量,但總體影響程度差異并不大,年齡、性別結構與城鎮失業規模的關聯度分別為66.052%與66.039%,位列關聯序第三、四位。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相當一部分崗位因勞動者退休而產生了空缺,這對適齡勞動者就業是有利的,可以較好地解釋年齡結構變遷對我國城鎮失業規模的影響,但同時應意識到這種影響主要體現于緩解總量性失業上,其對結構性失業的影響相對有限。性別結構同樣對城鎮失業規模產生影響,具體表現在職場性別歧視、行業性別壁壘等方面,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男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優勢地位依舊顯著,平等的就業機會在實踐應用中仍難以落實。
最后,社會變量對城鎮失業規模的影響相對較弱,所屬關聯均處于關聯序的中后位置,但從關聯度值來看,其對城鎮失業規模仍有比較重要的影響。失業保障制度是一把明顯的“雙刃劍”,從積極影響上看,該制度會為失業者提供技能培訓、就業信息,以實現再就業;從消極影響上看,該制度會助長勞動者怠惰情緒,從而產生自愿性失業,不過從表2關聯系數中可以看出積極影響仍占據主導地位。高等教育關聯為62.147%,說明社會教育有助于提升人力資本,從而有助于緩解結構性失業,符合經驗與事實,其關聯度相對較低可能由于高等教育投入周期較長,其對失業規模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時滯效應,高等學歷貶值、學生觀念變遷等亦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影響。
4 結語
2008年1月實施的《就業促進法》與2017年12月公開征求修訂意見的《失業保險條例》均從經濟、人口與社會角度提出了控制我國城鎮失業規模的指導意見,致力于促進我國勞動者的就業與再就業。然而,影響失業的因素是復雜多樣的,其作用機制亦不盡相同。由于我國龐大的勞動力基數及復雜的社會情形,單獨依賴經濟、人口抑或社會政策措施難以實現對我國城鎮失業規模的長期平穩控制。對此,應充
分把握包括通貨膨脹、產業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社會保障、經濟總量、高等教育等在內的影響因素作用機制,結合當前失業類型分布妥善選擇與之對應的政策工具與措施,充分發揮上述各因素的積極效能,這對控制我國城鎮失業規模、緩解社會失業問題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