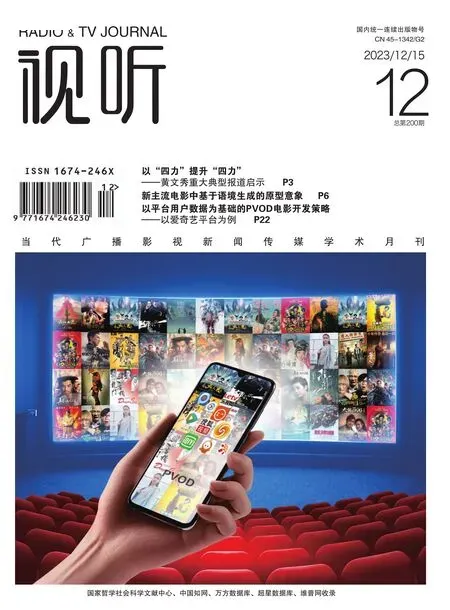新時代警務類紀錄片的敘事策略與形象建構
——以《119請回答》為例
◎袁萌
警務類紀錄片作為連接政府與民眾的橋梁,在熒屏上構筑著社會安全的底座。作為貫徹“紀實美學”理念的紀錄片,其體裁天然帶來的真實性保證,引導著觀眾對警務形象的“初印象”。然而,傳統的警務類紀錄片以宣傳為重,過度的宣教性淡化著人物角色的豐滿感與情感的細膩感,細節失真又讓警務題材紀錄片成為“肉剛血搏的臉譜圖鑒”。另外,敘事的單一化又使部分警務類紀錄片開著科普教育的“跑車”,脫離觀眾的真實需要軌道,偏離審美需要的航道,成為“聲畫版的宣傳手冊”。在此背景下,眾多警務類紀錄片涌入大眾視野。其中,國家應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與騰訊視頻聯合出品的24 小時全景追蹤式消防警務紀錄片《119 請回答》一經播出,便獲得大眾良好反響。該片憑借新奇的敘事方式、立體的形象構建、多元的傳播渠道順利“出圈”。熱愛此片的觀眾也主動進行消防知識的傳播與社會消防監督,“粉”起了片中的消防員。《119請回答》高收視率、高互動背后的傳播機理與創新模式值得學習與借鑒。
一、敘事“求新”:多元素結合全視角講述
(一)敘事主題:多元復合的內容文本
主題是觀眾未知紀錄片內容時先行吸引觀眾眼球的重要法寶,以往主題通常是內容表達的凝練,內容的敘述限于主題的框架,依據主題的范圍進行編排,直觀明晰。而《119請回答》摒棄一貫的故事情節串聯手法,通過事件的拼貼反映主題主旨進行敘事表達,觀眾先行通過主題名稱預想節目大致內容,而且事件的勾連又能夠沖破觀眾的預先期待,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該片共有六集,分別為《滾燙人間》《菜鳥先飛》《生死有時》《防患未燃》《超長待機》與《真心英雄》,拍攝的地點取自哈爾濱與重慶南北兩座城市,時間跨度從2015 年到2021年,長達六年。每日24 小時的拍攝讓紀錄片擁有龐大的素材體量,而通過預先對主題的設立,創作人員可以從龐雜的素材中分門別類,從個性中找到共性,提升紀錄片整體的結構性與事件的關聯度。另外,主題的不同也使內容具有風格化表現,為敘事的多元化提供有力保障。例如,第一集《滾燙人間》以救火事件為主,開頭便以一場燃燒了20 多層大樓的大火為切入點,通過畫面的抖動與現場緊迫的救火場景營造出火場的危險與救援的難度。之后每一個事件的銜接都以強調危急與險峻為主,沒有線性的時間關聯,致力于在不同的事件中表現救火的不易,最終的結尾也是一場極為困難的救火事件,首尾呼應保證了結構性上的完整。而第二集《菜鳥先飛》關注消防新手的成長。開頭通過多個新手的群像特寫切入,從幾位新手的視角出發,展現每一次事件所帶來的內心變化與業務熟練度。該集通過線性的時間順序,展現新手成長中面臨的一次次磨礪,觀眾從線性的時間敘述中伴隨新手一同成長。主題先行所帶來的敘事多元化與風格化,讓觀眾在觀看每一集內容時都倍感新鮮,從而更好地感受不同主題內容的豐富性表達。這種手法也讓每集的消防人員形象在不同的描繪中更加立體化。紀錄片從多角度切入去展現人物內心的真情實感,體察人物豐富的社會事業經歷。
處理事件是消防人員每日的核心工作。事件本身具有很強的情節性、故事性與符號性,通過以事件的方式串聯整個節目,可使節目從架構上極具警務特征,以此削弱節目的宣教意味,展現行為主義風格,讓觀眾通過一個個事件感悟消防人員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不需要過多的旁白與解說,事件本身便有很強的可讀性。據統計,《119請回答》共六集,展現了64個案件,但每個案件主次分明,有44 個主要案件和20 個次要案件。主要案件篇幅較長,重點敘述,通過畫面中“出警單”醒目的花文字與圖片預先告知觀眾,出警單中還會羅列報警時間、出警內容、事發地點、當日溫度等。而次要案件沒有具體的提示,只是通過多個案件中主要的工作場景快速且集中展現的方式來呈現消防員除救火以外的其他工作或表達消防員工作的辛苦。次要案件的穿插也打破了受眾對消防員只會救火的刻板印象,觀眾通過畫面能夠立刻感知消防員工作內容的復雜性與專業性。綜上,通過主題與案件的巧妙搭接,不僅節目的表現形式更加靈活多變,而且敘事的豐富性與風格化也有了巨大的伸展空間。
(二)敘事符號:多重隱喻的意義指向
法國社會學家羅蘭·巴爾特在索緒爾能指與所指的概念基礎上,擴展出對符號意識形態的深層次解讀,視為意指分析(也稱涵指),強調符號所指基礎上外延出使用者的感覺、情緒或文化價值交會時的互動性。①以往大多數政論片與警務片習慣刻畫大場面,以體現國力強盛和講述家國情懷,模糊個體的描寫使整個敘事缺乏故事感與段落感,往往讓觀眾有觀看宣傳片的感覺。紀錄片應帶有極強的人文情感,要從細節中窺萬象,不能單一地做宣傳的工具而忽視受眾個體的情感需求與事件背后的意義。要把握好細節,就要從事件中抽絲剝繭,尋求能夠調動觀眾情感的重要符號,強調符號背后所闡發的意義與作用。在《119請回答》中,諸多細節畫面的刻寫讓符號突破所指的語義界限,融入對社會、對情感、對精神等深層次的解讀,進而走向巴爾特所言的符號的涵指。如該片中,同一事件對火的畫面解讀產生了不同的“涵指”。在第一集老父親與中年男子的啤酒瓶造火案件中,父親與兒子在酒桌上相互不滿,父親便賭氣砸壞酒瓶點燃自己。片中兒子焦躁不安的個人畫面特寫與老父親口中責罵兒子不孝的特寫形成對比,此時的火便是父子感情破裂的涵指。在消防員到達后,父親口中多次重復著:“我心中有火。”此時的火首先是對兒子不滿的涵指,觀眾理解為父親對兒子的怨念深重導致的生理變化。之后經過醫護人員的檢查,發現父親胸肺受到感染,此時火的涵指又指向病危意義。隨后,通過對母親無錢治病的哭泣特寫與對女兒關心父親垂淚的采訪,火的涵指又指向家庭破裂。之后父親離世,火的涵指又指向死亡。最后,消防員李佰特對該事件進行解讀:“遇事應該要當平安的天使,而不是沖動的魔鬼。”此時火的涵指又指向教育意義。這一集中,通過多處的細節描繪與畫面拼貼,從縱火現場到父子爭執、入院就醫、家庭采訪、事件解讀等,火的符碼得到多方面的延伸,闡發出不同的解讀與意義聯系,讓觀眾從一場火中產生反思,窺見生活之變,以警醒現實生活。
除將符號本身的意義上升為涵指之外,物質的符號化也給該紀錄片帶來了更多的科普與教育意義。趙毅衡教授在前學者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將物質的符號化解釋為:“賦予感知以意義的過程,此過程從個人的感受開始,最終取決于人的解釋,此解釋可以是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個人化的。”②對物質符號的理解更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認識與解釋。《119請回答》常以物質特寫加解說、采訪、相關畫面的拼貼去講述道理、闡發現實意義,將物質符號化,進一步達到警務類紀錄片所要求的科普與教育目的。該方式摒棄了宣教性,自然而然地用“事實說話”,用“事實講道理”。例如在第四集居民樓道著火的事件中,該片多次對滅火后的樓道雜物進行特寫展現,在引出消防員現場對受災居民進行教育后,接入消防員個人采訪,并指出在樓道內堆放雜物會造成極大的安全隱患,尤其是老舊小區,一粒火苗極有可能引發巨大的火災。樓道堆放的雜物在消防員的現場教育與個人采訪中從單純的物質轉化為符號的表現,原先單純物質的功能被賦予了安全隱患與消防科普的符號意義。在第五集救貓的案件中,貓作為物質在救援過程中成為遇難者的符號。紀錄片多次將救援現場和冉奶奶的焦急與采訪畫面來回切換,采訪內容顯示冉奶奶由于眼睛問題,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是漆黑的,孩子也常年在外工作,白貓成為多年漆黑世界里唯一的伙伴。在這里,白貓物質符號化為一種陪伴,并延伸出城市空巢老人缺乏關愛的社會問題,為觀眾帶來了更多的思考價值。物質符號化的表現在該紀錄片中并不顯得生硬,其在具有邏輯的基礎上還蘊含人文關懷,其中的救援也不是單純的施救行為,而是在警醒當事人的同時展露其背后的社會問題,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敘事結構:曲折反轉的創作手法
消防人員的核心工作是處理事件,一個事件往往是復雜且現實的。以往的部分政務警務類節目常常通過刻意制造懸念和過度拆解事實來吸引觀眾注意,或因主題宣傳意識過重而采用“畫面+解說”的形式淡化事件的真實性與故事性。這種“刻意”與“過度”都忽略了從事件本身去反映矛盾沖突與去挖掘人物內心中的復雜情感。③《119請回答》便巧妙地通過從具體事件中截取具體的人物觀念、人物思想、人物行為來展現人與人的矛盾、人與社會的矛盾、人與現實的矛盾。該紀錄片以藝術的方式反映社會現實,潛移默化地傳遞主流價值觀,對人的道德行為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也實現了拉斯韋爾傳播三功能說的環境監視功能與社會協調功能。例如,在第一集女子因整容失敗而要跳樓的事件中,紀錄片通過對現場各種不同人的聲音來展現出事件多方面的不同態度與矛盾。首先,從被施救者的聲音中,觀眾得知她與整容醫院因手術失敗而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其次,從被施救者妹妹的聲音中,觀眾又得知她與妹妹在外貌形象上的認知矛盾;最后,從被施救者男朋友的現場溝通中,觀眾又得知他與被施救者之間在愛情理解上的矛盾。從多方聲音的出現來看,事件已從單純的施救成功與否轉化為了對事件背后問題的思考。該片無需過多的畫外音或解說的價值引導,而通過多角度的截取提升影片內部的情感張力。除此之外,該片還巧妙地利用數據與資料來闡發更深刻的矛盾沖突,表現社會問題。在第四集的居民住宅起火的事件中,紀錄片首先通過對多方居民的采訪,使觀眾了解到因火勢過旺引發的立體火災殃及了七樓和九樓,由此造成了鄰里矛盾。而在救援結束后,觀眾知曉著火原因竟是一根未熄滅的煙頭。緊接著,紀錄片插入多個視頻資料來描述一根煙頭所帶來的多方巨大影響,如致使夫妻二人在工作時喪生、2000公頃的草原過火、引燃物流站造成七人死亡等。原本居民鄰里間的矛盾,在影像資料中延伸出人與煙欲的矛盾、人與社會治理的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等,從而也讓觀眾意識到一個煙頭的威力不可藐視,從而直擊生活中被忽視和輕視的部分。可見,巧妙的視頻資料使矛盾的展現更多元,并能夠帶動觀眾從單一的認知層面上升到集體認識,從中可反思自身,而不再是單純地觀看,同時又從資料的警醒中影響日常生活,改變個體的自我行為。
紀錄片在矛盾沖突的敘事方式中,又存在著一定的曲折與反轉,兩種元素的并置在增強事件戲劇性的同時,又提醒著觀眾: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并不總是順利的,事件的處理也并不總是會成功的。例如,在第四集男子被困電梯的事件中,該事件發生了三次反轉。首先,消防車上輕松的氛圍營造了以為解決電梯故障就可以完成任務的假象,然而在搜尋電梯位置的環節中,消防員卻意外發現事情并不簡單,原來電梯所在的大樓位于坡地,內部結構復雜,被困人員所在的一層還需要繞行別樓的電梯才能到達所困地,這是事件的第一次反轉。消防員在多次輾轉找尋電梯一樓口時再次失敗,此時又形成第二次反轉。無奈之下,消防員找來了電梯維修人員,此時揭開謎底,原來電梯所停的一層是在一家火鍋店的后廚,火鍋店違規堆放雜物堵住了電梯口,由此形成第三次反轉。最后,被施救者自述來此地旅游,此事件讓他對該城環境感到無比失望,片子由此展現出人與城市印象的矛盾。同時,多次的救援失敗與最后的謎底揭開將矛盾沖突與曲折反轉相結合,敘事的戲劇性被充分展現,而這一切又都是基于事件真實,在環環相扣中不斷地抓取著觀眾的好奇神經。觀眾可在這戲劇化的展現中解讀出超脫故事本身的更多價值與意義,這是在敘事過程中多元素結合所帶來的觀影效果。
二、形象“求異”:多角度塑造立體化角色
(一)社會場域:舍己為人的城市保衛者
消防員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專業性,救援技能也是消防人員區別于其他職業的顯著特征。技術操作的全方位展現描繪著消防人員的專業形象,他們猶如一座照亮公眾內心希望的燈塔,在不計其數的公共危機事件中壘筑社會穩定的基石。首先,《119請回答》并不只是一味地對現場工作進行單一的重現,而是通過多元素、多視角、多技術的結合打造消防員的專業形象。第一集的高層居民樓失火事件,側重呈現消防員對講機中的指揮聲音與現場救援聲音,以打造專業形象。在火場前,指導員李佰特迅速評估現場大火,“立體火勢”“著火點”“內攻滅火”等專業詞匯讓滅火行動區別于日常的小火災救援,消防員在不到一分鐘的評估后迅速地再分為內攻組、外攻組、救援組與疏散組展開救火行動。救援現場不僅有滅火的聲音,更有對講機中的排兵布陣、火勢傳達、執行操作的聲音。很快,在消防員指揮與執行的絕佳配合中,火勢被成功壓制。可見,在對講機聲音的重現過程中,消防人員呈現出井井有條、臨危不懼、游刃有余的專業形象,無需過多解說來形容消防員的辛苦,而是在畫面與現場聲音的交相配合下各自發力,用真實打動觀眾。其次,一味地進行專業展示是眾多傳統警務紀錄片無法打動觀眾的重要原因,不僅割裂年輕受眾的觀賞偏好,而且讓警務形象在觀眾認知中逐步“撲克化”,形成單一的刻板印象。可見,尋求專業技能展現與受眾個性化需求的融合是警務紀錄片塑造警務形象的“難點”。《119 請回答》通過對消防員專業方面貼標簽的方式,讓他們的專業形象更加豐富。如在第一集女子跳樓輕生案件中,救援成功后,畫面中的姚驊剛被打上了“談判專家”的標簽;在第二集居民樓爆炸的事件中,李洪成功地找到了氫氣罐,揭開了大媽的謊言,被貼上“火場福爾摩斯”的標簽;第三集,在消防員精準切割的訓練中,阮洋洋因高超的無痛切割能力而被消防站稱為“較場口阮大夫”。除了對消防員專業能力的標簽化外,各種出人意料的高超技能也被注入娛樂元素,常常以“解鎖新技能”的標簽出現。例如,在第二集的廚房著火事件中,陳強通過濃煙的味道判斷出還有陰燃,畫面上出現“解鎖新技能:聞味識火”,而阮洋洋的專業能力展示也出現“解鎖新技能:蒙眼切割”的標簽;在第六集的摘馬蜂窩事件中,周言杰出現了“解鎖摘馬蜂窩技能”的標簽。這種多元素、多技巧的專業化展示,不僅多方位地展現著消防員的工作技能與職業特征,而且為他們貼上了更為生動豐富的屬性標簽,進一步將原先“撲克”式的形象進行了立體化的維度呈現。④消防員原先嚴肅的形象在各種多元素的并置中逐漸豐富化,對以往大眾認知中只是與火打交道的刻板形象逐個擊破。在豐富的畫面表現中,消防員變得生動和藹,讓觀眾從多元的標簽中產生深刻的印象,認識到消防職業工作的多元性與復雜性。
除此之外,穿梭于火場是消防員工作的必要過程,與火對抗、舍己救人是消防員的職業使命,也是其熒屏形象中最動人的地方。而這種赴湯蹈火、義無反顧、自我犧牲的精神背后常常凝聚著高尚的道德倫理精神,刻畫悲劇性的人物在引起人的審美快感的同時,往往伴隨著道德快感,喚起人們積極向上的審美感情。⑤對于悲劇人物的刻畫一旦流于俗套,平鋪直敘將無法撼動人心,浪費掉整個故事中重要的高潮元素;如果過于“神話”人物經歷,夸大人物行為,將會使觀眾產生排斥心理,降低影片評價。因此,在刻畫悲劇人物與塑造英雄形象上,應當把握經歷真實性與故事敘述審美性的平衡。在第三集的地下倉庫著火事件中,五名消防隊員的犧牲便是從警員段瑞波的個人日記與現場采訪中展開。首先,開場便是個人采訪:“我很少和人提起這件事情,我回隊之后聽隊長說,人沒了,去醫院人就沒了,沒搶救過來。”在自敘的過程中,現場畫面與個人采訪相互配合,打破線性的敘述方式,但在人物刻畫上并不局限于采訪與現場資料,而是在表現影像的同時,加入日記中的現場描述:“傅仁超和張曉凱當場就犧牲了,杜建華和萬金柏他們還能說話,我們隊的趙子龍被夾在離著火點更近的一塊石板下”“他們喊我去休息,我停不下來,不是不累,就是停不下來,真的停不下來”。紀錄影像無法展現人物內心所想,即使在個人采訪時面對鏡頭也會有所隱藏,而寫日記的方式不僅補充了現場無法觸摸到的內心真實,甚至能使觀眾通過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文字產生內心深處的共鳴,真正抵達人物內心所深藏的“無法言說的情感”,觀眾也可從日記中感受對逝去人物的思念與敢于犧牲的強大崇高精神。這種塑造方式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義。除了寫日記的形式外,消防員每年的默哀鮮花儀式、當年現場受難居民感人肺腑的致謝、對犧牲警員舊照片的重溫,不斷深化著消防員在觀眾心中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觸動觀眾的淚腺和神經,在熒屏前潸然淚下,喚醒其對消防員形象的崇高敬意。因此,要打破舍己為人的英雄形象塑造的敘事常規,只有尋求撼人心魄的角度,豐富故事的敘事模式,才會讓觀眾體察到悲劇人物所“悲”的內核。
(二)情感場域:鐵漢柔情的家庭守護者
往常,警務題材類的電視節目對警務人員“血氣方剛”單一性格的展現,不斷培養著觀眾對警務人員的片面化認知。過多片面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將會不斷地擴大涵化效果,致使消防員形象在大眾視野中淪為不斷被“他塑”的客體,失去個性角色的能動性。對消防員工作空間外的展現,是亟待改善大眾刻板認知的重要方式。節目對消防員的角色塑造是一個不斷“外延”的過程,他們不僅是火場上的好兄弟,還是妻子的丈夫、爸媽的兒子、爺爺奶奶的孫子等,其角色外延的表現也是讓消防員在這個與大眾有所區別的角色中尋求共性,在兄弟、丈夫、兒子等角色中回歸大眾生活,從溫情至深的敘事中尋求共鳴。在第二集老人被困的事件中,消防員姚潤便說道:“我現在出警看到一些老人,容易聯想到自己的家人,我的爺爺奶奶從小把我帶大,想找個時間回去穿上制服給他們看一下,看到我最帥的一面。”在姚潤自述的過程中,其身份的轉變讓案件也多了一絲溫情,觀眾從中也感受到他作為爺爺奶奶的孫子,因職業特性無法常回家的無奈。在第五集中,消防員阮洋洋的兒子來到消防站陪伴他。在一起游戲的過程中,警情突然發生,阮洋洋立刻放下手中的玩具離開,而在出警的路上卻懊悔不已。兩小時后,他回到警署,孩子已經睡著,愧疚不已的阮洋洋為孩子蓋上被子。節目在阮洋洋從消防員到丈夫的角色轉變中,延伸出了一名父親的無奈,觀眾在體會到消防員別無選擇的同時,看到的是他們為大家舍小家的崇高精神,也感受到了硬漢職業背后的細膩情感。在第六集最后,過年期間無法回家的消防員陸續收到親人們寄來的祝福,錚錚鐵骨的消防員陸陸續續地偷偷抹著眼淚,集體影像的展現更是讓情感值達到頂峰。可見,對角色固定身份外的挖掘是破除角色固定認知的有效途徑,也是讓紀錄片情感回歸大眾的有效手段。
三、結語
警務類紀錄片是警務形象傳播的絕佳載體,在熒屏空間中為大眾塑造可信賴、可崇拜、可學習的對象。但在傳統的紀錄片中,過重的宣教性不斷拉遠著其與大眾的距離,在深化受眾認知的過程中偏離紀錄片審美性的基礎。《119 請回答》通過多元素結合的敘事、多角度的形象塑造,很好地把握了人民對消防員熒屏形象塑造的要求,構建著有情懷、夠溫暖、接地氣的形象,對于推動社會秩序的穩定前進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注釋:
①[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羅蘭·巴爾特文集)[M].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68-72.
②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第二版)[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33-36.
③韓瑩.警務系列紀錄片中的敘事創新——以東方衛視《巡邏現場實錄2018》為例[J].中國電視,2019(05):43-46.
④陳儒,張新陽.探析警務觀察類紀錄片對警察職業形象的塑造[J].當代電視,2021(07):88-91.
⑤王玉瑋.中國當代電視藝術中的崇高美[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6):6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