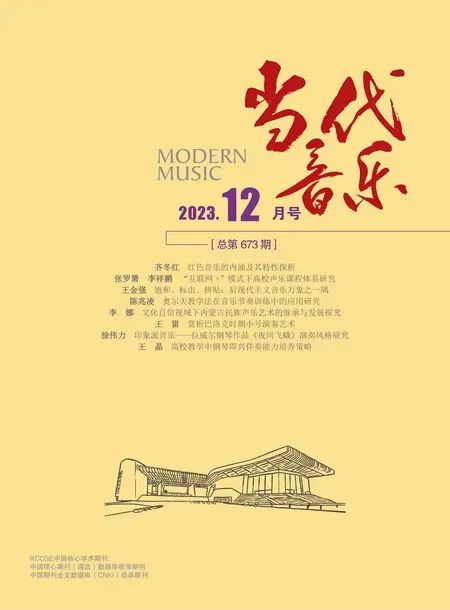淺談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獨特性
齊慧麟
在對中國民族民間舞學習的過程中, 筆者對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有莫大的興趣, 由此促使筆者對在當代背景下創作的民族民間舞蹈有所學習與研究, 發現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所具有的“獨特性”。 為此, 筆者對“獨特性”進行了深度的研究, 目的是日后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的編創中能夠更準確地把握其不同于其他舞種的特點。
在現當代背景下,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節目層出不窮, 優秀的作品日益增多。 但是, 如何評價原創作品的創作價值以及作品的優秀程度, 這基于中國民族民間舞特有的民族屬性、 風格特點以及動律、 體態特征, 也就是筆者所說的“獨特性”。 在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過程中, 編導通過對民族屬性、 風格特點、 動律、 體態特征的整體把握,再加上對其民族民俗習慣、 風土人情的理解進行創作加工,從而創作出完整且優秀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一、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原有的“獨特性”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 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背景, 因此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也有著它一定的 “獨特性”。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的獨特性與當地人們的生活習慣、性格特點、 體態特征、 民俗習慣、 風俗習慣以及地勢地域、經濟水平、 文化背景等一系列情況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是人民群眾集體創作的成果, 從群眾中來, 又回到群眾中去, 它是人民群眾情感的體現, 它的形式以及風格特點都是由一個民族的信仰、 精神、 審美意識所賦予的。 就同是漢族舞蹈的安徽花鼓燈與山東鼓子秧歌來說, 安徽花鼓燈舞蹈要求“溜得起, 剎得住” “緊收、 積蓄、 突射” 當中有“扭、 晃、 顫、 顛、 抖” 等靈活多變的舞姿, 舞動起來靈活、 輕快、 調皮。 而山東鼓子秧歌舞蹈要求“穩、 沉、 抻、 韌”, 體現了山東大漢似泰山般偉岸的形象特征, 舞動起來奔放不羈、 氣勢磅礴, 形成了一種粗獷豪邁、 英武矯健的形象與風格特點。 由此可以看出, 地域不同、 文化不同, 兩地群眾的性格與體態不同, 從而衍生出來的民族民間舞蹈也有著不同之處。 也正是因為這樣,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具有“獨特性”。
二、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的分類
筆者對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進行深度學習與研究后,發現其在如今的舞蹈發展中, 出現了很多以不同種類、 不同形式來表現的作品。 對如今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進行分類后, 筆者總結出以下幾類: 一是傳統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二是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在創作民族民間舞蹈作品中又分接近傳統類與脫離傳統類; 三是旅游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筆者這里指的旅游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也就是當地旅游業所做的實景演出; 四是專業類與業余類。筆者在此將傳統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與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進行分析。
(一) 傳統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說到傳統類民族民間舞作品, 筆者第一時間聯想到了由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系所舉辦的兩臺專場晚會,即“沉香·一” “沉香·二”。 這兩臺晚會里的作品均可稱之為“傳統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編導下鄉采風, 與當地群眾進行交流與觀察, 參加當地的風俗禮儀, 跟隨當地藝人學習當地純正的舞蹈動作。 對當地所聞、 所學、 所見, 進行歸納, 不添加任何的藝術創作與加工, 將當地群眾的民俗習慣、 風土人情、 體態特征以及動作的風格特點、 動律特征、 民族屬性原汁原味地搬上舞臺。 例如, “沉香·二”當中的“鈴鐺舞”, 它歸屬于彝族舞蹈, 俗稱“跳腳”, 彝語又稱“懇合唄”, 是彝族人民在祭祀時所跳的一種傳統民間舞蹈。 也有人說, 彝族先民在兵荒馬亂的戰爭時期, 領頭人為了能夠使將士們安心, 故籌建了歌舞隊, 將馬鈴在手中有節奏地搖響, 同時伴著詞曲, 以此鼓舞士氣, 穩定軍心, 同時也為犧牲親人而送行。 編導將其純正的歌舞搬上了舞臺, 將其固有的形式搬上了舞臺, 將其歷史的背景搬上了舞臺。
(二) 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說到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筆者第一時間聯想到了繼“沉香·一” “沉香·二” 之后, 由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研究基地所舉辦的“沉香·三”, 以及一系列由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系舉辦的“大美不言” 舞蹈專場。 筆者這里列舉的“沉香· 三” 中的作品就是前面所說的接近傳統類的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編導會在其創作的作品中融入當地民族所固有的民族民間舞蹈動作以及動作套路。 而“大美不言” 中的作品則是前面所說的脫離傳統類的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 編導將當地民族所固有的民間舞蹈以及動作套路打破, 在其風格動律上進行創作與編排。 接近傳統類的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與脫離傳統類的創作類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又有著不可置疑的共同性, 作品都是在傳統民族民間舞蹈與文化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創作與加工的。 編導將在當地所聞、 所學、 所見進行歸納后, 加以藝術創作與加工, 以及編導對當地的民俗習慣、 風土人情的理解, 和對當地舞蹈動作的風格特點、動律特征、 民族屬性的掌握, 從而進行故事的發展和動作的編排。 這里用高度老師所說的一句話“我們依照傳統模樣的東西, 做了無數種新的樣子”。
三、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創作的“獨特性”
(一)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創作的“獨特性” 的概念
所謂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獨特性”, 就是創作者將傳統的民族民間舞蹈素材, 如民族屬性、 風格特點、 動律特征、 體態特性、 民俗習慣、 風土人情, 在其創作的作品中建立創作者獨特的敘述方式。
民族屬性、 風格特點、 動律特征、 體態特性、 民俗習慣、 風土人情都可歸到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的“獨特性” 之中, 編導在其固有的“獨特性” 的基礎上加以自身的理解,從民族民間舞蹈的創作內容、 事件典故、 人情世故、 風土人情等方面進行對比后達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然后進行實際操作, 選擇將民族的“獨特性” 融入作品之中, 進行編創與創新, 從而體現了編導自身的“獨特性”, 同時也展現了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創作的“獨特性”。
(二) 作品舉例
高度老師創作的膠州秧歌舞蹈作品《一片綠葉》, 是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作品中的經典劇目之一, 劇目以膠州秧歌為基本動作元素, 在形式上、 動作上、 音樂上、 節奏上大膽創新與突破, 使得膠州秧歌在這里脫俗求雅, 蘊含著現代氣息。 形式上, 編導以“扇子” 代表“綠葉”, 開頭扇子從頭上掉落在地, 便意味著綠葉的凋落, 從此展開故事發展。 動作上, 編導運用膠州秧歌里的“8 字繞扇” “胸前抱扇” “推扇” “碾步” 等動作, 抓住“扭” 與“擰” 的動作特點, 刻畫出綠葉的嬌嫩與女子的柔弱。 同時, 編導將現代舞的動作呼吸和發力方式與膠州秧歌的動作元素相融合, 在動作力度上、 幅度上加大對比, 使動作松弛有度、流暢自如, 打破了傳統的套路性動作。 音樂上, 編導用了“交響樂” 的形式, 將交響樂的表現形式與民族樂曲融合。節奏上, 編導將整合的八拍打破, 在復拍上下了不少功夫,許多小味道便從這里出來。 筆者在與高度老師學習時, 經常聽到“這樣做, 是你做的。 要是換我做, 我肯定不這樣做”。 可以看出高度老師自身的“獨特性”, 正是這樣, 《一片綠葉》 的“獨特性” 才那么明顯。
楊麗萍老師創作的傣族舞蹈作品《雀之靈》, 也是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作品中的經典劇目, 楊麗萍老師通過對孔雀的仔細觀察, 模仿孔雀“迎風而立” “展翅高飛” 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動作, 將其與傣族舞蹈獨特的動律特點相融合, 加以編創。 同時, 還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突破, 筆者認為可以形容為更具個性化、 更具現代化、 更具圖像化。 她大膽地打破傳統, 吸收了現代舞能夠充分發揮舞者肢體能動性的優點, 創造出新的動作語匯。 在《雀之靈》 開頭,用“孔雀手” 直觀地表現出孔雀的形象, 以及將身體的各個關節都賦予節奏化, 造型變化各異, 表現出孔雀的機敏、靈活跟高潔。 這些動作源于傳統, 卻又別于傳統和體現了編導與《雀之靈》 本身的“獨特性”。
查龍浩老師創作的土家族舞蹈作品《喪俚調》, 該作品是筆者參加第13 屆首爾國際舞蹈大賽的節目, 并獲得民族創作青年組第二名, 以及文中提到的專場晚會“沉香·三”中的節目之一。 作品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土家族舞蹈的“跳喪舞” 為動作元素進行編創, 作品中主抓“跳喪舞” 的典型動作, 如八字步、 繞手、 哈腰、 屈膝、 擺胯等。 同時, 編導考慮到故事發展的延續性, 為了能夠讓人物形象更加鮮明, 更加貼切“跳喪” 這個題材,于是選擇了一個能感受到逝者存在的人物, 俗稱 “通靈人”, 用這樣一個在舞臺上少有的人物形象來敘述整支舞蹈。 還加入了使人物形象更為凸顯的形象動作, 如“仿佛聽見” “扶地聽聲” “瘋癲抽搐” 等。 筆者認為最值得一提的是, 編導用獨舞演員展現跳喪舞二人對跳的傳統動作,強烈地體現了劇中人物精神狀態恍惚, 不相信親人已逝去的事實。 同時又在其傳統的基礎上, 進行了形式上的創作,展現了作品《喪俚調》 別具一格的“獨特性”。
筆者認為,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的“獨特性”, 是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局限性”, 但正是因為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有了這些“局限性”, 所以才使得中國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富有“獨特性”。 因此, 創作中的局限性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轉化為獨特性, 它們是可以相互存在的。 那么中國民族民間舞的創作相較于其他舞種而言, 它更要遵循其體系, 其在動作、 音樂、 題材上會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現當代背景下,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創作多少會受時代所影響, 近些年有不少現代藏族、 蒙古族舞蹈作品都融入了當代背景下現代舞的意識與動作。 人們之所以能看出劇目所屬民族, 是因為編導充分把握其獨特性, 而不是被其局限。 我們既要在創作上打破局限性, 不斷創新, 也要運用舞蹈的“局限性” 來進行創作創編, 所以抓住各民族民間舞蹈的獨特性, 是民族民間舞蹈創作的本質。
結語
我們可以發現,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具有風格性與獨特性, 地域的不同導致風格的不同。 舞蹈編導對其進行學習與體驗后進行創作與加工, 抓住民族文化的特性, 充分地展現當地的民俗文化、 生活習性, 又將當地舞蹈的風格特點、 動律特點、 性格特點融入在作品之中。 編導為了保證風格準確、 主題貼切, 往往會選擇親身體驗, 扎根于當地,了解當地文化, 體驗當地風俗, 觀察當地人們的習慣, 學習當地民族的原生態動作, 為的是在創作劇目時能夠更準確地展現當地民族、 民俗文化, 以及當地人們的性格、 動作特點, 在這種“局限性” 下編出來的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具有筆者所說的“獨特性”。
民族的藝術就是世界的藝術, 將中國民族民間舞推向世界, 需要我們抓住其獨特, 突破其局限, 不斷開拓創新,發展具有本民族特色、 有文化烙印的民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