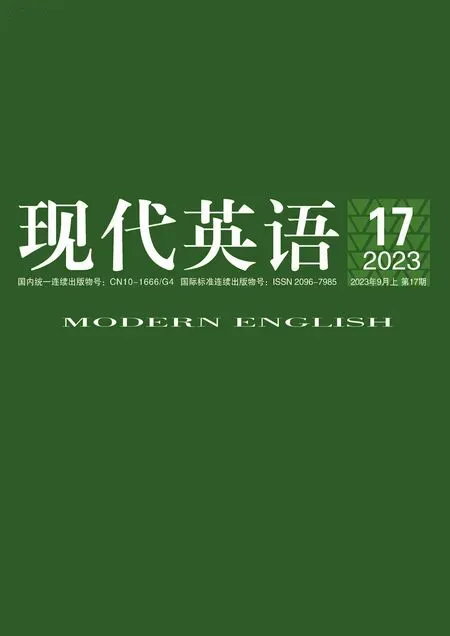翻譯課程“翻譯+領域知識+技術”分層教學模式初探
張志云 胡英花
(燕山大學,河北 秦皇島 066004)
隨著中國改革開發的不斷深入和全民英語水平的持續提高,中國社會對英語運用能力的需求也不斷升級,傳統意義上的翻譯亟待被“重新定義”[1],步入以語言為基礎、以數據和技術為驅動[2]、以“服務各行業”為主要內容的“語言服務”時代。 楊丹更是進一步指出,即便是整個中國外語教育,也需轉向“外語服務”[3]。 為應對“語言服務轉向”的挑戰,翻譯專業畢業生不能只做外國人的陪聊,而應作為價值鏈的一環服務于特定行業、機構、項目[4]。 正如蔡基剛所言,“只有皮皮(即翻譯技能)沒有內核(即領域知識)的翻譯畢業生是無法滿足社會和國家需要的[5]”。
在此背景下,文章對翻譯專業筆譯課程與大學英語翻譯拓展課的課程內容進行改造和對接,開展大致相同的翻譯課程項目,介紹一體化、層級化、差異化的翻譯技術和語言信息技術,通過翻譯能力前測后測、學生問卷、翻譯過程錄屏、翻譯成果教師交叉評價、學習過程和效果問卷,探索“語言+領域知識+技術”分層教學的可行性、模式和效果。 探索“翻譯+語言+領域知識+技術”模式下的教學改革路徑,符合新時代語言服務行業和外語教育的現實需求,直擊大學英語教學和翻譯專業教學的痛點,教改成果有望改變外語專業學生“僅能做外國人陪聊”的窘境,也有望改善大學英語課程“因與學生專業和職業需求脫節而被認為無用,且因高投入、低效率而面臨減課時或被取消風險”的尷尬地位。
一、 研究現狀
在“翻譯+領域知識”方面,崔啟亮在?全國MTI教育與就業調查報告?中指出,用人單位對MTI 學生提出的建議中,“最關注的兩條是提高責任心、加強專業知識學習”[6]。 翻譯碩士尚且如此,遑論翻譯專業本科生(大部分也是畢業直接面向就業市場)。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索翻譯與專業領域知識的融合方式,以提高本科生的專業領域翻譯能力。在“翻譯+技術”方面,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基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的機器翻譯和大語言模型取得顛覆性進展,傳統翻譯之外出現了不少新業務、新職位和新模式[7]。 另外,根據王華樹等對218 家中國語言服務企業的調研,大多數受訪企業普遍通過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CAT)調用機器翻譯并進行譯后編輯[8]。 因此,未來的譯員不懂技術將寸步難行。 但是,目前國內培養碩士層次“翻譯+技術”復合型人才的高校僅有北京語言大學、西安外國語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三家,本科階段只有北京語言大學在翻譯本科專業(本地化方向)專門培養“翻譯+技術”復合型人才[9]。 同時,肖維青等[10]推斷,翻譯本科專業開設翻譯技術類課程的比例很可能不太理想。 在“翻譯+領域知識+技術”方面,根據中國翻譯協會近年來的行業報告,翻譯技能與領域知識和翻譯技術的融合已成為行業的需求和共識,但是目前還沒有相關的教學改革實踐研究成果。
同時,因我國的翻譯教學在多個層次開展、面向不同的受眾、需滿足不同的需求,一體化、差異化、層級化的翻譯教學非常有必要。 以翻譯技術教學為例,開展分層教學的必要性如下:①本碩階段均設有翻譯技術課程,且本科階段的目標學生除翻譯專業學生外還包括英語專業學生及其他專業學生,培養目標和職業需求不同,只有差異化、層級化的教學才能有效銜接、避免重復;②同一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所需處理的翻譯任務的復雜程度也不一樣,翻譯技術滿足特定階段的翻譯任務需求即可;③譯員不可能總是在理想辦公環境下做翻譯,而必須在現實的硬件網絡條件下根據翻譯項目需求選擇合適的翻譯技術。 但是,除江杰[11]提出翻譯技術分層培養的建議和初步思路外,沒有檢索到其他關于翻譯技術分層教學的研究。
二、 研究設計及實施
(一)研究思路
文章對翻譯專業筆譯課程與大學英語拓展課的課程內容進行改造和對接,開展大致相同的翻譯教學和課程項目,介紹必備的翻譯技術和語言信息技術,通過翻譯能力前測后測、學生問卷、翻譯過程錄屏、翻譯成果教師交叉評價、學習過程和效果問卷,探索翻譯專業學生和其他專業學生在通用型實用翻譯、入門級專業翻譯項目過程中體現出的起始能力構成、翻譯策略和翻譯效果差異,并召集優秀學生志愿者進行實驗,探索通過合作進行專業翻譯的可行性、效果和方式。
(二)研究步驟
1. 前測
在每個模塊均進行相同內容和時限的課堂翻譯測試,難度為四級難度,旨在檢測學生在翻譯項目實施之前的語言能力和翻譯能力,分析學生的知識和能力結構,以便設計有針對性的翻譯教學方案,并與后測結果進行對比以檢測教學效果。
2. 課程對接和翻譯技術差異化分層教學
如表1 所示,文章針對翻譯本科專業學生和非翻譯本科專業學生兩類學生,設置3 個課程對照模塊,探索不同學生群體在通用型翻譯(語言基礎)、專業領域翻譯(語言與文科專業相融)和專業領域翻譯(語言與理科專業相融)方面的差異和可行性。

表1 翻譯課程對接
課程內容(均為第四學期開始開設)對接后,教師根據不同學生群體的水平和需求教授差異化、層級化的翻譯技術,開展大致相同的翻譯教學和課程項目,通過翻譯能力前測后測、測后問卷、翻譯過程錄屏、翻譯成果交叉評價、學習過程和效果問卷,研究兩類學生在通用型翻譯方面的起始能力構成、翻譯策略和翻譯效果差異。
在翻譯技術的差異化分層教學方面,針對語言類學生的領域知識短板和非語言類學生的語言技能短板,分別以翻譯技術(解決領域知識問題)和語言信息技術(解決語言問題)為重點和突破口,每個技術模塊都盡量包含傻瓜版、簡化版、高級版、專業版的工具庫,供不同水平學生根據具體情況自主選擇。
3. 教學持續改進
所有課程都實行項目式翻譯教學,并按如下步驟進行持續改進:①根據本輪課程的前測結果分析學生的知識能力構成,并結合上輪課程總結出的經驗教訓,根據學生情況定制項目式教學方案;②按照業界的標準流程實施翻譯項目;③根據項目結果和過程反饋,總結經驗教訓,并用于指導下次項目方案的改進。
4. 后測
后測方法如表2 所示,后測1 用以測試翻譯技能和語言信息技術方面的教學效果,后測2 測試翻譯技術用于專業領域翻譯的教學效果:

表2 前測后測示意表
三、 研究結果及討論分析
(一)前測、后測結果及分析
1. 總體數據及分析
課題組共回收132 份有效學生教學效果反饋問卷(SPSS 克隆巴赫α 系數為0.87),共有113 位同學認為課程內容對后續英語和翻譯學習非常或比較有用,59 位已畢業且崗位與外語相關的受訪者中有55位認為課程對所從事工作有用或非常有用,問卷結果證明了本教學模式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另外,三門課程的后測1 成績均比前測成績實現不同程度的提升,有的課程平均提分7 分,學生單體提高最高為15 分,說明學生在使用各種技術助力翻譯技能提升方面取得顯著成效。 三門課程的后測2 的平均得分最低為76 分、最高為83 分,完成度分別為76%、83%(客戶無需修改直接采用為100%完成度)均高于機器翻譯40%的完成度,說明學生通過相關技術的學習和使用能夠完成“能用”“夠用”的技術翻譯。 同時,課題組對三門課程的測試成績做了后測1 結果(翻譯技能提升)和后測2 結果(跨領域翻譯完成度)的相關性分析,發現相關性幾乎為0,說明掌握通用翻譯技能不代表就能進行專業翻譯,需要在傳統翻譯教學的基礎上加強專業領域翻譯訓練。 此外,課題組還分析了后測1 結果(翻譯技能提升程度)與前測1 結果(學生語言基礎)的相關度,發現二者呈現比較顯著的負相關,說明語言基礎好的學生利用技術實現翻譯技能提升的空間相對較少。 但是,?基礎筆譯?課程的負相關系數更低,說明如果在課程中引入比較高階的翻譯技術和翻譯理念,學生的翻譯技能提升會更大。
2. 分專業數據及分析
通過分析囊括不同專業類型學生的?實戰翻譯?課程的前后測成績,課題組發現比較明顯的幾條規律:
(1)在翻譯技能提升方面,中文專業(前測成績最低)的提升最高,然后是其他文科專業(前測成績最高)。 可能的原因是,這些專業在原文理解方面的能力要高于其他同學。 這是翻譯技術或人工智能工具迄今無法完全替代的優勢,應該作為翻譯課程教學的一個重點。
(2)前測成績較高的小語種專業和英語專業(平均成績分別為眾專業的第2 名和第3 名),實現的翻譯技能提升最小,可能因為外語類專業學生的中文理解能力較差。 還可能因為,這些專業的學生本身都有翻譯課程,他們對翻譯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且難以接受與現代翻譯理念緊密相關的翻譯技術。 因此,這三面均亟待加強。
(3)在跨領域翻譯方面,2023 年春?實戰翻譯?理工類專業學生的完成度最高,為84.25%,說明學生的專業相近程度與跨領域翻譯能力的相關度很大。 但是同為理工背景的學生,2023 年春?實用翻譯基礎?(翻譯技術模塊的課時較少)學生的完成度要低很多,只為76%,甚至低于同期的?基礎筆譯(漢譯英)?。 這說明在跨領域翻譯能力方面,充分翻譯技術訓練的相關度要高于專業相近程度。
四、 結論
在網絡信息技術突飛迅猛的今天,一般的知識在網絡上唾手可得,大大降低了領域知識的門檻,基于語料庫、大數據和大語言模型的諸多語言輔助工具也可以生成相當于英語母語本科畢業水平的文章,語言的壁壘也微乎其微。 因此,可將技術作為跨越“知識”“語言”壁壘的突破口,使用語言技術助力專業人士跨越語言障礙,使用翻譯技術助力語言背景人士跨越領域知識壁壘,可有效實現“語言+領域+技術”,并實現外語教育的“語言服務轉向”。 當然,針對兩類不同的學生受眾,技術教學也應該實現差異化、一體化、層級化的量身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