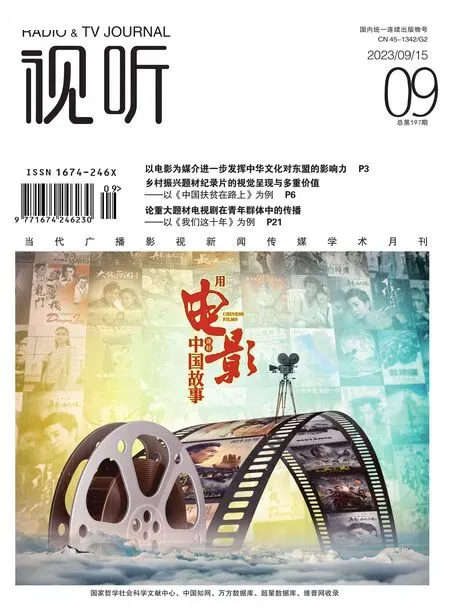鄉村振興題材紀錄片的視覺呈現與多重價值
——以《中國扶貧在路上》為例
◎馮笑
從打贏脫貧攻堅戰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新時代的中國正在描繪更加美好的時代畫卷。近年來,以鄉村振興為母題展開的藝術創作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文藝光譜中的一抹亮色。人們欣喜地看到,鄉村振興題材紀錄片作為極具藝術魅力與社會價值的影像形式,在新時代的創作需求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生產傳播態勢。此類紀錄片嫻熟地運用紀實主義的美學手法,捕捉呈現鄉村振興背景下最為真實可感的社會變遷,贏得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與廣泛贊譽。其中,由人民日報社出品的三集紀錄片《中國扶貧在路上》正是典型代表。該片攝制組耗時3 年,行程46000 多公里,采集1300 多個鄉村振興故事,終將產業振興、生態振興、教育振興等政策方針及數據成果轉化為鮮活生動的影像語言并娓娓道來,使觀眾得以從鄉村振興敘事中感受到潺潺流淌的辛勤奉獻與熱烈渴望。
一、鄉村形象:縱橫交錯的再現理路
攝影本身具有客觀真實的紀實屬性,但由此創作出的紀錄片卻并非現實生活的簡單復刻,而是體現為一種選擇性再現。創作者基于自身對再現對象的理解感知,將其認為“有意味”的影像片段從既有邏輯順序與敘事語境中抽離并進行二次組合與裝配,由此產生的新文本將不可避免地刻上其價值追求與審美旨趣的鮮明烙印。正因如此,探析鄉村在不同階段所呈現出的景觀特征和鄉民在媒介再現過程中的形象特點成為研究此類紀錄片的首要命題,兩者一縱一橫構成了鄉村振興的故事脈絡。
(一)傳承與超越的鄉村圖景
《中國扶貧在路上》集中再現了我國鄉村脫貧前、脫貧中和脫貧后三個階段的生存圖景,詳細剖析了跨越式發展背后的深層肌理。對于脫貧前的鄉村而言,閉塞與落后是其首要特征。一方面,攝制組大量使用全景鏡頭將重疊山脈、陡峭鄉路、殘破村落納入畫面,向觀眾直觀再現了彼時我國落后地區鄉村的真實面貌。另一方面,時常閃現的特寫鏡頭又為此添加了諸多細節真實作為注腳,布滿傷痕的雙手、滿是補丁的衣物、吱呀作響的窗欞等無不令人觸目感懷。
對于脫貧中的村莊而言,震蕩與覺醒成為紀錄片視覺再現的主題。一方面,為了改變閉塞與落后的面貌,強化“村莊單元”及城鄉之間的內外關聯,交通扶貧成為幫助許多落后鄉村擺脫貧困的不二選擇。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幫扶與引導下,新思維、新技術和新動力亦紛至沓來,鄉民愈發意識到單純依賴土地產出很難實現脫貧致富,唯有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方為有效路徑。于是,我們在紀錄片中看到了十八洞村盤山而建的鄉村公路、鄉民創辦的苗繡文化產業以及蓬勃發展中的特色旅游事業。在航拍視角下,一條條嶄新的通道猶如彩帶將城市與鄉村緊密聯結,曾經的地理枷鎖被徹底打破,拔地而起的現代產業建筑也使鄉村面貌煥然一新,種種視覺符號都昭示著脫貧致富、全面小康的大門即將訇然洞開。
隨著振興舉措的全面鋪開,現代化的居住、生產景觀成為脫貧后鄉村地理空間與生存環境再現的重點,其視覺特征突出表現為傳承與發展。傳承體現在鄉村聚落的歷史文化、民族習俗與現代化的社會生活實現了有機融合。日瓦鄉的藏式旅館、南強村的南洋風建筑、排莫村的傳統蠟染工藝等眾多具有珍貴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的特色象征符號既是各村落形塑自身“異質性”的主要文化標識,也成為折射各鄉村在脫貧攻堅道路上獲得跨越式成果的重要視覺表征。發展體現為鄉民們因地制宜建立的特色旅游、種植、畜牧等產業正逐步走向成熟并形成合力,由此獲得的不僅是擺脫貧困的切實路徑,更是邁向美好未來的持續動力。從原生態的自然景觀到鄉村日常的生活勞作景觀,現代化的元素不斷注入,鄉村的價值與意義也隨之更迭。它不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單位,而是成為一個社會文化單位,其寧靜質樸的特性、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都將在鄉村脫貧與振興語境中得到進一步凸顯。
(二)碰撞與變革中的鄉民形象
法國鄉村社會學家孟德拉斯曾提出“農民的終結”一說,并指出“這并不意味著農業的終結或鄉村社會的終結,而是從傳統小農到農業生產者的變遷,是一次巨大的社會變革”。《中國扶貧在路上》正是敏銳捕捉到了鄉村社會在振興背景下孕育著的歷史性變革,借由對新老兩代鄉民命運軌跡與心路歷程的細致描摹,將其生動真實地呈現在觀眾面前。
在我國源遠流長的歷史進程中,鄉民對于土地始終葆有著別樣的情愫。老一輩的傳統鄉民往往將土地視為賴以生存的根基,堅信通過自身辛勤耕種所創造的財富才是最可靠的,所收獲的累累碩果也將充分證明自我價值、贏得他人尊重。紀錄片中,傳統鄉民質樸勤懇的形象特征正是通過他們對這方土地的執著堅守而得以直觀呈現的。如第二集《扶貧智慧》中所記錄的鄉民鄭志龍,年逾七旬的他是種了一輩子酥梨的老把式,而在因病致貧后更是將酥梨種植視為擺脫困境的“法寶”而愈發精心照料。片中多次記錄了以鄭志龍為代表的傳統鄉民在田間勞作的真實場景,這既是對鄉民形象客觀性的有力佐證,也深刻折射出鄉民對脫貧致富的迫切渴望。與傳統鄉民不同,新生代鄉民的戀“土”情結更多指向他們對家鄉的眷戀,而非對土地本身的信仰。正如片中所展現的那樣,新生代鄉民普遍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掌握當下時興的概念與技術,逐步擺脫了傳統小農意識的束縛。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他們剝離了農民的身份屬性而回歸職業屬性,以新型職業農民的形象出現在鏡頭前,成為現代農業理念與技術的承接者與傳播者。例如第三集《志啟未來》中的四川省廣元市青川縣女孩趙海伶,她選擇在大學畢業后回鄉建設家鄉,在推廣新農業技術的同時,又以品牌營銷的方式將家鄉特產蜂蜜與野生菌由互聯網推向全國,帶動了當地眾多農戶增收脫貧,實現了自主創業與脫貧攻堅的深度契合。
二、敘事結構:同條共貫的時空流動
紀錄片并非若干片段的簡單羅列與集合,行動話語、戲劇沖突等元素遵循著特定的結構邏輯而交織成融洽有序的影像故事,其魅力來源于對現實生活的客觀記錄和對紛繁素材的選擇講述。《中國扶貧在路上》以鄉村振興為表現對象,從上千件素材中擇取21 個典型對象并連綴成篇,形成“在路上”的時空流動特征。
(一)個體影像共筑社會記憶
面對鄉村振興這一歷史性時刻,《中國扶貧在路上》的創作者并未拘囿于對恢宏歷史圖景的鋪排,而是更多將鏡頭聚焦于脫貧道路上的微觀個體,使宏觀抽象的政策數據具象化為鮮活可感的人物故事,從而有效構建起個體敘事與國家形象書寫之間的內在聯系。片中出現的具體人物、環境等細節的真實不僅構成了整體真實的基礎,也“在藝術與觀眾生活形態之間營造了一種‘同形同構’的邏輯關系”①,使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不自覺地代入規定情境,架構起相應的話語認同。
《中國扶貧在路上》開篇便以記者王紹據36年前向人民日報投遞的一篇反映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貧困狀況的報道為由,引出了“中國扶貧第一村”華麗嬗變背后的感人故事。從投稿前的忐忑不安到報道后引發全國反響,從早期的“輸血式”救濟到后來的“造血式”扶貧,觀眾透過王紹據的微觀視角見證了我國脫貧攻堅工作拉開序幕的歷史性時刻,感受到了以赤溪村為代表的鄉村聚落在脫貧前后的滄桑巨變,更深刻領會了扶貧工作一路走來的艱辛不易與必勝信念。而對于搬遷后就業、鄰里鄉情等常見顧慮,在片中也是由海國寶以回憶的形式提出,再以其自身生存現狀予以回應,一問一答間道出了中國扶貧智慧。此類敘事方式在紀錄片后續仍頻頻出現。更為可貴的是,創作者并未流連于對視覺奇觀的塑造,而是將著墨重點置于對鄉民們在脫貧致富道路上揮灑汗水的贊揚、對其不斷覺醒的脫貧意識的肯定和在成功脫貧后美好生活圖景的呈現,從而賦予了紀錄片貼近生活的煙火氣息與濃厚的鄉土人情。
(二)沖突敘事還原跌宕情節
《中國扶貧在路上》中鄉村聚落的致貧原因往往大相徑庭,其脫貧致富的途徑也因人、因地而異。創作者秉持求同存異的敘事理性,深挖差異背后共通的語義句法,以戲劇沖突為交匯點,還原出一幕幕自我救贖與他者相助共同交織的跌宕情節。
在自我救贖的敘事邏輯中,鄉民與所處的惡劣環境形成二元對立,這種對立體現為一種外在的、單向度的矛盾沖突形式,人物形象與環境形態的兩極化描寫構成了矛盾沖突的性格與存在基礎。而“惡劣環境”則既指先天形成的自然環境,如坐落在中緬邊陲的云南省滄原縣芒擺村,其高海拔地貌使得以陳云為代表的當地鄉民終日勞作卻難獲溫飽,也包括后天遭遇的多舛命運,如19 歲因病失明的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青年楊躍志。在這樣的沖突對立中,鄉民們直面苦難、借勢脫貧的奮斗事跡成為刻畫人物、推動敘事的核心力量。
在他者相助的故事模式里,扶貧者的先進理念與鄉民的局限思維形成了強烈對比。這種內在的、多向度的矛盾沖突本就不易解決,扶貧者們“外來人”的身份標簽也令轉變進程更為曲折,但汗水和真情終將換得鄉民們的信任與支持。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扶貧干部劉泉善用媒體力量,通過“榮譽校長”模式吸引多方社會資源注入到當地基礎教育事業中;河南省商丘市虞城縣韋店集村第一書記時圣宇用3個月時間跑遍8個自然村落展開實地調研,利用扶貧小額信貸政策幫助鄉民建立起蔬菜大棚基地、蛋鴨養殖合作社等現代農業設施。正是在鄉民們的笑容與贊許中,扶貧干部們實現了從“外來人”到“自己人”的身份轉換。
一方面,影片給予了矛盾沖突以充裕的鋪展空間,展示了鄉村在脫貧前夕積聚的變革偉力與致富之后生活的喜悅場景,因而飽含情感溫度與現實銳度。另一方面,創作者通過對人物刻畫、敘事節奏的精準把握,將宏觀的時代主題與價值理念巧妙隱匿于客觀鏡頭中,“既有效避免了宏大敘事和人物的概念化,又能通過具象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為抽象價值觀的導入和弘揚打下堅實基礎”②,實現了現實主義題材與紀實主義美學的雙峰并秀。
三、多重價值:傳遞民聲的影像信函
作為大眾媒介的紀錄片因其直觀性與普適性的影視語言而具備了跨越地理區域、打破文化區隔的傳播優勢,所承載的信息理念也得以通過“影像信函”的方式無遠弗屆地向社會各界傳遞。《中國扶貧在路上》從人本視角出發,立足時代、扎根基層,真實記錄與呈現了我國諸多鄉村完成脫貧攻堅的感人事跡,為這一宏大歷史變遷留下了極具社會價值、審美意味與精神感召的影視注腳,具有難能可貴的范本意義。
(一)針對脫貧攻堅成果的可視呈現
在鄉村振興駛入“深水區”的關鍵時刻,挑戰與難度與日俱增。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紀錄片《中國扶貧在路上》對既有脫貧成果和攻堅路徑的記錄歸納與可視化呈現無疑具有繼往開來的重要現實價值。
一方面,紀錄片從物質生活與精神價值兩個維度展開了對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形象的深度掃描,鄉民們生產方式的轉變、居住環境的改觀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思想觀念變革、鄉土文化傳承等多層次信息都被完整真實地呈現在觀眾面前,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思考當今鄉土中國的直觀窗口。而另一方面,對于我國扶貧道路上所遇到的自然環境惡劣、基礎設施落后、小農生存倫理抵抗等諸多現實困境,創作者也予以細致歸納,并借鄉民或扶貧干部之口講述其如何逆水行舟,促使外源推動與內源發展相結合,進而實現精準脫貧的路徑選擇。從紀錄片伊始的易地搬遷脫貧、教育精準扶貧到后面的特色產業發展、城鎮轉移就業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脫貧政策與機制,無不充分證明了我國脫貧攻堅的決心與智慧,突顯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創作者借此類脫貧敘事展開以案釋政,使觀眾對黨的各項脫貧政策與攻堅理念形成更加直觀感性的認知體驗,進而喚起其內心的由衷愛戴與擁護。
(二)折射脫貧攻堅進程的人文關懷
福柯曾言“話語即權力”,而以《中國扶貧在路上》為代表的鄉村振興題材紀錄片則將話語權力賦予了每位參與者,鏡頭流轉間展現了鄉民們的淳樸勤勞與扶貧者的實干奉獻。這種以集體行動為特征的參與式紀錄片的創作與傳播正是一場創建對話、引發思考、凝聚共識的人文化過程。
創作者對貧困鄉民的立體觀照和對鄉土文化的回溯詮釋奠定了影片溫暖堅實的人文基調。信息的不對稱使久困惡劣環境的鄉民們在面對變革時往往感到憂慮與彷徨,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也是普通民眾最真實的生存態度。《中國扶貧在路上》既為普通民眾情緒的宣泄與釋放提供了出口,也以人物命運的起伏為脈絡,多維度地呈現了鄉民們在變革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與轉變誘因,為“被遺忘的遠方”填補了情緒表達的信息鴻溝。片中的鄉民們最終克服萬難、成功實現脫貧致富,在迎來幸福生活的同時,也成為后繼者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榜樣。鄉村作為一個發展空間,支撐著整個鄉土文明,其價值與內涵也在紀錄片中被著重詮釋與書寫。一方面,紀錄片完整記錄了扶貧者與當地鄉民們在面對重大時代挑戰時如何從新角度探索鄉村價值,創造性地將原有劣勢和困局轉化為推動變革轉型的優勢與良機,從而實現外源推動與內生發展的融合互動,共同促進鄉村振興。另一方面,創作者主動挖掘鄉村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通過對各地風俗人情、服飾建筑、傳統工藝等元素的呈現,實現對鄉村精神文化的塑造與弘揚。侗族的舞蹈、苗族的吊腳樓、布依族的刺繡工藝等各具視覺沖擊的文化符號,已然成為我們管窺鄉土文明的一面“鏡子”。
四、結語
“主流媒體拍攝的脫貧攻堅題材紀錄片實質是一種宣傳媒介,由此再現出的鄉村圖景離不開國家話語的影響和對貧困鄉民群體及傳統鄉土文化的解讀。”③紀錄片《中國扶貧在路上》通過對兩者的細致描摹,勾勒出一幅鄉民們與扶貧者在鄉村振興語境下齊心合力、攜手同行的美好圖景,呈現出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時代潮流與進步特征,也為此后同類題材紀錄片豐富觀照視角、提煉內涵價值開創了可資借鑒的全新范式。
注釋:
①馮笑,張鄭武文.現實語境下制造題材紀錄片的人文敘事與時代價值——以《制造時代》為例[J].電視研究,2019(08):54-56.
②李軍輝.《大國工匠》:話語空間與紀實高度[J].中國電視,2018(03):106-109.
③劉娜,陳曉莉.基于再現理論的鄉村形象研究——以脫貧攻堅題材紀錄片為例[J].當代傳播,2019(06):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