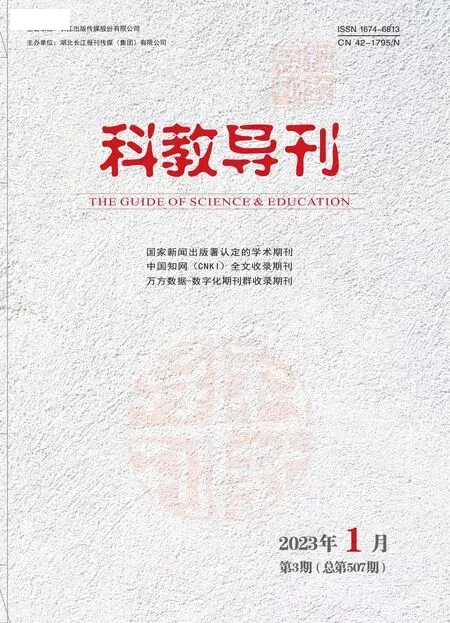基于導師作用發揮的國內外高校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案例探究
郭正宇,馬 亮,閆永帥,王 猛
(電子科技大學 四川 成都 610054)
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是世界上一流大學較為常用的博士生選拔形式[1]。為了克服傳統博士生“考試入學制”存在的一些弊端,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國內名校自2003 年開始探索以“申請―考核”制方式招生[2]。博士生“申請―考核”招生參與群體主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門、校院兩級管理人員、博士生導師、申請考生等,其中導師是博士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在博士生招生和培養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核心角色。然而在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實踐中導師作用發揮也面臨一些普遍問題,如導師參與環節、程度有限,“三隨機”“雙盲”工作機制削弱了導師的作用,或是監督制度不完善導致自主權過大,學術自律不足引發權力濫用等。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作為國外教育發達國家經驗的借鑒,其在國外運行過程中導師作用發揮如何?怎樣進一步規范和發揮國內導師在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中的作用?這些問題的探究和解決將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和優化博士生“申請―考核”招生選拔機制。
1 國外高校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中導師作用發揮的案例
德國被譽為近現代博士生教育的發源地,傳統的德國博士生教育是“師徒制”的典范[3]。對于德國高校的教授而言,博士生招生和培養是非常個性化的自主行為。博士生申請者能否獲得面試資格,主要由導師根據學習成績、科研情況、推薦人意見等材料決定。申請者征得導師同意后可向導師所在院系博士學位委員會提出申請,經該委員會研究同意即可獲得學院的錄取通知[4]。學院博士學位委員會具有一定的組織、監督和協調功能,對導師招生自主權有一定的約束,但總體來說是尊重導師意見。由于德國很多高校的博士生招生人數沒有限制,因此博士生導師作用在招生中能夠充分發揮,受到的制約主要來自本人學術要求、科研項目或經費情況等。
法國的博士生培養因其高水平的學術科研能力而享有盛譽[5],招生程序一般包括三個環節:論文撰寫、導師面試和學校考核[6]。首先,導師可以要求申請人撰寫論文,初步判斷其專業水平、研究能力。其次,導師還會通過面試考察申請人的教育經歷、基本素質、研究能力、表達能力、興趣愛好等。如果申請人通過導師面試,還需要參加由校方代表、相關專業教授組成的評審團考核。學校考核一方面能夠防止博士生導師在招生時出現無意偏差,又能夠對在招生過程中把關不嚴的導師給予提醒或警示。總的來說,法國大部分高校的博士生導師在招生中擁有較大的發言權,但自主權也受到院系或學校的監督制約。
美國博士生教育在20 世紀50 年代以后實施規范化和制度化改革,傳統的招考權從導師個體轉交到校院層面。博士生申請者通常需要選擇一項全美通行的標準考試(如GRE 等)并提交有關的申請材料。申請材料經學校研究生院審核合格后轉交相應院系招生委員會[7]。院系招生委員會對申請人的考察主要采用“集體負責制”,由專家組根據評審規則共同協商,按照希望錄取的順序排名推薦。在個別情況下學校還可以采用“導師負責制”選拔博士生,即導師獲得課題和經費后,根據個人的判斷物色博士生人選,由導師全權負責[8]。總體上講,美國高校的導師作用在集體決策中會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招生指標可以根據導師項目或經費情況確定,能夠享有一定的靈活操作空間。
日本博士研究生教育自20 世紀中期開始借鑒美國,形成了以學校研究生院為主導,院系(學科)配合的選拔模式。日本大部分高校的院系(學科)一般會按照研究生院的要求制定較為統一的招生程序和規則,并通過面試或筆試進行全面考核;在評判錄取階段,主要由各院系(學科)的專家共同評判并確定錄取結果。申請者一般要提前和導師溝通聯系,征得同意后方可提出申請;日本高校的導師在細分的專業領域一般具有較大的權威性和話語權。總體看來,雖然日本高校在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中建立了校院兩級工作規范,但博士生培養學徒制模式內核依然存在,導師作用能夠得到較大發揮。
對比德、法、美、日四國部分高校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情況發現,隨著全球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國外高校在考核標準或招生名額等方面給導師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權,但傳統的博士生“師徒制”模式正在逐步規范化、流程化。
2 國內高校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中導師作用發揮的案例
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主要包括個人申請、資格審查、材料評議、綜合考核、科學錄取等五個環節。由于管理制度、文化傳統、辦學歷史等差異存在,我國高校的博士生招生在資格授權、招生指標、遴選考核等方面導師作用更顯保守。通過查閱部分高校博士生招生簡章和有關文獻資料發現國內高校導師在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中的作用發揮各具特點。
在申請報名環節,部分高校或院系要求申請人須取得報考導師推薦或同意:如西安X高校允許導師差額推薦申請人報考,成都D 高校航空航天學院、上海T 高校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等均有要求報考導師必須是博士考生的推薦人,杭州H高校自動化學院要求考生資格由導師審核通過后推薦到學院;與之相反,有高校院系明確要求報考導師不能作為博士考生的推薦人,如北京Q高校的自動化學院。在材料評議環節,有些高校或院系允許報考導師直接參與申請人的材料評審環節:如南京D高校要求報考導師的材料審核成績占比30%,其余專家組成績占70%;北京Q 高校的自動化學院導師材料評分比例達50%。在綜合考核環節,有的高校允許導師參與專家組面試考核但不評分,而是額外賦予導師30%的審核成績,如南京N 高校現代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9];有的高校賦予導師組集體決策權,即所有報考導師共同組成考核組,如北京B 大學法學院、成都D 大學信息與通信工程學院等;有的高校賦予導師單獨考察的權力,如北京B 高校分子醫學研究所;還有的高校要求報考導師在綜合考核環節實行回避制度,如北京H 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在科學錄取環節,有些高校通過擬錄取名單產生賦予導師一定的自主權:如西安X高校錄取階段根據考核總成績等額劃定擬錄取分數線,導師和上線考生按照雙向選擇的原則進行擬錄取,如線上考生沒有在規定時間內被導師有效錄取將失去擬錄取資格,剩余名額由候選人員按照考核成績依次遞補;還有的高校在錄取階段按報考導師名下申請人的考核成績排序,從而確保同一報考導師的考生相對公平,如北京Z 大學。
3 思考和建議
我國博士生教育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國外高校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導師作用發揮機制不可照搬。比較國內外高校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案例,結合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導師作用發揮機制可以從以下環節著手考慮。
3.1 在報名申請環節加強導師作用發揮引導,健全責任落實機制
鼓勵導師積極參與博士生招生報考條件、評價標準、考核內容及要求等學術條件制訂有益于遴選更加符合培養目標的優質生源。針對業界聲譽好、學術造詣高的導師,可以結合當年科研需要、經費條件、生源質量等情況在招生指標方面給予適量調節空間;有條件的院校還可以在學校統一指導下根據導師(或團隊)實際情況設置報名條件、招生指標、考核方式等。同時,高校要加強制度保障、完善責任落實機制,比如:建立更加細致、規范的信息公開規則;導師承擔更高比例的博士生培養成本;實施更加多元的博士生淘汰分流機制;落實更加科學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等。
3.2 規范導師在材料評議環節的作用發揮,平衡集體和個性需求
由于“申請―考核”制招生不再單獨設置統一入學考試,材料評議結果是確定申請人復試資格的重要依據。各學科專業應當統一制訂包含客觀和主觀評價內容的材料評議標準,導師在標準制訂中應當扮演核心角色,充分體現其學術自主權。材料評議可采用導師組集體負責制,成績使用方式和復試入圍標準及復試比例應當提前向社會公布。通過以上方式能夠在材料評議環節賦予導師考察申請人一貫表現的權力,同時也能有效消除評價標準掌握尺度差異可能帶來的不平衡。
3.3 突出導師綜合考核環節話語權,建立標準化、模塊化考核方式
綜合考核是考察申請人創新能力、專業素養和綜合素質的直接環節,考核結果是確定最終錄取名單的主要依據。在考核形式、內容要求、工作流程、評價標準等方面建立標準化、流程化、模塊化的考核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院系要以學科專業為單位成立綜合考核專家組,報考導師應當作為成員在考核過程中充分表達其意見和觀點。在綜合考核環節可以考慮適當引入同行或專業機構開展第三方評價,既能夠達到監督的效果,又能夠促進考核評價更加全面、科學。為了消除極端值可能引起的偏差,綜合考核成績應當去掉一個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用平均分計算。通過以上方式既能夠保障導師在綜合考核環節的話語權,又能夠通過集體決策減少個人意見可能帶來的偏差,確保綜合考核結果的公平性、科學性。
4 結語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國學歷學位教育的最高層次,導師是博士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在博士生招生和培養過程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如何更好地規范和發揮導師作用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研究,并不斷完善的工作。只有充分調動導師群體在博士生“申請―考核”制招生中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不斷完善指標分配、學術評價、激勵和約束等機制,才能做到公平和效益兼顧,更好地為國家遴選和培養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