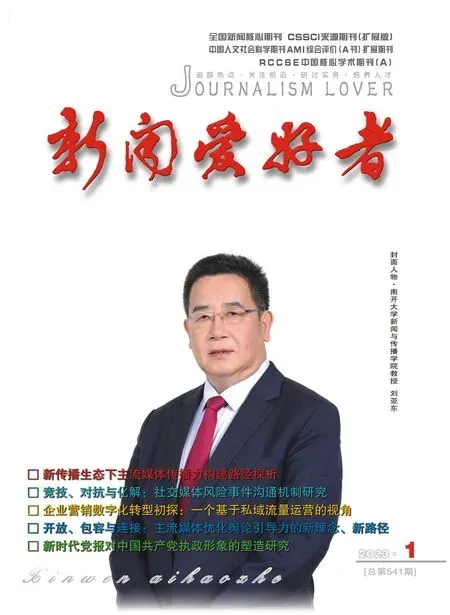基于內容分析的美食類短視頻特征研究
□劉 磊 袁 夢 李詩雨
“美食博主”一詞最早興起于韓國的《美食真人秀》節目,該類節目大致為主播坐在鏡頭前,向網友展示自己吃飯的全過程,憑借受歡迎程度獲得打賞;2014年底,網友“處女座的吃貨”組建了中國吃客分隊,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加持下,美食類視頻一時間在B 站、快手、抖音、斗魚等視頻平臺掀起波瀾,各大平臺涌現出許多中國本土美食博主,觀看美食短視頻“云吃飯”一躍成為門檻最低、性價比最高的宣泄“口腹之欲”的方式,博主推薦而后網民打卡的形式也成為實體經濟回暖的有效路徑之一。本文以內容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選取抖音、B 站等國內大型視頻網站單個平臺上點贊次數超過10000 次,共計622 則美食類短視頻作為研究樣本展開分析。
一、美食短視頻類型呈現多元化樣貌
(一)“以吃為主”類型
此類型是一種較為傳統且最為簡單的美食短視頻樣式,該類視頻的相關分析可拆解為美食與博主兩大要素,二者的重要性在“以吃為主”類型的視頻中不相上下。首先,優質的美食自帶流量,原本就受到大眾青睞的食物與視頻內容產生合力,進一步提升了傳播效果。其次,具有人格魅力并能引起受眾共鳴的美食博主也可以形成風格化品牌,優質美食附加鮮明的個人特色可以不斷吸納“鐵粉”。筆者從小貝餓了、密子君、張喜喜這三個“以吃為主”的美食博主主頁,分別抓取了133 則、144 則、143 則短視頻,對其封面上標注的食物進行分析。得出此類博主食用的多為年輕人群體間廣受歡迎的高熱量食品,這類食品是年輕人聚餐或在家中簡單烹飪的首選。同時,此類視頻的“黃金五秒”能迅速吸引受眾,視頻前五秒在話語結構上有規律可循,語態生動活潑,大多表現為展示食物,對受眾提出問題或給出建議,偶爾也會使用俗語,“飯搭子”等網絡熱梗,偶遇粉絲的橋段也時有發生。透過相似的食物類型及片頭我們可以窺見“以吃為主”類型美食短視頻存在創意缺位的同質化問題,未來作為生產者的美食博主需突破視頻內容固化的瓶頸,不斷調試,尋找創新的更優解。具體而言,美食博主應積極挖掘自身視頻的錨定點,即圍繞個人特色做精細、深化發展,盡力為粉絲創制新穎且高質的視頻內容,防止因審美疲勞造成的粉絲流失。
(二)“且吃且探”類型
“且吃且探”顧名思義,是指博主去餐廳體驗,對餐廳的食品、環境及服務進行考察,通過短視頻或直播的形式,結合自身評價分享給受眾。“且吃且探”型視頻廣受歡迎,美食博主探索范圍較為豐富,并不囿于知名品牌連鎖店,熱衷展示生活截面,走街串巷尋找極具當地特色的街邊美食,其中一部分博主注重網友的反饋與互動,接受“點菜”前往網友呼聲較高的餐廳。此類美食視頻呈現的食物大多為中高端中餐,評論專業化、黃金前五秒更具趣味性、著力打造品牌化為其主要特點。以“真探唐仁杰”近期發布的72 則作品為例,吃食價格主要集中在千元以內,消費級處在百元以上千元以內,屬于中等偏上水平,因此受眾亟須此類博主提前“試錯”。博主點評部分是短視頻的精華,尤其是以“真探唐仁杰”為代表的身份特殊性博主,他們從廚師轉行美食博主,積極發揮自身的專業效能,評價的可信度與專業度較高。該類型視頻的前五秒以博主評價金句為主,附加具有辨識度的開場白,趣味性特點尤為顯著。換言之,此類美食博主在有效幫助廣大受眾“試錯”的同時也在筑牢粉絲基礎,努力打造隸屬于自己的品牌,為受眾生產更優質的作品。
(三)“多人情景”類型
“微短劇”是隨著短視頻發展而迅速走紅的一種新興劇集形式,多人情景型美食短視頻可類比對標為美食界的“微短劇”。微短劇具有時間更短、劇情反轉強烈、人物特征突出等特點。[1]此類博主剝離城市環境的喧囂,將拍攝場景搬至鄉村,自成一體。食用的食物均為自己制作,因此“多人情景”類型美食短視頻在繼承微短劇情境化特點的基礎之上,還肩負文化傳播的內生使命。如博主“康仔農人”的部分視頻存在方言對話的場景,大量自然符碼的編織融合塑造出質樸的農人形象,并在“黃金五秒”的片頭展示具有意象性特征的秀麗鄉村風光和農人辛勤勞作的畫面,讓受眾產生置身世外桃源的臨場感。同時其還在主頁添加“鄉村守護者”標簽,利于自身精準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國地方鄉村文化的傳播,為鄉村振興助力。
二、美食短視頻受眾特征分析
(一)使用與滿足的特征
卡茲等學者將媒介接觸行為概括為一個因果連鎖過程,即“社會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觸—需求滿足”,并提出了“使用與滿足理論”,該理論認為:受眾接觸某一媒介,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特定需要。[2]基于自身的需要,受眾會主動挑選可以讓自己得到心理滿足的短視頻觀看。反觀美食類短視頻,受眾的觀看實則是一種“凝視”,通過“凝視”獲取陪伴的需要、對美食相關知識的需要以及關注度的需要。美食博主瞄準受眾群體,把握了受眾尋求此種替代性滿足的心理。基于對受眾使用與滿足特征的分析,筆者也對該特征極化后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資本逐利下,流量意味著變現的可能,但一味追求高熱度帶來的高收益而過分迎合市場,視頻創作會陷入逐利的偏狹窠臼,資本的泥沼湮沒了視頻背后的社會意義。因此,美食博主若舍本逐末,過度渴求流量而忽視視頻內涵,只會阻滯自身發展,終有一日將受到受眾拋棄。
(二)Z 世代受眾特征
Z 世代也稱“網生代”,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們一出生就與網絡信息時代無縫對接,受數字信息技術、智能手機產品等影響較大。[3]美食類短視頻的受眾年齡集中于20 至29 周歲,大部分與Z 世代年齡區間重疊。因此,網絡信息時代下作為Z 世代的美食短視頻受眾特征主要體現為碎片化接收與精準接收。首先是碎片化接收。傳統的閱讀模式在互聯網時代已被快節奏、碎片化的短視頻取代,Z 世代更青睞短、平、快的內容帶來的接收愉悅,碎片化接收已然成為一種習慣。一方面,美食類短視頻時長短、內容豐富,契合當今受眾對短時間高信息量帶來的視聽快感的追求;另一方面,美食視頻的陪伴感特征也需要其視頻時長控制在受眾一餐時間以內。其次是精準接收。在大數據算法推薦的技術背景下,當受眾完整地看完一條美食短視頻,未來可能會較為頻繁地刷到同類型視頻,精準接收由此體現。同時,在觀看的過程中受眾也可自主選擇是否繼續觀看或長按點擊“不感興趣”的選項,這一步選擇決定了觀看美食短視頻是否能從填補閑暇空白轉變為一種日常化習慣。筆者在“新抖”平臺上整理了幾位美食博主粉絲的活躍時間,調查顯示,大部分粉絲活躍時段峰值為晚間,部分視頻在午間也會迎來短暫高峰,調查數據充分證明受眾對美食短視頻的接收模式正從空白消遣轉變為慣習式觀看。
(三)社會參與的特征
“社會參與論”認為受眾個體和受眾全體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在美食短視頻傳播的過程中,受眾的接收呈現“游牧”特征,即“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義”。博主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刺激受眾從而產生溢出效應,受眾會選擇在生活或網絡場域模仿美食博主的行為,實現從網絡生活到社會生活的轉變。在“且吃且探”類型視頻的評論區中,有許多關于博主開場調侃式話語的模仿復現,也有一部分受眾會選擇在食品烹飪方式或食材搭配上向博主學習。“社會參與論”還認為受眾更容易接受自己親身參與形成的觀點。所以部分受眾樂于模仿美食博主的做飯方式、積極打卡其推薦的餐廳,將烹飪和打卡過程以短視頻的形式發布在網絡平臺上,受眾的主動參與進一步擴大了視頻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此種自發性創作也為短視頻美食區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成為行業內一種全新的發展引擎。
三、美食短視頻營銷特征分析
(一)打造品牌忠誠,實現流量變現
大數據時代電商快速發展,且頭部主播掌握主要流量和資源,如果說“直播帶貨一哥”李佳琦激發了女生的消費欲望,那么頭部美食博主便激發了“吃貨”們的欲望。部分頭部美食博主入局較早,意識到受眾的欲望一旦被激發便會產生流量變現的動力,于是開始著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形象。抖音商城中充斥著“某某推薦”“某某同款”“某某專享”的字眼,這背后是品牌價值鏈的重要一環——傳播,整個傳播布局內含多元利益主體的博弈,我們需厘清其背后的運轉邏輯。受眾、美食博主、商家這三者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同構關系,商家化用美食博主流量,依托用戶黏性,最終將受眾精準引流到相關商品;美食博主則力求打造自身品牌,不斷提升受眾品牌忠誠度,最簡單的渠道便是利用商家提供的直播場景紅利進行帶貨;受眾重視性價比,需要商家提供優質的售前售后服務,也需要美食博主購買渠道提供的優惠價格,受眾的自主選擇性在整個商業運作過程中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下面對美食博主線上帶貨宣傳的變現模式作簡要利弊分析。第一,帶貨模式為博主和受眾雙向溝通及粉絲黏度維系提供便利。受眾可以在美食短視頻評論區或是直播間詢問產品相關信息,問題也可以及時得到解答,這種高效的互動模式能有效提升受眾使用滿足的體驗感。第二,流量、商家資本的涌入成為美食博主不斷更新優質視頻的內驅力,優質視頻又能進一步拓寬受眾廣度,三者實現了良性循環。但帶貨模式對美食博主依賴度較高,在選商品時需細致謹慎,否則受眾對博主的信任度將大打折扣,環環相扣影響后續變現。
(二)探店打卡,助力實體經濟發展
天眼查數據研究院發布的《新經濟下2022 新職業百景圖》涵蓋了2019—2021年出現的上百種新職業,探店博主就包含其中。[4]探店博主呈井噴式發展與疫情大環境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其一,疫情影響下部分年輕人失業,繼而轉型為探店博主。其二,疫情使人們可支配的收入驟減,因此生活中需要一個“測評員”幫助大家“避雷”,探店博主搖身一變餐飲行業“測評員”。其三,疫情環境下餐飲行業受到劇烈沖擊,外出就餐的人數和頻次都呈下降趨勢,疫情好轉后,餐飲商家也急需彌補疫情沖擊造成的損失來維持生計。[5]在此背景下,探店博主發揮中介作用成為溝通受眾與餐廳的橋梁,進而助力作為實體經濟之一的餐飲業復蘇發展。一方面,博主使受眾能線上“云體驗”餐廳的各項服務,最終將受眾精準引流至商家。另一方面,優質的博主在享受流量紅利的同時也會反哺受眾,更加積極主動地為受眾尋找值得打卡的線下餐飲店。換言之,博主探店打卡帶動餐飲消費是一種三方互利的模式,受眾需要測評所以觀看博主探店視頻,博主需要受眾觀看帶來的流量所以積極發掘寶藏打卡地,餐飲店需要受眾消費維持經營所以期待博主的宣傳。
(三)傳播地方文化,助力鄉村振興
視頻視聽結合的感知傳播體系擁有純視覺或純聽覺媒介無法比擬的信息容量。政策扶持和短視頻平臺流量傾斜為鄉村振興注入了發展的催化劑。海量的地域性文化被搬至前臺,如前文所述,大部分“多人情景”型美食短視頻以宣傳家鄉的美食文化為視頻內核,繪就美好鄉村圖景。該類美食博主產出的優質視頻內容在增強用戶黏性的同時也推進了文化黏性,結合時代熱點、人文情愫,塑造屬于自己的鄉村品牌,激發鄉村振興的生機與活力。部分鄉村美食博主不僅致力于線上通過短視頻宣揚傳統文化,對線下公益也有所觀照,“康仔農人”在疫情期間為百色市紅十字會捐款10 萬元,優良的品格與獨特的人格魅力也成為美食短視頻的點睛之筆。
四、結語
在短視頻平臺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用戶自主性極大提升,每個用戶都可以自由生成專屬內容。美食視頻行業的低門檻快速發展致使行業內部魚龍混雜,傳播者素質良莠不齊。部分博主以突破底線的“非常”手段吸引受眾,從被央視點名批評鋪張浪費的“大胃王”模式,到獵殺二級保護動物的“燒烤鯊魚”,劣質博主為博人眼球不擇手段,內含扭曲的價值取向。目前美食短視頻行業尚處于問題頻發的不穩定階段,一方面美食類短視頻生產者應提高社會責任感,做自己的“把關人”;另一方面受眾也應提升審美素質,不給低劣博主嘩眾取寵的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