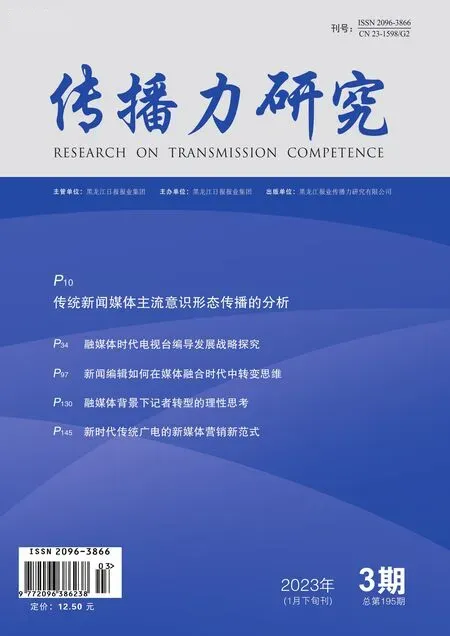接受美學理論視域下晚會主持的提升思考
◎孫大彬
(寧波廣播電視集團,浙江 寧波 315000)
一、接受美學的理論解讀
接受美學是以“受眾中心論”為核心主張的,其強調一切生產都應從受眾出發。接受美學“主張藝術作品的歷史本質,決不能被單純的藝術品生產的考察和作品描述所抹殺,相反我們應把美學看成生產和接受的辯證過程”[1]362。因此,與其說接受美學所重視的是受眾,不如說接受美學所注重的是如何在受眾和生產者之間形成一個良性的相互關系。在接受美學最初萌芽的60年代,康斯坦茨學派提出了“走向讀者”這一全新的美學思路,而姚思則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了“期待視野”的概念,之后又有學者提出了“召喚結構”和“隱含的讀者”的概念。
(一)姚斯的期待視野
“期待視野”是姚斯文學史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其在卡爾·波普爾科學哲學概念的基礎上,吸收海德格爾的“前理解”與伽達默爾“合法的偏見”的歷史性和生產性提出的。[2]姚斯提出在文學接受活動中,讀者的文學閱讀經驗及趣味、素養等綜合形成的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欣賞要求和欣賞水平,構成了思維定向或先在結構,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而這即是所謂的期待視野。
因此,由于期待視野的存在,受眾或讀者在觀看一個作品前,已然存在某種預先設置的結構和判斷,這種結構和判斷是根據受眾之前所有的各種經驗、知識、記憶和情感融合產生的,因此,受眾或讀者在形成觀看行為時,會讓作品與內心預先設置的結構產生碰撞,如此才形成了最終的審美體驗。如此,如果將這一概念移置到諸如電視節目或藝術傳播類節目中,那么期待視野就意味著受眾會事先對這些節目進行類型內容、偏好和主題風格的判斷,從而在觀看時與節目形成某種隱秘的內在聯系,觀眾會不自覺地帶著過往的經驗和預先形成的期待視野看待這個節目,但是在姚斯的理論中這種期待視野是更多拘泥于文學領域的,并且是一種所謂的“前理解”,其在概念上并不完善。對此,還可以做出進一步的補充。首先,期待視野并非只施加一次影響,而是一種綿長的反應,是一個隨著節目進行不斷作用的過程。其次,期待視野是會在不斷觀看下逐漸變更和擴大的,當節目打破了原有的期待,觀眾便會形成新的期待視野。如此當我們將期待視野看作是一種前理解,那么節目或晚會主持都可以預先通過各種形式來幫助觀眾塑造前理解,從而縮短審美距離,讓節目和主次為觀眾提供更好的觀看和審美體驗。
(二)伊瑟爾的隱含的讀者
伊瑟爾在接受美學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隱含的讀者”這一概念,在伊瑟爾“隱藏的讀者”概念中,隱含讀者不是實際讀者,而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預期設計和希望的讀者,即隱含的接受者。它存在于作品之中,是藝術家憑借經驗或者愛好,進行構想和預先設定的某種品格。并且,這一隱含讀者業已介入創作活動,被預先設計在文藝作品中,成為隱含在作品結構中的重要成分。顯然,這個“隱含的讀者”排除了許多干擾因素,更符合作者的“理想”,甚至可以說,是第二個作者,即作者自言自語時的聆聽對象。
因此,如果將“隱含的讀者”這一概念放置到節目的創作或是晚會的主持上,即是在節目和臺詞進行設計和彩排時,其所有創作不僅是在面向現實的受眾,同樣是在面向隱含的受眾。如果我們將文學文本的創作視作是作者和自己內心構想的理想讀者的一場對話和交流,那么節目或是主持的創作同樣可以看作是一種對潛在互動的把握和預想,而這正是隱含的讀者可以在晚會主持這一實踐上所起到的作用。
(三)“空白”理論
伊瑟爾在提出“隱含的讀者”這一概念之后,又進一步提出了“召喚結構”的概念,而其中所引申出的“空白”理論則可為節目制作或晚會主持提供十分有益的啟發和指導。所謂“空白”理論在伊瑟爾的主張中被稱作是“本文中懸而未決的可聯系性”[1]376,朱立元先生進一步解釋說:“所謂‘空白’,就是指本文中未實寫出來的或未明確寫出來的部分,它們是本文已實寫出部分向讀者所暗示或提示的東西。”[3]倘若我們將其放置到晚會主持中,則可將其理解為一種通過前后文的聯系以及持續的雙向互動下,對受眾給予的一種潛在的引導和暗示,這種引導和暗示能夠幫助受眾更好地理解事物并讓主持獲得更好的表達效果。
二、接受美學與晚會主持的關系分析
(一)“受眾中心論”對互動關系的重視
晚會主持與其說是掌控整個活動流程,更多的其實是在構建一種雙向的可持續流動的互動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受眾即觀眾作為了接受的主體,并被邀請到整個活動流程的創作中,主持人的語言表達和非語言表達皆是在引導觀眾進入到現場的視聽體驗和審美體驗中,幫助觀眾更好地梳理現狀并形成持續性的感受。如此接受美學之于晚會主持即是在明確受眾的主體地位,讓主持人和制作人時刻意識到互動關系建立的必要性,主持的實踐絕非是機械的運動,而是需要根據不同的節目和當下現場的具體情景而時刻調整變化的,主持人有著明確的媒介任務,并應該成為活動中的引導者和掌控者,不僅需要時刻保證流程的正常進行,同時更需要在互動下豐滿活動的間隙,為觀眾提供更多的想象和感受。
(二)“期待視野”和“隱含的讀者”對主持的認知改變
“期待視野”和“隱含的讀者”在主持中的引用,實際上是為主持提供一個全新的認知視野和思考方向。通過對這兩大概念的理解,可以發現主持不再只是一種簡單的現場傳播行為,而是一種可以進行事先預謀和規劃的,具有綿延性質的實踐活動。意即主持在其準備階段,已然可以對之后到場的受眾進行審美和感官上的影響,首先在“期待視野”下可以明確觀眾在觀看一個節目或是到赴一個晚會前,其早已擁有了一個提前設置好的結構,也就是“前理解”,而主持和節目所要做的正是縮短這種審美距離。因此,主持人在進行彩排、流程設計和臺本創作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前來的受眾的審美偏好和審美需求,并通過提前的宣傳以及準備,影響觀眾的“前理解”。其次就“隱含的讀者”而言,無論是節目設計還是語言的表達主持人必須做到“觀眾”的時刻在場,并意識到無論是舞臺和服裝的設計抑或是語言的表達,都將成為觀眾的審美因素之一。如此,“期待視野”和“隱含的讀者”即能通過其獨有的概念內涵為主持提供全新的實踐認知。
三、接受美學視閾下晚會主持的提升對策
(一)風格延續下針對不同受眾進行相應主持設計
主持人主持風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為了塑造自身的主持形象,在風格的延續下與觀眾形成某種內在的默契,同時亦是為觀眾提供一個可預判的審美視野,由此就“期待視野”而言,主持風格的定位和形成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其意味著主持人有自身特有的語言表達方式和外在一脈相承的形象特點,同時還具備一定的個性和特質。但是作為晚會主持人而言,其并不一定會只接受一種類型的晚會,而是時常需要面對不同的晚會和受眾,如此風格延續下更為重要的是能夠自如且自覺地調整主持的整體設計。不同的晚會和受眾,具有著不同的需求和偏好,例如,筆者在之前所主持的“寧波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文藝晚會”,其所面對的受眾是來自市內各個部門各單位的黨員,由此其在偏好上會更注重隆重而正式的視聽表達,其晚會本身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誕辰,是一個十分具有歷史意義和節點意義的晚會,如此筆者在主持稿的設計和外在形象的設計上皆呈現出強烈的主題性和恢弘色彩,并突出了歷史感、時代感和榮譽感。之所以如此設計,恰恰是在受眾的“期待視野”下所形成的,受眾的經驗和偏好以及晚會本身的特性,決定了晚會在審美體驗上的需求和方向,這些因素即決定了筆者在進行主持設計時,會相應地進行調整和預設,從而達成縮短審美距離的目的。
再例如央視近年來推出的“主播說聯播”系列,正是為了對應當下多元的受眾群,其在內容設計上常常貼合當下的語言習慣和審美潮流,在主持形象的塑造上同樣多變且更符合當下的個性,而并非一味的按照過往生硬死板的設計。雖然直播系列不同于主持,但其內在的設計邏輯是相互對應一致的,皆是為了更好的預判并契合觀眾審美,讓主持節目在“期待視野”的滿足下獲得更好的外在呈現和節目傳播。
(二)“隱含的讀者”下構建隱秘的互動關系
晚會主持實際上亦是一個文本敘事的過程,其中文本的形成始終是在面向著“隱含的讀者”,而晚會主持無論是從角色的定位抑或是文本的敘事都是在構建一種隱秘的互動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可簡單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敘事中主體角色的定位、敘事語言的選擇和敘事互動的設計。首先在主體角色的定位上,所要注意的是主持人所期望形成的敘事是何種敘事,其所面對的受眾是何種群體,對于春晚而言,春晚主持人所應該扮演的即是一種親民的主持角色,其既需要有個人的表達,同時又代表了集體,因此,我們經常能在春晚中聽到關于“我們”“咱們”的敘事;其次則是敘事語言的選擇,在面對年輕群體具有都市時尚氣息的晚會上,可更多的選擇具有現代性的語言表達,活用網絡語言和流行語言,而少用太過宏大的表述,在面對更為莊重的場合時,則使用特定的具有儀式感的語言形式;最后則是敘事互動的環節設計,一方面可通過臺本的設計,主動的和受眾形成現場互動,例如,2018年的春晚中尼格買提說道:“不瞞大家說,今年春晚上臺之前,我也發了一條微博。我說,此刻最想念的就是媽媽包的餃子,但是現在只能遙寄相思和祝福,發完馬上就有人懟我了,想知道他們怎么懟我的嗎?”這里,尼格買提即選擇了通過臺詞直接與現場形成互動,此外再如2023年的春晚中,有一段這樣的互動:“謝謝,朋友們,這張桌子上放著的是春晚節目組今年收到的一小部分的觀眾來信,可能您想不到啊,現在網絡都已經這么發達了,我們還會常常收到觀眾一筆一畫手寫的信件,我們想告訴大家的是,這些信我們都看到了而且十分珍視,并連同眾多的中國電影人,就以觀眾來信為創意來源,創編了春晚史上的第一部微電影,送給所有關注春晚,熱愛春晚的人們,講一講《我和我的春晚》。”在這段臺詞中,其實就隱含了三層不同的互動,一是之前觀眾來信的節目互動,來信的提前收集和電影的提前制作為當下的節目制造了更豐盈的內容;二是在場觀眾在信息接受下形成的互動,觀眾會好奇來信的內容并想象自身與春晚的故事;三是節目結束后,微電影觀看所產生的后續互動。另外,可以通過主持流程的設計來制造互動機會,例如抽獎、現場游戲等等。此外,互動的時機和互動的切入點同樣需要進行選擇和考慮,一方面應該緊密的跟隨時事和熱點,另一方面不能影響晚會現場的流程安排和連續性。
(三)“空白”理論下對主持節奏的掌控
在晚會中,所謂的空白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流程中的間隙時間,另一方面則是語言中未直接表明或旨在暗示觀眾的內容。很多晚會主持人在進行主持時,習慣用語言填滿整個流程的空隙,這很容易讓觀眾形成疲倦感和緊張感,因此主持時需要活用“省略”“停頓”“概要”和“場景”這四種敘事技巧,為觀眾提供背景和情景的同時,讓觀眾有余地進行消化和想象,而不是一味地全盤托出。此外在語言內容上,更多的是對觀眾進行認知和感受的引導,而不是進行所謂的解釋和交代。例如,在2015年的春晚上,李詠:“董卿,把春節晚會比作視覺盛宴,應該說毫不夸張。節目里有好聽的,也有好玩的;有開心的,也有感人的。接下來給大家來一個高難度驚險的怎么樣?”董卿:“好啊,下面我們就請大家來欣賞一個雜技《綢吊頂技》。各位請注意:這個曾獲國際大獎的節目中有很多令人驚嘆的絕技,會讓我們一飽眼福。”這里所使用的語言內容其實就是在場景交待和要素引導下,留下空白,從而讓觀眾有一個提前的審美判斷和審美期待,并促使觀眾形成更豐滿的感受。類似這樣的場景敘事在晚會主持中有著很大程度的占比,而場景的交代是為了給予觀眾可感或可想象的時空,并在主持過程中,調動整體氛圍,為后續的表達作鋪墊。再如,概要的使用,所謂概要即是不提及人物事件的具體信息和細節,而是選擇一筆帶過的形式,形成相應簡短的描述,這樣的主持語言在類似春晚這樣的大型晚會中亦是十分多見,能夠較好地舒緩或加快主持節奏。如果回顧2023年的春晚,空白理論同樣隨處可見,“謝謝,這聲感謝送給臺上的演員,更要送給所有的小哥,是你們早出晚歸、風雨兼程,便捷了我們的幸福生活,更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歲月里守護了我們的一片晴空,朋友們,在這樣一個萬家團圓的夜晚,依然有很多的小哥穿行在大街小巷,奔走于千家萬戶,想對你們說一聲,辛苦了,《小哥》。”這里不僅使用了場景元素,同樣用概要和省略的方式描述了外賣小哥辛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