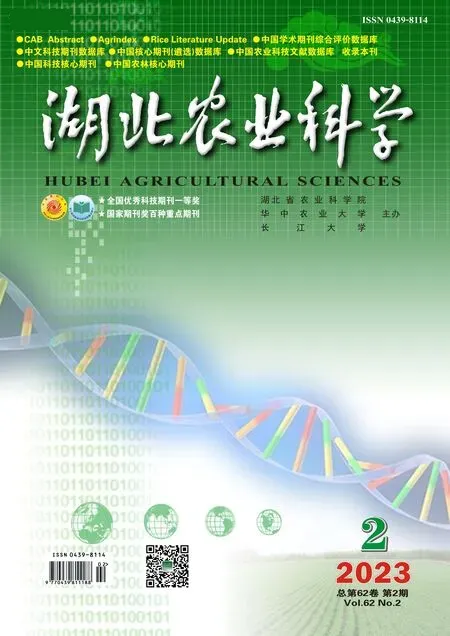碳中和目標下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的關系研究
——以江蘇省為例
陳佳輝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南京 211100)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向來是一組互生的矛盾關系,隨著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環境承載力逐漸達到臨界值,其中尤以氣候變化最為嚴峻。為此,2020 年中國在聯合國第七十五屆大會上宣布將采取更有力的舉措,力爭于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爭取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這為中國未來低碳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明確了目標[1]。而促使社會經濟體系按照預期的排放路徑實現碳中和目標,以碳循環與水循環尤為重要[2],兩者作為地球重要的循環過程,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而又互相重疊,實現碳中和需要高效水循環系統的輔助和支撐,同時,對水環境的保護和治理,也有利于生態經濟的長效發展。因此,進一步分析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發展的關系,既可以更有針對性地促進雙方的正向互動,也能更好地推動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1 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的相關性
水環境污染是環境污染的重要表現之一,表現為各種有害的化學物質造成水的使用價值的降低或損失。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結構開始優化升級,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帶來污染物的增加,諸如未經無害化處理的工業污水排放至當地水體,農業生產所需的化肥、農藥等對周邊水系的影響,大量人口聚集的城市每天會產生大量的生活污水等,這些污水的排放勢必對水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長此以往,水環境態勢逐漸惡化,又反過來制約生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導致城鎮居民缺乏必要的干凈飲用水、工廠無法獲取所需的生產用水、農業灌溉用水不足等。因此,需要選取水環境污染的主要源頭,就其與生態經濟的關系進行探析,并最終獲取具有顯著相關性的污染類別,研究其與生態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以期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
1.1 研究區域概況
選取江蘇省作為此次研究對象,進行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的相關性分析。江蘇省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地跨長江、淮河南北,境內地勢平坦,湖泊眾多,氣候宜人。作為經濟大省,該區域的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的關系具有鮮明的典型性和借鑒意義。整理該省2012—2021 年10 年的經濟數據,如表1所示。

表1 2012—2021 年江蘇省經濟發展狀況統計數據
1.2 指標選取
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區域人均生產總值作為研究的因變量,并根據歷年《統計年鑒》公布的水環境污染指標,選取工業廢水排放量、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工業源COD 排放量、農業源COD 排放量、城鎮生活源COD 排放量、工業源氨氮排放量、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和城鎮生活源氨氮排放量作為自變量,其水環境污染指標數據統計見表2。使用python 3.7 軟件繪制8 個自變量之間的熱圖,數值表示相關系數,如圖1 所示。

表2 2012—2021 年江蘇省水環境污染指標數據
由于直接選取8 個指標探析其與生態經濟的關系,會造成變量過多,不利于分析結果的合理性,且由圖1 可知,原始數據的相關系數普遍大于0.5,即各個變量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因此適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對生態經濟具有較大影響的典型指標。使用SPSS 25.0 軟件,將原始的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Z-score),得到各個指標的標準化數據,經過處理,獲取主成分矩陣求解結果和主成分載荷陣[3],如表3、表4 所示。

圖1 不同自變量之間的熱圖
由表3 可知,提取出的前兩個主成分可以解釋全部方差的95.778%,即這兩個主成分能夠代表原8個指標數值95.778%的相關性。結合表4 數據對主成分量進行加權求和,得出主成分綜合分值,并根據綜合分值大小進行降序排列,得到表5。

表3 矩陣求解主成分結果

表4 主成分載荷陣
由表5 可知,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和工業源COD排放量具有最明顯的表現,因此,選擇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和工業源COD 排放量作為最能代表水環境污染的指標,進一步探討其與生態經濟的關系。

表5 環境污染指標
2 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之間計量模型的構建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是分析區域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關系的重要工具[4],其揭示了經濟發展與環境質量的關系:地區經濟發展初期,環境狀況較為良好,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環境質量隨經濟發展而逐漸惡化;當經濟增長到達某一特定的“轉折點”,環境質量就隨經濟發展而逐漸改善[5]。
EKC 的本質是研究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然而,由于受到現實環境的復雜性和各種不可預測因素的作用,經濟-環境之間不是單一模式的影響關系。因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并不單一地表現為倒U 型關系,其曲線形態也有可能變化為正U 型、正N 型、倒 N 型等形態[6]。
2.1 研究方法
線性回歸是通過對觀察到的數據擬合一個線性方程來模擬兩種或兩種以上變量之間關系的統計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影響因變量y的因素往往不止一個,其受到n個影響因素,即自變量x1,x2,…,xn和不可預測的隨機因素ε的影響,因此可列出經典線性回歸數學模型如下。
式(1)為因變量y對自變量x1,x2,…,xn的線性回歸方程,其中,βn(n=0,1,…,m)是偏回歸系數,εi(i=0,1,…,p)是互不相關的隨機變量。
根據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數據,則式(1)可變為如下方程。
對于給定的t組樣本數據,可計算其條件均值,具體表現如下。
由微積分的原理可知,當Q對的一階偏導數為 0 時,Q最小,即:
由式(5)可得:
和分別為線性回歸模型Yt=b1+b2xt+εt(t=1,…,u)的參數b1和b2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量[7]。
根據SPSS 軟件多種曲線回歸模擬分析的結果,比較P、R2和F3 項參數,從而建立工業廢水排放量與人均GDP 之間以及城鎮生活污水排放量與人均GDP 之間的最優模型[8]。其中,P為顯著性水平,當P<0.05 時,則表示存在顯著差異,即回歸方程通過顯著性檢驗;R2是衡量估計的模型對觀測值擬合優度的高低,當R2>0.6 時,則表示回歸曲線擬合優度較高,回歸方程可用于預測,總之,R2越接近1,則擬合優度越高,越接近0,則擬合優度越低;F用來檢驗總體回歸方程的有效性,F越大,差異越明顯。
2.2 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關系模型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構建計量模型,并結合表2的數據,使用SPSS 軟件進行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關系的線性(Linear)、二次(Quadratic)以及三次(Cubic)的回歸曲線模擬。其模擬結果如表6所示。首先,查看P,3 個回歸曲線的P均小于0.05,所以3 個回歸曲線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其次,查看R2,比較線性、二次和三次回歸曲線的R2可知,0.518<0.6<0.719<0.732,即三次回歸曲線擬合優度高于線性和二次回歸曲線,且高于0.6;最后,查看F,比較線性、二次和三次回歸曲線的F可知,8.582<8.934<9.562,三次回歸曲線的差異性最明顯;因此,綜合考慮發現,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關系以三次回歸曲線擬合更優,為了更直觀地查看回歸曲線,借助SPSS軟件繪制兩者之間的三次回歸曲線。
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如圖2 所示,結合表6 中的相關數據,可以得出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EKC 模型擬合方程為y=19.929-33.55x2+6.155×10-12x3,可以看出其并未呈N 型或倒N 型趨勢,而是更接近正U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這與傳統的倒U 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恰好相反。根據EKC 擬合方程和圖2 可知,該曲線的極值點存在于人均GDP 的115 168 元與123 607 元之間,即2012—2018 年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成反比,生態經濟的增長緩和了農業源氨氮排放量;2019—2021 年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成正比,生態經濟的持續發展加劇了農業源氨氮量的排放。

圖2 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的三次回歸曲線

表6 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關系模型
2.3 工業源COD 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關系模型
參照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關系的模型設定方法,將相關數據導入SPSS,進行工業源COD 排放與生態經濟之間關系的線性、二次以及三次回歸曲線模擬。其模擬結果如表7 所示。首先,查看P,3 個回歸曲線的P均為0.000,小于0.05,所以3 個回歸曲線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其次,查看R2,比較線性、二次和三次回歸曲線的R2可知,0.85<0.932<0.944<0.946,線性、二次和三次回歸曲線的R2均大于0.85,表明這3 個回歸曲線擬合優度均較高,且三次回歸曲線擬合優度高于二次和線性回歸曲線;最后,查看F,比較線性、二次和三次回歸曲線的F可知,59.522<61.785<110.479,表明線性回歸曲線的差異性最明顯,三次回歸曲線次之,二次回歸曲線最差;因此,綜合考慮,工業源COD 排放與生態經濟之間的關系與線性回歸曲線更為擬合。為了更直觀地查看回歸曲線,借助SPSS 軟件繪制兩者之間的線性回歸曲線。
工業源COD 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如圖3 所示,結合表7 中的相關數據,可以得出工業源COD 排放與生態經濟之間的EKC 模型擬合方程為y=41.954-x,并不存在EKC 特征,而是呈單調遞減的線性負相關關系。根據EKC 擬合方程和圖 3 可知,2012—2021 年工業源 COD 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呈負相關,即生態經濟的持續增長,減緩了工業源COD 的排放。

表7 工業源COD 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的關系模型

圖3 工業源COD 排放量與生態經濟的線性回歸曲線
3 小結與建議
收集整理江蘇省2012—2021 年10 年間的水環境污染和生態經濟發展數據,以人均GDP 作為衡量生態經濟的典型指標,通過主成分分析法選取具有顯著相關性的水環境污染指標,即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和工業源COD 排放量,進而使用EKC 曲線構建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發展相關性的計量模型,分析其與生態經濟之間的作用關系: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工業源COD 排放量與生態經濟之間均呈非典型的EKC 曲線形態。其中,農業源氨氮排放量與生態經濟在2018 年以前呈負相關關系,2018 年以后呈正相關關系;工業源COD 排放量與生態經濟始終呈負相關。也就是說,隨著生態經濟的持續發展,工業源COD 排放量逐年減少,說明中國工業產業的結構優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農業源氨氮排放量卻在2018年經歷拐點,并隨著生態經濟的持續發展,逐年上升,說明現階段農業種植過程中過度使用化肥,且沒有做好農業源廢水的處理工作。
為此,首先需要對各項水污染源頭采取控制措施:各工業企業對工業源廢水污染的控制要始終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不斷進行生產結構優化,改進生產工藝,推行清潔產品,提高工業廢水的二次利用率,實現一水多用,從源頭上遏制廢水產生;對農業生產產生的面源污染,應采用雙效汽提+蒸餾技術,將廢水的氨氮以濃氨水或氨氣的形式回收,同時可以將濃氨水或氨氣納入到生產環節,作為生產原料回用[9],既削減了農業源氨氮的產生量,又資源化氨氮廢水,一舉多得。水環境污染與生態經濟之間既互相制約,又相互促進。因此,在生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過程中,要秉持生態文明價值理念,使GDP 增加成為自然自我修復、恢復秩序的熵減過程,形成負熵GDP,使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和引擎[10],實現水環境治理與生態經濟發展的和諧共生。